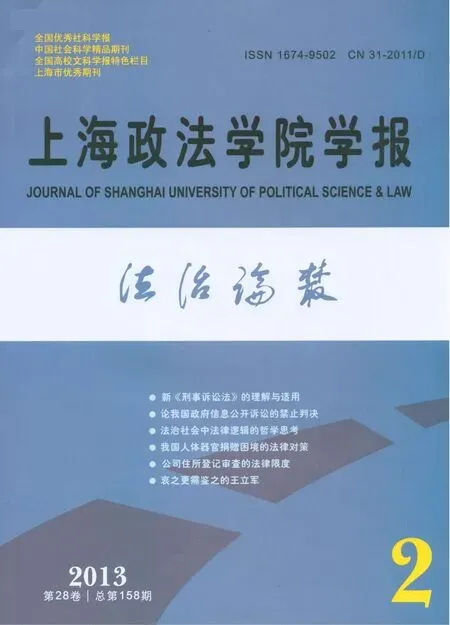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基础与框架
2013-04-10吕建高尚剑伟
吕建高 尚剑伟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1816)
●法学论坛
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基础与框架
吕建高 尚剑伟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1816)
制定指标监控受教育权的实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并付诸实践的重要努力。受教育权指标的构建必须从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寻求合法性来源。可获得性、可准入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能够准确阐释受教育权的概念和内容,它们是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概念框架。结构指标、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指标分类,它们是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类型框架。具体的受教育权指标应该实现概念框架和类型框架的结合。
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指标;国际人权法
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自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初等教育的普及。在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实现初等教育普及”的第二项目标更是凸显这一趋势,而且,该目标敦促各国在2015年前确保所有适龄儿童能够实现初等教育。然而,尽管对教育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重视,但是受教育权的实现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人权活动家积极倡导利用指标监控人权实现,并主张通过制定人权指标监控各缔约国的人权实施状况,从而有效促使各国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其它权利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利用指标监控受教育权的实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并付诸实践的重要努力。
一、构建受教育权指标的规范基础
创设人权指标的目的,是促使义务承担者对自己的人权义务负责。通过对人权公约遵守情况的监控,这些指标能够评估缔约国是否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为了监控缔约国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遵守,指标制定尽可能符合国际法律框架的要求尤为必要。只有使指标制定具有规范性基础,才可能为人权监控机构以及其他主体向政府主张权利提供正当理由,否则政府会以这些指标不合法为由而表示拒绝。因此,受教育权指标应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尤其是要遵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文简称《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它首先要求人们对受教育权的内容有一定的正确理解。尽管经社文权利不容易被人们准确理解存在争议,但受教育权(它也属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非如此。这项权利在国际和地区人权条约中可能是最发达的权利之一,尤其是初等教育。例如,条约机构发布了关于受教育权的一般性意见,而且,近年来,很多学者也对受教育权展开了充分讨论。相关的条约文件主要包括《世界人权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其中,《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全面包含了受教育权的规定。例如,公约第13条不仅概括了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相关的国家义务,而且涉及与教育内容相关的义务。同时,公约还规定,父母有权根据他们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为子女选择教育,也有权成立私立学校。公约第14条则规定了国家具有制定行动计划的义务,即在《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批准并生效后,如果全民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还没有实现,缔约国就必须采取行动使义务教育逐步免费。除此之外,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进一步就受教育权发布了两份一般性意见:即关于受教育权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和关于初等教育行动计划的第11号一般性意见。
其次,《儿童权利公约》是批准最为广泛的国际人权条约,其中也包含受教育权的详细规定。例如,《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和第29条重申了《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所保护的受教育权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增加了新的内容,其中包括提供教育和职业信息、鼓励入学、使学校纪律与儿童的自尊相符合以及促进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义务等。然而,仔细阅读《儿童权利公约》,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该公约规定的人权标准低于《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仅由《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条款除外)。为了规避这一问题,《儿童权利公约》第41条规定了保留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其它国际和地区人权条约规定更高的人权标准,以这些标准为准。①《儿童权利公约》第41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应影响更有利于实现儿童权利且可能载于下述文件中的任何规定:(a)缔约国的法律;(b)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法。按照这种规定,受教育权指标的构建完全可以以那些规定最高保护标准的人权条约为基础。
最后,除了国际公约,也应该考虑地区人权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等。这些规定人权标准的地区通过人权条约进一步对受教育权予以确认。当然,这些条约只对加入条约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存在两种与人权相关的情形:一方面,地区人权条约可能会重复一项受国际人权条约保护的权利。在这种情形下,地区人权条约对该项权利的确认会进一步在地区层面巩固这项权利;另一方面,地区人权条约可能会确认一项国际人权条约没有规定的权利。此时,它就创设了一项仅适用于地区人权条约缔约国的新权利。在这种情形下,与该权利有关的指标只与相应的缔约国有关。
二、构建受教育权指标的概念框架
众所周知,只有阐明受教育权在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的概念和内容,才能保证制定的指标满足合法性需求。然而,简单罗列权利的内容对指标的确立并没有多大帮助。实际上,在制定合适的指标之前,重要的是确定权利的性质。准确理解所衡量义务的概念和范围是考量缔约国是否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一个必要步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制定指标衡量缔约国遵守国际义务的前提就是要“阐明具体人权的内容”。②Gauthier de Beco,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State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3, no.24, 2008, p. 27.
然而,众多衡量受教育权的现有意见无法对该权利的内容达成共识。例如,坎普(Isabelle Kempf)针对受教育权的概念框架建立了一个信息金字塔。③Isabell Kempf, How to Measure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ndicators and Their Potential Use by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1998/22, 1998, para. 6-7.在金字塔的第一层,她制定了很多重要措施来评估缔约国如何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例如识字水平和初等教育入学水平。金字塔的第二层涉及广泛的指标,如政府在教育、交通和午餐计划方面的开支。在第三层,她对文化背景、权利履行中的语言障碍、功能性识字以及正常的初等教育期限展开分析,进而评估可能影响受教育权的社会、政治和环境背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坎普提出的框架并没有详细阐释受教育权的概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最近也就利用指标衡量人权义务提出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应该说,人权高专办的报告对于评估国家是否遵守经社文权利具有积极意义,但缺点在于未能提供具体的工具来监控和评估缔约国对具体条约的遵守。例如,就受教育权而言,人权高专办列举了该项权利的特征,并指出受教育权具有4项属性:(1)普及初等教育;(2)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可准入性;(3)课程和教育资源;(4)教育机会和教育自由。①OHCHR, Report on Indicators for Promoting and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2008, HRI/MC/2008/3, p. 28.然而,基于这些属性拟定的指标不与任何条约直接关联,因此,就衡量对具体条约规范的遵守情况而言,它们不是最有效的或最准确的指标。
由人权高专办报告确立的受教育权的特征范围,比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对《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中受教育权条款的解释范围更窄。相比较而言,经社文权利委员会通过“受教育权的4A框架”——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准入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以及可适应性(Adaptability)——对该权利范围和属性的界定更为宽泛。②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U.N. Doc. E/C.12/1999/10, 1999, para. 6-7.这份由联合国前特别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Katarina Tomasevski)首次提出的框架更为全面地融合了受教育权的众多特征。③Katarina Tomasevski,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Education, U.N. Doc. E/CN.4/1999/49, 1999, para. 50-74.因此,笔者拟用4A框架详细阐述《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受教育权。实际上,尽管经社文权利委员会采用了4A框架,但它并没有解释该框架是如何与《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受教育权用语直接相联系的。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试图把4A指标与《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条约用语明确联系起来。
1.可获得性
可获得性描述了政府有义务确保教育机构和教育规划具有足够的数量,并且必须具备必要的设施使其正常运转(如充足的校舍建筑、分别适用于男女生的公共卫生设施、安全的饮用水、受过培训且可获取相当薪水的教师、教学材料、以及诸如图书馆、计算机设施和信息技术等其它设施)。为了使教育具有可获得性,政府必须允许兴办学校,并提供必要的资源。
可获得性概念得到《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的明确保护,但不同教育等级的保护程度各不相同。具体而言,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中等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这就表明,尽管国家必须使所有适合条件的人都能享受初等教育,但中等教育并不受此限制。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④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dopted on Dec. 16, 1966, U.N. Doc. A/6316, arts. 13(2)(a)-(c).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应该根据能力以合适的手段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备某种统一标准的人才可以享受高等教育,这些标准能够衡量个人是否具备充分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
除此之外,根据《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的规定,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包含所有教育等级的体系。这就意味着:(1)国家必须建立一套教育基础设施以确保提供所有等级的学校;(2)这些设施便于维修;(3)教学物资和设备质量良好;(4)具有充足的教师。①Klaus Dieter Beit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by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 p. 531.对此,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解释到,“在一国管辖范围内,人们必须能够获得一套足够数量且有效运行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规划”,必须有足够数量“受过培训且可获取相当薪水的教师”。而且,国家必须:(1)不得关闭私立学校,以显示对教育可获得性的尊重;(2)通过建立健全教育体系(如开办学校、制定规划、筹备教学物资、培训教师)来实现教育的可获得性。②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U.N. Doc. E/C.12/1999/10, 1999, para. 6, 6(a), 50.
2.可准入性
可准入性意指教育准许所有人进入,并向所有人开放。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认为可准入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教育必须不得歧视地向所有人开放。《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和第3条明确承认非歧视原则在教育准入中的重要性。该委员会特别要求,国家有义务确保第三方允许女孩进入学校。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制定激励措施,如实施基于家务劳动的工作政策、为父母设立金钱刺激计划、提高孩子的结婚年龄进而提升女孩的入学率。此外,公约第13条要求缔约国设立充分的奖学金制度。对此,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进一步指出,设立奖学金的要求应该被解读为公约非歧视性的平等规定,奖学金制度应该提升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和女孩)进入学校的公平性。
第二,教育必须在物理(physical)层面准许所有人进入。这就意味着,选择学校办学场所应该方便所有人都能进入,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之人和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或种族。它还可能意指在当地设立学校,为特定人群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使用相关教学方法的替代技术(如在线教学)。
第三,教育必须在经济层面准许所有人进入。虽然不同等级的教育应该在经济上准许所有人进入,但是规定教育免费的要求受到公约第13条关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相关用语的不同限制。就初等教育义务而言,如果缔约国在条约生效后没有向所有人免费提供,就必须在条约批准后的两年内制定计划,并在合理期限内引入免费初等教育。尽管《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初等教育必须免费向所有人提供,但是中等教育必须“以一切适当的方法”准许人们进入。当然,缔约国可以决定采用何种适当的方法使中等教育准许人们进入。在经社文权利委员会看来,最适当的方法是使中等教育逐渐免费。
此外,该委员会还认为,间接费用(如向父母征收的义务税)或配备相对昂贵校服的义务是受到禁止的。③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1: Plans of Action for Primary Education, U.N. Doc. E/C.12/1999/4, 1999, para. 7.然而,该委员会又指出,其它间接费用经过具体审查后可以允许。但到目前为止,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还没有明确规定允许哪些间接费用。
3.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涉及与教育质量与合适性相关的形式和本质问题。这是一项以人的尊严原则为基础的职责,它要求教育质量对学生、社区以及更广义上的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不应包含歧视,而且应该恰当地融入学生的文化、语言和社会背景之中。更宽泛地说,可接受性描述了政府确保学校拥有最低标准的特定教师、学生、教育教学设施和课程体系。
可接受义务是从条约用语中总结出来的。例如,《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3款规定“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这充分说明教育必须具有可接受性。经社文权利委员会指出,教育的形式和实质(包括课程和教学方法)必须被学生以及适当情况下被父母所接受,它们受限于第13条第1款规定的教育目标和缔约国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此外,该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必须极力保证课程达到第13条第1款规定的目标,并且维持一个透明体系,以此监控国家的教育目标是否符合公约规定。而且,该委员会特别指出,国家有义务通过向所有人提供文化上合适且优质的教育,从而实现教育的可接受性。
4.可适应性
可适应性提出教育应具有灵活性,能够对各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学生需求做出回应。为了实现教育的可适应性,政府应该向学校提供资源,使学校能够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从而满足学校所服务的社区需求。除了个性化的课程之外,学校必须同时监控教师和学生的表现,并根据监控结果适时做出修正。不具有适应性的教育制度很可能在弱势群体学生中(如怀孕的女孩)导致较高的辍学率。同时,为了确认某个缔约国是否尊重、保护和实现该项权利,就必须使用指标来衡量该国所承担的受教育权义务的各个要素。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进一步强调,教育必须具有适应性,这样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此外,国家必须允许教育的自由选择,避免国家或第三方干预,并且满足最低的教育标准。
三、构建受教育权指标的类型框架
对《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中受教育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界定后,需要考虑拟定合适的指标,以便对侵犯受教育权的行为进行界定。尽管有很多建议提倡用指标衡量受教育权的实现,但它们无法被证明对界定侵犯具体条约义务的行为是否有用。①Katrien Beeckamn, Mea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ducational Versus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2, 2004, pp. 71-84.由于托马舍夫斯基的受教育权4A框架准确描述了受教育权的概念和范围,因此,笔者拟在4A框架的基础上制定受教育权指标。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托马舍夫斯基注意到使用指标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指标的相关问题,但她没有制定具体指标体系来衡量缔约国对4A框架的遵守。而且,笔者认为,4A框架应该被分解为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这种指标分类由联合国健康权特别报告员亨特(Paul Hunt)首次于2003年提出。②Paul Hunt,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Enjoy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U.N. Doc. A/58/427, 2003, para. 15.2006年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文件遵守的监控指标报告》采纳了亨特的指标分类,并将其用于对所有人权实现的衡量。③Report on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U.N. Doc. HRI/MC/2006/7, 2006, para. 13, 17-19.后来,美洲人权委员会为了监控经社文权利的实现,也采纳了亨特的术语。而且,2008年人权高专办《有关促进和监控人权实施的报告》再次确认了“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框架,并认为这种指标框架能够体现义务承担者各自做出的承诺、努力和结果。使用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这种分类,能够保证衡量国家义务的所有方面,例如,该国的国内法律是否与条约义务保持一致、该国是否已经开始履行条约义务以及这些权利在国内的实际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分类可以把缔约国履行各个4A框架义务的优势和劣势区分开来,进而更好地评估其违反公约义务的情形。
根据联合国2006年的报告,结构指标体现的是法律文件的批准和通过以及便于人权实现的基本制度和机制。与此类似,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结构指标不仅应该用来考察“书本上的法律”是否与缔约国的条约义务相一致,而且应该考察缔约国是否按照国际法义务确立相关制度。当然,结构指标和过程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将结构指标局限于监控某国的法律是否体现、吸纳和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而过程指标则被用来说明某国是否建立合适的制度并采取措施来履行义务。
过程指标衡量的是缔约国在实际生活中制定法律和政策实现权利的程度。2006年的联合国报告认为,过程指标与即将变成结果指标的国家政策文件相关,而结果指标与人权的实现直接相关。尽管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表明,结构指标包括缔约国是否制定政策和程序来履行国际法的规定,但是,笔者主张,与履行条约义务而制定的规划和策略相关的指标更适合归类为过程指标。因此,尽管结构指标涉及某国的国内法是否符合国际条约义务,但过程指标解决的问题是,为了实现权利,缔约国确立了哪些机制来执行现有法律。
结果指标衡量的是现实情况,即国家实现权利的程度。实际上,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衡量的都是条约的遵守情况。结果指标关注的是努力的结果,而过程指标关注的则是缔约国付出的努力本身。此外,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结果指标不仅是对权利实现的直接衡量,而且它还体现指标在评估权利享有方面的重要性。换句话说,结果指标衡量政府策略的实际影响,而过程指标则是衡量这些策略的质量和程度。①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Guidelines for Preparation of Progress Indicator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EA/Ser.L/V/II.132, 2008, para. 31-32.
尽管人们接受的其它指标分类方法(如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也有助于确立缔约国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但是,笔者认为,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框架对于监控经社文权利的实现最为有用。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框架将国家义务分为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②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3: The Nature of State Parties Obligations, U.N. Doc. E/1991/23, 1990, para. 1.而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框架确立的是国家在所有人权方面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例如,尊重受教育权的消极义务禁止干涉父母为其孩子选择学校的决定。相比之下,保护受教育权要求积极义务,因此国家必须有所作为,其中包括采取步骤确保女孩不被第三方因其怀孕而从学校开除。实现受教育权也是积极的,因为国家必须确定无疑地采取行动,如逐渐引入免费中等教育。将国家的人权义务分为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目的在于评估缔约国是否履行相关权利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
与之相比,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框架阐明了国家控制具体条约义务的程度。换句话说,这种框架把指标分成衡量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的指标。就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是否履行其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而言,尽管国家可能具有同等的控制水平,但国家对其行为义务(由结构指标和过程指标衡量)的控制要明显高于对结果义务的控制(由结果指标衡量)。因此,国家对结构指标和过程指标所衡量的义务具有较高的控制水平。在考察结构指标和过程指标时,国家在这方面的人权侵犯行为可以明确地归因于它的不作为。另一方面,国家对结果指标所衡量的义务具有较低的控制水平。当评估国家在这方面的人权侵犯时,考虑国家的控制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评估涉及合法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它不仅能促进对条约规范的遵守,而且能促进国家在实现经社文权利方面的合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监控受教育权实现的指标应该以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为基础,尤其要严格遵循《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托马舍夫斯基提出的受教育权4A框架,准确阐释和分析了公约中受教育权的概念和范围,因此,受教育权指标的制定应该以4A框架为基础。此外,前文所述的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框架是最受国际社会认可的衡量国家义务的指标类型。基于此,应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并按照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模式对4A框架进行分解,最终确定受教育权的具体指标体系。
(责任编辑:马 斌)
G40-05
A
1674-9502(2013)02-081-06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
2013-02-2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理学研究》(项目编号:08BFX0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