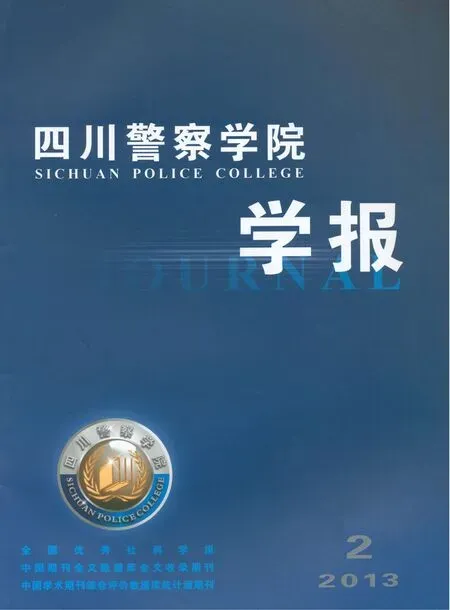商业外观作为竞争性法益的理路
——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论范式
2013-04-10王思喻
王思喻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0031)
一、引言
商业外观法律保护是外力施压和内在需求的结果。一方面,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源于美国司法实践并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知识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不论是为了防止对已成功持续使用并产生标识性利益的商业外观的自由搭乘,还是维护消费者对商业外观背后的产品或服务的信赖,市场竞争下现实的利益需求确实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出现了一批与商业外观保护有关的司法案例。法律实践进一步催生学术讨论的热情,然现有研究或是停留在介绍性地传播美国的商业外观法律保护制度而缺乏对商业外观保护在地化的理性思考;或是经验式地认为现实需求的重要性足以证成商业外观作为权利的正当性;或是从多学科、多理论、多角度出发讨论商业外观的法律属性而忽略其是其所是的本质;更或者在相关基础理论、立法文本和司法态度尚未明朗化的前提下讨论商业外观的资本化运作。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如何回答问题,即问之所问、问之所及和问之何所问三个层次。问之所问是对象问题,问之所及背景问题,问之何所问是发问者的意图[1]。对象问题就是要明确商业外观的内涵和外延,背景问题的回答不仅要有现实思考更需要历史回溯方能明确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而发问者的意图试图回答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给予我们何种体验和反思而实现商业外观法律保护的理论超越。“理路”一词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道理,二是思路安排[2]。“道理”即要为商业外观的竞争性法益观证成,“安排”即要指出商业外观法律保护的制度模型。
二、商业外观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商业外观概念的模糊性——一个开放的利益体系。
对象问题是商业外观法律保护遭遇的首要挑战。商业外观,系由英语“trade dress”翻译而来,是一个舶来品。美国联邦商标法——《兰哈姆法》并未对商业外观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界定。美国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系由司法判例发展而来。美国著名商标法大师麦卡锡教授曾简单定义商业外观为:“负载于产品或服务上并呈献在购买者面前的任何诸元素的结合。”[3]在Gibson Guitar Corp.v.Paul Reed Smith Guitars一案中,法官认为:“商业外观的范围包含了所有与产品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可识别性的安排、特征或装饰的包装或其它能够起到商品来源识别功能的东西[4]。美国学者指出,该定义包含传统产品的包装,包括标签,包装和容器,并在Hartco Engineering,Inc.v.Wang s International案中得到证实。在Herman Miller,Inc.v.Palazzetti Imps.&Exps.Inc.案中,商业外观的范围已扩大到包括产品的设计或配置,包括产品本身的大小,形状,和颜色[5]。1992年的Two Pesos.Inc.v.Taco Cabana,Inc.案基本确定了商业外观的内涵和外延,我国学者多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来定义商业外观:“商业外观是经营的整体形象,包括餐馆的整体外观和形状、识别性标识、店内厨房地板图案、装饰、菜单、上菜的器具、服务人员的着装以及其它反映该餐馆整体形象的特征。而商业外观如果具有显著性的话,就不必通过使用获得第二含义才获得商标法的保护。”[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起草的《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中将商业外观纳入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之中,但并未集中使用“商业外观”一词。该示范条款关于商业外观的表述包括“商品外观”和“商品或服务的表示”。前者包括商品的包装、形状、颜色或者其他非功能性特有的特征,且与工业设计的混淆也纳入该范围;后者包括企业的工作服和店铺风格[7]。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其判例将商业外观和产品的包装、形状作了区分,但都可以受禁止仿冒法的保护[8]。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仅规定产品的形状(三维的外观、形状或者设计)受到禁止原样模仿的保护。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虽未直接使用“商业外观”这一术语,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两个法律文件确立的保护范围与美国商业外观保护的司法实践确立的范围基本一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项明确保护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解释》第3条又将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式样、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扩大解释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装潢”。 与美国判例法确定的保护范围相比,我国仅保护知名商品的特有商业外观,但对商业外观外延的理解是一致的。
近来,有美国学者提出氛围也应当纳入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对象中。姑且不论其是否恰当,结合商业外观作为受法律保护客体的历史考察和域外经验看来,这至少证明其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统一的立法模式。理论是灰色的,商业之树常青,商业外观是一个动态的法律概念,是一个开放的利益体系,随时都可能有新成员加入其中。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法律以跟随社会生活回应现实诉求,但法律保护对象的不确定性与作为形式主义理性的法的稳定性背道而驰。不同的域外经验更是说明商业外观法律保护的在地化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全球化之间关系的紧张。无论如何,催生出符合本土资源的商业外观法律保护制度并非易事。而商业外观的概念如何厘定就是横亘于此的第一道难题。但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对于法律的内容有所陈述,并且超出制定法的现实之外,对于法律的现实有所陈述的法律实体概念。”[9]从这个角度看,以上种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商业外观法律保护的应然与实然的可能对应关系。是“法律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这一法哲学命题的具体化。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商业外观的概念又是大致明确的,生活在商业关系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依靠基本的常识来判断商业外观意指什么。这种体验是可靠的,法律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归纳和体验。这也并非说明对商业外观概念的理性和抽象是不必要的,本文试图指出永远不会有完备的商业外观保护法,任何希望对商业外观作出一劳永逸的界定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从感性材料向理性的抽象始终存在。这就是本文对商业外观概念模糊性所主张的态度。
(二)商业外观法律保护的尝试——一套多元的立论基础。
1.评标识性权利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标识性权利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有着天然的说服力,其论证路径和商标权作为标识性权利受到保护一样。正如李明德教授指出:“任何可视性标记,包括颜色、字母、数字、图形、三维标志,只要能够指示商品服务的来源,就能够作为商标使用。所以,包装装潢就是另一种商标。”可见,很多受保护的商业外观都符合商标注册的条件,可成为立体商标、图形商标等受到商标法的保护。从商标制度的演进来看,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不过是商标法律保护历史演进中的浪花一朵。有研究指出:“商标的演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到商业外观”的过程,而这得益于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5]标识性权利一语从商标功能来讲反映了商业外观的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识别功能,这是商标的基础功能,也是商业外观的基础功能。国内外商业外观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商业外观保护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权利方的商业外观具备显著性,无论是固有显著性或使用取得显著性;二是被诉产品或服务的商业外观与权利人的商业外观混淆性相似;三是该商业外观不能具有功能性,包括实用功能性和美学功能性。而商业外观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前提除需证明竞争关系存在外,也要证明混淆与非功能性以及显著性。这也与世界范围内保护商业外观的规定如出一辙。综上,标识性权利为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正当性证成在商业外观的识别来源功能和由此产生的质量担保功能上找到证据支撑,在现实商业生活中,经营者也的确通过令人印象深刻和富于美感的商业外观来强化消费者对经营者的认识。
但该立论基础的缺陷同样明显,仅从标记性和识别性来为商业外观保护正当性证成显得过于保守。正如商标法的发展进程中还出现了商标的广告宣传功能和商标表彰功能一样,商业外观更是广告宣传功能和表彰功能的集大成者。商业经营者之所以选择独特的具有整体性消费体验的商业外观的理由就在于商业外观作为商品或服务的一系列元素的结合相较于普通商标更能造成一种强烈的感官体验,消费者对某一具备商业外观的产品或服务的选择所关心的也不仅仅是质量,而更有消费者其自身地位、面子的象征。[10]这都是标志性权利无法论证的。
2.评无形财产权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财产权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不仅是随着包括商业外观在内的商标泛财产化倾向而出现的。支持商业外观作为一种完整的财产权的理由包括:第一,从商业外观管理的角度看,商业外观作为一种标识性利益产生于持续的使用和成功经营策略。商业外观本身并无太大价值,真正的价值是商业外观产生的商誉。商业经营者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当然属于自己的财产。第二,继续追溯可以发现早在罗马法中就已提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划分,商业外观作为一种凝结着商誉的无形财产并无不妥。第三,洛克的劳动财产学说认为是劳动使人们对原来处于共有状态的财产产生了私人占有,这也常被用来论证知识产权的正当性[11]。第四,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制度、转让制度从实然法的层面证明包括商业外观在内的商标作为财产而非单纯的识别性标记而存在。
财产权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的缺陷在于将包括商业外观在内的商业标记作泛财产化处理本身就是危险的,它可能未曾考虑到商业外观与一般有体物的区别而忽视该种信息资源下私权与与公共领域的界限,与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3.评商事人格权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该观点的提倡者认为商事人格权即:“商主体特有的经法律确认而以商事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商主体之商事法律人格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权利。同自然人的人格权可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样,商事主体亦有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商业形象权就是商事具体人格权的一种[12]。”联想商标淡化概念所使用的“弱化”、“污损”、“褪化”等法律语言,似乎也隐含着对人格利益受损的描述。商事人格权理论与商标淡化理论有所契合。既然承认商标淡化理论的司法实践,承认商事人格权作为商业外观保护的立论基础并无不可。
该观点似乎是回归民法传统寻求答案,但缺陷是结论所依据的前提本就颇具争议性。自然人的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没有争论。但通说和立法认为商事主体的具体人格权仅仅限于名称权、名誉权,创设新的具体人格权尚缺乏依据。且商业外观最终体现为一种财产利益,用自然人的肖像权推导出法人的商业形象权似乎是在承认法人的精神利益,这无疑是对人格权与法人制度的巨大突破,尚不成熟。
三、商业外观作为竞争性法益的提出
(一)整体主义的知识产权理论范式对商业外观保护立论基础的整合。
一般说来,法学理论范式可分为个人主义的理论范式和整体主义的理论范式。个人主义的理论范式以民法理论为代表。民法强调“权利本位”,主张私权神圣。尽管民法理论当中也存在“禁止权利滥用”的基本原则,但其强调的是个人权利之外是他人的权利,是从划分权利界限的角度来谈的,在一主体和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公共空间。而主流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知识产权是当然的私权。在该理念的主导下,知识产权的理论范式也更强调维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权利人的个体利益。而知识产权上的利益平衡原则和公共领域研究更多是从合理限制知识产权的角度展开。正是在这种“权利本位”论下,前文所述的三种商业外观的立论基础才成为可能,他们要么更多地关注消费者权利的维护而得出标记性权利的结论,要么以商业外观所有人为核心推导出财产权和人格权保护两条路径。这就是商业外观保护在理论范式层面遭遇的困境。当个人主义的理论范式不能解决商业外观保护对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所提出的挑战时,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论范式呼之欲出。必须澄清的一点是,整体主义的理论范式并非知识产权学界所批判的知识产权公法化倾向。本文认为传统罗马法公法私法的二元体系早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生活所体现的利益诉求,公法私法间存在第三法域也早已被很多学者认同。本文主张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就是要将包括商业外观法律保护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放到第三法域中进行考量。实际上,笔者注意到知识产权学界已经出现了整体主义理论范式的雏形。有学者主张知识产权法理论范式包括反对知识产权中的国家意识和反对私权或公权对公共领域的挤占[13]。也有学者主张知识产权中的权利弱化和利益分享机制的理论范式[14]。本文认为,无论是公共领域、权利弱化抑或利益分享其内在理念反映了知识产权理论范式从个人主义向理论主义的转向。以保护私权为宗旨的传统民法不可能孕育出向公共领域这样具有社会法(经济法)属性的理论范式。具体到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问题,具有经济法属性的竞争法所注重的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的观念应当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竞争法天然具备兼顾竞争者、潜在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关系结构。
(二)私权属性为分析工具的对商业外观法律保护的整合。
以整体性理论范式为主导并不是要否认商业外观权益所具备的私有属性。相反,通过“私”的手段实现公共利益保护的目的是一种经济高效并有效整合现有法律资源的途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私”的手段实现商业外观利益的合理分享。在民事权益体系中,本就有权利和法益的区分,权利和法益不是概念游戏的结果,在保护强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虽学界对权利和法益有不同的称呼,如“未上升为权利的法律上的利益”和法益就是等同概念。且虽法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广义的法益就包括权利,而狭义的法益不包括权利。但为逻辑和实际操作的考虑,对民事权益体系的划分应当是周延的,应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权利和法益。本文认为狭义的权利乃由法律明确认可,主体、客体和权利行使及侵权救济都基本完备的法律上的力量的自由。而法益是尚未由法律直接确认,且没有或难以类型化的却又依公平、正义及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法律加以保护的未上升为权利的利益[15]。对于权利和法益区分的实际意义,王泽鉴先生以台湾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为例认为:“‘民法’第184条规定为调和‘行为自由’和‘权益保护’两个基本价值,区别不同的权益保护而建构了侵权行为责任体系。若是权利被侵犯,权利人只要证明加害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即可。若是权益被侵犯,权利人还要证明加害人的行为有违善良风俗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而权益的损害又被称为纯粹经济损失。”[16]
(三)竞争性法益是商业外观存在的应有形态。
本文认为,竞争性法益才是商业外观存在的现实形态和应有形态。
首先,世界各国对商业外观的立法实践都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基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自身的价值并不存在于民法、知识产权法或其它财产法当中。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首要立法目的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法最初就是为了保护诚实商人而设计。商标法起源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如最初的商标侵权之诉是从假冒之诉开始的那样,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美国法官在判决中反复提到:“商标保护的原始目的是保护某一经营者免受任何不法转移受保护贸易的行为。”[17]可见,诚实竞争、公平竞争背后的财产利益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经营者的法益。如前所述,我国经济法学界研究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不同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反不正当竞争法既不像私法坚持权利本位,也不像公法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竞争法的核心是社会本位。社会本位的法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就商业外观来看,它一方面维护了经营者的贸易利益,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利益本就是竞争法的题中之义。承认商业外观的竞争法益地位很好地弥补了标识性权利、无形财产权以和商事人格权三个理论基础无法协调的缺陷,也与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和公共领域的思想保持了一致。竞争法益的本质就是适度保护,而不像绝对的权利那样拥有绝对的垄断,也不像一般利益那样游离于法律保护的大门之外。
第二,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商业外观的侵权责任范围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仿冒者总是模仿特定主体的商业外观,但权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难以界定。商业外观侵权带来的损失可能是潜在的,它往往表现为一些机会利益,以一家餐馆为例,损失的潜在消费者如何确定就是问题,消费者消费的高低也是任意的,即使按照“侵权人所得利益”的原则赔偿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很难确定哪些消费者是因为混淆而选择了侵权方的餐馆。如果不是因为混淆,侵权损失就不应计算在内。况且保护商业外观究竟是保护财产利益还是保护类似于自然人肖像权的法人人格权已经出现争议,诸多前提概念尚未澄清。因此不宜认为商业外观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宜从禁止的消极保护的角度来设计商业外观保护制度。
第三,从权利冲突看,不应给予商业外观以权利形态存在的强保护状态。商业外观的设计者可能与商业外观的经营者发生分离。于此情形,以一建筑作品为例,某一设计师A是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人,某餐馆B在该作品上建立了商业外观权。从著作权角度分析,A设计师是在先权利人,A将该建筑作品许可给与B有竞争关系的C使用。按侵权法理论,如果商业外观是一种权利,那么B无论如何可享有禁止C使用并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C不得以善意作为抗辩理由。如果商业外观仅是一种竞争性法益,C或可援引善意作为抗辩,还可能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成立商业外观共存的状态。实际上,商标共存制度已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中得以体现。从平衡著作权人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经营者利益的角度,给予商业外观作为法益形态的弱保护更为合理。
四、结语
对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的讨论还将继续,知识产权理论范式还将继续游移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不变的是对商业生活的关注、对商标法律体系的改造和提升。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5.
[2]工具书—中国知网[EB-OL].2013—1—16.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RDD.
[3]THOMAS MCCARTHY,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8:1,at 8-3(4th ed.).
[4]Gibson Guitar Corp.v.Paul Reed Smith Guitars,LP,423 F.3d539,547 n.10(6th Cir.2005).
[5]SCOTT C.SANDBERG,Trade Dress:What Does It Mean?29 Franchise L.J.10 2009-2010.
[6]杜 颖.社会进步与商标观念:商标法律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3;57.
[7]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841.
[8]孔祥俊.论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J].人民司法,2005,(4).
[9]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7.
[10]徐聪颖.论商标的符号表彰功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15
[11]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M].周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9-75.
[12]范 建,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34.
[13]康添雄.范式与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的演进[J].法学杂志,2011,(9).
[14]曹新明.关于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之研究——一种新的知识产权理论范式[A].?张玉明.西南知识产权评论[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3-26.
[15]李 岩.民事法益的证成——以有限理性为视角[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1).
[16]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0;297.
[17]Canal Co.v.Clark,80 U.S.311,322-23(1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