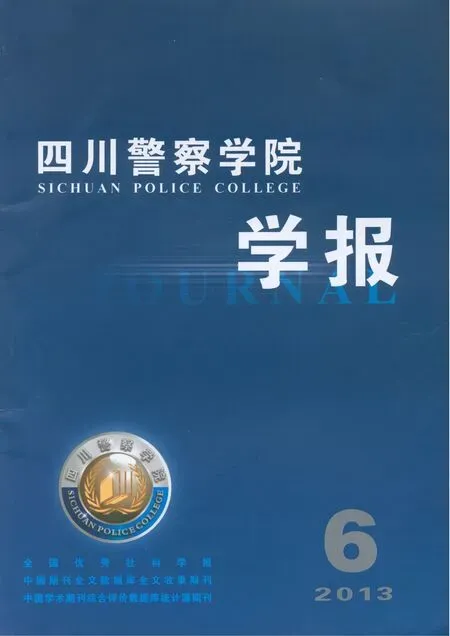内幕交易罪的司法难题及原因、对策
2013-04-10李浩
李浩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63)
内幕交易罪的司法难题及原因、对策
李浩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63)
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频发,无论是“杭萧钢构案”还是“上海组龙内幕交易案”都在司法认定方面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议。这充分表明,在认定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待解的难题。只有在对这些司法难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重构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改善内幕交易行为的取证路径、强化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完善机制设计,才能破解司法难题,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保障证券法律法规得以遵守和执行。
内幕交易;内幕信息;司法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2月4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萧钢构”案作出一审判决:罗高峰犯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玉兴犯内幕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王向东犯内幕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4037万元。同年3月26日下午,受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萧钢构”一案被告人罗高峰、陈玉兴、王向东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被称为“牛市内幕交易第一案”的金融大案方才尘埃落定。
实际上,无论此案的侦破还是审判工作,都遭遇了不小的困难。自从杭萧钢构案进入警方视野以来,侦查工作举步维艰。一方面,由于杭萧钢构案不同于以往由内幕消息知情人自己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形式,而是由证券事务代表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前任证券事务代表,后者伙同他人共同买卖股票。对此类新型的内幕交易案件,并没有前例可以借鉴,这在事实和法律认定方面都是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罗高峰、王向东、陈玉兴已经建立了“攻守联盟”,加之内幕交易取证难是公认的司法难题,关键性证据的难获取直接导致案件侦破工作的停滞不前。
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针锋相对。围绕以下几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罗高峰是否具备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资格?2.陈玉兴偶然听到的消息,这种情况下他算不算“非法获取内幕消息的人员”? 3.陈玉兴从罗晓君处得知的仅仅是“谈300亿合同”的信息,该信息并没有包含合同的全部条款,不完整的信息算不算内幕信息?谈判算不算内幕信息?4.杭萧钢构董事长单银木在公司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算不算泄露了内幕信息?会后信息是否已经实质公开,不再属于内幕信息等等。
无独有偶,2010年的黄光裕内幕交易案、上海祖龙内幕交易案、刘宝春、陈巧玲内幕交易案;2011年的李启红内幕交易案、姚荣江内幕交易案都在司法认定及取证方面遭遇了较大难题,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这些争论也恰恰反映出,我们在处理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待解的难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普遍性。为此,笔者试图从这些司法难题的表现入手,逐层剖析,究其深层原因,以期为这些难题的破解提供新思路。
二、司法难题的表现及原因
(一)内幕交易案件司法困难的表现。
1.司法认定标准难统一,内幕信息构成要素问题悬而未决。内幕交易数额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定罪与量刑,但司法实践中对于内幕交易数额的认定却一直莫衷一是。尽管《关于经济犯罪追溯标准的规定》第29条规定了内幕交易数额在20万元以上即可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内幕交易的数额是以买入的净额为准,或是以卖出的净额为准,又抑或是以买入累计数额为准,还是以卖出累计数额为准,或者是以买入和卖出两者的累计数额为准,该《规定》均没有做出相关说明[1]。
自“杭萧钢构案”以来,内幕信息的构成要素尤其是是否必须具备“确定性”就一直是内幕交易审判的辩论焦点[2]。对此,学理、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认定标准。虽然在“董正青案”中,法院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内幕交易的基本特征是重要性和非公开性,确定性并非内幕信息的基本特征”。但由于我国不属于判例法国家,先前判例对后续审判没有约束力,加之内幕信息确定性问题的高度争议性,该案的相关司法观点并没有为法律实务界所完全接受。在之后的“黄光裕案”中,内幕信息是否须具有确定性仍然是控辩双方的辩论焦点。内幕信息的构成要素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2.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执法和司法成本高。资本市场关系复杂,准入门槛高,涉及证券、期货、法律、会计、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诸多领域,犯罪分子往往具有较深的专业背景,熟悉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和信息技术。证券、期货交易具有无纸化、信息化等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互联网、3G通信等先进技术传递信息和意图,加大了事后取证的难度,导致实践中查办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数量与实发案件数量相差甚远。
此外,我国在惩治内幕交易案件时,并未采取美国证券法中“有罪推定,严刑峻法”的模式,加之证券监管部门往往掣肘于利益集团的影响,执法司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这使得在查处、惩治内幕交易行为时举步维艰。
3.内幕交易案件案情复杂,涉案层次高。由证券、期货犯罪的本身性质所决定,证券、期货犯罪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面广,涉及投资者众多,严重危及资本市场运行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如在2011年的李启红内幕交易案中,形成了以被告人李启红为核心,其家族成员紧密配合的家族式犯罪网络,涉及人数众多,成员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再如,在“天山纺织内幕交易案”中,由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多为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等,因此内幕交易案的涉案人员往往具有较高的层级和地位。而且近年来,内幕交易有向经济决策管理领域蔓延的态势,公职人员卷入内幕交易的案件有所增多。如,国内内幕交易涉罪的最高级官员李启红,其曾任广东省中山市市长。在2010年因内幕交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宝春内幕交易案中,刘宝曾任南京市经委主任。还有广东省韶关市原副市长李健、公安部经侦局原副局长兼证券犯罪侦查局北京直属总队队长相怀珠。这些人员均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内幕交易谋取巨额私利,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社会影响恶劣。
(二)内幕交易案件司法困难的原因。
1.立法含混不清,带来司法难题。
(1)对“内幕交易”的行为样态的理解分歧。对“内幕交易”的行为样态的准确把握,是理解和适用内幕交易罪相关规定的基础。我国《刑法》第180条规定:“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将内幕交易行为概括为以下三种样态,即:交易行为、泄露行为、明示或暗示行为。
根据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1993年9月2日发布的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证券内幕交易行为:①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②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③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④其他内幕交易行为。根据以上规定可以将内幕交易行为简单概括为四种行为样态,即交易行为、泄露行为、建议行为以及其他行为。
与此相对应的是,《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则将内幕交易行为概括为:交易行为、泄露行为和建议行为三种样态。《证券法》第76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2条规定:“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泄露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的建议的,根据不同情况,没收非法获取的股票和其他非法所得,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为何我国《刑法》规定与《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前置法的规定之间存在差异,是否可以理解为立法者在圈定证券犯罪圈时有意地摒弃了证券法律法规中的 “建议行为”?《刑法》第180条中的“明示、暗示行为”与证券法律法规中的“建议行为”有何区别?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交集部分[3]?
实际上,刑法作出此种不同规定是一种囿于现实之举,在早前的司法实践中,有关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的犯罪都很难取证,而且,内幕人员一般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往往自己不从事交易,而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让他人操作,之后参与分成,而经《刑法修正案(七)》修改后的《刑法》第180条规定“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相对来说降低了司法取证的难度,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加强了刑法对证券、期货市场的保护力度[4]。
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实务部门对于此新增要件的认定却容易产生困难与混乱。这一方面是由于证券、期货交易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证券犯罪行为人通常熟知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监管等各个环节,精通会计学、经济学、法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很难发现具有较强隐蔽性的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行为本身具有特殊性,在刑法适用与司法认定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疑难性,加之《内幕交易犯罪解释》对于“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活动”的司法认定问题却没有专门且明确地规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司法适用的难度。
(2)对“内幕信息”的界定含糊。何谓“内幕信息”,根据《刑法》第180条第3款之规定,内幕信息的范围依照法律、法规确定。根据2005年10月修订的《证券法》第75条第1款规定,“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在该法第75条第2款列举了内幕信息的八项具体内容,其中,第一项将内幕信息限定为该法第67条第2款所列的重大事件。对于期货交易中的内幕信息,根据2007年4月15日施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内幕信息”,是指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包括: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期货交易所作出的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发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期货交易所会员、客户的资金和交易动向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通过对《刑法》、《证券法》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可以发现,虽然法律文本对“内幕信息”有具体规定,但是,仅仅通过法律文本的解读,确实难以准确把握“内幕信息”的实质内涵,更难以应用到具体案件认定中去。例如,公司重大盈利,既不属于《证券法》第75条所列举的八种“内幕信息”之一,也不属于《证券法》第67条所列举的十二种必须公告的“重大事件”之一,但此事件事关该公司内部财务变化,对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有较大影响,进而对投资人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评价为内幕信息是毫无疑问的。
2.证券犯罪取证艰难,降低司法效率。“证据难”问题是世界各国打击证券内幕交易犯罪的共同难题。随着对证券内幕交易行为打击力度的加重,证券犯罪的隐蔽性便越来越强,由早期的明目张胆逐渐转为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方式进行,尤其网络工具在证券交易中的广泛应用,行为人的真实身份一般与网络身份并不一致,操控行为由实体化转为虚拟化,作案证据又可在极短的时间内销毁,甚至不留痕迹,使其犯罪行为极其隐蔽,取证艰难。
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罪“证据难”问题有其独特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
(1)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欺骗性。证券内幕交易犯罪就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犯罪活动,而内幕信息最大的特征就是秘密性、非公开性。正是内幕信息先天具有的秘密性与非公开性使得证券内幕交易行为很难被发现。再加上,从事证券内幕交易者多数为具备证券专业知识的业内人员,其通常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他们在进行证券内幕交易时通常会通过合法的形式对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伪装,并且,证券市场天生具有的波动性更使得内幕交易行为不易被发现。因此,证券内幕交易犯罪活动,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使得司法人员在对该种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时难度较大。
(2)案件查处主体一元化,互助协作不足。在我国,司法机关是对证券内幕交易案件进行的查处唯一主体。虽然《证券法》授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定的权利,但是该法第186条明确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发现证券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表明,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不亲自对涉嫌犯罪证券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也没有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取证的义务,而是将调查取证责任完全转移给了司法机关。在证券行业这个信息如此不对称的领域,涉嫌内幕交易的行为人所在单位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更易于掌握涉嫌内幕交易的行为人的行为证据,而司法机关在没有其他专业部门相互协作和信息互动的情况下进行取证,势必会显得举步维艰,这对于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查处是十分不利的。
(3)取证具有滞后性且证据规则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由证券犯罪的隐蔽性与欺骗性特点所决定,证券犯罪活动往往不会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而通常是在证券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造成了不良影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以后才开始进入引起司法部门的视野。而此时,证券内幕交易已经完成,某些证券内幕交易的证据已被犯罪行为人销毁或掩盖。很可能证券内幕交易的证据仅仅限于交易的电子记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口供以及证人证言。关于获取内幕交易犯罪有关的电子记录方面,司法人员必须借助于相关单位的合作,如果相关单位拒绝合作或迟缓行动,都可能造成难以搜集到相关证据,或错过搜集证据的最佳时机。而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方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有意销毁或掩盖部分证据,并清楚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隐蔽性很强,证据不易搜集,所以通常会拒绝供述犯罪行为。而关于证人证言,由于能知晓内幕交易行为的人通常是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或者因时隔以久,证人的记忆难免会变的模糊,难以取得有效的证人证言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证明力较弱。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券内幕交易罪的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司法操作中均是由控方进行举证,但是,由于证券内幕交易行为证据难以搜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从证据掌握方面而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往往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
3.公职人员涉足、地方保护主义,增加司法阻力。近年来,从南京市经委原主任刘春宝,到广东韶关市原副市长李健,再到公安部经侦局原副局长兼证券犯罪侦查局北京直属总队队长相怀珠,官员涉嫌内幕交易的案件屡屡发生,表明政府官员已经成为内幕交易的新主体。
2011年10月27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万元、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5]。据调查,李启红利用其担任市长的职务便利,在从中山公用集团董事长谭庆中处所获得的该集团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后,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串通其丈夫、弟媳等人购买该公司股票,共筹集投入670多万元,不到2个月获利1980多万元。官员参与内幕交易不但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投资秩序,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还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信力,同时由于官员手握大权,其往往会对侦查和司法审判工作进行阻挠。一方面,政府官员掌握众多的社会资源,占据强势社会地位,天然具有接近“股市内幕”的优势,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头脑,部分腐败官员已经不满足于传统形式的“权钱交易”并开始借助于手中权力融入资本市场,通过各种方式积累资本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投资机会,进行更为隐蔽的资本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部分不法分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往往极力迎合这部分腐败官员的需求,将提供股市内幕信息作为拉拢、巴结官员的一种新手段。为官员提供内幕信息具有更强的便利性和隐蔽性,而且较之传统的行贿手段也更易与为腐败官员所接受。因此,在业内便出现了“送钱不如送消息”的奇怪现象。个别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内幕信息透漏给腐败官员,官员再将内幕信息变成其肆意敛财的工具。更有甚者,为腐败官员提供从内幕信息,到投资建议,再到提供虚假账户的“一条龙”服务。再者官员参与内幕交易的案件频发,还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官员从事内幕交易的监管存在真空地带有很大的关系。在内幕信息监督的设计上,证券法主要侧重于对公司高管人员等的监督,并没有对官员进行监督的相关规定。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并不限于公司高管等人员,在推动当地公司上市的过程中,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也很有可能知悉内幕信息。同时内幕交易犯罪监管和调查的门槛较高,证监部门鞭长莫及,纪检部门又往往缺乏经验,加上部分部门内部职责不明确,使得某些腐败官员有机可乘。
这种“权力型”内幕交易,其形式和手段更加隐蔽,危害也更大。首先表现在,为了规避监管、逃避打击,涉嫌官员一般不直接参与交易,往往借助或指使其他人间接进行证券交易。有的内幕信息知情涉案人,甚至收购社会人员身份证开设股票账户交易,加上股票交易可以电话委托、电脑下单或委托他人操作,给查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在证券监督部门或者侦查机关对其内幕交易行为进行调查时,腐败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介入到调查当中去,利用未必或者利诱的形式,对证券监管和司法活动进行干扰,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司法活动带来较大的阻力。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一直由政府主导,政府直接管市场,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证券市场,在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戒时可能会考虑到对市场、对社会的影响[6]。上市公司一般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与本地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直接相关,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案发,地方政府往往首先考虑地方利益,对于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以罚代刑”,对于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也往往进行一定干预。
4.司法适用的扭曲,违背立法初衷。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活动中,部分法院出现了以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处理官员利用他人提供的内幕信息进行大肆敛财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刑事法律资源配置的扭曲的表现,混淆了两罪的界限,违背了金融领域的法律资源配置的初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1)此类案件本身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对于此类案件(尤其是金融领域内外勾结型案件),从外在表征来看,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利用他人提供大的内幕信息获取了大量财物,这在犯罪构成上与受贿罪极为相似。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其核心行为,势必会致使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犯罪活动得不到刑法上的准确评价。
(2)司法人员思想意识的保守性。部分司法人员,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司法工作人员,由于自身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受“经验主义”的影响,往往在判案时倾向于将犯罪归类为传统的自然犯罪,而对内幕交易罪等新兴罪名往往不会主动予以适用。实际上,金融本身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人员如果不能及时对新兴罪名进行研究学习,主观上过于保守,恪守以往的办案经验,重视自然犯罪,忽视新型犯罪,在处理证券犯罪时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的错误。
(3)取证的艰难性迫使内幕交易罪不受青睐。证券内幕交易犯罪就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犯罪活动,而内幕信息最大的特征就是秘密性、非公开性。正是内幕信息先天具有的秘密性与非公开性使得证券内幕交易行为很难被发现。在加上,从事证券内幕交易者多数为具备证券专业知识的业内人员,其通常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他们在进行证券内幕交易时通常会通过合法的形式对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伪装,并且,证券市场天生具有的波动性更使得内幕交易行为不易被发现。相比之下,对受贿罪的取证反而显得容易得多,因此,部分司法人员在对案件进行处理时受“结案率”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出现违法操作的情况。
三、司法难题的解决对策
(一)重构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
对内幕信息的认定产生争议的根源在于我国证券立法体系的混乱与遗漏。只有重构“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司法难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从“未公开性”、“关联性”、和“重要性”三个方面对内幕信息进行界定,此种认定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未公开性和关联性是从质的角度对内幕信息内容进行界定,重要性则是从量的角度进行界定。但要补充的是,在依据这三个标准进行认定时,还应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在认定“未公开性”时,应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个性因素”。由于公司的规模不同,社会影响力不同,加之信息的性质和内容、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等均有差异,所以认定内幕信息是否公开时不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必要确立市场消化的判定标准,可以将内幕信息的开始期、消化期、价格敏感期等作出相关规定,关于市场消化的衡量标准细化,可以配套出台,司法解释或给予一定的参照案例。
第二,对于“关联性”的认定,应将内幕信息与市场中的谣言和误传区别开来。我国《证券法》在第67条中列举了12项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大事件,并在第75条第2款对内幕信息犯罪的规定中列举了7种信息。毫无疑问,这都是司法实践中认定内幕信息关联性的依据,但是,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却无法将市场中的谣言、误传同真正的内幕信息区分开来。因此,有必要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第三,在认定“重要性”时,可参考“理智投资者标准”。我国现阶段是用价格敏感性标准来衡量信息的重大性,这种标准先天具有较大的不足与局限性,因为价格有时并不能准确及时地对信息作出敏感反应。那么对于重大性的标准该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的TSC Industries v.Northway,Inc案中确定的重大信息标准,即如果一个理智的投资者,在他作出投资时,可能认为这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重要的,那么它就是重要的[7]。
(二)改善内幕交易行为的取证路径。
首先,司法人员要进行自我完善,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内幕交易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端正办案态度,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内幕交易案件的查处。另一方面,司法人员要定期参与培训,不断充实自己,增加在证券、期货、会计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储备,并学习运用高科技手段对证券交易记录等证据进行搜集、截取与分析。
其次,司法机关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保持信息互动。司法机关应积极与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单位或与交易行为有关的单位合作,通过这些单位内部管理程序搜集相关证据。
再次,要积极创新证据形式。内幕交易作为一种证券领域的犯罪案件,因涉及并购重组、上市公司业务运作等复杂的专业问题,司法机关在认定时往往需要商请中国证监会就相关案件的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等问题作出专业认定意见。然而,这种证据形式却往往因为不属于法定的证据形式而不能产生证据效力。只有在“上海组龙内幕交易案”中才首次对证监会认定函的证据属性及类型进行了明确的认定,指出证监会认定函是“国家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所制作的书面文件”与各种命令、决定、通告、指示、信函、证明文书一样,属于“公文书证”,具备证据效力。从而对证监会认定函的证据能力和属性类型作出了明确界定,这显然是在司法认识上更进了一步。
(三)强化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完善机制设计。
执法力度不足与制度设计不完善是内幕交易司法实践的一大顽疾。正是此顽疾导致在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处理时,司法介入往往显得过于保守。一方面表现为法院审理的证券犯罪案件数量非常之少,大部分案件以追究行政责任来代替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部分法院则会拒绝受理一些证券民事纠纷,或者受理证券民事案件存在前置条件。再者,司法渠道的不畅通再加上衔接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使得我国对内幕交易的规制始终不能出现理想的效果。例如,证监会发现了某个企业正在利用内部信息操纵股价,但是由于跟公安部门没有很好的对接,造成股价仍然持续上涨,再持续下跌,在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之后,公安部门才发现问题,然后再去追查,即使能够追查到,普通散户的利益也已经受到损害。
为了解决内幕交易司法中的种种难题,我们有必要强化执法力度,充分重视和利用检察监督的力量,通过建立健全行政与行业管理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减少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杜绝以罚代刑现象的出现,既使得行政力量肯放手,又使得法治力量能接手,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检察机关介入证券市场,运用法律监督权,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监督、监督支持起诉等方式,坚决查处内幕交易行为,尤其是公职人员参与的内幕交易行为,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杜绝内幕交易监管真空地带的出现,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保障证券法律法规得以遵守和执行。
【参考文献】:
[1]任志强,汤志鹰.侦办内幕交易犯罪案件的思考[J].犯罪研究,2007,(3).
[2]赖朝晖.透视内幕交易刑事司法的最新动向[J].中国检察官,2011,(8).
[3]张小宁.证券内幕交易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4]葛 磊.新修罪名诠释——《刑法修正案(七)深度解读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5]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6]白建军.证券犯罪惩戒应坚持“严而不厉”[N].中国经济时报,2005-09-14.
[7]张 军.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The judicial problems,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sider trading
LI Hao
In recent years,insider trading cases become more frequent,whether the"Hangxiao Steel Structure case"or the"Shanghai Zulong insider trading case",has both aroused great controversy concerning on judicature cognizance in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ields.It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bout insider trading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which we should handle in the future.Only by basing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judicial problems,reconstructing the standard that judges insider information,improving the forensics path of insider trading,enhancing the insider trading enforcement,and promoting the mechanism design can we deal with the judicial problems,protect the justice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as well as ensure the securities laws to be complied with and enforced.
Insider Trading;Insider Information;Judicial Problem
DF6
A
1674-5612(2013)06-0024-08
(责任编辑:赖方中)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般项目《近年金融领域刑事司法状态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0BFX042
2013-05-30
李 浩,(1984-),男,山东临沂人,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经济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