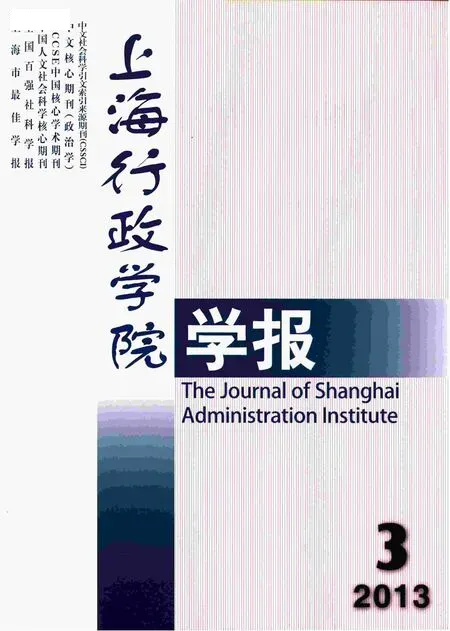中澳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比较
2013-04-10张继平熊敏思
张继平 熊敏思 顾 湘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
引言
2012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的第三届“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政府间审查会议”制定了2012-2016年陆源污染治理的行动方案,中国及其他100多个国家承诺今后将要采取相关的治理行动。据2012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陆源排海污染物持续增加,海洋生态系统明显退化。澳大利亚拥有的海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世界最大的专属经济区,且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由于近岸人口密度大、海洋产业众多,因而受到陆源污染的巨大威胁。2006年澳大利亚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收集和分析,制定并实施了详尽的陆源污染治理国家行动计划,对污染源进行了有效控制。本文将从政策执行的主体、手段、监督三个方面对中澳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政策进行比较,力图为中国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高效执行提供经验和启示。
一、中澳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主体比较
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实施公共政策的人和组织。执行主体构成的合理性、权责分工的明确性和主体间协调的流畅性都影响着执行的效果。
1.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主体的构成
澳大利亚陆源污染治理执行主体多元,目标统一。首先是政府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与州、地方政府的合作下开展了海岸带管理、国家污染物名录编制等行动计划;其次是非政府机构的合作,许多社会事务由非政府组织、公民社区自主管理。非政府组织如EDF(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通过社会捐助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并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再如澳大利亚零售商协会,为减少近岸白色垃圾,对政府承诺大面积减少塑料袋的生产。目前,澳大利亚已有越来越多的水环境保护志愿者、企业、社区参与近岸水质监测的工作。
中国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主体的构成较为单一,主要由环保、海洋、海事、渔业等海洋行政部门组成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称环境保护部)在陆源污染治理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区域督查中心及地方环保部门对其进行治理,海洋行政部门配合开展陆源污染治理行动。此外,中国非政府组织已成为环境保护中的新生力量,如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少、资金和专业人员短缺,没有形成治污合力。同时,由于我国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多以行政命令为主,造成了公众参与意愿较低,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2.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主体的权责分工
执行主体间的合理分工、权责对等有利于提升执行效率。澳大利亚以法律的形式将海洋陆源污染治理的任务进行明确划分。在《澳大利亚海洋政策》(Australia's Oceans Policy)中,明确规定了各级海洋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及公众的责任。
中国陆源污染治理部门在职能上还存在边界不清、分工不明的问题。环境保护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处主导地位,可利用的行政资源较多,而其它相关部门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部门权责分配没有量化,导致执行主体权责不对等,形成行政资源“一边倒”而引发部门间的利益争夺②。如在陆源污染治理专项“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中,由于行政边界模糊,使得环保、海洋、海事、渔业等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形成摩擦和阻滞。
3.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作方式
执行主体合理的协作方式能够缓解、调节矛盾及紧张关系,从而使合作关系更顺畅、更高效地达到治理目标。澳大利亚在吉普斯蓝湖区陆源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主要通过各种会议、论坛等形式来促成各利益相关者的咨询、磋商,制定各方利益代表认为最有效的执行方案,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各方因利益不统一而造成方案执行低效,但同时也增加了行政成本。
中国在解决海洋陆源污染问题时,一般是由环境保护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由于环保部门与专门海洋行政部门治理对象不同,在陆源污染治理过程中,现存的管理模式与海陆一体的现实相悖。条块分割,各部门的管理目标、对象、手段存在差异,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导致了部门协作效能低下,协作不通畅③。因此,完善协调机制,是减少执行主体间的摩擦的重要途径。
通过以上比较可得出,澳大利亚陆源污染治理执行主体的构成多元、目标统一且分工明确,协作方式切实、高效、灵活。而我国执行主体结构较为单一,以政府机构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公众等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低、力量分散,且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各部门责任不明确、权责不对等且缺乏协调沟通,使得陆源污染治理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中澳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手段比较
政策工具理论认为,政策执行的成败在于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工具②。通过中澳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手段的比较,为增强中国执行手段的多样性提供借鉴。
1.命令控制手段
命令控制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使政策在执行时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同时还要有严格的处罚措施,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④。
澳大利亚通过法律、政策等形式为陆源污染的治理行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陆源污染治理的国家行动中,一是对治理区域的科学调查和案例分析,结合已颁布的法令,如1975年联邦政府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为了防治陆源污染颁布的《大堡礁海洋公园法案》以及199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并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改进,作为行动框架。二是实施了形式多样、操作灵活的辅助性政策,如区域海洋计划,因地制宜地为各州提出具体行动方案,指导地方治污工作。三是通过一些合作项目,如政府资助项目(The Community Water Grants Program),促进社区对当地水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在澳大利亚,只要违规排污,都要受到严厉惩罚,并交纳高额罚金。对直接犯罪人可判处高达七年的有期徒刑。如新南威尔士州在1989年颁布了《环境犯罪与惩治法》,被认定是环境刑法中最为严密、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典。
中国在陆源污染的治理行动中,法律数量虽多但可操作性不强。例如在“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中,可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近30部,种类和数量丰富,但这些法规基于国家宏观层面,涉及范围较广且颁布时间过早,对具体、典型的区域如渤海海区缺乏针对性且预防性的法规,因此,对陆源污染的治理目前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也给违法者提供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此外,惩罚措施不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执行力度。2008年9月,由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完成的《中国环境监察执法效能研究项目总报告》显示,“一个在地级市的企业如果一次违法排污,平均受到的经济处罚是4.97万元,而该企业违法期间获得的收益是232万元,违法与守法成本相差46倍”⑤,可见悬殊之大,违法排污成本过低导致了企业的消极行为。
2.经济调节手段
经济手段是为了在有效控制海洋污染的同时,保证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显示,1989年已有14个成员国使用150多种经济手段管理环境⑥。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在陆源污染治理过程中,形成了强有力的经济管控手段,例如实施了环境税、经济补贴和税收减免、押金返还制度、排污交易许可权、排污超额阶梯付费制度等经济手段,并已在实践中逐步运作成熟。
中国目前的经济手段较为单一,已实施的控制陆源污染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设施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等。但目前实施范围较广的是排污收费制度,其他的手段尚未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陆源污染政策执行中,经济手段的运用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3.宣传教育手段
澳大利亚为了治理海洋污染,制定了澳大利亚清洁日(Clean Up Australia Day),通过法定节日增强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调动了公民对海洋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也注重引导对下一代的教育,例如学生进行户外体验,让学生观察自己生活的周围环境,促使他们检查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环境保护的思考⑦。
在中国,往往通过记录片、宣传栏等形式对公众进行教育。虽然公众对陆源污染事件的投诉和新闻媒体的曝光日渐增多,对提高执行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宣传教育形式和途径相对滞后。如通过网络媒介进行宣传时,由于目标群体受教育水平局限、宣传内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公众接受的海洋环保教育非常有限且影响不深,达不到预期目标。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得出,澳大利亚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手段综合且灵活,能够适应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需要。中国在陆源污染治理过程中,以命令控制手段为主,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机制作为保障;经济调节手段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教育相对滞后,在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手段的综合性运用方面还需加强和完善。
三、中澳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监督比较
政策执行监督的主体、途径和力度都对治理政策的贯彻落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澳在陆源污染政策执行的监督主体、监督途径、监督力度方面存在差异。
1.监督主体的比较
澳大利亚陆源污染治理的监督主体广泛,涉及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大众。第一,在澳大利亚,国家海洋部长委员会、区域海洋计划督导委员会对海洋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监察专员可以独立行使调查权、监督建议权、责任追究权和廉政教育权。第二,企业主动进行的自主监督。澳大利亚企业监督体系完善、诚实守信、自我监控能力强。发生违法行为后主动承担法律制裁。第三,以公众监督为主。澳大利亚激励大学、工业部门、地方政府等权威的专业机构共同参与调查研究,大大提高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不仅节省了行政成本,同时还激发了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威尔士,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常被作为环境污染的监测指标,发生严重污染时,渔民将会主动报告有关当局⑧。
中国陆源污染政策执行的监督主体主要以政府内部监督为主,企业及公众参与意愿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环保、海洋、海事、渔业海洋行政部门及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对全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由于各自负责的水域有所分工,又缺乏统一的海洋污染治理监督机构,在陆源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各部门的工作处于多龙治水水仍泛滥的状况。中国企业缺乏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中国大多数企业仍过多关注眼前利益,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高,意识不强,更谈不上自我监督及相互监督。近年来,在我国陆源污染排海的重大事件中,公众在控制陆源污染、保护海洋环境中的监督和维权已渐露头角。例如近期江苏启东市民因王子纸业污染排海项目获批而进行了群体性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媒体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最终,当地政府还是决定永久取消王子纸业的排海工程项目,这预示着公众参与意愿及公众监督意识的不断增强。
2.监督途径的比较
澳大利亚的监督途径较为完善,通过合作机构间的相互监督、设立申诉体系及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监督。首先,政府与非政府机构间形成相互监督的局面。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科学调查和研究,一方面为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数据,另一方面对执行的效果进行监督。其次,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在澳大利亚,各行业都设有独立的申诉体系,澳大利亚政府及各州专设机构专门调查、调解公民对政府或公务员的不满行为及腐败行为,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最后,广泛的社会调查。例如澳大利亚生态健康监测计划(EHMP)是综合的海洋、河口、淡水监测计划。它通过对东部昆士兰18个近海海域的区域生态环境评估、18个河口和摩顿湾的整体评估,来确定水质的好坏⑨。这项计划为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同时利用网络将这些数据反馈给公众,并通过发放民意调查问卷使公众主动参与对陆源污染治理质量的监督中来。
中国陆源污染政策执行的监督包括行政部门的监督、社会媒体及大众的监督。一是政府内部的监督,通过监察部门及人大的走访、巡视等方式,对各级环境部门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监督;二是通过社会媒体、大众的网络举报、媒体曝光等途径对政府进行监督和问责。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信息不透明、不准确、不对称等问题,削弱了社会大众的监督力量。
3.监督力度的比较
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包括对陆源污染监督性监测的范围、站点的数量和监测指标的设定,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
澳大利亚开展的生态健康监测计划是最全面的海湾、河口、流域监测计划之一,旨在评估管理活动的有效性。一是监测的范围广,监测的范围涵盖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评价区域面积约为2.3万平方公里;二是站点数量多,在近海沿岸共设248个站点,这些站点监测陆源污染对近岸流域的排放;三是监测指标综合,利用生态健康的生物学指标和理化指标来测定水域的健康状况,评价结果每年发布一次。生物指标和理化指标能根据不同站点因地制宜地设定,同时监测结果给出了人类活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我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是目前历时最久的陆源污染治理行动。从2001年起展开了对9.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监控;在监控区近岸共设49个站点,并通过水环境质量、生态系统健康度等构建指标体系。《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中期报告显示污染治理有一定效果,但不尽人意。例如渤海海区未达到清洁水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仍呈增长趋势,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流的污染物超标排放量居高不下。因此,中国在监控范围、站点布局、指标设定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澳大利亚监督主体广泛、监督途径多样、监督力度高效为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保障。中国目前监督主体主要以行政机构为主,构成较单一;监督的途径还需拓展;监督性监测的力度还应加强。
四、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启示
澳大利亚陆源污染治理起步较早,也曾经历了管理措施缺乏、政策执行低效、陆源污染严重的时期,但这些问题引起了整个澳大利亚对海洋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在陆源污染治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上的比较,为中国陆源污染政策执行主体结构的优化、执行手段的加强和执行监督的强化提供了启示。
1.重塑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主体
陆源污染源分散、范围广、牵涉的部门多、治理过程非常复杂,在陆源污染治理过程中,不仅是上级给下级分派任务,还需要政府与非政府间的沟通、协作。
一要加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合作。鼓励有关污染治理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增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促进政府、民间团体、企业、个人在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广泛合作。二要权责明晰。尽快建立统一的协调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部门,有利于海洋污染治理工作的统一部署、逐层落实,同时缓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部门利益的争夺造成政策执行的低效率。三要建立可行的协调机制,为执行主体间高效的沟通和协作提供平台。
2.改进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手段
陆源污染治理的手段并没有优劣之分,要根据政策目标,刚柔并济,通权达变,才能使不同的手段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高效实施。
首先,加强惩罚力度,完善惩罚机制,保证命令控制手段的有力实施。其次,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多管齐下、全面谋划。再次,在陆源污染治理的过程中,理性使用命令手段。防止过多依赖行政手段而造成的局限性。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促进综合手段的运用,才能更有效地达到治污目标,实现海洋生态文明的战略。
3.增强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监督
政策执行的监督是政策高效实施的必要保障,为了使陆源污染治理政策卓有成效地实施,一要着力扩大监督主体。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鼓励更多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监督的队伍中来,以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二要着力推进多元的监督方式。要通过互相监督、同行评审等方式发现亮点和不足,进一步加强量化绩效管理模式。三要着力加强监督力度,科学合理地设定监测指标,提升监测力度和质量,同时扩大监测数据公开的范围,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有利于扩大公众监督的途径。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0年。
②涂峰:《政策执行中的治理困境--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99页。
③王琪、丛冬雨:《中国海洋环境区域管理的政府横向协调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4期,第63-64页。
④宋国君:《环境政策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32-33页。
⑤涂晓芳、黄莉培:《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环境治理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2页。
⑥马中:《环境与自然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12页。
⑦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Threat Abatement Plan.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Water,Heritage and the Arts,2009.
⑧朱新平:《澳大利亚水产养殖的未来》,《中国渔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第36页。
⑨王菊英、韩庚辰、张志锋:《国际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最新进展》,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59-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