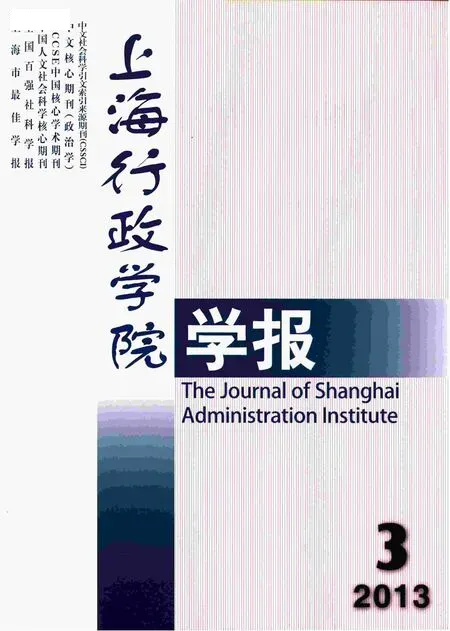威廉·里克尔与实证政治理论*
2013-04-10戴扬
戴 扬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4)
威廉·里克尔(William Harrison Riker,1920-1993)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创立的“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PPT)给社会科学界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变革,他建立的“罗彻斯特学派”(Rochester School)彻底改变了20世纪政治学研究的风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里克尔所倡导与创建的实证政治理论,即理性选择理论一直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流。迄今为止,虽然围绕该理论的争论不绝于耳,但它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本文旨在探索这位杰出政治学家的思想轨迹,探究他创建的实证政治学理论,评析该理论在政治学中的贡献与局限。
一、威廉·里克尔其人其事
威廉·里克尔①1920年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市,28岁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卡尔·弗里德里希,其博士论文《产业组织中的委员会》,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案例研究方法。但那时,他已经对于当时政治学所学习的主流内容心生不满。因此,他开始追寻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科学研究。1949年,里克尔在位于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顿的劳伦斯学院取得教职。接下来的数十年,他一直留在那里,建立了政治学系并努力推行和传播他的政治学方法论思想。1953年,里克尔出版了教材《美国的民主》,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民主是每个人的自尊。这一句简短的话包含了民主理想的全部……如果自尊是民主之善,那么阻碍它的一切就是民主之恶”②。改变主流政治学研究方法、建立新的研究方法一直是里克尔思想中一粒萌芽的种子。变化从1954年开始,当时两位兰德公司的学者夏普利和沙比克③发表了一篇被他们称为“权力指数(power index)”的论文,文中将权力指数定义成一个数学公式,将立法者的权力表示为一个其改变决策能力的函数。运用数学语言解释政治过程这样一种新风格立刻打动了里克尔。受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邓肯·布莱克《集体决策的基本原理》(1948),肯尼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以及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等著作的影响后,他开始将这些著述融入自己的课程,作为其“新政治学”的基础,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尝试运用“新”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这包括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强调微观基础、博弈论、空间模型、理性行动的集合论以及集体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尽管这些方法与结论在当时还属边缘研究,距离里克尔构建实证政治理论的“宏愿”也还相去甚远,但是它们已经为里克尔运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从事联盟起源的研究做了最初的铺垫。1960到1961年,里克尔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政治联盟理论》,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1963年,罗彻斯特大学期望建立一个具有发展潜质的政治与经济学系,严格地说,就是希望应用物理学的科学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而此时,里克尔的努力被校方注意到,他被邀请负责在罗彻斯特大学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学系。自此,里克尔开始拥有操练自己思想的场所。首先,他计划开设了14门新的课程,包括政治学范围,策略理论,实证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现象的度量问题,政党,立法行为,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宪法解释的问题,国家安全政策以及当代政治哲学。然后,他招聘一批青年才俊 (Richard Fenno,Ted Bluhm,Peter Regenstrief,Jerry Kramer, John Muller,Gordon Black etc.)来协助自己完成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所创立的政治学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截至1973年,该系已经毕业26名博士生和49名硕士生。这些学生分别进入到美国的各个大学,例如,卡耐基梅隆大学、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他们当中包括彼得·奥德舒克 (Peter Ordeshook),巴巴拉·辛克莱尔(Barbara Sinclair),理查德·麦克凯尔维(Richard McKelvey),约翰·阿尔德里奇(John Aldrich),戴维·罗德(David Rhode),以及如今在美国政治学界尤其是实证政治理论领域相当有影响力的肯尼思·谢普斯尔(Kenneth Shepsle)和莫里斯·费奥里纳(Morris Fiorina)等人。
之后的30余年,里克尔一直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断地拓展理性选择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在大学里开设新的课程让学生们接受经济数学(包括博弈论)的洗礼,培养越来越多乐于从事“新”政治学研究的未来学者,一步一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以至于成为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可以说,里克尔是将理性选择理论有系统地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阿玛蒂和布宜诺·德·麦斯奎特认为,里克尔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者,甚至比经济学家还要早④。据统计,里克尔一生共发表了15本书、69篇学术论文,从1972年到2001年,他的著作总共被2000位不同的学者、在500种不同的期刊上引用了将近3700次,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政治联盟理论》(1962)一书,总共是664次,平均一年17.5次⑤。
二、实证政治理论:核心假设与理论基石
在政治学界,实证政治理论也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这主要是由于该领域研究者对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实证政治理论,则通常是学者们偏爱的自称,有时这些学者也自称罗彻斯特学派。当然还有学者以公共选择理论称之,这是由于该学派的开山鼻祖威廉·里克尔曾经是美国公共选择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学者开始偏爱使用实证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名称,原因是与实证政治理论的早期发展过程不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进入这一领域⑥。
简言之,实证政治理论是政治学家追求建构一般性理论的结果,是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的理论,即在某些假设前提之下,经过严谨的逻辑演绎推理得出一系列可被经验检验的定理,这些定理经过检验筛选之后,逐渐积累成为用来解释尤其是预测政治现象的知识。用里克尔自己的话来说,这种一般性的政治理论应当具有三种功能:第一,描述政治现象;第二,帮助研究者预测政治现象;第三,通过理论预测,可以让改革者更加务实地选择“可行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应该做”的方案⑦。并且,这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在学界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营造一个能够集中火力投入的研究‘焦点’(focal point);二是演绎推导出来的结论,在尚未接受经验检验之前,为我们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起点;当然,当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落差产生时,就是新一波理论改进与下一波更深入理论发展的动力所在,这是推动学界进步的路径”。⑧
要了解实证政治理论是什么与不是什么,首先需要理解它最重要的两项理论基础:第一,理性——个体做出理性决策;第二,博弈论与策略行为——个人做出决策之前会考虑其他个体的行为。⑨
1.理性与理性选择
实证政治理论认为,理性强调的是个体做出理性决策。简言之,理性就是人类所有趋利避害的行为。⑩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行为研究中心为期1年的研究工作,给里克尔所推行和倡导的实证政治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在与其他领域学者(例如经济学家)的交流中,里克尔获得新的灵感,此时,他重塑了“理性”概念,并且将他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从政治学领域拓展到了演化生物学。里克尔与莱瑞·弗里德曼(Larry Friedman)的对话为此提供了证据。⑪里克尔认为,理性行动与政治结果的关系表明,政治结果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与人类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相关。此外,里克尔认为理性行为是演化而来的,政治理性作为一种衡量目标达成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与生物学上的物种存活与演化成功是相类似的。尽管人性并不是如此单一,但在里克尔眼中,理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通用的“记分卡”:任何成功的结果都是由于理性的行动,反之任何失败的结果则与行动的非理性有关。⑫在实证政治理论家看来,人类具有“理性”的基因,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是一种习惯或惯例,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或者说是历经自然选择长时间演化而来的。他们并不像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认为行动者具有充分的信息;他们并不认为行动者的理性行为是经过有意识地计算;他们之所以运用模型来描绘利益算计,是试图表达行动者面临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实证政治理论家所理解的“理性”是人类所有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意味着人类被赋予的自由意愿以及在众多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权利。从方法论层面看,理性选择是从个体理性出发解释集体选择结果,属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在里克尔看来,用模型解释政治现象具有科学性:因为真前提不能推出假结论,理论若被事实证否,必然是前提不正确,而逻辑推演可以让我们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只要不断修正前提,理论对事实的解释力就会越来越强。而批评者认为,理性选择其实是“套套逻辑”,因为理性选择根据一系列前提假设进行逻辑推演,并依此进行实证研究,如果发现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就回过头来修正其假设,那么该理论永远可以自圆其说,无法判断其理论真伪,不符合科学精神⑬。格林和夏皮罗也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不合乎科学理论的条件,因为研究者可以任意设定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将那些不符合其前提的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将不能被解释的现象视为非理性⑭。对此,实证政治理论家认为,理性选择的核心假设虽不见得完全合乎现实,但已趋近于行动者在进行选择时的思维过程,再加上其理论假定的简洁性——简洁的假设易于被修正,复杂的假设将使错误的理论难于被修正,“大致的对比精确的错更可贵”——理性选择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具有进步的可能⑮。正如台湾学者林继文所指出的,理性选择以构建科学的政治理论为目标,但它只是达成此目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理性选择要能成为经验理论,需和广义的经验研究(包含历史学)结合:前者提出一套“若X则Y”的规律,后者告诉我们X是什么。许多批评理性选择的人忽略了这一点。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针对个体的理性偏好,所有的理性选择模型都必须采取“完全性”和“可传递性”的假定。换言之,这是公理。(2)个体偏好和个体行为之间必须存在逻辑关联,而所有理性选择模型都必须如此设定。这是理性选择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偏好或许不容易观察,但只要偏好和行为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即可通过对行为的观察来修正对偏好的假定。(3)个体行为能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集体选择。所谓机制,可能是制度,也可能是某种博弈规则,但是必须要清楚标示,解释才能完整。(4)理性选择理论必须对个别行为者的偏好进行假定才能进行预测。理性选择从未假设行为者的偏好是同质的(如利己不利他)。因此,偏好乃因人而异,对偏好的描述也是个别性的。如果理性选择的模型符合条件(4),那么它即可成为经验理论。⑯
事实上,理性选择已经在与其他研究途径的交融中,拓展了其研究领域,获得了新发展。例如将理性选择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便成为“分析性叙事”(analytical narratives)。⑰
2.博弈论与策略行为
在威廉·里克尔之前,政治学研究还没有关注到政治过程中决策者之间的策略互动。里克尔认为集体选择是理性的政治行动者之间进行的策略性选择的结果。自他开始,博弈论广泛地进入到政治学领域。
所谓博弈是策略交往的一种建模方式,后者是指如下情形:个人的行动后果依赖于其他人的行动,并且所涉各方会意识到这种相互依赖。一个博弈是一套完整的识别系统,包括参与人,每个参与人的所有可行的行动方案的列表(包括视其他人行动而定的行动或基于偶然事件的行动)——被称为策略集合,每个策略集合对应的报酬,以及博弈的顺序和每人拥有的信息。参与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比如企业、贸易联盟、政党或国家。⑱
博弈论关注均衡概念,在博弈论中均衡是指在一个预先设定的环境中关于人们的选择及其相关结果的预测。这一预测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如果选择的制度背景是……,并且如果人们的偏好是……,那么可能存在的唯一选择和结果是……。”因此,均衡的解释取代了对于事件的新闻式解读和环境因素与政治结果之间的统计关联。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博弈论中均衡的运用主要是试图提供因果解释。⑲
里克尔将N人合作博弈的联盟理论应用于分析政治过程,并提出了政治联盟理论。他认为政治中实际形成的联盟是最小获胜联盟,即如果某一成员退出或背叛,该联盟就不会获胜。例如,在由5个党组成的议会中,至少3个党结盟才能获胜。里克尔指出,在N人零和合作博弈中,如果博弈参与者是理性的,信息是充分的,那么实际形成的联盟总是最小获胜联盟。⑳
继里克尔之后,他培养的很多优秀学生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在他们的努力下,不确定条件下的博弈均衡理论被用来分析涉及不确定性的政治决策及其过程的模型化。例如,在选举政治中,不完全信息模型被运用到这样一些问题上:人们为什么投票、候选人竞争与投票行为等。
现在,博弈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已蔚然成风。尤其近些年随着演化博弈论的发展,政治学家们纷纷效法经济学家,探索如何将演化博弈论引入政治分析。率先在政治学中应用演化博弈论的学者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考尔曼,米勒和佩奇(Kollman,Miller,and Page);本多和斯威斯坦科(Bendor and Swistak);欧贝尔(Orbell)。在他们的著述中,演化理论被用于模拟个体限制信息处理能力的动态过程。例如,演化博弈论放松了个体完全理性的假设:随着时间流逝,对于短视的博弈参与者而言,更少成功的策略和类型被更多成功的策略所替代,那要归因于演化选择过程。[21]如今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演化模型已经被大量地应用于集体行动问题和利他行为的演化。这包括投票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公平契约和文化竞争。[22]
三、威廉·里克尔的实证政治理论:为政治学留下了什么?
实证政治理论的研究议题涉及很广,近乎覆盖到政治学所有的分支领域,不但有选举研究、议会研究、政党研究,还涉及国际关系、公共行政等分支领域,甚至包括制度研究[23],与实证政治理论有关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笔者择其要端考察里克尔所创建的实证政治理论在政治学中的贡献与局限。
1.联盟理论
正如前述,里克尔的研究使得实证政治理论在政治学里诞生,使得政治学界认识和接受了理性选择和博弈论在政治分析中的重要作用。里克尔认为可以通过分析行动者决策的微观基础来研究政治学,行动者就犹如运动中的原子微粒一样能够被模型化,正因如此,如果能够了解一个原子微粒的动能及其所释放的能量,那么原子的运动轨迹就能够被预测。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行动者的偏好以及塑造其选择的环境来预测他的行动。通过这一思路,政治学家能够通过对个人决策变量的分析将集体行动的结果模型化。
在《政治联盟理论》一书中,里克尔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联盟的形成,建构了他的模型概念,如不确定性、动力决策过程、稳定或“均衡”,他指出政治中集体选择的结果是来自于政治过程中理性与策略行动者之间有意识的权衡的结果。[24]正如卡普兰所说,《政治联盟理论》一书,是里克尔以N人合作博弈论为基础建构一般政治理论的尝试。[25]在里克尔的研究中,联盟主要是指立法机构中的联盟组织、政党或政治党派中的集团。他指出,实际形成的政治联盟是最小获胜联盟(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所谓最小获胜联盟是指这样一种联盟:如果某一成员退出或背叛,该联盟就不会获胜。[26]用里克尔自己的话来说,“在与补偿性的多人(n-person)零和(zero-sum)博弈类似的社会情形中,参与者结成了他们相信将确保胜选所需足够大的联盟,而并不一味追求更大。[27]
里克尔认为,最小获胜联盟法则是适用于三人以上的零和博弈,参与者在其中可以交流和协商。同时,他指出,最小获胜联盟的形成需要满足一组条件,即(1)博弈参与者在博弈框架内达成一个共同目标;(2)参与者有足够的资源来“赢得”博弈;(3)如果其中任何人退出联盟,即无法获胜。[28]科拉·斯特拉姆进一步指出,联盟形成的动态过程是:获胜联盟是通过原始联盟(protocoalitions)的不断扩张而创建的。所谓原始联盟并非指掌握了足够资源可以赢得胜利的联盟,根据里克尔的假设,原始联盟主要通过参与者之间一对一的承诺来不断扩张,直至联盟成员无意再对其他参与者做出这种承诺为止。[29]
与此同时,里克尔还通过历史事件与过程的逻辑演绎来检验结论,例如,他分析美国两党制的演化,他对18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所谓“腐败交易”的分析。此外,他也分析国际关系与福利,并由此开创运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新领域。迄今为止,里克尔的政治联盟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探索议会体系中政府联盟的形成。对于联盟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该理论的可验证性问题。而事实上,最小获胜联盟理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得出一个唯一的均衡解,或者说它无法找到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然而,无论怎样,联盟理论在实证政治理论的体系化过程中始终产生着深远影响。
2.制度的理性选择研究
二战以前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主要涉及5个方面:(1)历史与案例研究法,主要存在于当时颇为流行的公法研究和伦纳德·怀特的公共行政研究领域;(2)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新闻研究方法;(3)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的心理学方法;(4)约翰·戴伊(John Dewey)的政治与民主理论;(5)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强调观察与统计的行为主义方法。[30]其中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盛行的行为主义方法,可以说是实证政治理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近亲”,因为它强调统计相关性以及经验检验,只是它不具备理性选择所具有的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以及寻求一般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同时实证政治理论提供了行为主义所不能提供的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民主的方法。[31]
对里克尔而言,“合法”的政治学仅仅是依赖于演绎模型和经验检验的人类制度的实证分析。[32]
实证政治理论主要借鉴理性选择(很类似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讨论规则对决策结果的影响,里克尔所要解释的是:在一个零和博弈与“赢家通吃”的世界中,政治决策是怎样通过资源分配而做出的。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民主制度在政治现实中是如何运作的,也有助于解释政策决策的复杂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角色如利益集团、执政者和政府官员等的作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如Tirole,Grossman,Helpman,Dixit等都纷纷进入这一领域。从这一层面上说,里克尔又开拓了政治学中的新制度研究。如果说,安德鲁·肖特是经济学界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研究的先驱,那么里克尔则是政治学界将博弈论作为制度研究基础的先驱。
可以说,里克尔为制度的形成寻找到了微观基础,在解释制度形成与制度稳定性的问题上,他在理性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方面寻求答案,认为制度或政策的形成是人与人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即偏好诱致均衡(preference-induced equilibrium)。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偏好来源的解释,成为他面临的难题,尽管其学生肯尼斯·谢普斯尔为解决该问题提出了结构诱致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的概念。谢普斯尔认为结构与程序以及偏好共同推动了政策后果的形成。作为一位研究国会政治的学者,他同时举例指出,由多数党或资深议员主导的相关委员会成员的偏好对政策后果有着过度影响力,即政策结果往往随着关键行为者偏好的改变而改变,制度结构和程序赋予他们过度的控制议程的权力。可以说,所有的行动,并非是所有偏好的直接加总,其原因勿宁说在于,对结构和程序的控制产生了有时相当微妙的影响。[33]然而,谢普斯尔本人亦认为结构诱致均衡仍留有一个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即结构诱致均衡方法注意到结构和程序的后果,却忽略了产生结构和程序的原因。因此,如何建构一个能够解释制度的生成、存续与变迁的一般理论,成为所有关注制度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四、结语
综上,本文回溯了美国实证政治学的先驱威廉·里克尔的学术思想与研究重点,探讨了里克尔所倡导的实证政治学的理论内涵与方法论基础,从联盟(或集体行动)和制度两个层面上,探析了他对政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实证政治理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实证政治理论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知彼”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尤其是对于实证政治理论方法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深入理解,其中包括博弈论模型的建构;其次,借鉴其联盟理论中对于集体行动的理解,解释中国经验中的选举问题;最后,应用制度的理性选择研究,探讨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变迁,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焦点。
注释:
①关于里克尔的主要经历与思想,参见:Amadae.S.M.&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Rochester School: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271-283;Shepsle,K.A.,Loser in Politics and How They Sometimes Become Winners:William Riker's Heresthetic,Perspective on Politics 12:307-315.
②Riker,William H.,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3,p.19.
③Shalpley,L.S.and Martin Shubik,A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Committee Syst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8,1954,p.787-792.
④Amadae.S.M.&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Rochester School: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290.
⑤Maske,K.&G.Durden,The Contributions and Impact of Professor William H.Riker,Public Choice,vol.117,2003,p.191-220.
⑥Amadae.S.M.&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Rochester School: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289-290.
⑦Riker,William H.,Application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31,1992,p.5-6.
⑧陈敦源,吴秀光:《理性选择、民主制度与‘操控游说’:William H.Riker新政治经济学的回顾与评述》,《政治科学论丛》(台湾)2006年第12期,第189页。
⑨McCubbins,Matthew D.and Michael F.Thies,Rati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6,August,p.3.
⑩McCubbins,Matthew D.and Michael F.Thies,Rati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6,August,p.4.
⑪S.A.Amadae,William H.Riker's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in S.A.Amadae,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163.
⑫S.A.Amadae,William H.Riker's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in S.A.Amadae,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164.
⑬Opp,Karl-Dieter,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9,11(2),p.179-184.
⑭Green,Donald P.and Ian Shapiro,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27.
⑮Tsebelis,George,Nested Games: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17.
⑯林继文:《虚假霸权:台湾政治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政治科学论丛》(台湾)2006年第9期,第76-77页。
⑰Bates,Robert H.,Avner Grief,Margaret Levi,J.Rosenthal and Barry R.Weingast.,Analytical 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⑱Samuel Bowles.Microeconomics:Behavior,Institutions,and Evolution.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4:31-32.
⑲Peter C.Ordeshook.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reface,13.
⑳Riker,William H.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32.
[21]Oleg Smirnov,Applications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Paper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2004 September,3:3
[22]Conley,John P.,Ali Toossi,and Myrna Wooders.2001.Evolution and Voting:How NatureMakes us Public Spirited.Economics Bulletin,v.28,n.24.Guth,Werner,and Kerstin Pull.2004.Will Equity Evolve?An Indirect Evolutionary Approach.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73-282.Vega-Redondo,Fernando.1993.Competition and Culture in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Equilibrium Selection:A Simple Example.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5:618-631
[23]Weingast,Barry R.,Political Institutions: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in Robert E.Goddin and Hans Dieter Klingemann ed.,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24]Riker,W.1962.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3.
[25]Morton A.Kaplan,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by William H.Riker,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47,Combating Organized Crime(May,1963),p.137.
[26]Riker,W.1962.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32.
[27]Riker,W.1962.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32-33.
[28]科拉·斯特拉姆:《联盟理论中的规模原则:最小化获胜联盟法则》,[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Stein Ugelvik Larsen):《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77页。
[29]科拉·斯特拉姆:《联盟理论中的规模原则:最小化获胜联盟法则》[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0页。
[30]S.A.Amadae,William H.Riker's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in S.A.Amadae,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156-175.
[31]S.A.Amadae,William H.Riker's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in S.A.Amadae,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161.
[32]S.A.Amadae,William H.Riker's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in S.A.Amadae,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167.
[33]肯尼斯·谢普斯尔:《制度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1]Riker,William H.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2]Riker,William H.&P.C.Ordeshook.An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3.
[3]Riker,William H.The Future of a Science of Politic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11,1977:11-38.
[4]Riker,William H.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4,1980:432-46.
[5]Riker,William H.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San Francisco:W.H.Freeman,1982.
[6]Weingast,Barry R.,Political Institutions: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in Robert E.Goddin and Hans Dieter Klingemann ed.,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7]Peter C.Ordeshook.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8]Amadae.S.M.&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ROCHESTER SCHOOL: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269-295.
[9][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M].任晓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