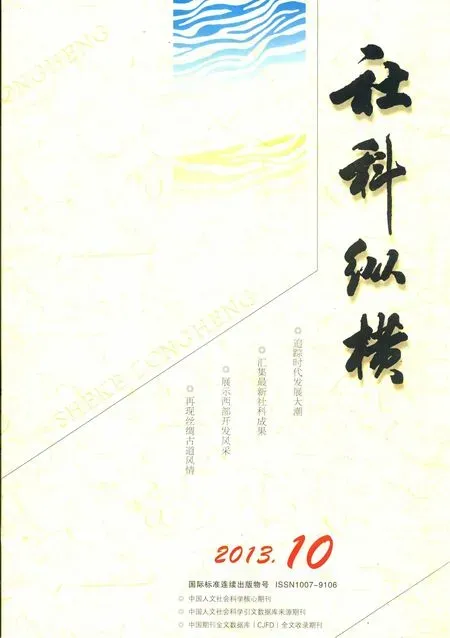从倡导到批评——清末《女子世界》对女权态度的演变
2013-04-10郭晓勇
郭晓勇 马 培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一些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强国、强种的角度思考女性解放问题,引入西方女权学说,提倡男女平等。到20世纪初年,“女权”作为一个新词汇开始被频繁使用,形成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女权”口号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新阶段。不过,关于如何提倡女权,晚清学界存在着分歧。这其中,《女子世界》杂志对提倡“女权”态度的演变,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学界对女权问题的认知程度。
一、“女权”之发轫
女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男女平等到男女平权,进而倡导女权的过程。西方男女平等的观念,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他们在中国进行的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以及对近代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介绍,无疑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男女平等”主张。康梁等人出于强国保种的目的,提出戒缠足、兴女学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男女平等的认识,主要与女学有关。如梁启超所言:“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岐矣。”[1]就是说,是把男女平等作为兴办女学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到20世纪初年,随着西方女权理论的传播,男女平等思想开始向男女平权跃进,“女权”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开始被频繁使用。“女权”一词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能见诸1900年《清议报》上登载的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译文。梁启超在按语中提到:“先生喜言女权。”[2]同年,在该刊第47号,刊登了日本学者石川半山的译文《论女权之渐盛》,对西方国家女权状况做了一些介绍:“其俗视崇女子与否,以判国民文野。故举世靡然从风,敬重女子,礼数有加,故其权日盛。”对于西方女子争取参政权的活动,作者持一种乐观态度:“然女权日长,浸至二十世纪之间,难保无女子参与政事也。”[3]石川这篇文章,被蔡元培等人予以转载,文中的思想亦为人所熟知。
“女权”一词真正得到普及,则应归功于马君武和金天翮的译介与阐发。马君武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向国内译介女权学说。1902—1903年间,他先后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即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以及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介绍到中国,推动了女权学说的传播。在1903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弥勒约翰之学说》中,马君武专辟“女权说”一节,译述穆勒的《女人压制论》与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他把女权革命与民权革命相联系,认为要想实现民权革命之“天赋人权”,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4](P137)。
1903年8月,金天翮的《女界钟》一书出版,在思想界引起很大震动。该书以“天赋人权”学说作为争取女性权利的思想依据,对中国妇女所受各种压迫进行控诉,系统讨论男女平权问题,提出妇女应该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以及婚姻自由等六项权利。纵观全书,金天翮把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寄托在“国民之母”这个载体上。他明确表示:“汝之身天赋人权、完全高尚、神圣不可侵犯之身也,汝之价值千金之价值也,汝之地位国民之母之地位也,吾国民望之久矣!”[5](P83)金天翮这些言论,在当时获得了广泛赞同,也提示了晚清知识界对“倡女权”的迫切要求。1904年《女子世界》的创办,恰恰是对如何“倡女权”的具体实践。
二、“倡女权”的急先锋
1904年1月17日,由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在上海创刊,成为倡导女权的重要阵地。作为《女子世界》的发起人之一,金天翮在发刊词中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6]与之相呼应,丁初我在《女子世界颂词》中也提出:“欲再造吾中国,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欲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7]。显然,金天翮、丁初我是站在救国、强国的角度来思考女权问题。在他们看来,女权不昌,导致民权堕落,进而国权沦丧。他们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如天醉生就担忧道:“女子无权,国力已减去了一半。把这一半拖妻带女的病夫,去当那四面的楚歌,岂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8]因此,他们用了很多文字来描述对“新世界、女中华”的赞美与向往,甚至断言:“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7]
然而,现实中的女子尚不具备理想中的“国民之母”资格,存在着种种的缺陷。在《说女魔》中,丁初我径称“我女子真世界魔王哉”,并将病因归结为“情魔”、“病魔”、“神鬼魔”、“金钱魔”等恶疾,认为只有排除魔障,新我女魂之空气,否则“我女界绝无清明之一日,我民种绝无争存之一朝”[9]。自立则通过历数女子“柔顺”、“卑抑”、“愚鲁”等积习,得出“女子实无魂矣”的结论,并认为:“苟非举数千年之积习谬种遗传之恶现象一扫而空之,如汤之沃雪,水之灭火,欲其孕育文明以复天赋人权,不亦难呼?”[10]现实中女子的弊病如此之多,不免使人质疑“国民之母”的构想,如亚特所言:以此今日孱弱污贱之女子,而欲其生伟大高尚之国民,是将化铁而为金,养鹯而成凤也,可得乎,不可得乎?”[11]
既然女子存在种种弊病,就需要“去旧质,铸新魂”。这种美丽构想与现实落差的内在焦虑,使得《女子世界》在创办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一种亢奋状态,成为倡导女权的急先锋。杂志中,经常可以看到“女权时代”、“女子世界”、“女中华”之类的词语,表达了对女权时代的热切向往。在他们看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女性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依旧是熙熙攘攘,在衣食堆中打盹,不知国亡家破为何事”[8]。要挽救民族的危亡,女子应该与男子一起抵御外辱,共担救国重任,“是故男子当尽爱国之责任,女子亦当尽爱国之责任;男子当尽国民之义务,女子亦当尽国民之义务也”[12]。为了鼓励女子,他们大力表彰古今中外的杰出女性,以发掘女性的优长之处,甚至表示女子“天性良于男子者万倍,其脑力胜于男子者万倍,其服从之性质,污贱之恶风,浅薄于男子者且亿万倍”[7]。
由于认识到现实中的女性所处地位低下,《女子世界》也登载了大量反抗压迫,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摧残的文章,号召女性进行“女界革命”。对于女性几千年所受压迫,他们大声疾呼:“诸君固曰受男子数千年之压制,浸浸淫淫,成为习惯,非我辈之咎也。恶,是何言!恶,是何言!诸君岂无耳目无手足欤?诸君岂无脑筋无血气者欤?”[13]对于传统女性的“三从”,杂志批评道:“三从耻复耻,从父从夫又从子。从父犹可言,家庭教育受髫年,夫妇实朋友,母从子命尤荒谬。须知男女平等,尊卑贵贱复何有?”[14]对于传统婚姻,他们斥为“毒网罗,惨地狱,坑陷了千千万万的同胞”,认为婚姻是“儿女第一切肤事情,与父母无干,更与媒妁无涉”[15]。
《女子世界》这种言论,对于女权伸张,增强女性自信心,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也不免会出现一些激烈言论。作为主编,丁初我在杂志创办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就很激进,他提出“女子家庭革命说”,高呼:“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他认为“论男女革命之重轻,则女子实急于男子万倍”,“愿同胞溅热泪,运妙腕,奋一往无前之精神,持百折不回之愿力,相机而行事,因势而利导,种种天赋完全之权利,得一鼓而光复之。”[16]这种“一鼓而光复之”的乐观心态,也使得刊物充满了很多光复女权的豪言壮语,即如《女中华歌》所唱:“女学既兴女权盛,雌风吹动革命潮。吾华男子太无状,献谀屈膝穷俯仰。多少兰闺姊妹花,相将携手舞台上。”[17]这种慷慨之词虽然读起来痛快淋漓,但对女权的过分揄扬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大概也是缘于此点,促使蒋维乔写下《女权说》一文,由此而引起一番争论。
三、从倡导到批评
倡导女权,铸造国民母,必然要涉及改造的方法、途径问题。对于如何倡导女权,金天翮在发刊词中只笼统提到“:吾今日为中国计,舍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外,其何以哉?”[6]对于女学与女权的关系,并没有说明。最先谈到女学与女权关系的,是广东女学堂学生张肩任。她在《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中指出:“我中国数千年来之女子,柔弱不振,庸昧戆愚,何以故?谓无女学故。女学不兴,则女权不振。”[18]对此,竹庄(蒋维乔)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他把中国女子怯弱原因,归结为“女学不兴之害也”,认为“今我国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遑论女权!”[19]他呼吁女子应该奋发其争存之能力,各自努力于学问。这种教育先行的论断,表明学界对于女子教育认识的深化,也得到大家的赞同。然而,当蒋维乔发表《女权说》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时,却引起争议,并导致整个刊物对倡女权态度的转变。
在《女权说》中,蒋维乔开篇即直陈:“今世之慷慨侠烈号称维新之士,孰不张目戟手而言曰:伸张女权也,伸张女权也。吾夙闻其言而韪之。”蒋维乔有此论,是看到妄谈女权存在着很大弊端:奸猾之人会以自由结婚之名诱骗女学生,而少年女子既无知识又无阅历,“安有不受愚者呼?”更何况,还有“本非安分之女子,借游学之名以遂其奸利之私者”。因此,蒋氏无不担忧地指出:“妄谈女权而不先养成女子之学识,之道德,徒以结婚自由之说,便于肆意妄行者灌输之。其流弊之所至,吾甚懼焉。”至于解决的方法,蒋维乔认为还是要通过教育,“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20]。
蒋维乔对妄言女权的批评,其实自立在先前也表示过忧虑,认为婚姻媒妁骤迟,“必举世无复有法律,无复有明教矣”[21]。他的言辞,远不如蒋维乔严厉,所以没有引起争议。而蒋维乔对女权的批评,则遭到柳亚子的激烈反对,并斥之为“比顽固党还可恶”。在《哀女界》中,柳亚子对蒋维乔的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
“吾恶真野蛮,抑吾尤恶伪文明。吾见今日温和派之以狡狯手段侵犯女界者矣,彼之言曰: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呜呼!是何其助桀辅桀之甚,设淫辞而助之攻也!”[22]
柳亚子字亚卢,对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自然十分熟稔。在他看来,人的权利是天生的,“苟非被人剥夺,即终身无一日可离”,以此推论,那么女权的实现就是无条件的。因此柳亚子对中国女子“即学问不足,此岂有不可与男子平等”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会导致“女界其终无自由之一日”的后果。他提出:“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22]
柳亚子与蒋维乔的分歧,并不在于女权或者女学本身。蒋维乔并不反对女权,只是认为“女权萌芽时代,不可不兢兢,恐欲张之,反以摧之也”[20]。在他看来,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谈女权,是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柳亚子对女学也不反对,他真正忧虑的,是蒋维乔对女权流弊的批评,会影响妇女解放的进程。假如数十年后再推行女权,可能“大好江山又不知几易主矣”。所以,他主张女权的实现应该是无条件的,凸显出女权革命的价值所在。
柳亚子和蒋维乔的争论,也引起了丁初我等人的注意。在《女界之怪现象》中,丁初我一反之前对“女子世界”的赞颂,对女界的怪现象进行了批评:“吾恶假守旧,吾尤恶伪文明;吾赞成旧党之頑夫,吾独痛斥新党之蟊贼。”对于那种假借倡导女权,狼狈为奸,互相标榜,互相倾轧者,丁初我深恶痛绝。他不但认为“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容有新文明”,还声称:“今且祝文明、自由之速去吾国,毋再予新党以便利,遗旧党以口实,使数十百年之后,国民结口不敢谈新学,群以吾女子为文明之罪人,亡国之媒介也。”[23]与之相呼应的,是《新罪业》一文。该文列举女权学说传入中国四年来女界所犯新罪业七种,包括:受虚荣、耽逸乐、观望不前、沾染气焰、虚掷、被吸、无成立等。作者表示:“将至苦至辣之言论,忠告吾女青年前,作诸青年永远之纪念。”[24]
丁初我等人对女界怪现象的批评,出发点实际上与蒋维乔一样,都是一种对“女权”的保护,担心被所谓的“伪文明”利用、败坏。他们痛感之前对女权的积极倡导,已经带来很多问题,“假自由平等之名以恣纵,毋宁守其旧道德”[25]。因此,他们对女权的态度,也由先前的积极提倡,转为不断的批评。他们这时候关注的,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为女权的实现提供保障。所以,《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一文,可以看做是《女子世界》诸人对女权的最终态度。作者丹忱直言:“吾不暇哀中国女子之无权,吾先懼中国女子无女权之预备。”在他看来,中国女子不患无权,而是缺少驾驭这种权利的资格,而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通过教育,“是故对无教育之女子而语以女权,是犹对三尺童子而语以自由,对田夫野老而语以民权,其有不紊乱败坏者,鲜矣!”[26]其着眼点,教育自然是当务之急。
《女子世界》围绕女权问题的争论,揭示了“女权”作为一个外来学说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疑惧与困惑。丁初我等人对女权的态度,由倡导转向批评,是出于一种保护的心态。他们所担心的,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会有人挟之以谋其私、行其恶,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这种心态,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态度相似:“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27](P118)因此,他们对女权态度转向批评,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认识的一种深化。在当时女性尚处于依附地位情况下,他们坚持女学先行,以女子教育作为男女平等的保证。这种比较温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日趋激进的情况下,有着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1]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N].时务报(第45册),1897-10-21.
[2]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N].清议报(第38号),1900-2-11.
[3]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N].清议报(第47号),1900-5-11.
[4]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A].马君武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J].女子世界,1904(1).
[7]初我.女子世界颂词[J].女子世界,1904(1).
[8]天醉生.敬告一般女子[J].女子世界,1904(1).
[9]初我.说女魔[J].女子世界,1904(2).
[10]自立.女魂篇[J].女子世界,1904(2).
[11]亚特.论铸造国民母[J].女子世界,1904(7).
[12]莫虎飞.女中华[J].女子世界,1904(5).
[13]刘瑞平.敬告二万万同胞姐妹[J].女子世界,1904(7).
[14]复权歌[J].女子世界,1904(10).
[15]汪毓真.论婚姻自由的关系[J].女子世界,1904(9).
[16]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J].女子世界,1904(4).
[17]女中华歌[J].女子世界,1904(4).
[18]张肩任.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J].女子世界,1904(2).
[19]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J].女子世界,1904(3).
[20]竹庄.女权说[J].女子世界,1904(5).
[21]自立.女魂篇·光复女子之权利[J].女子世界,1904(4).
[22]亚卢.哀女界[J].女子世界,1904(9).
[23]初我.女界之怪现象[J].女子世界,1904(10).
[24]新罪业[J].女子世界,1905(11).
[25]初我.新年之感[J].女子世界,1905(11).
[26]丹忱.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J].女子世界,1905(15).
[27]梁启超.新民说[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