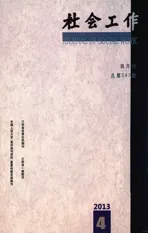城中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启示
2013-04-10文雅
文雅
城中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启示
文雅
过去三十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城中村”。城中村社区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城市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尽管政府管理部门将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作为解决城中村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实践证明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难以应对城中村的诸多特殊情况。如今,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始探索发挥社区自身能力,鼓励社区自我管理和发展来解决城中村的社会问题。从2012年起,上海浦东新区某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的城中村社区,联合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开展了一项城中村综合服务项目,旨在以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改善社区个体及家庭的生活工作状况,增进其信心和自身能力,以自助互助提升社区环境和社会功能。本文以该项目实践和经验为基础,对城中村社会工作的特点和模式进行了针对性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具有借鉴价值的建议。
城中村社会工作介入模式角色定位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城中村(Urban Village)”是指许多外来人员进入城市后自发选择的聚居地域(李培林,2002)。其鲜明特点是以外来暂住人口为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建构方式、以城乡结合部为区位选择的自发性集中居住地。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特定现象,其低廉的生活、居住成本和靠近较多的体力工作场所等特点,使得城中村成为大多数外来人口的居住首选。然而,作为城市发展中自然衍生的异质社区,城中村在居住条件、生活习惯乃至居民素质和周边社区存在较大差异,其空间无序性和人口流动性大、人员构成复杂和生活、卫生水平相对低下等等不利因素,使得社区内部普遍存在着较多社会问题,城中村也被认为是城市中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姚永玲,2008)。
如何解决城中村的社会问题成为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推动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成为政府部门应对的一个主要方向(卓彩琴,2007;李招忠,2004)。在实践中,城市管理者逐步认识到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城中村中的诸多新情况,同时也希望能改变过往政府大包大揽的局面,逐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依托社工机构及专业人员的参与,并通过充分发挥社区自身能力,鼓励社区自我管理和发展,在政府的支持协调下共同解决城中村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上海浦东新区某街道办事处联合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在其辖区内的一个典型城中村社区开展了一项来沪人员综合服务计划,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改善城中村的来沪人员个体及家庭的生活、工作状况,增进其信心和自助互助的能力,缓解社区矛盾,提升社区环境和社会功能。笔者由于博士研究设计的需要,有幸参与了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并从自身的实践和感受出发,对城中村社会工作的特点和方式做了针对性的观察和思考。
二、城中村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社区社会工作一直是社会工作的重点,其与个案、小组并列为社会工作的工作基本方法(周沛,2002)。社区社会工作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确定社区问题与需求;动员社区资源,争取外力协助,有计划、有步奏地解决或预防社会问题,调整或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加强社区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能力,发掘并培养社区领导人才,以提高社区的社会服务水平,促进社区的进步。
社会工作介入是推动城中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方式。社区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传统的社区介入发展模式和以资产为本的发展模式(community-based capacity building)(Kretzmann etc,1993)。传统的社区介入模式以社区需要或社区缺失(needs-based or deficits-based approach)为重点,属于问题或需求导向的服务形式,从社区存在的问题或缺失的方面着手,提出相应的服务策略或方案。而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则以社区资产或社区能力为介入重点,强调所有社区居民、不同持份者(stake-holders)乃至整个社区都拥有各自的特点、潜能及专长,这些可为社区居民自己、别人、家庭甚至整个社区的发展做出贡献。显然,后者是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思路,笔者认为这一基于社区充能视角(empowerment)的社区发展模式对于城中村的社区社会工作很有意义。
从城中村的社会实践发现,居住在城中村里的外来人口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势思维,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比不上本地人,比如个人技能和收入、户籍、语言和人脉等等,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会受到本地人和机构的歧视或欺负。“我们外地人没关系,没背景,走到哪里不受欺负?法院、律师所都是本地人开的,只会偏袒本地人,不会为我们外地人说话的。”“这里住的都是外地人,能好到哪里去?外地人没有什么文化,只能这样子了。我们碰到困难,谁都不会管我们。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孩子能继续在这里读书,以后找份好工作,不要再住在这里,也不要像我们到哪里,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忍。”这些思维在他们日常谈话中经常流露。
以社区缺失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其工作焦点放在社区的缺陷和不足上。从其表象上看,即认为社区是有问题的,需要来自外部的帮助(比如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才能有效地治理。从其结果上看,这样的模式固然能通过外力或者借助外来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解一些社区问题,然而,同时这种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甚至强化了社区居民自身已有的弱势思维或者弱势身份,而且在这种弱势思维定式下,社区居民和社工组织往往容易忽视社区和个人自身的资源、优势和能力,相当于放弃了社区内部的“造血”机制,因此,很难有效保障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以资产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中,社工在社区工作中从“资产”和“能力”的角度去了解社区情况。根据社区资产建设理论(Ferguson,etc.,1998),社区资产可分为四大类:个人资产,包括社区内居民的天赋、知识技能、资源和价值观等等;社区组织资产,包括社区的文化娱乐、社交或公民组织及小组,比如自发成立的社区俱乐部或QQ群等;社区团体及部门资产,包括地区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等。比如社区居委会等;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主要指社区设施,如公园、图书馆及自然环境等必要的物质资源。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作介入聚焦于社区缺陷和不足的思路,以资产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实际上就是在一种“优势视角”下的注重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社区发展模式,强调每一个社区都拥有自己的优势资本,社区资本不仅仅包括有形的、外在的资本,例如社区的自然资源和物资资产、个人的技术和能力,还包括社区团体和组织、居民的关系网络、居民的社区知识和价值观、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在城中村开展的社会工作应采用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社工不仅要看到社区的问题,更要看到社区存在的可供自我发展的资产、优势和能力。
在笔者所参与的城中村项目中,社工结合社区实际,组织和发展志愿者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体现了以能力建设为主的社区社会工作思路。通过在社区宣传自我参与和志愿服务理念,在来沪人员中招募志愿者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卫生、安保、助老等志愿服务活动,城中村的居民们既认识社区存在的问题和现实需要,也认识到自身有权利,同时也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中。这样,来沪人员对本社区有了更多的认同和归属感。因此,城中村的社会工作需立足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以能力建设为抓手,针对社区居民的特点及需要,帮助城中村的居民实现充权,促进社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循环。以这样的社区发展思路,居民能够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发挥自身的力量和优势,整合社区资源,将城中村建设为适合外来人口聚居和个人发展的城市社区。这种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康社区,也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的概念遥相呼应(Hancock,T.etc.1988)。
三、社会工作与政府合作中的角色定位
参与城中村建设、为外来人群提供社会服务,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也为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在城中村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并非一帆风顺,很多工作常常会遭遇瓶颈。首先,当前城中村社会工作是在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架构下开展的,而且社会工作还受到资源和经验不足的困扰,以及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缺乏认知、易受社会负面情绪影响等等。除此之外,在城中村社会工作中,容易被忽视但却对工作成效有深远影响的因素,还有社会工作从业者和合作者之间的正确角色定位,特别是在政府购买的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以及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有一些研究讨论了政府在社会工作中所扮演角色的现状和问题(倪红刚等,2007;陈友华等,2012;李涛,2012)。倪红刚等(2007)分析了政府在社会工作政策立法、投入和宣传等方面的角色缺位,以及在社会工作中的越位和错位,比如福利、救济等服务的包揽以及与社会工作组织的非平等竞争关系等等。陈友华等(2012)提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工作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的NGO属性和其所需资源多来自于政府施予、缺少基本独立性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与社会工作的保持专业独立性之间双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并强调这是社会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李涛(2012)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进程的角色,强调从社会组织的专业功能出发,建立政社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参与过程中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协助政府职能转移。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讨论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及社工的关系及其现状,但没有明确描绘在具体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角色定位,或多或少忽略了社会工作在政府合作项目中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以推进社会服务为主要目标之一。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社会服务也是其主要职责之一。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社会工作离开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是不现实的,而且在实际社会服务项目中,社工组织需要借助政府的资源及其强大的执行力。但是,即便如此,社工在工作过程中仍然需要自己的明确定位,即他们是政府的合作者,而不应该是简单的为执行者(或者存在下属意识)。
然而,在城市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及社会工作现有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政府部门往往与社会工作组织在合作中(特别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中)常处于主导地位,比如在社会服务中指定工作方法、具体流程等等。为了实现社会服务的优先目的,社工很多时候需要协调各种关系、甚至调整具体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正所谓“人在情境中”,社工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去工作。然而,同样为了社会服务的宗旨,社工应认识到自身也是“构成情境”的一部分,社工的工作应该是与大环境相互作用的,而不应是完全受到环境的制约。实际上,社会服务的合作不应只按照政府合作者意志和思路来设计和实施项目,而是应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和需求,来制定可行和有效的项目服务计划和流程,发挥工作能动性将能有效地提高合作项目的社会服务效果。因此,既需要重视合作方(特别是居委等政府基层部门)的意见,也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结合社会工作理念和服务社区对象的实际情况,找到最合理的服务方案和计划,并把它们向合作方解释以期达成认同和共识,这实际也为社会工作大环境的良性变化做出贡献。
以下这一段参与城中村服务的社工和一位居委干部之间进的对话或许能带来某些启示。
社工:“对于活动室的管理,我们建议通过在社区里招募志愿者、由他们来完成。具体的管理办法可以通过开会和居民一起讨论制定。”
居委干部:“活动室的管理主要不就是大门的管理吗?我们指派一个楼组长或社区积极分子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简单的工作搞得如此复杂呢?”
社工:“这是因为社区工作不光是自上而下,也要注重居民的参与,呼应他们的关心和需要,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居民志愿者来管理活动室是促进他们自助、参与社区管理的好机会。由居民来制定职责和开放时间,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
居委干部:“难怪以前居委做了很多为居民们服务的事情,有的效果却不理想,甚至得不到居民的理解。你们社工的建议值得考虑,看来以后开展工作需要注重居民的参与。”
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社工没有直接采纳居委干部的建议,而是通过沟通和协商,把自己的建议分析和解释后,让居委领导接受并改变了对其工作方法的看法。后来实践也证明了这样的工作方法达到了预期效果,富有成效,获得了社区居民的满意评价。
可以看出,在城中村的社会工作中,社工需要正确定位自己的工作,既不盲从、也要重视和政府各层的职能部门人员沟通,包括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如街道组织和居委会。作为政府和社区直接联系的部门,街道和居委的直接影响力不容小视,而且由于长期和社区居民打交道,这些基层组织的干部和办事员大多数能够体恤社区民意,通过沟通和解释,能够提高他们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这对改善工作环境,推动合作,提高工作效果有积极作用。
四、城中村社会工作对社会工作者素质提出的挑战
在城中村的社区工作面临的问题往往多元而且复杂,这给社会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城中村居民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的高度连结性(由于相同的地域、背景、就业等),以及他们之间信息互通的口口相传特性,使得社工的工作和个人表现不仅直接影响着其社区工作的成效和整体社工团队的形象,甚至对基层政府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城中村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处境与所谓“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公共管理理论中(米切尔,赵成根,2004),“街头官僚”是指处于基层的直接和公民打交道的公务员或政府雇员,比如说警察、公共福利机构的人员、街道干部等。这些个人对公共资源有一定的控制权,而且他们的决策能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利益。可以说,“街头官僚”直接关系以至代表政府的形象,其行政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相关政府政策的执行(叶娟丽等,2003;胡远方,2012;尹文嘉,2009)。
在很多国家,社会工作者也被认为是“街头官僚”之列(胡远方,2012;孙吉海等,2006)。但在国内,和“街头官僚”们拥有的自由衡量权(discretion)相比,一线社区社工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十分有限,这种有限和与所期待能力的不对等,给社工在社区开展工作新增了额外的难度。尤其是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由于特定的社区环境和个人经历,居民对社工容易表现出不信任及较强的戒备心理。在社区社会工作的初始阶段,他们倾向于采取被动或抵触防范的方式。社工需要提高自身素养,更多地运用专业的工作方法、付出更多精力与村民们建立关系和互信。
笔者参与城中村项目时曾亲历的事件:为了减轻城中村的来沪家庭负担,社工机构在暑假开办了暑托班服务,旨在通过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的努力,使城中村的外来家庭的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寓学于乐的暑假。但是,暑期班的初期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居民不理解甚至怀疑这样的公益行为,认为暑托班就是为了赚钱,不愿意让孩子参加。然而在一次意外事件后,社工工作遇到了转机。某天,社工在城中村张贴活动宣传海报时,一名身着制服的管理人员非常粗暴地阻止,并要求立即撕下海报,警告这属于非法张贴,要予以罚款。在社工试图解释时,他突然强行将海报撕毁并丢在地上,并声称在村里没有他的同意就不能贴任何东西。围观的村民偷偷地对社工表达了支持,告诉我们这些人很霸道,经常欺压附近的小摊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工坚持和对方解释自己的工作是公益性的,而且宣传活动与当地居委经过了协商并得到了支持。虽然,事件还是以海报被撕下,社工妥协离开而告终,但是这一意外情况使得一些村民改变了对暑托班和社工的态度,有些村民建议到其他地方贴,甚至建议“就贴到店子里面他就管不着了”,而社工也抓住了这个时机与村民建立良性互动,村民也开始慢慢愿意接受社工的公益宣传和活动。
这一事件凸显了城中村居民们对某些粗暴管理方式的不满和对部分政府人员的不信任,也说明坚持社会工作组织和社工的公益性以及采用和正确的工作方法,在城中村的社会工作是能被居民所接受的,同时,它从侧面显示了在城中村开展社会工作的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有利条件。从另一角度看,城中村的社会工作的复杂程度对一线社工来说是不小挑战。尤其是对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社工来说,在城中村的经历和体会容易产生某种挫败感,有些社工甚至发出“为什么在这个社区工作越久,越不喜欢这里”的感叹,这些都需要引起社工机构的重视和关注,如何帮助社工、尤其是年轻社工做好准备进入城中村工作,并使他们在工作中成长,需要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相关社工机构的更多思考。笔者认为一方面社工需要尽量发挥自身的资源和优势,结合外在支持和帮助,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来自行业内部的支持和同步的专业教育和培训以及督导变得异常重要,也是保证能顺利达成工作目标的重要条件。
五、结语
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城中村的社区社会工作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别是政府正在改变对社区工作大包大揽的做法,逐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通过购买服务和与社工机构合作的方式,鼓励社区自治和社区发展,促进城中村和谐社区的建设。
在城中村社会和服务项目以及具体的开展过程中,社工组织选择有针对性的社区介入模式参与城中村的社区建设,从“资产”和“能力”的角度去了解社区情况,能为弱势群体与外来人口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社工组织在工作中积极处理与政府合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正确的角色定位,重视社工在合作项目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能有效保障城中村社会工作和服务的效果。
同时,城中村里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人员构成都给站在社会工作带来的新挑战。从社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和管理的角度,社工们必须通过精心的个人选拔、专业的督导工作和工作培训,掌握合理有效的工作方法;深入了解城中村社区实际情况和社区居民的不同诉求与需要,做出具体可行的行动规划,给不同需求的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从细微之处入手,避免不切实际的指标,社区社工才能开创出令包括城中村居民及社区、政府等各方满意,并能够继续合作和工作的良性发展局面,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社区发展为本”。
致谢:感谢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朱眉华教授和郑俨副总干事对本文写作提供的支持。
[1]陈友华,苗国,彭裕,2012,《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面临的体制性难题》,《思想战线》第3期。
[2]胡远方,2012,《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探析——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第4期。
[3]李培林,2002,《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4]李涛,2012,《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进程中的功能和角色》,《社会与公益》第8期。
[5]李招忠,2004,《政府与“城中村"社区》,《求索》第6期。
[6]米切尔·黑尧、赵成根,2004,《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7]倪红刚,徐燕娜,2007,《政府在社会工作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中国社会导刊》第20期。
[8]孙吉海,国林霞,2006,《浅析街头官僚理论》,《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第7期。
[9]叶娟丽,马骏,2003,《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0]尹文嘉,2009,《从街头官僚到街头领导:一个解释框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11]姚永玲,2008,《城市管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2]卓彩琴,2007,《改制后城中村村民角色冲突与社会工作介入》,《理论学刊》第3期。
[13]周沛,2002,《社区社会工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4]Ferguson,R.F.and Dickens,W.T.(Ed.),1998,Urban problem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5]Hancock,T.and Duhl,L.,July,1997,Promoting Health in the Urban Context.Copenhagen:FADL (WTO),1988.Scott Patrick G,Assessing Determinants of Bureaucratic Discretion:An Experiment in Street-level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6]Kretzmann,J.P.and McKnight,J.,1993,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Chicago,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Center for Urban.
编辑/汪鸿波
C916
A
1672-4828(2013)04-0062-06
10.3969/j.issn.1672-4828.2013.04.008
文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H3A2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