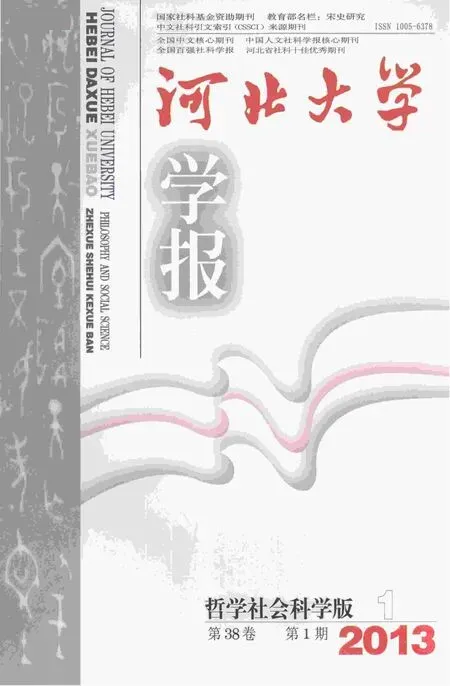龙山文化玉礼器的审美特质
2013-04-08李晶晶
李晶晶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3)
龙山文化玉器距今约4000年左右,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因于1928年4月首次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重大考古遗存而得名。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如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其中以处于山东的龙山文化最为典型。龙山文化玉器不仅是大汶口文化玉器的直接延续,而且在整体风格上还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从出土的玉器来看,龙山文化玉器的种类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礼仪类玉器,有玉琮、玉牙璋、玉钺、玉璇玑以及新石器玉器中首次出现的玉圭等;另一类是各色玉饰品,如玉环、玉笄等。与之前相比,龙山文化时期的治玉工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多以透雕为主,玉器大都琢磨精细,温润光亮,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与审美情趣。本文仅从龙山文化颇具特色的玉礼器如玉圭、玉冠饰、鹰攫人首玉佩等入手,由立体造型、平面纹饰两大方面来分析龙山文化玉礼器中所蕴含的审美意蕴以及审美特质。
一、造型艺术分析
在遥远的史前时期,龙山文化玉器是非常重要的一支玉器文化,它的玉礼器造型丰富而生动,不仅承接了原始玉器的古朴与自然,又在治玉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加强了玉器的装饰与审美意味,彰显出独具一格的时代风貌与艺术特征。
首先,龙山文化玉礼器的造型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龙山文化玉器的器身大都比较轻薄,其造型融合了南北方各自的特点,简洁质朴却又不失精致细腻。以龙山文化首次出现的双面神人兽面纹玉圭为例,其长17.8厘米,上部较窄稍厚,下部较宽稍薄,上宽4.5厘米,厚0.85厘米,下宽4.9厘米,厚0.6厘米,整体呈一扁平状的细长方体,磨制光滑[1]。该玉器制作规整,长身玉立,器身细薄,给人以古朴秀雅之感,实与龙山文化著名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件出土于山东临朐朱封的玉冠饰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特征[2]。它位于墓主人头部的左侧附近,通长23厘米,由首、柄两部分组成。其柄部为青灰色圆锥体,呈与蛋壳高柄杯相似的细长竹节状,在首部则以乳白色玉料镂雕成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其镂孔形状各不相同而又基本左右对称。在出土时周围散落有约980件小绿松石片,可能为镂孔中的细小镶嵌物。仔细分辨后,可以看出在蝶状的平面中琢磨有眼耳口鼻俱全的神人面像,造型奇特而精美,体现出高超的玉器工艺水平与古龙山人独特的审美趣尚。
龙山文化玉礼器的另一造型特征是寓多种元素于一体。在龙山文化玉礼器的器身内包含有不同的组成元素,或为简单几何外形的组合,或是不同意象的叠加,这类玉器常常被赋予宗教礼仪上的功能,呈现出朴素而神秘的审美意味。比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一件玉璇玑,其器身以环形作为主体,状如一块扁平的玉璧,但在其外缘部分却附出三个形状相同、并且具有同一指向的锯齿[3]。看似静止不动,却给人一种流动旋转之感。这类玉器曾被认为是可与玉琮相组合成旋转窥管的天文仪器,用以观察星宿变化。但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玉璇玑应该是一种装饰品,可能还具有宗教礼仪上的意义。正如《尚书·舜典》所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可见,玉璇玑是古时供祭北斗七星的专用礼仪用器。此外,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鹰攫人首玉佩也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宗教礼仪玉器的典型代表。它长9.1厘米,宽5.2厘米,厚2.9厘米,其玉料呈青黄色片状,边缘略薄,两面图案大致相同。玉佩上部镂雕出一只展翅雄猛之鹰,圆目、勾形嘴、头戴长冠、鹰头侧转,在其双爪下各抓攫一个头戴船形帽、披发侧视的人首。这件玉器很可能反映的是古龙山人与图腾祭祀有关的社会宗教习俗。因为山东龙山文化所在的区域正是古少皞氏族部落的领地,《左传》中说道:“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挚”与“鸷”相通[4],可见,少皞部落以凶猛的鹰鸟为图腾,正与该玉佩的造型及文化内涵不谋而合。
总之,龙山文化玉礼器的造型体现出新石器晚期南北玉器的特点,既具有北方玉器的质朴感,又流露出南方玉器的精致之美。它的造型虽以简单的几何形、象生形为主,但是在其制作的过程中,却以古龙山人原始朴素的审美思维,镂雕出具有丰富而神秘的美感的器物,足以让后世之人为之欣赏与惊叹。
二、纹饰艺术分析
从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礼器中可以看出,其器身的纹饰大多比较疏朗简洁,但却强调对造型的呼应与结合,甚至在某些器物的部位以组合的形式进行重点刻划。在这些或繁或简的几何线条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义,正如“纹样的本质,就是在于它的审美意义,亦即装饰意义”[5],因而龙山文化玉器的纹饰得以成为能引发审美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
龙山文化玉器的纹饰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纹饰与器物高度结合为一个整体,线随形转[6]。这一纹饰类型的典型器物当推鹰攫人首玉佩。此玉佩通体透雕而成,在玉器的上部雕刻出神气毕现的鹰鸟纹,并以流畅的几何线条勾勒、镂雕出鹰的勾嘴、圆目、利爪、展翅等栩栩如生的形象。玉佩的下部则是由两个左右对称的侧视人首组成,以微凸的浅浮雕与细致的阴刻线琢磨出人首的冠饰、披发以及面部的轮廓特征,使得玉器的纹饰与造型得到高度地统一。另一件具有此特征的玉器则是玉冠饰。其颀长的柄部饰有间距不一的凹弦纹与竹节纹,在其冠首部的镂雕蝶状平面上,则以细腻轻浅的阴刻线刻划出以凹字形、工字形以及丁字形为主题的纹饰。玉冠饰上的镂孔与刻纹虽形状各异但大致左右对称,有学者认为,这件饰品首部的轮廓看上去近似一个头戴皇冠的神的形象。因为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冠饰的顶部雕琢出呈扇形、正中有缺口、两端略卷翘状的“皇冠”,在皇冠的下端则镂刻出眼耳鼻口俱全的神人兽面纹,其兽面的两侧还以卷曲的线条琢磨出双翼与象征高贵身份的珥饰。以上这两种玉器的纹饰都与器物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器艺合一,线随形转,充分显示出龙山文化玉器精良的镂雕制作工艺与古龙山人对于器物的审美创造力。
另一种龙山文化玉器的纹饰特征是组合纹饰增多,并且在器身的正反两面中以不同形式出现。在龙山文化玉礼器中,大都光素无纹,但在某些区域却雕刻出精细的人神兽面纹与几何纹的组合作为器身的装饰。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龙山文化玉器的正反两面常常刻划出不同的纹饰图样,颇具神秘的意味。比如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文化典型玉器——双面神人兽面纹玉圭就是如此。它的器身长而薄,大部分都光滑无纹饰,仅在靠近玉圭背部一端的正反两面刻有不同的神人兽面纹饰。它们都以一对怪异、重圈的大眼作为抽象面纹的中心纹饰,并且在面纹的头顶正上方,都阴刻出“介”字形的顶冠。所不同的是,一边的“介”形冠顶的正中央向上顶起,而另一边的顶冠则作横向延伸并两端向上卷翘成牛角状。另一件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龙山文化鹰纹圭也再次体现出这一纹饰特征。此圭的纹饰主要集中在器物的中下端,由两部分组成,上节是主体纹饰,下节则是由小型神人兽面纹及卷曲的圆涡纹组成长方形装饰带。所不同的是,玉圭一面的主体纹饰是展翅向上飞翔的鹰鸟纹,其姿态十分奇异,鹰首直冲云天,两翅向外舒展,形同一个“介”字;另一面则刻着抽象的神人兽面纹,华丽繁复的“介”字形顶冠高高耸起,面目狞厉,充满着威严神秘的力量与气势。
总之,龙山文化玉器的纹饰能与器物的造型紧密结合,或是线随形转,与器身有机融为一体,或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作为器身的装饰,在抽象流转的纹饰线条中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征与颇具原始神秘感的形式意味。
三、审美意蕴
龙山文化玉礼器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蕴,通过古朴生动的造型与神秘精美的纹饰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出器物外在的视觉美感与内在的节奏韵律,显示出史前龙山文化玉器别具一格的时代风采与审美特征,并且,龙山文化玉器之中的象生类礼器还寓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反映出原始先民们天人合一的诗性审美思维与古朴而神秘的艺术趣味。
首先,龙山文化玉礼器从整体上看,给人呈现出一种飞动之美。不论是它简约秀雅的造型,还是流动顺畅的纹饰线条,无不体现出器物的灵动生气。比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玉璇玑,它的造型形如一块扁平的玉璧,但在其环形的外缘位置,却附着三个呈同一个方向的锯齿,看上去就像一个呼呼生风的齿轮在不停地流动旋转。有学者认为玉璇玑是古人因宗教礼仪上的需要制造而成的,是当时专门用于供祭“天心”即北极星的礼仪用器[7],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极星总是在微微地旋转着,称“含元出气”,因而以“璇玑”名之[7]。因此,玉璇玑的造型不论是从实用的角度还是从宗教礼仪的需要上看,都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自然而然的流动之感,是实用、审美、宗教礼仪三个方面高度结合的物质再现。从纹饰上看,龙山文化玉器虽然在器物的大部分光素无纹,但是在其主体部分却刻划出流动精细的线条花纹。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数兽面纹与鸟纹。它们多被装饰在玉器的某一个部位,或为中段,或为底端两侧。以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双面神人兽面纹玉圭为例,在其底背部的正反两面均刻划着不同的兽面纹。它主要以两个怪异的大型目纹为中心,以旋转顺畅的曲线围绕着眼部重重展开,给人一种神秘的流动之感。另一件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龙山文化鹰纹圭上,除了刻有与前者相似的神人兽面纹外,在其背面还雕刻着造型奇特的鹰鸟纹。鹰首高昂向天,两翼向外展开,似乎马上就要一飞冲天,其线条流畅、细密,刚劲有力,充分体现出生命的飞动与勃勃生机。
其次,龙山文化玉礼器充分体现出了生命节奏之美。其以透雕为主的造型工艺,以及阴刻线与阳刻浅浮雕相结合的纹饰手法都凸显出虚实相生、阴阳相济的生命律动节奏。例如龙山文化的鹰攫人首玉佩,它主要在一整片玉料上雕琢出雄鹰与人首的轮廓,其因通体透雕而形成的镂孔错落有致而又左右对称,在虚与实的结合中,为单纯的器物注入了生命的灵气。并且,它还在轮廓之上用细密的阴刻线与微凸的浅浮雕勾勒出雄鹰与人首的具体姿态与面目特点,这种凹凸有致的视觉呈现,线与形的高度融合,使造型简单的器物也变得生动而立体,体现出生命内在相反相成的节奏韵律。再比如山东临朐朱封出土的玉冠饰,它的首部主要是以一小片乳白色的玉料镂雕而成,形同一只翩翩展翅的玉蝴蝶。其雕琢手法非常细腻繁复,众多大小不一的镂孔更是构成了一张神秘抽象的神人兽面,充满着原始而独特的审美趣味。其细长的柄部则以凹弦纹与竹节纹作为装饰,跳脱了以往玉器固有的审美体验,整体看来给人一种轻盈与秀美之感。由此可见,龙山文化玉器体现了史前人类对自然万物阴阳相济的最初体悟,在虚实相生、阴阳结合的雕刻手法中,彰显出生命自然的动感韵律。
再次,龙山文化玉礼器还生动显示出神秘之美。在玉礼器中蕴含着先民们原始浓烈的情感体验,体现出飞扬而奇特的创造性想象力。它们超越了器物的实用和装饰功能,显现出丰富神秘的社会和宗教礼仪性的功能与含义。以龙山文化首次出现的典型器物——双面神人兽面纹玉圭为例,它的器身长而薄,琢磨细致而光滑,明显已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玉器,而是带有宗教礼仪上的功能。尤其在它背部一端的两面雕刻着不同的神人兽面纹饰,其怪异的重圈大眼、神秘的“介”字型冠顶、繁复流转的线条纹饰都与后世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十分相似,它所表现的不再是占史前玉器大部分纹样主题的抽象的几何纹,而是一种怪诞的、变形的、超越了现实的神秘形式,它也不再是之前的简单纹样的重复,而是多种纹样组合叠加在器物的平面,线条繁复细密却刚劲有力,正如李泽厚所说的“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8]。在这种怪诞神秘的形象的创构中,寄寓着龙山原始先民们强烈的宗教情感体验,并且这一热烈的原始情感激发出了他们飞扬不羁的想象力,使他们沉浸在与艺术相似的创作的非理性“迷狂”之中。因而在他们手下诞生的神秘兽面纹,具有了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意义与艺术魅力。
此外,龙山文化玉器中的象生造型玉礼器以及纹饰中的象生纹样充分体现出蕴含于器物之中的生命意识。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由于对自然万物认知有限,原始人“相信万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绪与人类一般”[9]。并且,原始人认为“美术像都与被造型的个体一样是实在的……图像与被画的、和它相像的、被它代理了的存在物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能赐福或降祸”[10]。因而在龙山文化中出现了不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生形玉器。例如出土于陕西省神木县石峁的一件玉人头饰,它在一块近似圆形的扁平状乳白色玉料上细致琢磨出一个人的侧面轮廓。其头顶部饰有一个略高的圆形发髻,并在面部阴刻出一个橄榄形大眼,鼻子则呈鹰勾形,嘴唇微张,脑后有外凸的耳形脊。头下有颈,嘴角处还有一个圆形穿孔,可供人配系[11]。这件玉首饰虽然造型拙朴,纹饰简单,但却十分形象地勾勒出几千年前原始龙山人类的样貌与形态,栩栩如生而又生气灌注,被认为是古龙山人所崇拜的祖先神形象,拥有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还有龙山文化中的首次出现的典型器物——玉圭上面所刻划的主体纹饰如神人兽面纹、鹰鸟纹等,都是龙山人在日常生活与大千世界中观物取象的结果,鲜明生动地描摹出了原始先民心中对于自然万物及自身的独特体悟与非凡的想象,在天人合一的原始诗性的思维中,取法于天地众生,充分体现出龙山文化玉器之中原始古朴的审美思维与艺术境界。
总之,龙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不仅是大汶口文化玉器的直接延续,其玉礼器在整体风格上更是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彰显出别具一格的时代审美特征。它的玉器造型虽然是简单的几何形、象生形,却既体现出北方玉器的原始质朴之美,又具有南方玉器的精美细致之感,充分体现出龙山先民们原初的审美意识与匠心独运;它的玉器纹饰与器物的造型能有机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线随形转,纹型合一。尤其是在龙山文化同一玉器的正反两面常常刻划出不一样的纹饰图案,充满着神秘的意味。其在纹饰主题中大量出现的神人兽面纹线条流动顺畅、刚劲有力,与后世的饕餮纹十分相似,颇具威严与狞厉之美。并且,龙山文化玉礼器在阴刻线与阳刻浅浮雕的结合中以象征的笔法雕刻出阴阳相济、虚实相生的生命节奏,彰显出器物之中丰富的审美意蕴。而一批象生类礼仪性玉器的出土,更是生动形象地呈现出古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和礼仪文化内涵,体现出蕴含于玉器之中的深厚蓬勃的生命意识与原始先民们炽热的宗教、艺术情感以及非凡不羁的想象力,从而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文明迈向了更为成熟繁荣的发展阶段,并日渐成为对后代玉器影响深远的史前玉器板块之一。
[1]牟永抗,云希正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卷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2:230.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J].考古,1990(7):587-594.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邓淑苹.晋、陕出土东夷系玉器的启示[J].考古与文物,1999(5):18.
[5]田自秉.中国纹样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
[6]潘守永,雷虹霁.鹰攫人首玉佩与中国早期神像模式问题[J].民族艺术,2001(1):128-130.
[7]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94-95.
[8]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9.
[9]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
[10]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73.
[11]周南泉,张广文.玉器品鉴与收藏[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