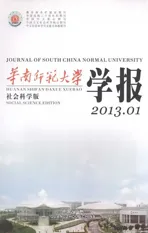刑罚的有限性、非连续性与量刑均衡
2013-04-08王联合
王联合
(广东商学院 法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量刑均衡是刑罚裁量的一般原则和基本要求,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中的体现,是指审判机关对犯罪分子判处的刑罚,要与他所应担负的刑事责任相均衡,责任重则刑罚重,责任轻则刑罚轻。①参见马克昌:《刑罚通论》,第26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可见,量刑均衡在本质上是“刑责均衡”,即“同责同罚”、“异责异罚”。在司法实践中,有些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不同,却只能判处相同的刑罚。这种“异责同罚”从表面上看与量刑均衡相矛盾,其实不然,从某种程度来讲是量刑均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本文通过对刑罚的有限性、非连续性和刑事责任的无限性、连续性的分析,来论证一定条件下的“异责同罚”是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从而为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量刑均衡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刑罚的有限性与刑事责任的无限性
刑罚作为对犯罪分子适用的惩罚措施,相比其他制裁措施虽然是最严厉的,但就惩罚程度而言,刑罚仍然是有限的,死刑即是刑罚体系的上限,而通过刑罚来实现的刑事责任却是无限的。
(一)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决定了刑罚的有限性
在整个刑罚体系中,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无疑是惩罚程度最高的刑罚,可以说死刑是刑罚的上限,由此决定了刑罚在惩罚程度上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对于有些犯罪分子,如果所犯罪行极其严重,例如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杀害了多名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即使判处死刑仍嫌轻,也只能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没有惩罚程度更高的刑罚可供适用。在古代,往往通过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来增加死刑的惩罚程度,以便让犯罪分子遭受更大程度的痛苦,从而达到刑责相适应,以满足民众的报应诉求。在我国古代,死刑手段残酷,花样繁多,计有斩、绞、车裂、枭首、磔、凌迟、腰斩、烹、醢、凿颠、抽肋、汙潴、囊扑、定杀、投崖、炮掷等近二十种,凡一切能致人于死的方法,莫不收括殆尽。而且死刑不只以消灭肉体为满足,更挖空心思,对临刑的犯人折磨、凌辱,使其于生命结束前备尝各种痛苦。尤其是“具五刑”,先刺面以辱之,次斩趾以废之,再杖击以毙之,复枭首以示众,更醢其骨肉,残酷如此。②参见高绍先:《中国刑法史精要》,第399-400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在汉朝与魏晋时期,死刑分为普通死刑和特殊死刑,普通死刑有三种:枭首、斩、弃市。“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①张裴:《注律表》。特别残酷的死刑如磔、汙潴、烹等专门施于特殊罪犯。“至于谋反大逆,临时辅之,或汙潴或枭菹、夷三族。”②《晋书·刑法志》。可见,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代表了不同的惩罚程度,适用于不同的犯罪分子,反映了罪的不同和刑事责任的差别。而通过各种肉刑和死刑的合并执行,同样是为了增加刑罚的惩罚程度,以弥补刑罚的有限性带来的惩罚的不足。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当今社会不仅废除了肉刑,而且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更加人道,不可能再通过刑罚的并罚以及不同的执行方式来提高刑罚的惩罚性,刑罚的有限性表现得更加突出。
(二)犯罪的无限性决定了刑事责任的无限性
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的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的轻重是由该罪主客观方面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的大小来决定。从客观方面来看,危害行为及其产生的危害结果直接决定了罪的轻重,从主观方面来看,罪过的主观恶性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罪责的轻重。而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主观恶性等都是没有上限的,今天看来是最严重的犯罪,明天可能发生更严重的犯罪取而代之,我们永远不知道将来还有什么更加严重的犯罪会发生。刑事责任作为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其轻重是由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共同决定。犯罪行为在危害程度上并没有上限,决定了刑事责任在大小方面也没有上限,可以说只有更严重的刑事责任,而没有最严重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具有无限性。在贝卡里亚看来,“既然存在着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既然存在着作为私人利益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的契约,人们就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分割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③[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80页,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事实上,就犯罪种类来看,也许存在贝卡里亚所说的最高一级的犯罪类型,但是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来看,是不存在最高危害程度的犯罪行为的。可见,由各种危害程度的犯罪行为所排列构成的这一无形的犯罪阶梯是没有最高一级的,是可以无限地往上增加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刑事责任阶梯也必然是没有上限的,可以说只有更严重的刑事责任,而没有最严重的刑事责任。
二、刑罚的非连续性与刑事责任的连续性
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主刑共包括五种刑罚,从重到轻依次是死刑、无期徒刑、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拘役、管制。当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较小时,可以判处较轻的刑罚如管制、拘役或者期限较短的有期徒刑等;反之则要判处期限较长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从十五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之间,从无期徒刑到死刑之间事实上是不连续的,中间存在着刑罚的断层。因此有必要对刑罚的非连续性进行分析,以便公正地适用刑罚,正确地理解量刑均衡。
(一)十五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存在刑罚的断层
不难发现,无期徒刑与十五年有期徒刑虽然是相邻的刑罚,但并不是连续的刑罚,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量的差别和质的不同。事实上,无期徒刑并非无期,如果人的平均寿命是75周岁,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量刑时的平均年龄是30周岁,无期徒刑就相当于四十五年左右的剥夺自由刑。当然,准确的数值需要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才能得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通过减刑或假释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而根据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通过减刑或假释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一半的规定,无期徒刑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至少相当于二十六年有期徒刑。总之,由于十五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的非连续性,二者之间存在刑罚的断层,从刑罚阶梯通过刑事责任阶梯与犯罪阶梯的对应关系来看,与这一刑罚断层相对应的犯罪是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刑罚的,其结果必然是或者轻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重判为无期徒刑。如果把超过十五年有期徒刑量刑标准的犯罪都判处无期徒刑,即意味着对处于刑罚断层的犯罪都重判为无期徒刑,显然对这些犯罪分子是不公平的;反之都轻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话,对于其他犯罪分子也是不公平的。相对公平的做法应当是对处于刑罚断层的各犯罪行为平分为二,把靠近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这部分犯罪轻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把靠近无期徒刑的这部分犯罪重判为无期徒刑。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把无期徒刑虚拟为四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话,十五年到四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中间值是三十年有期徒刑,因此可以把三十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作为适用无期徒刑的标准,即超过十五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一倍以上的犯罪可判处无期徒刑。对于虽然超过了十五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但尚未超过一倍的犯罪,只能轻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总之,通过统计学方法对无期徒刑虚拟为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后,不仅将十五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罚断层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无期徒刑的量刑标准提供了可能。
(二)死刑与无期徒刑的非连续性
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刑罚是最严厉的,与作为终身剥夺自由的无期徒刑这一生刑相比,具有生和死的本质差别,因此其非连续性是必然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无期徒刑并非无期,考虑到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都可以通过减刑、假释等行刑制度缩短实际执行的刑期,无期徒刑在惩罚的程度上甚至不如刑期较长的有期徒刑,在没有上限限制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古代,仅仅剥夺自由是不具有惩罚性的或者惩罚性较小,因此在奴隶制的五刑墨、劓、剕、宫、辟中并没有自由刑,在封建制的五刑笞、杖、徒、流、死中徒刑和流刑虽然可归入自由刑,但其惩罚性比现在的自由刑要大得多。事实上,流刑是对死刑的一种从宽处罚:“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清律于流刑亦称:“不忍刑杀,流之远方。”①参见高绍先:《中国刑法史精要》,第412页。由于罪犯所流之地多为“远恶之地”,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因此流刑的惩罚性是很强的,仅次于死刑。古代的徒刑虽然期限不长,但在徒刑之外往往又加杖、笞或刺面等肉刑,结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和人的寿命短等因素,从事劳役的徒刑的惩罚性也是很强的。如果说在古代的自由刑和死刑之间由于肉刑的存在使得整个刑罚体系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那么在废除了肉刑的现代文明社会,死刑与无期徒刑的非连续性不仅是客观存在和必然的,而且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
刑罚的非连续性是就整个刑罚体系而言的,是指从轻到重的不同刑种之间,就惩罚的程度或性质而言存在着刑罚的断层或者质的飞跃,至于每种刑罚内部甚至某两种刑罚之间可能是连续的。我国的主刑中管制与拘役之间是不连续的,拘役到有期徒刑是连续的,十五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之间都是不连续的。刑罚体系的这种局部的连续性与整体的非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直接影响到刑罚的裁量和对量刑均衡原则的理解。
(三)犯罪轻重程度上的连续性决定了刑事责任的连续性
一个罪的轻重是由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而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是连续性的线性概念,各种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各种轻重程度的犯罪都是存在的,由所有轻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组成的犯罪阶梯自然是连续的。由于犯罪的轻重决定刑事责任的大小,犯罪的连续性也就决定了刑事责任的连续性。犯罪阶梯并不是不同罪名的犯罪由轻罪到重罪的排列,而是同种罪或不同种罪轻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的排列,在犯罪阶梯的某个位置,可以包含轻重程度相同的数个不同种犯罪行为。事实上,每一种犯罪都可以包含无数个轻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每一种犯罪都有各自的犯罪阶梯或者都对应着整个犯罪阶梯的一部分。总之,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其轻重程度可能是相同的,刑事责任也可能是一样的,性质相同的不同犯罪行为其轻重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刑事责任也可能是不同的,由各种类型的轻重程度相同或不同的犯罪行为便组成了一个连续的犯罪阶梯,与其相对应的各种大小不等的刑事责任便组成了一个连续的刑事责任阶梯。
三、量刑均衡是刑责均衡
(一)量刑均衡不是罪责均衡
对于量刑均衡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其含义大同小异。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量刑均衡,就是指同罪同案同判,异罪异案异判,司法裁判在时空上保持高度的一贯性和一致性”②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第370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具体来讲,量刑均衡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案件自身情节与所判刑罚均衡,即罪责刑相适应;(2)同罪不同案件之间的均衡,即对于犯罪性质相同、情节相同或相似的犯罪案件应当给予相同的处罚,不能同罪异罚;(3)不同罪不同案件之间的均衡,即对于犯罪性质不同的案件,根据其刑事责任的大小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至于量刑均衡所要求的时间上的均衡及不同法院之间的均衡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因此没必要作为量刑均衡的一种类型。量刑均衡既然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中的体现,刑罚的轻重不是直接与犯罪相适应的,而是与犯罪行为及行为人所决定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的,因此准确的表述不应是“同罪同罚”、“异罪异罚”,而应是“同责同罚”、“异责异罚”。有学者认为,量刑均衡必然要排斥刑罚个别化,有碍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①参见曹利民、郑馨智:《对量刑均衡的一些思考》,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1期。如果把量刑均衡理解为罪刑均衡,而罪指的是犯罪行为而非行为人,确实有排斥刑罚个别化之嫌。但事实上量刑均衡是指刑责均衡,而责任的大小不仅与犯罪行为有关,而且与行为人的个人情况有关,量刑均衡不仅不排斥刑罚个别化,而且量刑时必须考虑刑罚个别化。
(二)量刑均衡是同种罪的不同犯罪行为之间的刑责均衡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犯罪论是静止的、固定的,而刑罚论却是运动的、发展的。②参见[日]团藤重光:《死刑废止论》,第156页,(东京)有斐阁1991年版。不论是立法上对犯罪配置法定刑,还是司法中对一个具体犯罪裁量刑罚,都是在不变的犯罪构成的阶梯与可变的刑罚构成的阶梯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对于明知的立法者,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使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③[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81页。这里的犯罪阶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进而对应一个由犯罪行为和行为人所共同决定的刑事责任阶梯,量刑即是根据案件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确定其刑事责任所处的阶梯位置,从而决定应判处的刑罚。虽然刑事责任阶梯是客观存在的,但就目前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是无法单独确定一个案件所处的刑事责任阶梯位置的,因此就一个案件的主客观事实情况所决定的刑事责任大小与其所判处的刑罚轻重是否均衡也是无法判断的。事实上,对一个案件的量刑是否均衡只能通过与同性质的其他相似案件的量刑相比较才能得知。如果对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两案件裁量的刑罚相同,即同责同刑,可以说是量刑均衡,反之则是量刑失衡。至于不同罪之间,根据其刑事责任的大小通过立法已经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只要同种罪之间做到了量刑均衡,不同种罪之间的量刑均衡自然能够实现。当然,如果立法本身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司法的量刑均衡只能是同种罪之间的量刑均衡,不同种罪之间的量刑均衡只能通过法定刑的修改来实现。总之,量刑均衡虽然存在于任何两个罪的刑罚裁量中,但从认识判断及刑罚裁量的角度来看,量刑均衡主要是指同一性质的不同犯罪行为之间的量刑均衡,据此可以对量刑均衡作如下界定:量刑均衡是指同种罪的不同案件之间,刑事责任相同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相同,刑事责任重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重,刑事责任轻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轻,刑事责任的大小与刑罚的轻重成相同比例。其中“均”是指根据刑事责任的大小均匀地分配刑罚,反映的是刑事责任不同的案件之间纵向的轻重不同但成相同比例的刑责关系;“衡”是指对于刑事责任相同的案件裁量相同的刑罚,反映的是刑事责任相同的不同案件之间横向的刑责关系。
四、异责同罚未必是量刑失衡
(一)量刑失衡是刑责失衡
“所谓的量刑不均衡现象,即对同一案件或相似的案件,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或者同一审判组织内部的不同法官之间对被告人判处的具体刑罚及其执行方式都不尽相同。”④曹利民、郑馨智:《对量刑均衡的一些思考》。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而一个案件也只能由某一个审判组织来裁量刑罚,根本不存在两个不同的判决。虽然可以通过测试的方式让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法院的不同法官对同一个案件进行模拟量刑,但也只是测试意义上的不同量刑结果,并不存在司法意义上的不同判决。而相似案件既可能是指刑事责任相同,也可能是指刑事责任不同,如果刑事责任不同,裁量的刑罚自然不同,此时并非量刑失衡,因此应当通过不同案件的刑事责任是否相同来判断量刑是否均衡,用相同案件或相似案件来表述量刑失衡是不准确的,即量刑失衡是指刑责失衡而非罪刑失衡。量刑失衡与量刑均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据上述关于量刑均衡的论述,对量刑失衡可表述为:所谓量刑失衡是指对性质相同的不同案件裁量的刑罚与其刑事责任的大小不相一致。具体包括:(1)刑事责任相同所判刑罚不同;(2)刑事责任不同所判刑罚相同;(3)刑事责任重的刑罚反而轻、刑事责任轻的刑罚反而重;(4)刑事责任的大小与刑罚的轻重虽然一致,但刑罚轻重之比与刑事责任大小之比明显不相等。前三种量刑失衡容易为人所认识和肯定,第四种量刑失衡可能被忽视,但在法定量刑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却是一种常见的量刑失衡现象。例如,在一个三年到十年的法定量刑幅度内,两个性质相同的案件假如刑事责任之比是1∶1.5,如果较轻的罪所判刑罚是四年有期徒刑,较重的罪所判的理想刑罚应当是六年有期徒刑,实际裁量的刑罚在六年上下浮动半年被认为是均衡的话,裁量五年或者八年有期徒刑可认为是量刑失衡,此时较轻刑罚与较重刑罚之比是1∶1.25或者1∶2,与刑事责任之比1∶1.5明显不相等。量刑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量刑失衡在本质上是法官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的不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越大,不正确行使导致的量刑失衡就可能越严重。为此,通过制定相应的量刑细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因不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导致的量刑失衡。
(二)刑罚的有限性与非连续性决定了异责同罚的必然性
对于前述量刑失衡的第二种情形即“异责同罚”,不能一概认为是量刑失衡。根据刑罚的有限性和刑事责任的无限性可知,当刑事责任达到某种严重程度而判处最高刑时,由于没有更重的刑罚可供选择,对超过这一严重程度的更重的刑事责任也只能判处相同的最高刑,这样对超过某种严重程度的刑事责任的不同犯罪裁量的刑罚都是相同的。例如,同样是故意杀人罪,刑事责任的大小往往和被害人的人数成正比,被害人越多,刑事责任就越大,但最终可能都判处被告人死刑,即“异责同罚”。根据刑罚的非连续性与刑事责任的连续性可知,对处于刑罚断层的不同刑事责任的犯罪,由于没有与这些刑事责任相对应的刑罚,只能从轻或从重判处断层两侧相应的刑罚,从而使得这些犯罪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同,但所裁量的刑罚相同,即“异责同罚”。例如,对于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犯罪,其法定刑是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当达到某一数额时如果需要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达到另一更高的数额时需要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对介于两个数额之间的盗窃犯罪,如果其他主客观事实情况大体相当,这些数额不同的盗窃犯罪虽然刑事责任不同,但也只能判处相同的刑罚,或者轻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重判为无期徒刑,或者相对较轻的部分轻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较重的部分重判为无期徒刑。如此以来,不管怎样处理都会出现处于十五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罚断层的犯罪行为,尽管其刑事责任不同,但可能判处相同的刑罚。总之,正是由于刑罚的有限性及非连续性,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无限性及连续性,使得对不同刑事责任的犯罪可能判处相同的刑罚。可见,量刑均衡虽然排斥“同责异罚”,但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异责同罚”,也即一定条件下的“异责同罚”的存在是必然的,非但不意味着量刑失衡,反而是量刑均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刑罚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是观念的产物,且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渐趋轻缓。刑罚的轻缓化判定了刑罚有限性的不断变化,即刑罚体系上限的逐渐降低,因此在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无期徒刑即是刑罚体系的上限。也许有一天,当人们的报应观念进一步发生改变时,无期徒刑也会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最严厉的刑罚只是某一期限的有期徒刑。在废除死刑甚至无期徒刑的情况下,无期徒刑与死刑之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罚断层便不复存在。可见,刑罚的轻缓化在强化刑罚的有限性的同时,刑罚的非连续性却在逐渐减弱甚至完全消失。总之,抽象地谈论刑罚有限性及非连续性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具体分析一国刑法所规定的刑罚体系,才能对刑罚的有限性及非连续性做出准确判断,才能科学地解决司法中的量刑均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