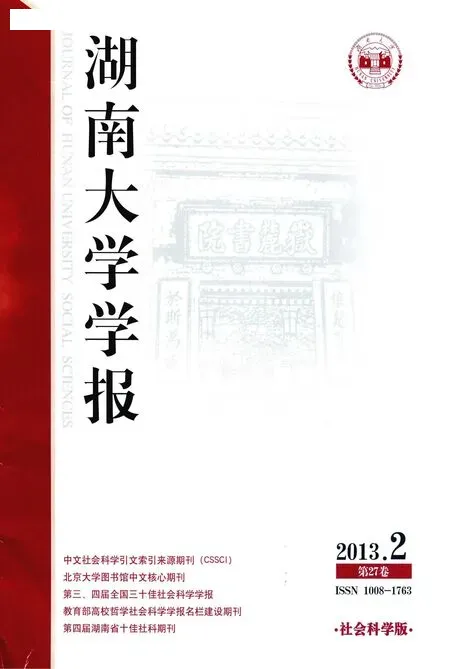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的政治思想解析*
2013-04-07王彦迪
王 成,王彦迪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宁海一个官宦家庭,其父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做官“以德化为本”著称,百姓赞之为“我民父母”[1](《方克勤传》)。方孝孺师从有“开国文臣之首”[1](《宋濂传》)美誉的宋濂,是宋濂最为得意的 门生。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方孝孺应建文帝之请,出任翰林侍讲学士,后值文渊阁,深得朱允炆赏识。曾主持修撰《太祖实录》、《类要》等。朱棣篡位后,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以彰正统,遭拒。朱棣怒而诛其十族,诛连受害者达数百人之多,制造了王权专制社会中最大的冤案。方孝孺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使他入仕之后,决心忠心辅君,纠正洪武时期烈猛治国、重典驭臣的弊政,与建文帝一起厉行善政,治国以仁,爱民如伤。事实证明,由方孝孺辅佐建文改制而成的“建文新政”效果明显,深得民心,“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建文失国后,“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2](《庚巳编客座赘语》)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其政治主张主要见于《逊志斋集》、《方正学先生集》以及《明史》相关纪传中。
一 民本思想指导下的君职说
方孝孺之师宋濂曾经提出“君权民授”说,认为:“有民斯有国,有国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则君,舍之则独夫耳,可不畏哉!”[3](《燕书》)在宋濂的政治逻辑中,先有黎民百姓才有国家,先有国家才有人君。人君之权来自黎民百姓的授权,并非上天赐予。如果说有人间主宰身份的“天”,那么,百姓就是人君的“天”。何人可出任人君完全由百姓决定。百姓立之就是人君,弃之就是“独夫”。人君要保其君位,就要以仁义治国,以仁义待民。方孝孺深受宋濂“君权民授”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君职”学说,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为此,他提出如下主张:
第一,君职起源于“养民”的政治需求。方孝孺认为,政治生活中的独尊君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先民面临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生存颇为困难。落后的物质资料生产状态下不可能存在剩余财富,也就不可能出现等级差别和君主这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职业分工,“生民之初,固未尝有君也”[4](《君职》)。后来,先民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中渐渐走出了屈从被动的境地,生产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导致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剩余产品出现了。这种剩余社会财富的存在激起了人们据为己有的强烈欲望和冲动。迅速膨胀起来的私欲伴随财富的剧增而越来越难以遏制,于是出现了各种纷争并直接造成财富的无谓损耗和大量生灵的罹难。可悲的是,仅仅依靠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初民”根本不具备智慧与能力,以解决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纷争。“众聚而欲滋,情炽而争起,不能自决”。在人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情况下,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人君出现了,“于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长之”[4](《君职》)。通过方孝孺的分析不难看出,君主固然绝非从来就有,但是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要生存下去,决然离不开君主。“天之生人,岂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势有所不能,故托诸人以任之,俾有余补不足。智愚之相悬,贫富之相殊,此出于气运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齐也,而卒不能免焉”[4](《体仁》),“智或可以综核海内,而愚者无以谋其躬;财或可以及百世,而馁者无以啜之菽。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势不可也。势之所在,天不能为,而人可以为之。故立君师以治,使得于天厚者,不自专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后天地之意,得圣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说起。”[4](《体仁》)君主是“有才智者”,能够领会上天的意志安排,可以针对人类社会各类不同的纷争,制定相应的稳定措施,从而消弭动乱,还天下以太平,为人类的进步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所以,人君有资格代表“天”成为人世间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和是非善恶的裁判者。君职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急切需求,这是“天意”。
第二,君职的核心是“养民”。方孝孺认为,君职的核心是代天养民。“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4](《甄琛》)。在 方 孝孺看来,上天无论对人、对事都是公正无私的,在君主职位设立及其职责界定问题上同样如此。上天设立君主这一职位,绝对不是因为对君主有所私、有所偏、有所爱,希望君主在世间无条件地独享大富大贵。“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而是赋予君主“养民”的重要职责,即“涵育”人民,“将使其涵育斯民”,使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僚臣胥吏能够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俾各得其所也”[4](《深虑论》)。就是说,上天做君主这样一种职位设计,职能规则内在地要求君主教育广大臣民,在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上天为自己安排的席位上各尽其责。君主虽然是上天选拔出来的“有才智者”,但是,君主面对的是“世变愈下,而事愈繁”的局面,不断变换的世事,江河日下的世风,不断增加的政治、社会事务,林林总总,如果仅依靠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完全治理过来。“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也”[4](《君职》)。所以,君主要完成上天赋予的君职使命,必须选拔一批可以使用的人才任以为官,“于是置爵秩”[4](《君职》)。换言之,君主所以要任用大批官吏并给予爵位俸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上天赋予的职责。于是,司法、行政、社会事业纷纷兴起。各种政治、社会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赋税的支撑。君主教化百姓支出的各类物质耗费属于公共开支,自然要通过百姓交粮纳税的途径筹集。
君主一方面教化百姓,使他们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明白是非曲直,在善恶面前能够做出正确抉择,“主政教,作礼乐,使善恶各得其所”[4](《君职》),另一方面还要养民。
社会的政治现实却是,君主只有一人,天下百姓千千万万,“一人至寡也,天下至众也,人君何以养之哉?”[4](《甄琛》)方孝孺开出的药方是:以天下物养天下民。“惟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而已。”天下万事万物是无知无识的,“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哪些可用于养民,哪些不可用,君主应善于辨察,取之有方,“其可用而用之”,不可随心所欲,用之无度。“故人君者,导之以取之之方,资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间者,不至于无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于无节,此君人者之职也。”[4](《甄琛》)以此为基础,方孝孺提出“宁余于民,无藏府库”[4](《隋文帝》)的养民、富民思想。
其一,私己厚敛,亡国之选。方孝孺以秦、隋二世而亡为例指出,秦与隋的第二任君主都是私己之徒,“昏惑之主,欲富国者,必厚敛民以适其欲”[4](《隋文帝》)。秦二世与隋炀帝均属“昏惑之主”,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毫无节制地盘剥百姓,致使人民不堪重负而造反,“侈纵以致败亡”[4](《隋文帝》)。历史的教训表明,君主应当藏富于民,让百姓富裕起来。在天下财富有限的情况下,一旦富国与富民出现矛盾,方孝孺主张富民为先,富国在后,宁愿让财富藏之于百姓之手,也不要收之于官家的府库之中。百姓富足,可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进而促进国富目标的实现。
其二,取消盐铁茶专卖,让利于民。方孝孺认为,“茶盐之类皆属于官”[4](《甄琛》),这种官府专卖的制度设计明显是借助权力垄断与民争利,是君主未尽其职的表现:“人主不知其职在乎养民,而剥民以自养,凡物之适于用者,尽笼而取之,而与民为市”[4](《甄琛》)。这种不恤民情的做法,不仅导致君民对立,而且将大量本属于民的财富聚集于君主手中,容易导致君主奢侈纵欲。如此不合理的体制笼罩之下,百姓不仅不能获得本来属于自己的利益,君主还可能变本加厉侵夺百姓利益,损民自肥,“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横被其害”[4](《甄琛》),“此岂天地生物之意?”[4](《甄琛》)所以,方孝孺呼吁政府放开盐铁茶叶的垄断经营,还利于民。这样“恩加黎庶”,不仅百姓可以深切地感受“天子至仁”,而且“四夷咸宾”[4](《郊祀颂》)。通过让利于民而“养民”,是“国以仁兴”[4](《郊祀颂》)的具体表现。如此,江山社稷“百世之保,流以源长”[4](《郊祀颂》),朱明天下就可万古长青。
其三,轻徭薄赋,俭以爱民。洪武时期,江南地区实行重赋政策。为完成朝廷赋税安排,“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为此“而流离失所者多矣”,“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5](《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方孝孺建议建文帝“必视前政之得失而损益之”[4](《深虑论》)。不能只是看到前朝取得的政治成就,对存在的过失视而不见。如果仅“知其德”而“不知其失”,并采取措施“革其由”,必将导致国家昏乱。他建议对洪武朝的税赋政策进行调整,“去其不善而复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变更其所难,循求其宜于民情”[4](《深虑论》)。建文帝接受了方孝孺的建议,调减了江南税赋。方孝孺赞颂建文帝践行了“武王周公之法”[4](《深虑论》),“宁缺储积,而不忍以敛妨农”[4](《郊祀颂》)。为解决调减税赋带来的政府收入下降问题,方孝孺提出厉行节俭财用的主张。“为天下者,曷尝患乎无财也哉。天下未尝无财也,苟用之以节,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4](《读汉盐铁论》)方孝孺认为,君主是否节财俭用对于社会尚俭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君民与官民关系健康与否,所以君主应该成为节财的表率,“人君节己厚人,不专其利,崇俭黜欲”,这样就可以实现“邦国乃裕”[4](《读汉盐铁论》)的发展目标。
方孝孺认为,教民与养民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在这个问题上,君臣应该厘清各自的职责,“天之意以为位乎民上者,当养斯民;德高众人者,当辅众人之不至,固其职宜然耳”[4](《君职》)。所以,作为君、臣这两种政治活动中的主要角色,一定要对自己的职责有准确定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否则“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赋税之不时,力役之不共,则诛责必加焉;政教之不举,礼乐之不修,弱强贫富之不得其所,则若罔闻之”[4](《君职》),教民与养民又怎能得到落实呢?所以,方孝孺主张,君臣百官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教民、养民的职责,既要教育民众在政治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尽到自己为民的义务,又要通过政权通道,为社会供给政策法令以养民。尤其应该坚决避免“劳天下之民以自奉”[4](《民政》)。
第三,“诚以格君”是君职落实的主要途径。《尚书》有言曰:“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缪,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6](《囧命》)方孝孺继承这一思想,提出落实“君职”的主张——“诚以格君”。就是说,作为人臣都有责任全心全意地帮助君主改正错误,使君主借助外力“格其非心”,完成养民使命。
方孝孺认为,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一人而加乎万姓之上”[4](《重爵禄》),其一言一行是朝廷百官、普通百姓效法的榜样。君主不正无以正人,君主这种政治角色天然地要求“正以持身,仁以恤民”[4](《杂诫》),对此,君主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君臣同心以“格君”是帮助君主实现身正、政通、人和的必要条件。具体说,“格君”有两条路径:
其一,臣民的规谏、匡正,是为外力。帮助人君纠正错误,“去人君之非”,使其达成完美人格,是臣子应尽的职责。甚至“众庶”也有向人君进谏的责任。
其二,“人君之学”,即人君通过学习实现内圣品格。其核心是“治心”、“立政”。方孝孺认为,人君“治心”应注意由五方面入手,从而实现“正心”:“持敬以弥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纵之渐,养慈爱之端以充其仁,伐骄泰之气以固其守,择贤士自辅以闲其邪。”[4](《君学》)“治心”的工具性手段是礼乐仁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也。”[4](《杂诫》)通过“扶天理”“诛人伪”[4](《后正统论》),帮助人君以仁义礼乐治国理政,“明而不至于苛,宽而不流于纵,严而不迫于刻,仁而不溺于无断,智而不入于诈妄,纳谏而能委任,无逸而能不变,此为政之本也”[4](《君学》)。这样,“政教行乎天下”[4](《深虑论》),加上国家充足的储备,就可以实现大治。
方孝孺提出君职说,应该说抓住了君主集权时代政治体制运行的根本,即君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王权专制时代,这需要智慧与勇气,也与方孝孺遇上建文帝密切相关。方孝孺倡导“格君”,对遏制人君欲望膨胀,限制君权肆意蔓延,确定君主的政治责任,调节君臣、君民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阶级整体与长远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更为可贵的是,方孝孺将人君放在社会管理者的地位进行考量,认为人君如果不能尽其职,百姓可以将其废黜,“君之职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远矣。怠而不自修,又从侵乱之,虽诛削之典莫之加”[4](《君职》)。方 孝孺 的 这 一 思 想 显 然 较 之 孟 子“诛一夫”之说更为激进。
二 治国以仁的政治主张
以仁义治国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方孝孺亦然。他说:“古之圣人,不忍杀一不辜,行一非义而取天下”。[4](《梁武帝》)圣 人 在 夺 取 天 下 中 行 仁 义,治 理 天 下 更 是 如此,“仁足以施法政,义足以洽乎民心”[4](《君量》)。人君本着仁爱情怀,推行治国理民的各项政策,其恤民之心可以保证国家各项法令法规顺利贯彻实施。“义”又能使社会的方方面面祥和融洽。要 形 成 这种“德 洽 令 孚”[4](《君量》)的 美 妙 局 面,方孝孺主张“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他说:“古之圣人既行仁义之政矣,以为未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隐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 无非仁义而 不怨。”[4](《深虑论》)可见,方孝孺的治国主张乃是仁以施治,法为保证。具体说,包含下述内容:
第一,主张“视民如伤”。“王者之学,以古为师,穷理正心,固守勇为,法尧为仁,法舜为孝,视民如伤,文王是效,简册所陈,善政嘉猷。”[4](《正学》)在方孝孺心中,视民如伤是行仁政以治国理民的必然需要,有了视民如伤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治政者就能像上古圣王那样重民、惜民、爱民了。由此出发,方孝孺激烈抨击了历史上盘剥万民、竭泽而渔、视民如草芥的做法,呼吁统治者“正德、利民、厚生”[4](《周官》),对待百姓“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4](《读邓析子》),在百姓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雨露阳光。这样“物阜而民康,实皇家太平之基”[4](《箴》)。方孝孺的这一主张在建文帝时得到很好的贯彻,为大明王朝创建了“四年宽政解严霜”[7](《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的气象。
第二,主张推行井田制,提倡藏富于民。洪武时期,朱元璋采取了系列保民措施,并试图以残酷的刑罚震慑贪腐官员与豪强劣绅,却未能从根本上阻止强势群体对土地近乎疯狂的掠夺。有些地区的军卫屯田尚不能幸免,遑论普通百姓了。有鉴于此,方孝孺强烈主张推行井田制,“孰非民乎?孰富孰贫乎?孰衣文绣,孰如悬鹑乎?屈为佣隶,天宁不仁乎?仁莫如井田。”[4](《杂问》)可见,方孝孺行井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抑制豪强势力的土地兼并,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古梦想,让百姓拥有基本的生存依托,绝非腐儒式的简单复古。方孝孺希望通过井田制的实施,既能满足国家的基本赋税要求,又能让百姓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勤劳节俭致富,从而实现百姓的福祉。推行井田制,不仅能够阻遏贫富极化趋向,而且有益于缓解社会矛盾,钝化趋于尖锐的贫富与官民对立。显然,方孝孺的这一思想是朱元璋“厚民生”“重民命”治国策略的进一步细化与落实。
第三,主张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方孝孺说:“为国之道,莫先于用人。”[4](《深虑论》)治国以仁、重民爱民的政治主张能否得到落实,关键在人才选拔与治国理民之吏的任用。“国之本,臣是也”[4](《杂诫》)。方孝孺以史为鉴,剖析了用人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因果联系:唐玄宗时期,张九龄一度为相,以其品行高洁使朝中“小人困不得志”。张氏免相后“唐室渐乱,而几亡国”[4](《张九龄》)。“二世之任赵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4](《深虑论》)都是用人失当导致国家走向衰亡的惨痛教训。故此,治国理民需要人才,人才务必有德。德才并具是方孝孺理想的人才标准。在方孝孺眼中,人才的首要品质是忠君,要有慷慨赴国难,殉国忘其家的精神。同时,还要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其次,为官者要具备“公廉”品质。方孝孺说:“国之所尚者,公廉”[4](《孝思堂记》)。就是说,官员应该以“公”为心,以民为意,不贪货财。官员公廉与否,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社稷安危、国家存亡。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大多与官员廉洁与否相关。一个国家的官员如果不公廉,势必导致“国贫”:“聚敛之臣贵,则国贫。”[4](《杂诫》)再次,为人臣要“大度”。方孝孺说:“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君子,而败于私智之小人。智之于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则流为诡诈险侧。”[4](《郑灵公》)在人才使用上,方孝孺主张“各尽其才,而如其所欲”[4](《深虑论》)。这 样,将 人 才 安 排 在政 治 体 系 最 适合的位置,使他们才尽其用。为了更好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方孝孺主张对人才要“推之以诚,而待之以礼,使邪佞无所进其谗”[4](《深虑论》),对 卓 有 贡 献 的 人“任 之 终 其 身 不 为 久也,爵之极其崇不为滥也”,尸位素餐者“黜而屏之不为少恩也,罚而殛之不为过暴也”[4](《深虑论》)。
第四,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方孝孺坚持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反对严刑酷法,认为“治天下有道,仁义礼乐之谓也;治 天 下 有 法,庆 赏 刑 诛 之 谓 也”[4](《深虑论》)。在 方 孝 孺 眼里,“道”具体体现为“仁义礼乐”,“法”则表现为“庆赏刑诛”。他以日常饮食为喻分析说:“仁义礼乐为谷粟,而以庆赏刑诛为盐醢,功成而民不病。”[4](《深虑论》)就是说,对于黎 民百 姓而言,其生存离不开仁义礼乐就如同少不得食粮那样。刑诛庆赏如同鱼、肉、盐等制作而成的酱,虽然其重要性比不得仁义礼乐,但也是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者一本一末,相辅相成,“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4](《深虑论》)。治国、治 民、为 政,万 不 可 舍 本 逐 末。否 则,“弃谷粟而食盐醢,此乱之所由生也”[4](《深虑论》)。
三 “立法利民”的法治思想
方孝孺虽为儒者,但并不一概反对法治。他认为,立法的核心是利民,法是保护民众利益、打击不法侵害的有力武器,可以“禁暴乱、贪猾、诡伪、盗窃”[4](《深虑论》)。国 家为民众提供法的保护,民众就会拥护政府,进而保证社会稳定,国运长久。说到底,法对于人君而言,既“利其国”,更可“保其子孙之不 亡”[4](《深虑论》)。于 国、于 民、于 君 均 不 可 或 缺。具 体说,方孝孺的“立法利民”法治思想包括下述内容:
第一,“立法以防害民”[4](《深虑论》)。方孝孺认为,立法的目的是卫民,防止侵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不是通过严刑酷法阻止民众为乱。历史上的许多王朝法网严密,犯禁者众,“常布满海内之狱”[4](《深虑论》),说明立法思想存在偏差,立法以防民乱是舍本逐末。“法制所以备乱,而不能使天下无乱。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药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 法 者 未 有 不 亡 者 也。”[4](《深虑论》)方 孝 孺 认 识 到,“人 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治之外者矣。”[4](《深虑论》)所 以,“圣 人 之 为 法,常 治 之 于 未 为 之先”[4](《深虑论》)。防患于 未 然 是 立 法 的 根 本。他 说:“‘獖 豕 之牙,吉’。獖牙非无牙也,有牙而不能伤也。”[4](《深虑论》)就是说,野猪生有极具破坏力的獠牙,如果不予约束任其狂奔,就会伤损农田。用猪栏将它管制起来,野猪即便有獠牙也无法伤害庄稼了。法律就是政府设置的猪栏,立足点是护民而非害民。要让法律真正起到“以防害民的作用”,方孝孺提出下述主张:
其 一,立“为 治 之 法”[8](《所染》),反 对“一 准 其 私意”[4](《深虑论》)。方孝孺认为,为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立法必须公正,体现“公意”,官员不应该“出于己”,“一准其私意”,将“一家之法”强加于民,变为“天 下之法”[9](卷32),这样的立法本身就是非法的,结果是“自乱其法”[4](《深虑论》),不仅无法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相反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直至王朝覆亡。
其二,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这是方孝孺对洪武朝普法实践继承的结果。方孝孺认为,欲令百姓守法,必先使其知法、明法,明确法律的边界,进行普法宣传的目的就是让百姓知法,“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为”[4](《深虑论》)。“民畏笞骂为杀戮”[4](《官政》),当然自觉 守 法,不 会 违 法 犯 罪。百 姓 不 去 触 动法律红线,当然不会受到刑罚处罚,立法设禁是爱民的直接体现。如此“为法者不烦,守法者不劳,而民不敢为乱”[4](《深虑论》)。
其三,加强执法。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加强对执法官吏的教育。利民之法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利民的作用,执法官吏是关键环节。执法官吏必须“知立法之意”,这样才能很好地依法办事,行“仁义之道”[4](《深虑论》)。否则,“欲天下之治,而不修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为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则治,俱弊则乱,俱 无 则 亡,偏 存 焉,则 危。”[4](《官政》)另 一 方 面,对“玩法”者严惩不贷。法律的尊严、社会的稳定、民众的支持离不开对玩法者的严惩。“可以无犯乎法,而犹犯之者,此诚玩法之民”[4](《深虑论》),这 些“玩 法”者,不 仅 践 踏 了 法 律 的 尊严,破坏了社会秩序,侵害了他人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定,所以“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4](《深虑论》),必须予以重惩。这种惩罚,既可以使“民晓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4](《深虑论》),而且具有警示作用,“法之可畏而不犯”[4](《周礼辨疑》)。
第二,主张先教后诛。方孝孺虽然主张重惩“玩法之民”,但他坚决反对严刑峻法。他认为,强秦之亡源于严刑峻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0](第75章)重刑甚至死刑用滥了,对于民众来说无异于轻刑。轻刑若不轻易使用,一旦使用,也会被人们视为重刑。“圣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义”[4](《治要》)。所以,后世治国者应该吸取教训,改弦更张,抛弃过度依赖严刑峻罚治国理民的错误做法。方孝孺认为,治理国家有五种重要的工具性手段:“政也,教也,礼也,乐也,刑罚也。”[4](《杂诫》)法律是五种重要工具之一,“无法不足以治天下”[4](《治要》)。治国理民,法律当然不可或缺。但是,“天下非法所能治也”[4](《治要》)。刑罚虽然貌似在治国理政中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导致“天下尚法”的弊端。过度依赖法律,特别是重刑手段,实际是未把握恰当运用法律的要领,“不提其要者,刑人接于市,而人谈笑犯法不为之少”[4](《治要》),所以,方孝孺主张“不轻用法于吾民”[4](《治要》),应该“先教后诛”,“欲其无贪黩也,必先使之畏戮辱而重廉耻”。就是说,要教育人民知道廉耻,自觉守法。只有那些冥顽不化者方才施以重罚,这对于树立法的权威大有助益。难能可贵的是,方孝孺所谓“教”,是建立在满足人民基本生存条件基础上的“教”,而非空洞之“教”。他说:“不治其致病之源而服药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4](《深虑论》)治病必须首先找到致病的根源,然后下药方才见效,否则,不明就里,随便医治,只能致人死亡。因此,在社会治理方面,方孝孺主张探究“致疾之由”。他说“天下固未尝好乱也,而乱常不绝于时,岂诚法制之未备欤?”[4](《深虑论》)导致天下动荡不已的根源并非法制不完备、不健全,而是官员、苛法伤害了“元气”。“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4](《深虑论》)。恢复元气的方法,方孝孺认为主要在于“使之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而后禁之,则攘夺盗贼可止也”[4](《深虑论》),让百姓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有田可耕,有工可做,有米可食,有衣可穿。这些生存必需的条件具备了,百姓不可能去冒险犯法。即便有个别“至凶极悍之徒,萌无上之心,亦无由而事成”[4](《深虑论》)。在普通大众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谁愿意跟在犯上作乱之徒身后去犯险呢?方孝孺既重法又重人,既重人又重物的法治思想找到了法网严密、严刑酷法之下社会依然动荡不休的深层根源,对于医治社会之疾显然堪称良方。
第三,“治人”与“治法”并重。方孝孺认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有良好的法治;良好的法治只有在“治人”(能行法之人)推动之下才能得到良好的实践:“欲天下之治,而不修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为要,人次之。两者俱存则治,俱弊则乱,俱无则亡,偏存焉,则危。世未尝无人也,然取而用之,与用而责成之,无其法,则 犹 无 人 也。”[4](《官政》)方 孝 孺 主 张“治 人”与“治法”并重。不仅要有“治法”,而且要有“治人”。如果没有好的、可用于推动落实法律的人(“治人”),无论多么完美的法(“治法”)都不可能得以很好的贯彻实施。方孝孺对历史上的王朝衰落进行了总结,认为其败亡存在共性:要么法制残损,要么统治者不守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他认为,周王朝贤君少庸君多,罕见“治人”,却存续700余年,原因就在于“治法”。期间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短暂的“治人”与“治法”并俱,很快再现了文武二王时期的盛世。所以,“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4](《深虑论》)。方孝孺眼中的汉唐两代,法嫌粗疏,幸遇贤君,于是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二朝最终因为没有贤君“乱而亡”。所以,方孝孺得出结论:汉唐的问题出在“法不足周事”,不能完全归咎于“守法之非人”[4](《深虑论》)。按照朱熹的说法,“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11](卷108)。即“治人”与“治法”存在辩证关系,不能将国家衰亡的责任简单归因于某一方面。社会治理注重“治人”与“治法”并举,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
四 结束语
以上本文仅就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从民本角度做了分析。可以看出,方孝孺的政治思考无不与对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深切关怀息息相关。虽然方氏某些理论设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具有强烈的“空想”色彩,但对于其身后600年,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者而言依然闪耀着熠熠的智慧之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绩固不待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同样前无古人。时下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经济与行政领域的权力垄断,导致某些部门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与民争利,乃至夺民之利,生出竭泽而渔之嫌,国家财富迅猛增长而人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严重下滑,百姓财富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相对“剥夺”,法制建设滞后且漏洞百出而失去了对权贵阶层的有效约束与震慑使其可以肆意横行为害社会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必须正视的是其对国家执政之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不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使人民的福祉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终极目标指向,而仅仅将人民作为权贵阶层牟利的工具和手段,那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最终走向就有可能被拖离正轨与最初的设计背道而驰。
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的政治思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镜鉴。方孝孺民本思想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他强调了治政者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养民”,并据此提出打破官府借助国家权力进行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的传统,主张让利于民,倡导富国必先富民,降低百姓赋税,官府俭而补税之降的爱民措施。其次,他力倡视民如伤,仁法结合,慎选官吏,仁法与礼法相结合,落实藏富于民的政策主张。另外,他还主张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百姓利益,通过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对“玩法之民”予以坚决打击。方孝孺的上述主张在建文帝时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缔造了绚烂的盛世局面。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如何真正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核心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无疑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困局,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突破的瓶颈。执政者不仅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更需要在实践中寻求落到实处的现实路径。毋庸置疑的是,方孝孺的民本思想为这条路径的设计成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素材。
[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顾起元.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宋濂.宋文宪公全集[M].台北:中华书局,1965.
[4]方孝孺.逊志斋集[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
[5]栾保群,吕宗力.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朱鹭.建文书法拟[M].明万历刊本.
[8]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