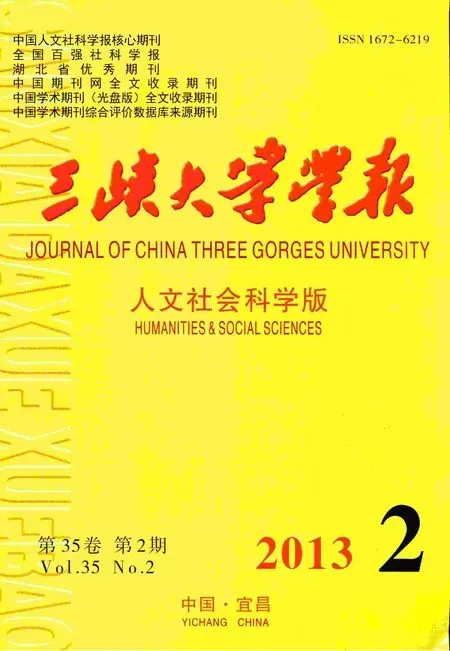清朝判断“华民”国籍的原则探析
2013-04-07颜志文
颜志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在1843年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共计十六款,《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总计十五款。几乎每款都是涉及到“英商”应该怎样,“华民”应该如何。换言之,两条约明确规定“英商”、“华民”的权利和义务[1]。但是对于“华民”,纵观条约全文,耆英与璞鼎查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就国际法而言,“华民”是属于国籍范畴。所谓国籍是指人、法人及某些财产与一国拥有的特殊关系,根据国际法原则,该国国内法为行使管辖权而赋予的法律关系[2],即各国都有权根据国内法或历史惯例决定谁是它的公民。而清政府的第一部国籍法是1909年颁布的《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3],这就意味者此时清政府只能用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历史惯例作为判断“华民”的标准①。历史惯例是什么?史无明文记载。而国籍是指管辖权、保护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用逆推法,通过对1843年,开海贸易前后,所发生的涉外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清政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享有管辖权、保护权,即可得出清政府用以判断“华民”的历史惯例。据此笔者认为清政府用以判断“华民”的历史惯例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血统性原则,其二是文化性原则,其三是地域性原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原则的人,才是“华民”。下面笔者就逐一论述构成中国传统的国籍观的三个原则。
一、血统性原则
其是指以血缘关系作为判断“华民”的历史惯例之一。换言之,有中国血统就可能归清政府管辖,就可能是“华民”;反之则可能归外国政府管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得到证实:
首先是李泰国案。曾任中国的首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是英国人,关于此点,史有定论。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却误传其为“华民”。如“天津之役,殷兆镰奏称李太(泰)国即广东嘉应州人,而魏默深(魏源)曾识其父于金陵。盖世有夷官,父子同名,循外洋例”[4]。又如恭亲王“闻李泰国系广东民人,世为通使(事),市井无赖之徒,胆敢与钦差大臣觌面肆争,毫无畏惮……拟请敕下桂良等,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刻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并晓喻各夷,以该通事本系内地民人……”[5]从上述两条史料,我们可知李泰国之所以被误认为是“华民”,是由于魏源误认为李泰国之父李太郭是广东嘉应州人,殷兆镰又以讹传讹上奏朝廷,所以恭亲王奕䜣才会错误认为李泰国之父李太郭是广东嘉应州华民。进而我们从恭亲王认为李泰国之父为华民,李泰国就是“华民”,就归清政府管辖的逻辑思维中,可以得出清政府判断“华民”的历史惯例之一是只要其有中国血统,就归清政府管辖,就是“华民”。
其次是额洼哩斯塔、噶毕约则案。1843年,开海贸易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根据《南京条约》,西方人不允许进入内地。但许多传教士纷纷私自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其管理权属于西方领事,一旦发现后,只能交由西方领事处理。由此而产生许多外交事件。而通过对这些外交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即探究清政府是如何确定其西方人的身份,从中可得反证。在这些案例中最典型的是额洼哩斯塔、噶毕约则案。据《筹办夷务始末·卷75·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己丑》记载:“驻藏大臣琦善、帮办大臣瑞元奏:……西藏年班堪布等由京回藏,奴才等风闻有随行可疑之人,当饬噶布伦汪曲结布查获三人,呈送前来。奴才等公同查验,俱系蒙古喇嘛打扮,讯问皆能汉语,于清文、蒙古文字均能讲诵,惟唐古特文字语言尚未熟悉。一名噶毕约则,一名额洼哩斯塔,共祖兄弟,佛兰西人,在所属之奔底舍哩地方居住,素习天主教。噶毕约则于道光十六年由福建起程,经江西、湖北等省至京,其弟额洼哩斯塔,于道光二十一年由广东起程,经湖北至京,在盛京地方彼此会遇,遂一同行住,于热河、察哈尔、归化城及蒙古地方,均经往来。……上年行至西宁,闻唐古特番商由京回藏,遂一同前来,即被拿获……奴才等查该犯等,甫经至藏,即被查获,既无可质讯之人,即所供经过各处,亦系一面之词,而起出夷书夷字,又复无人辨认,若悬揣推求,转不足以成信谳。……西藏既无可质讯之处,谨不揣冒昧,于讯供后,即分起委员解交四川督臣”[6]。由此我们可知噶毕约则与额洼哩斯塔系法国传教士,先后来华传教,道光二十五年被驻藏大臣琦善拿获,并上奏道光帝。而由于二人通晓汉、清、蒙等文字,因此道光帝认为二人“恐未实系佛兰西人”,要求四川总督宝兴详查。据《筹办夷务始未·卷75·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载:“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奏:……兹于五月二十一日由藏将该夷人等解到,臣随督同在省司道向其讯问,该夷人等皆能汉话,据供一名噶毕约则,一名额洼哩斯塔,均系佛兰西人,同习天主教,认为兄弟,均在外传教……伏查该夷人等所供各情是否属实,无可质证,传授天主教亦例所不禁,且察验该夷人发眉眼色,迥与中国人不同,其为外国夷人并非内地奸徒假冒,无须再是推求。……”[6]由此我们可知四川总督宝兴认为噶毕约则与额洼哩斯塔的确是法国传教士。其依据是“察验该夷人发眉眼色,迥与中国人不同,其为外国夷人并非内地奸徒假冒”。对宝兴的方法,道光帝也认可。由此案,我们可知清政府判断噶毕约则、额洼哩斯塔为法国人的依据是“该夷人发眉眼色,迥与中国人不同”。
而从表面上看,道光帝、琦善、宝兴是以外貌作为判断国籍的依据。即“黄头发、绿眼睛”的法国人是法人,而“黑头发、黄皮肤”的法国人是“内地奸徒假冒”。但是道光帝、琦善、宝兴为什么会以外貌作为判断国籍的依据?这是因为由于血统和种族的因素,“华民”和“西人”在体貌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当时人看来,有西人外貌,必有西人血统,则归西方政府管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就道光帝、琦善、宝兴等人判断国籍历史惯例的实质而言,仍是以血缘作为的依据。即有西方人血统的,则必是“西人”。
二、文化性原则
文化性原则是指有清一代把是否服膺中华文化作为判断“华民”的历史惯例之一。而中华文化的外在标志是中华的衣冠制度。也就是说穿中式衣服者为“华民”,归清政府管辖;否则即便是有中国血统也被视为西方人,归西方领事管辖。
关于此点,我们可以从发生于1851年的陈庆真案中得以证实。《陈庆真的口供》载:“据陈庆真供,年二十三岁,父母俱在。兄弟八人,小的系同安县店前村人。素识灌口乡王泉,商共创小刀会名目,……系欲谋逆,共扶真主。”[7]据《张公去思碑》“(陈庆真)真华而生夷,故夷酋挟公。公曰:吾民也,吾治之,汝无与,夷恐,退,乏其力。”[8]闽浙总督裕泰“钦奉上谕:……查该处会匪,先经(升任)兴泉道张熙宇访获首犯陈庆真一名,并将讯非会匪,在陈庆真屋内闲座之周德等三人同时拏获。正在讯办间,即有英吉利国领事夷目苏里文照会该升道,以陈庆真等生长该国所属息力(新加坡)地方,应作为英国民人归该夷目办理……。”[5]由上述史料,我们可知陈庆真是福建厦门同安县店前村人。早年其父到新加坡,娶马来亚女子为妻,生陈庆真。1849年陈庆真返回厦门,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的通事,而后又担任英国怡和洋行的书记官。1851年,被时任兴泉永道张熙宇以小刀会会首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杖责至死。
英国政府认为陈庆真是英国属地公民,应归英国领事管辖。并且在1851年正月初八日,厦门领事苏里文照会兴泉永道张熙宇提出:“本属国来厦之人民,祖籍多有在内地者,因生长本属,即系英国编氓,凡到中国经营,遵照和约,只准在五口之例,不许擅离远游。并循例赴管事官衙门挂号。倘有不遵循者,例应查究。未知本属到厦人等,有无冒昧不来到及有原故私往内地致干犯约之咎者。查照善后条约所载,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约擅入内地游者,即听该处捉拿送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等语。则是如有被拿供系英国之民,别无凭据可查对,即应当询之英国管事官,则无难释疑矣。兹将登挂本署号簿各姓名先行移查,第未审开列之后,尚有未挂号之人否。俟有续来报挂者,另行补文移知,并将该民人送署验看,此后遇有拿获供称英国百姓者,即烦移询商办,方昭公允。合就备移贵道,希即查照施”②。由此条史料,我们可知陈庆真由于出生于新加坡(息力),所以尽管其祖籍在内地。英厦门领事苏里文根据英国国籍法中的出生地原则认为陈庆真拥有英国国籍。因此根据《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陈庆真仅是违背条约擅入内地游玩,清政府仅有权捉拿并送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
而张熙宇对苏理文的照会中的观点并不赞同,回复说:“查贵领事此次照会,系恐中国人生长贵国属岛之人,回到内地或兹生事端,原是好意。惟查前定各条约中,并无中国人生长英国所属地方,回至中国仍作为英国人民之例。现在五口通商,英国客商携眷居住不少,其在五口生长之人,并无作为中国民人之说,将来回英国,更无作为中国编氓之理,彼此易观,事理不难分晓③。由此可知张熙宇对英厦门领事苏里文提出的出生地原则为判断国籍的依据并不认可,并且在回复中提出本升道查两国人民,总以衣冠制度为分别,其留发服英国衣冠者,应作为英国百姓,归英国管事官管理。其薙发而服中国者,应作为中国之百姓,归中国地方官。如此界划分明,可免将来争执。”③即张熙宇提出把是否服中国衣冠作为判定其是否归清政府管辖的标准,
张熙宇判定“华民”的方法是其个人的观点,或是清政府判定国籍的历史惯例?另据新任驻闽浙总督裕泰和福建巡抚徐继畬就此事的奏折:“臣以为中国民人衣冠制度,均与英人迥别,自不能因其生长英国属岛,即作为英国民人。”[5]由此可知张熙宇的方法是得到新任驻闽浙总督裕泰和福建巡抚徐继畬的支持。并且时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亦就此事照会英国驻华公使文翰:“两国人民总以衣冠制度为分别,其留发而服英国之衣冠者,应作为英国百姓,归英国领事官管理;其薙发而服中国衣冠者,则应作为中国百姓,归中国地方官管理。”④而徐广缙更是以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办理夷务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换言之,此时的徐广缙的地位相当于日后之外交部长[9]。得到其认可,就意味者不再是张熙宇、裕泰个人的观点,而应是清政府判断“华民”的历史惯例。
三、地域性原则
地域性原则是指把所处的区域作为判断“华民”的标准之一。即尽管有中华血统,又服中国衣冠,但是其私自离开中国,就不再是“华民”,清政府就放弃对其进行管辖和保护。但在其返回中国后,清政府就恢复对其管辖和保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得到证实:
首先是“红溪惨案”(又名噶喇巴番众杀害汉商)。1740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的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称巴达维亚)对华人进行过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行持续一周,万余华人在公司屠刀下丧生,华人鲜血染红了雅加达河,史称“红溪惨案”。关于“红溪惨案”已有多文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清政府对“红溪惨案”中的华人的态度。例如福建水师提督王郡认为华人“因其为各国贸易聚集之所货物颇多,往往不辞险远前去兴贩。而积有资财饶裕者遂娶有室家,生有子女,数辈相承,不次万计,名为汉种,而实则久作番民,该地所谓土生仔也。”[10]又如署福州将军策楞“臣等详察此案始末情节,熟加筹划。此等被番戕害汉人,皆久居吧地,当前次禁洋开洋之时,叠荷天恩宽有,而贪恋不归,自弃化外,按之国法,皆干严宪。”[11]一代理学大师蔡新认为“(乾隆)六年噶喇巴番众杀害汉商,闽大吏上其事,请禁南洋商贩以困之,议未定,内阁学士以(蔡)新留心经济,致书问新,新复书谓:南洋事诚不法,然汉商本皆违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为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揆之国体无大伤”[12]。从上述三条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在惨案中遇害的华人,清政府认为皆是“悖旨逗留之人”,都是“自弃化外。名为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因而按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仍逗留海外的华人就只能按当地风俗管理。清政府不享有管辖权,自然不会保护他们。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是“华民”。而后来之所以禁止和噶喇巴的贸易,是因为担心“番性贪残叵测,倘嗣后扰及贸易商船,则非前次逗留者可比,势必大费周章。”[11]
其次是陈怡老案。尤溪籍人陈怡老于1736年乾隆元年去巴达维亚贸易,娶土著妇女,生育子女,并充任荷兰殖民政府辖下管理华人事务的甲必丹,1749年(乾隆十四年)回国[13]。据“乾隆十五年福建龙溪县民陈怡老久居噶喇巴贸易,贿通夷目,谋充甲必丹。于十四年五月潛回福建廈门。为地方官访获以闻。照例远遣。”[14]。乾隆诏令“将私往噶罗巴,充当甲必丹之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入官”[15]。由上述两条史料我们可知清政府是以大清律例处理陈怡老。换言之,陈怡老回国后,清政府承认其是中国人,结果陈怡老被没收家产判处充军。在大清是“华民”,离开大清就不是华民。因此才有前文张熙宇所说“并无中国人生长英国所属地方,回至中国仍作为英国人民之例”
四、余论
中国传统的国籍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血统来划线,其实质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地域来划线,其实是化外之民的体现。而衣冠制度作为标准则是儒学法制化表现。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国籍观,与近代西方的国籍观相会时,国籍冲突就难免会产生,甚至引起激烈的外交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的马神甫案和亚罗号案均带有其影子。
注 释:
① 但是关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国际法,学界是有争论的。周梗生在其《国际法》提出“西方学者常说国际法是近代欧洲的产物……那显然是不正确的。每一个时代凡属有许多国家并立,相互交往。自然就有适应这时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交往规则和习惯产生。”参见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40至41页。王铁崖在其《国际法》也提出“有了国家,国家之间就必然有往来关系。也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这些在国际关系中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就是国际法。在这个意义上讲,古代世界是有国际法的。”笔者赞同上述前辈的观点。
② 英国公档局藏中文档F·O 663/57A。转引自黄嘉谟:《英人和厦门小刀会起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②:教乱和民变》,第214-215页)。
③ 张熙宇给苏理文的照会,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见英国公档局藏中文档 F·O 663/52-56 Chang hi yu to translation February 23,1851(Received on March 91851),see F·O,第228-125页。转引自黄嘉谟:《英人和厦门小刀会起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② :教乱和民变》,第215-216页)。
④ 徐广缙致英国公使文翰的照会,咸丰元年,三月十七日,英国公档局藏中文档。转引自黄嘉谟:《英人和厦门小刀会起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②:教乱和民变》,第219页)。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34-40.
[2](韩)柳炳华.国际法[M].朴国哲,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06.
[3]杜裕根,蒋顺兴.论近代华侨国籍与中国国籍法[J].江海学刊,1996(4).
[4]夏 燮.中西纪事(卷七)[M].
[5]贾 祯.(咸丰)筹办夷务始末(卷26咸丰八年五月,咸丰元年3月)[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卷75·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已丑、卷75·道光二十六年闺五月)[M].北京:中华书局,1964..
[7]佐佐木正哉.咸丰三年厦门小刀会起义[M]//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181-217.
[8]陈乃干.清代碑传文通检[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5.
[9]矛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三联书社,1997:522.
[10]清高宗实录(乾隆六年七月十一日.福建水师提督王郡为报访查噶喇巴国杀戳汉商事奏折)[M].
[11]乾隆实录(乾隆六年七月十五日.署福州将军策楞等为报噶喇吧国杀戮汉商并请禁止南洋贸易事奏折)[M].
[12](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六·蔡新[M].
[13]冯尔康.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M]//林天蔚.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1991.
[14](清)皇朝通典卷九十七·噶喇巴[M].
[15]王彦威,王 亮.清季外交史料(卷87)[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