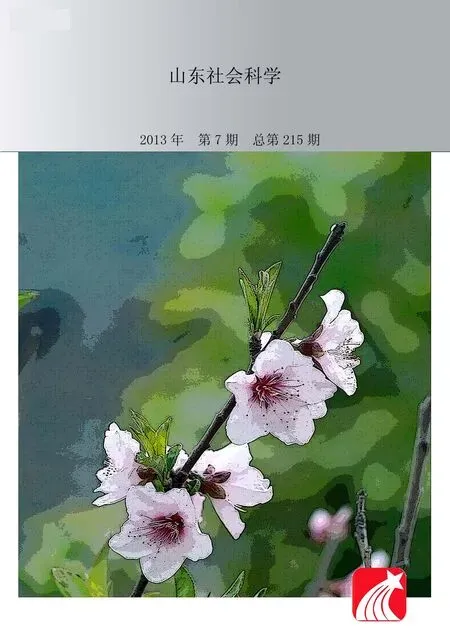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2013-04-07辛明玉
辛明玉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4;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王渔洋,名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是清初著名的多产作家, 著述诗文、小说、诗话等作品共计36种560多卷。渔洋生逢明清王朝交替、社会动荡之际,明王朝随着崇祯皇帝驾鹤西去已寿终正寝,清王朝凭借铁蹄席卷华夏而蓄势待发,在上思国泰、民求安康的时代潮流下,他未及而立即以《秋柳四章》惊誉全国,继以“神韵”理论开拓诗学,毕生以“一代诗宗”主盟诗坛,将明清时期山东诗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这是山东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郑方坤《国朝名人传略》说:“本朝以文治天下,风雅道兴,巨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断然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于家有其书,人习其说。盖自韩、苏二公以后,求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学足以贯穿古今、其识足以别裁伪体,六百年来未有盛于先生者也。”注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二,广文书局1971年出版,第112-113页。
浪大滴水成,山东地域文化数千年积淀成就了王渔洋;山高人为峰,王渔洋光大发展了山东地域文化。王渔洋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集成者、代表者、开拓者,他带有山东文化最强最优的基因,研究“王渔洋现象”,就是以王渔洋为圆心,将研究视角从现在主流研究的个体、现时、主体、本体向后推移放大,更多地从群体、历史、客体、矛盾的角度去分析还原它,解剖“王渔洋现象”这个麻雀,仰视明清之际山东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时空特点的图谱,从深层次把握明清时期山东文学勃然而兴的深刻原因。
一、生济南文献之邦,山东文化视角下的“王渔洋”
在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上,从创作主体和作品水平来看,山东出现过三次高峰: 一是汉魏建安诗歌时期, 山东诗歌以曲阜孔融、平原弥衡为代表居全国先列; 二是宋代词学时期,山东以辛弃疾、李清照为代表驰誉南北;三是明清之际历城李攀龙、新城王士禛先后宗主明清诗坛, 山东出现了庞大的诗人群体,成为当时全国诗坛的中心。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序中说:“国初诗学之盛,莫盛于山左。”注卢见曾:《国朝山左诗抄》,清乾隆二十三年雅雨堂刊本。“今世诗格当家,无逾齐鲁,古之辕固、毛、薛,皆其产也。一旦出而振起颓唐,泽于大雅,齐鲁文学,彬彬天性。王师无敌,建大将旗鼓,若龙蛇风雨从之。”注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12页。引文出自本书较多,以下不一一注明,只在文中注明页码。山东诗学异军突起的背后,是无数文人学士的创作活动,王渔洋是其中的佼佼者、成功者,是山东文学兴盛繁荣的代表。“对于地方文学的影响因素包括该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文风貌和风土人情等方面。在某一个朝代,也许是其中的一两种因素起到主要作用, 在另一个朝代,也许是另外几种因素起到主要作用。”[注]李茂民:《地方文学史的新收获——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具体来讲:
(一)继先承统,延续族脉
家族制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制度,在传统社会,家族是人成长成就的首要环境和第一资源,王渔洋的成就是其家族文化的成功。主要有三个突出方面:一是人格独立,唯理唯真。渔洋自述:“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当明中叶,门户纷纭之时,无一人濡足者,亦可见家法之恭谨矣。”(《池北偶谈》卷六)在明清官场结党风气盛行的背景下,王渔洋终其一生无结党营私之陋,而以孜孜诗学之美,有坦荡荡大胸怀,使他成为皇帝、诗界、遗逸都能接受的人物,远离党争门户之害,终成一代诗宗盛名。二是修德为先,重道重义。《先忠勤公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池北偶谈》卷五)综观渔洋一生,他蜚声海内除了文功之外,还有文德,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不恃官高为荣、不以位重为骄,论文才不论贫富,这为他成为一代文宗提供了道义基础。他与蒲松龄的布衣之交鲜明体现了这一点,他主政扬州获得东南遗逸认可恐怕也主要得益于这一点。三是诗学传家,重文重教。《先忠勤公家训》: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渔洋先祖方伯公常揭一联于厅事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池北偶谈》卷五)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200多年间出进士 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成为“江北青箱”。王渔洋家族在做事、做人、做文领域的累世之功为背景,王渔洋的天降人才为机遇,将其推向“文坛领袖”的巅峰,这既是家族演进的偶然,也是家族文化发展的必然。
(二)模山范水,延续诗脉
山水地理是文学产生发展的环境依托,家乡山水风物哺育了渔洋诗歌风情,渔洋诗歌也使家乡景致唱响全国。究其一生,家乡山水成就了渔洋诗歌,歌颂家乡是渔洋毕生情结。一是一树一石皆入诗,山水出诗人。泰山五岳独尊、雄踞东天,黄河奔腾大地、东流入海,泉水趵突腾空、轻灵秀美,都成为他笔下倾心吟咏的对象,家乡山水风光深厚滋养了渔洋意境清远的山水诗,赋予了渔洋诗歌以磅礴大气和飘逸灵性,启发他写下赞扬自然风光的优美诗篇,山水诗歌造就了“诗歌山水”,并在其心中埋下了神韵的种子。《为人题芙蓉泉亭子》、《九日千佛山》、《初望见历下诸山》、《泺口》、《华不注》等诗歌颂家乡的山山水水。特别是顺治十四年,渔洋创作了著名的《秋柳四章》蜚声大江南北,一时和者无数。家乡山水为渔洋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意向,是渔洋山水诗歌走向全国的起点。二是一时一地皆为文,勤奋出诗人。“王士禛以诗著名于当时及后世,然亦博学,康熙一朝京朝官合诗人与学者为一者,可与当时著述甚富的朱彝尊比肩。”(第23页)渔洋虽然自幼聪颖超人、才思敏捷,但非常勤奋,勤于读书,中年以后勤于著述。家乡生活点点滴滴都入诗,时时处处皆留文,以生活的诗化记录诗化的生活。诗词之外,王士禛常倡议古今典制和人事、评论政务得失、辨别事理真伪、稽考亡佚、点评诗文、存文献掌故等,著述了大量散文、笔记杂著等。三是一景一事皆动情,多情出诗人。王渔洋自述:他七八岁入家学,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篇,便觉怅触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池北偶谈》卷十六《诵诗》)渔洋在《秋柳四章》诗序中说:“昔江南王子,感落叶而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泣。仆本恨人,性多感慨。情寄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秋柳之伤和明清易代之伤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鸣使其成为时代的悲歌,奠定了王渔洋日后登上诗坛盟主地位的基础。《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从这个角度说,《秋柳》动人是胜在情感,悲天悯人、感时伤怀、多情善感的才情气质,成就了渔洋诗歌的情感特质。明人王鏊云:“山川之秀,实生人才;人才之出,益显山川;显之维何?盖莫过于文。”[注]王鏊:《吴中小志丛刊》,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77页。按照现代文学地理学,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深刻影响。山东山川壮丽、四时美景,为渔洋诗歌作了文学意象的准备;渔洋奇绝诗才、勤奋精研,为渔洋诗歌作了文学知识的准备;渔洋天生多情、敏感多思,为渔洋诗歌作了审美倾向的准备。渔洋诗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是山东山川地理天然孕育的奇葩。
(三)去国怀乡,延续文脉
万里远牵乡国梦,一丝长系故人情。渔洋对于山东地域文献整理作出了突出贡献。渔洋自叙:不佞自束发受书,颇留意乡国文献。主要有三大方面的文献:一是仰望先贤,嗜好遗迹。渔洋整理了宋代李清照和辛弃疾两位山东先贤的事迹,在小说中列举了十余条之多,记录了二人的身世创作情况及作品的辑佚记录,明代以来济南诗派也是渔洋关注的重点,搜求记载了李攀龙及家人蔡姬的生活遗迹,搜集整理刊印了边贡及其子边习的遗作。二是关注故里,嗜好考证。在《池北偶谈》中考证了范仲淹在淄川长山范公泉、范公祠等遗迹,鲁仲连陂传为鲁仲连所居,齐人辕固生故里为新城牛固;通过《水经注》和曾巩诗考证了娥皇女英祠方位,对舜及二妃的故事引经据典进行了记录和考证。《香祖笔记》中对汉终军故里、尹太宰尹家亭子等十几处名人故居和墓地位置进行挖掘整理,可见高山仰止之意。三是重视轶闻,嗜好掌故。《池北偶谈》等书中记载了历城明翰林王公敕能御风出神、知未来休咎的奇人,济南舜祠舜井水忽溢高数尺、须臾泛滥的异事,对《龙城录》王宏、本乡严子陵、宋杜善甫等济南历朝历代人物故事加以搜集记录。考证了崂山山名的由来,记录崂山道士的传说故事、宗教信仰情况。地方文献是地域文化的根脉,文献整理是文化继承的前提,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渔洋作为一代文宗,对家乡文献高度关注,不仅是收集储备,更是文化再创造,促进了山东地域文化根脉的传承。
由此看出,山东地域文化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造就渔洋诗歌成就:新城王氏家族的雄厚文化积淀,是渔洋诗歌成就的物质载体;地理风貌是山东诗歌传承的最佳内容,是渔洋诗歌的主要文学客体;历史文献是山东诗学传承最佳艺术形式,是渔洋诗歌的主要文学素材。山东地域文化在主体、客体、形式上为地域诗学大爆发作了充分准备,机缘博奕必然地将王渔洋推向了山东诗学爆发的中心。张云章说:“若其尽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绍古今之统者,则非此数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统系古今之作者,盖数百年而一生之人也。”(第1520页)
二、尊康乾盛世之宗,全国文化视角下的“王渔洋”
山东地域文化走向全国并成为领袖,关键是参与全国文化的系统博弈,并表现出最佳的精神特质。从全国文化比较角度,渔洋诗歌崛起有三方面深层原因。
(一)逢世扬盛,才高为宗
渔洋成为一代诗宗是官方、学界、民间的一致赞允。一是康熙认可。出于“治道在崇儒雅”的观念,康熙非常崇尚儒家学说,康熙十六年明确提出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强调兴礼教文化。康熙将王士禛提拔进入翰林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从地域文化看,王渔洋出身儒学之乡,山东文化乃中国正统儒学文化发源地,其象征意义就更加突出,这既是王朝随机选择的巧合,也是山东文化地位的必然。此后,多数明朝遗民半推半就地参加博学鸿儒科考,也充分证明了这一选择的历史影响。二是诗界认同。康熙十年,时任刑部尚书的李敬为《渔洋诗集》作序时说道:“他日庙堂之上,以文章扬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第135页)康熙多次向群臣询问诗文兼优之士,首揆高阳李公(霨)、桐城张读学(英)、临朐冯公(溥)、中书舍人陈玉璂等都是饱学之士,都向康熙推荐渔洋,认为他是一时共推,其诗一时之论、以为可传,渐成京城诗界的领袖人物。羽翼并时、魁杰振起,门人弟子“如日之随影”,海内文士“远近翕然宗之”。渔洋文学地位的确立,无疑是随历史变迁的必然发展趋势。三是民间认识。《秋柳》诗四章传遍大江南北,和者无数。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与明末文士诗酒文宴、共同唱和,编有《红桥唱和集》,得到东南遗逸群体的认可。王掞《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赞渔洋说:凡公所撰著与其所论定,家有其书,户诵其说。得一言之指示,奉为楷模,经一字之品题,推为佳士。明末清初,面临着民族对立、文化断裂、社会断层的突出矛盾,渔洋位登诗宗,既是一个新文化标志性人物,也是山东地域文化的符号性人物,是满汉民族融合、文化融通的重要桥梁,是官民融合、南北融通的重要桥梁。这充分体现了新王朝、中国文化发展对山东地域文化的选择和认可,体现了山东文化作为儒学故里、海内独尊的重要地位和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二)政廉绩优,德厚聚人
作家的道德决定着作品的层次与价值,道德修养是王士禛走向一代诗宗的重要阶梯。一是为官以廉。渔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45年仕途始终恪守“清、慎、勤”,起到了诗增政声、政促诗誉的作用,为成为一代诗宗占据了道德高点。同为高官的山东诗人刘正宗,人品不佳最后被革职查办,查慎行是宋诗派巨擘,因“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革除国子监生员,反衬出渔洋道德情操的高洁和为官的谨慎。二是为文以勤。渔洋不但自己勤于著述、精于诗词,创作了大量意境优美的诗歌,写作了小说杂文等作品,而且热心诗歌交流活动。整理了家乡的重要文献,为山东文化传承作出积极贡献;渔洋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组织群体活动。渔洋的热忱一方面说明了他对诗学的真诚热爱,也说明了他热心公益、情系黎民、教化百姓的古道热肠。三是为人以诚。在任扬州推官期间,以礼贤下士姿态与东南遗逸唱和,受到吴嘉纪、林古度、杜溶、冒襄等遗民诗人的赞誉。钱谦益表示“窃欲以狂澜之既倒,望低柱于高贤”的期望。渔洋博采众长、汲引后进,一篇之长,一句之善,辄称说不去口,以公齿颊成名者不可计数。这种做法获得了海内士子的倾心赞服,为其登上诗坛正宗提供了民意氛围。官德立声,文章立名,综观渔洋一生,时人后人没有诽谤其文德修养的,由此可见其道德评价之高。
(三)探物究理,论立诗风
风格是文学个性的体现,理论是文学风格的升华,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成熟。历史上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等都曾经论述神韵,基本上都将其作为诗歌创作的方法或标准,渔洋将其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和根本问题,这是诗论的巨大开拓,给渔洋诗作提供了理论根据,全面理解其理论要注重三个角度:一是博综该洽,以求兼长。俞兆晟《渔洋诗话序》王士禛自述其一生“论诗凡屡变”:“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第4783页)从时代的大背景下,渔洋诗变既反映新王朝文治思想的路径选择,也反映了文学界对文学继承的路径选择,渔洋作为时代的文学旗手,他的诗变鲜明体现了时代困境。从渔洋来看,渔洋欲将宗唐与宗宋矛盾相结合,走出一条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诗路,这是渔洋诗变的指导思想,也是其诗学实践的核心,“是时代和某个特定人物之间双向选择的必然现象”[注]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页。。因此,渔洋宗唐抑或宗宋,只是时人后人的刻板认识,实质是融唐合宋的“清诗风格”。实践证明,这是清诗的繁荣昌盛之路,终成以宋诗精神为主干的清诗,取得超元越明的成绩,《晚晴诗汇》收诗人6100余家,《清诗纪事》收诗人6470余家,数量均远胜唐诗和宋诗,渔洋作为一代诗宗的贡献自是不言自明。二是尊重差别,文风分殊。渔洋在博采众长的思想指导下,对各种诗学形式保持充分的宽容,体现了其博大宽广的学术胸怀,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诗学领袖的远见卓识,这在他和施闰章的争论中得到体现。陆嘉淑《渔洋续诗集序》:“窃尝见先生与宣城施先生论诗矣,宣城持守甚严,操绳尺以衡量千载,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则推而广之,以为姬姜不必同貌,芝兰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以疵颣白璧。”(第688页)渔洋自述学宋“未尝恣于无范”,学唐为主,学宋元只为充实学唐,这再次印证其融唐合宋以创清诗传统的高远眼光。三是诗风雅正,大气敦厚。渔洋诗多变只是形式多变,但温柔敦厚的诗风却一脉相承,而温柔敦厚是正统诗风的标准。陈维崧评价道渔洋诗歌:“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第139页)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清初励精图治背景下,渔洋诗歌描写了康乾盛世的时代愿景。由此来看,神韵理论使渔洋诗走向成熟,使其诗由自发阶段跃升到自觉阶段,为其成为一代诗宗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一个开放、发展、和平的诗学理念,这种精神气度与即将到来的康乾盛世来讲是一种天作之合。
山东文化造就了渔洋厚积薄发的文学积淀、厚重载物的德性情操、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唯有这种积淀方能俯察世间万物之变化,唯有这种情操方能仰观天地乾坤之运行,唯有这种胸怀方能经纬历史社会之兴替。推而广之,这也是山东地域文化雄踞中国大地的成功秘诀。
三、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的特点
一个时代孕育一种文化,一个地域造就一方文学。明清山东文学能够在全国率先发展,它根源于时代的沃土,同时源于优秀的地域文化特质。文化繁荣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但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发展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物质支撑
一是经济发展推动。明代中叶山东人口仅740余万,清代嘉庆年间增至2890余万,道光年间突破3000万,成为当时仅有的几个人口大省,同期山东耕地面积从57万顷增至110余万顷。二是文化融合助推。明清时期,大批四川、山西等地人口大规模移民山东,地域文化之间优势融合与互补,造就了崭新的山东地域文化。明天启礼部左侍郎文震孟曰:“海内族姓之贵者,莫最于王氏。其望盖二十有二,咸以分封食采,而太原、琅琊尤著。若新城之王,固琅琊之裔也。自北海徙济南凡十世,跻巍科登腆仕者代不乏人。遂极人文之盛。”[注]文震孟:《山东新城琅琊王氏世谱序》。三是科举制度激励。清朝建立后,科举录取名额较明朝增多,选官制度更偏重于科举,文学与科举的天然联系,使科举群体成为文学的潜在群体,这是中国选官文化的特色。以渔洋家庭为例,自嘉靖辛丑年(1541年)至清道光丙申年(1836年),共出进士29人、举人69人、贡生113人。
(二)家族文化传承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载体
钱穆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传统社会,世家大族是文化上利益共融、文化共通、情感共鸣的团体,家族对于文学据有始基而核心的位置。明清时期,山东三代以上科举入仕的大家族有200余家,其中影响突出的大家族有数十家,同时也是文学世家。渔洋家庭就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族,出现了一批为官清廉、为人清正、为文清秀的作家群体,现存有著述传世者有40余人,其中明代18人、清代26人。
(三)因时代而通变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心理动因。
与时通变是山东文学的重要文学传统,孔子论《诗》, 确立了“兴、观、群、怨” 的论诗原则,南北朝时期山东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惰,兴废系乎时序”。明清之际,渔洋伯父侍御百斯公(与胤)甲申之变中同妻子尽节,渔洋等山东作家经受住了社会变革的冲击。渔洋平生诗学三变也鲜明体现了通变思想,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说:“当我朝开国时,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公以大雅之才,起而振之,独标神韵,笼盖百家,其声望足以奔走天下。”[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四库备要本。通变的客观精神,是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歌德指出:“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与此形成对照,当渔洋宗盟文坛时,东南遗逸无意参与竞逐,与士禛并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后荐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地位影响与渔洋相比差之千里。
(四)天行健君自强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
山东作家群体集体自强是山东地域文学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一是爱诗相承。山东历经边贡、李攀龙、王士禛三位文坛领袖,孜孜努力,巍成一派,王渔洋将明代两位济南诗派领袖的精髓融于一身,将济南诗派的繁荣推至顶峰。渔洋位列一代诗宗,是几个时代山东文人奋斗的结果,《蚕尾续文》中说:(边华泉)历官南京户部尚书,所至登临山水,购古书金石文字累数万卷,而家无中人之产,身后至无以庇其子姓。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宦海沉浮40余年,吟诗研诗是其重要内容,无论官居何处、政务繁闲,不废登临吟咏,结交风雅文士,一生创作5000余首诗。二是美德相因。山东作家追求人格正统、思想正统,入朝为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居野则安贫乐道、正直宽厚,理家则为人诚信、团结互助。居易录卷十五记,李沧溟视秦中学政,某巡抚以檄征其为文,李遂挂冠。由陕归来,李攀龙在家乡筑白雪楼,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不与权贵往来。三是热肠相继。乐于助人、心系家国是山东人的传统美德。据考证:“清中叶的王渔洋、袁枚、沈德潜等人,更给予女诗人以切实的指导和多方面的支持。”[注]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渔洋在为官任上,游历、考察都形成文字,他关注乡国文献,所记的诗友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工、担者、锄者、僧人、闺秀,甚至乞丐等,他们有一篇之胜,或一言可采,都予以宣扬,因此很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注]李毓芙:《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