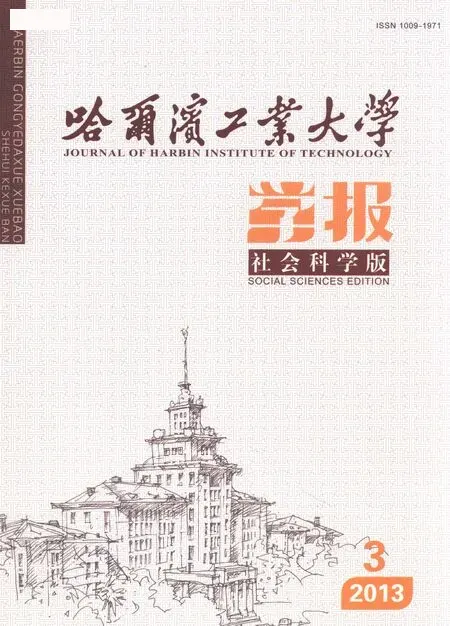论张承志宗教题材小说中的人道精神
2013-04-07李有智
李 有 智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210093;2.宁夏社会科学院 回族研究编辑部,银川750021)
一、宗教书写:关注人的处境
张承志写宗教,其意并不在宗教本身,如宗教的神秘、幽玄等,而是以宗教来表现人、人心、人性也即人道,写宗教实为写人道。在《心灵史》序言中,张承志明确写道:“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1]宗教仅是一种题材因素,是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较为集中、突出的一个部分,虽有时看似宗教色彩明显,亦属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色彩,而非其他。写了宗教,不等于就是宗教文学。至于他本人宣布皈依宗教,这是个人的一种姿态,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
宗教题材会为文学带来一些新的面貌和气象,如精神领域的拓展、心灵深度的开掘等。在张承志之前,当代文学中的宗教因素多为佛教、基督教等,伊斯兰教仅有零星的涉及;张承志首次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引入当代文学中,这是他的贡献。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作家往往把宗教作为某种背景因素,但张承志则将宗教文化作为主体,并且把自己的情感也投入进去”。从宗教文化母题叙事角度看,《心灵史》所塑造的“宗教人格与宗教精神”,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贡献”[2]。
严格地说,张承志目的不单是在描写伊斯兰教,而是写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也不是这个民族的全体,而是其中人数较少的一个群体(哲赫忍耶)。张承志深入民间后,发现他们被遮蔽了200 多年悲惨又悲壮的历史,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种为信仰和尊严而不惜牺牲的精神,一种在他看来属于真正维护心灵的人道精神。对比当下,他认为“孔孟之道”影响下的中国,最缺乏的即是这种人道精神,因此,在整个90年代,张承志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用小说、散文以及学术随笔来张扬信仰、人道,目的就是为中国文化提供参照。这体现了他的善意、他对中国文化的最深热爱。
1984年,张承志走向了民间,这是他立场、观念上的变化,其结果是在创作中拓展了题材领域,并为当代文学展现了前此所未有的人物群像、绝境中的生存景象、执著的信仰等。具体地说,他的小说和散文表现了哲派民众在历史上的受难境况,后来又逐渐将描写范围扩延到整个回族;而作为描写对象的回族,它与伊斯兰教本质上不可分割,宗教性特征要大于民族性特征,所以表面上看,张承志反映民族生活的作品中,具有一种浓厚的宗教色彩。有时在谈论诸如宗教、信仰、奇迹等话题上,张承志的文字显出至为愤激的情绪,即便如此,他从来没有把宗教或信仰当成唯一、绝对的标准,也从来没有把文学当成负载宗教精神的工具。他关注的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所强调的“都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的问题”[3],也即一种人道精神。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得至为明显。
二、“口唤”与“暗杀”:小说中的两个关键词
《终旅》和《西省暗杀考》是被忽视的两部小说,对它们的研究远远不够,这也可能与小说本身的难度有关。小说背景皆为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其中都出现了一个宗教色彩极浓的句子或术语,即“口唤”,《终旅》中“听说沙家堡大寺被官军围了,听说寺里已经放出来舍命保教的口唤”,《西省暗杀考》中“师傅就是在这个日子里,给众人下了那件事情的口唤”,这是理解小说主题、情境、氛围等诸多因素的一把钥匙。
“口唤”是回族伊斯兰教常用语,具有特定含义,“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同意’、‘允许’,主指:1.穆圣对教民的指示;2.中国伊斯兰教有的教派及其支派(门宦)教主对教下的口头命令,必须服从和执行。”[4]凡接受了“口唤”的人,甘心舍命,义无再辞,确实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神秘意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死,与一般战争中以单纯取胜为目的大为相异,而且心无牵系,满心欢喜之情,非常理所能解。
《终旅》中的主人公接受了“口唤”后,便忽匆匆、兴冲冲离开生活了三十年的穷山沟,几十年来从未出过远门,这是他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离家。小说设置了一个具有极强对比性的结构:人物前往沙家堡时的兴奋之情与他身处的赤贫绝境之间,是如此的难以协调;心境的明亮与身后村庄的黯淡之间,于色彩上亦恰为比对。小说在主人公赶赴战场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时时回溯并点出他生存的那个“荒瘠的山沟”,“从小破衣烂衫,从小饥着肚子”,从小过着上山刨石头、下山啃洋芋的日子,几十年来忍受着“饥寒痛苦”,这一切不仅仅由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也是由“官家”所造成的。“官家是些什么呢,他从小就费劲地想。看不见也不认识,旱季里像股干干的黄风,收秋时像阵冰球般的冷雨,寒冬腊月呢,不像漫天的雪,像那股子要命的‘冻’”。然而,就在如此的自然、社会环境中,这个穷苦的农民以及山沟里那些相同处境的人,这些山野自然的弃民,这些官家的弃民,却仍然人一样的存活下来,并未退化至动物般境地,原因即在于他们有了“心里的神圣”。这就是沙家堡——“沙家堡是一口气。你能灭了男男女女的庄户人,你能灭了条条山沟的庄院窑洞,你就是灭不了这口气”。正是沙家堡给了穷人存活下去的精神动力,给了穷人那种人所应有的尊严,现在连这一点都要剥夺掉,无怪乎十七条沟里的回回们全部都要奔赴而去了。这是张承志在带有宗教色彩的小说里描写的人道精神,随后长篇小说《心灵史》又强化了这种精神。
《西省暗杀考》首章即写“口唤”,在名为“一棵杨”的小村庄,师傅给伊斯儿、竹笔满拉、喊叫水马夫三人传下了“口唤”,去暗杀左宗棠。小说的主角就是伊斯儿,在与师傅一同祈祷时,他的内心世界出现了一种变化:“心里明敞大亮,伊斯儿觉得,连心里对左屠夫的仇怨,连心里对正月十三亡人的情份,都化了一片灿烂的明亮了”;刺杀行动的前夜,他在念赞词时又进入了陶醉状态,“真真切切看见一湾湖水,绿波轻荡。湖中有三座沙岛,黄沙澄净”,暗示了对象出现的地点。这是小说叙事上出奇的想象,但也不全是作家凌空蹈虚、凭空想出来的情节,它有着依据,在苏非主义哲学中称之为“费纳”(阿拉伯语音译),“以追求神秘的陶醉境界为特征”[5],达到忘我、超越的层面。可是当前两人皆以失败而死,“冥冥中的养主,把事情放到了伊斯儿的肩上”的时候,他在“一派空明”的幻境中看见一纸“白图”,同伴已死,大势已去,只好回到“一棵杨”再等时机,从此那种幻境也完全消失了;左氏死后,因为失掉了目标,伊斯儿“心里生成了一股仇恨”,发誓要宰掉左氏“后人”。
“暗杀”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字眼。战争时期,暗杀也是取胜手段之一;清军与回民军之间发生战争,处于弱势一方的回民军也采取了这种手段。这个情节反映出了当时真实的社会氛围和历史状况。清末政治腐败,一些革命志士“因受英雄史观和欧洲虚无党的影响,在革命中急于求成而又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于是醉心个人恐怖主义的暗杀活动,以此为革命成功的捷径”,他们“认定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由宣传革命进入暗杀活动的时代。他们主张仿效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提倡古代刺客、侠客(如荆轲、聂政)那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尚武精神……”[6]。这部小说也是对历史真实情境的一种想象性复原。
小说有一处情节容易引起读者困惑和误解:伊斯儿决定要杀死左氏后人,而且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再次失败;他不是不知道,杀掉一个可能根本不了解其先人所犯罪行的无辜者,于道义、于情理均说不过去,所以他艰难地对提醒他注意的那个人说“我等着后世里打官司”。但在“补考”部分也即结尾部分,当左氏后人真的出现了,此人在前往新疆上任的路途中顺便拜访清真寺,这时伊斯儿竟然表现得极为淡然,让徒弟们“代师送客”,自己“带上一双花镜,又潜心钻研”经典了。按照一般逻辑,先前以那样舍业毁家的决心,寻求报复,小说的大半笔墨也是用在寻仇情节上,可当目标主动送上门来,为何漠然待之,形成如此明显的反差?
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全部作品的关节所在,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其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限。此前,清政府镇压了回民军,事实上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伊斯儿他们的心理中,战争的阴影并未消除,仍然与清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也就是说清政府依然是回民的敌人,因此以左氏后人为暗杀目标虽于道义不合,但符合对立状态中那种特有的敌我逻辑,也可说此为民族心理上战争状态的一种延续。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华民国成立,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西省回民的血仇宿敌,豢养了左屠夫、刘刽子手的清官家,在革命党的手里亡了”。既然清政府已经灭亡,那么清政府与回族人民的对立状态也随即结束,这也意味着“宿敌”没有了,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前提,在此前提下,左氏后人能够被允许进入清真寺,盖因其人乃民国的一介公民,其先人所犯罪行与作为后人的他无涉。一切已成历史,曾有的罪恶也已远去,不再纠结。这就是伊斯儿为什么能对仇敌后人淡然待之的原因,其中体现出一种宽容的人道精神。张承志《潮颂》一文中写道:“应当说,历史上有过的屠杀已经被历史否定了。也应当说,存活于赤穷的人民也正一天天饱暖起来。还应当说,回族等族舍命死守的理想也愈来愈被尊重。但是糟辱人心——不尊重人道,无疑是二十世纪的眼睛最难揉的沙子。”[7]据此亦可见关注人道是张承志作品的一个主线。
三、《心灵史》:人道主义书写的极致
《心灵史》曾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有影响的十部长篇小说之一,为张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将他推入了论争的漩涡,引发多种命题的讨论;而持批评意见者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上,忽视了文本自身的文学性。
关于《心灵史》的文体形式,张承志本人并不认为是一部小说作品,而是“熔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的混合文体。这种自我定位的说法在有些批评家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比如旷新年认为“这部书是叙事和抒情、启示录和诗篇、史诗和抒情诗的统一和融合。它本质上是诗,但采取的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它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它既是叙事,又是抒情,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同时也是宗教和哲学。”[8]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和观点。但王安忆却独持相反意见,将《心灵史》作为一部小说:“我为什么还是把它作为小说呢?抛开它的名字不说,它写的是一部教史。有很多人否定它是一部小说,觉得怎么是小说呢,觉得很奇怪,根本无法把它作为小说的对象去研究。甚至于宗教局也出来反对,他们觉得它煽动了一种宗教狂热。”她的理由是:第一,小说寻找的是“一个心灵的载体”,描写的是一个“心灵的世界”而“不是一本教史”;第二,小说的序言中一段话证实了她的结论,它构造的“心灵世界”的一个特征是为了“心灵的纯洁”而不惜牺牲,“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故事具有着一种不真实性,这恰是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她宁可将小说中的叙事者“看作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我’,不仅讲述了哲赫忍耶的故事,还讲述了他讲故事的前景。他虽然笔墨不多,但却没有间断刻画描绘‘我’。他描绘‘我’是‘久居信仰的边疆’——北京城里的‘我’;‘我偏僻地远在北京’,等等,都是将我描写成一个边缘人,然后如何走入信仰的中心——哲合忍耶。这就是在关于哲合忍耶的全部叙述之后的叙述,也就是‘心灵史’所以命名的由来”[9]。
《心灵史》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信息,而人道主义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
在《心灵史》里面,人道主义在并没有哲学或伦理学上那种复杂的含义,它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尊重人,把人当人看,小说序言中多处写道:“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
批评界和学术界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命题,比如陈坪在一次专门讨论《心灵史》的座谈中说,人道的第一义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张承志似乎用哲合忍耶那种非功利、纯情感的道德态度来和受着儒家文化熏陶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功利性、纯理性的‘人道’认识作比较”,那是一种“发于本心的自然生存状态。他们待人的热诚、无私的爱以及全身心的投入和给予,不是因为他们必须遵循什么道德原则,而是他们不得不如此做,因为这是作人不可追问的终极奥秘所在,它是不证自明的”;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张承志对不久前关于“人道”的讨论怀有某种轻视,认为知识分子的认识是肤浅的,“是理智动作的结果,是纯思的产物”[10]。
《心灵史》其实从一个非常朴素的意义上描写了人道或人道主义,通过具体的形象叙述了它逐渐生长、生成的过程;而且,这个人道并非哲赫忍民间固有的、或只有民间的才是最好的,它是民众以百年的流血史争取来的。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心灵史》叙述的仅仅是一个比较而言具有特殊历史的群体,并从这个群体的历史中引申或升华出一种结论,达到普遍性的层面,也即“人的觉醒”。
作品第一门用大幅笔墨叙写了三种困境,当克服了这些困境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人终于站立起来了。
第一种困境:绝境一般的自然环境,“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尤其以陇山为中心的地区,风土呈着极度哀伤和恐怖的面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如此的环境里人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种认识其实已经是常识了,无须多说,但《心灵史》中确实有一群人“无望地在这片穷山恶水中迎送生涯”。
第二种困境:社会环境方面,穷人是弃民,“穷人,这是个在中国永不绝灭的词”,这一切皆由统治者即短篇小说《终旅》中所说的“官家”所造成;极度贫穷的另一面,却是堆金积银的贪腐。在物质被剥夺了的同时,穷人作为人的社会性因素也被剥夺了,缺乏社会交往,就像《终旅》里的主人公,活了30 多岁,始终没有走出过那片“荒瘠的山沟”,更不用说娶妻生子了。
第三种困境:文化或宗教的困境。在此种困境里面,穷人不只是无法供养子女上学读书,获得知识;宗教功修方面的权利事实上也失去了。哲赫忍耶是苏非主义的一个派别,此派传入之前就已经有了各种宗教教派,但宗教也有过分注重仪式因而趋于世俗化的倾向,结果是穷人做不起功修、也信不起宗教了。《心灵史》突出地写了一个穷人,以概其余,作家说“如此的一些故事极其重要”:“有一户住在村角的农民,家里只有半块烂席铺炕。以前他是从来不上寺礼拜的,他躲着邻里亲戚,避着回民的一切节日。每逢到了自己父母忌日,他总是借口外出,离开村子。人们为悼念亲人、为履行信仰者的义务——都有各自的一些尔麦里(干办、集聚诵读《曼丹夜合》这部经)——而他是孤独一人,院里没有一只鸡,缸里没有一点细粮。赤贫的人不单念不起书,也信不起教。他呆滞地坐在高高的荒山坡上,熬过自己不敢正视的日子。”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倘若长久地生存于此种环境,人本身的意识、精神等必将会退化,落到一个极低的境地中,即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人之为人以及人为了实现自身本质的那种需求、追求亦将随之萎缩、消失,此时的穷人就成了真正的穷人——既是物质上的赤穷者,更是精神上的赤穷者。《心灵史》关注、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松散状态的人群,一些木然仰送日子的穷人。
而哲合忍耶给这些穷人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并不是哲赫忍耶教义本身有什么特点,作品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说明这不是作品所关注的重点;而是这种教义为穷人铺了一条路,与穷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具体来说:
第一,于金钱、物质方面,不要穷人再行“施散”(阿语“海地耶”),穷人做功修时无须再交纳各种费用,这对家里仅有“半块烂席”的穷人来说太重要了。
第二,仪式上的简单、朴素,使任何一个有心灵追求的人皆可或追随导师、或独自干功,进入心灵修炼境界。
这个教义的全部意义即在于它“推翻”了“文化上的不平等和无形压迫”,激活了穷人身上那种人所应有的追求:原来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应以贫富贵贱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即人是平等的;一个人只要追求心灵的丰富,无须借助外力或某种虚浮的外在形式,即人是自尊的;最主要的,穷人于苏非神秘的境界中体验了心灵自身的喜悦、满足,即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哲派教义带给穷人的礼物,以及由此引起的那种持久的响应,《心灵史》用了“震撼”一词来形容,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这种变化就是人的觉醒,是一种作家刻意表述的底层的人道主义——穷人借此形式找到了人的平等、尊严和自由,此时,贫穷和歧视不仅可以忍受,甚至可以超越了。所谓“穷人宗教”,即建立此种意义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张承志从来没有单纯地赞美过穷贫,也从未说过只有穷人那里才存在着真正的人道主义,他所使用的术语是有严格限定的。《心灵史》多处描述了“底层贱民”获得“心灵自由”之后、精神上焕然一新的气象:“人间依旧。黄土高原依然是千沟万壑灼人眼瞳的肃杀。日子还是糠菜半年饥饿半年天旱了便毫无办法。但是穷人的心有掩护了,底层民众有了哲合忍耶。穷人的心,变得尊严了。”
理解了这种具有特定内涵的人道概念,那么,与人道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宗教概念即牺牲,也就不难解释了——当人的意识觉醒并且实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当人从那种模糊浑沌的状态终于觉悟到了尊严和自由,这时候再想把他们打回到过去的那种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哲派民众当时面临的危险,就是他们已经获得的尊严和自由将再次被剥夺,为了守住这种尊严和自由,他们唯有以死相拼。《心灵史》叙述的第一次起义,其中当然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原因,但最突出的情节即民众那样疯狂地扑向城市,目的确实很单纯,只是要解救出他们的教主,因为正是这个人为他们启蒙,让他们实现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这种牺牲精神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这是由宗教中强烈的救赎观念所决定的。所以,牺牲精神不是哲合忍耶所独有,“牺牲之美”也不是《心灵史》首次所揭示、宣扬,凡与宗教相关联的起义等历史事件中,都存在着这种牺牲精神。显克微奇表现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中,罗马全城的军民到处捕杀基督徒,但后者决不反抗,“只要把他们围住,他们就跪在地上唱赞美歌,毫无反抗”,“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凶残暴虐的迫害,殉教者们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驯服和真诚”;第五十六章写罗马人在竞技场中用野兽咬杀基督徒,场面空前惨烈血腥,而基督徒们“居然唱着歌”任由猛兽撕咬,当一些牺牲者抬头看见彼得为他们祝福、告别,“脸上都显得明亮起来”,他们相信自己的灵魂会飞向天堂。《心灵史》第二门“书耻”一节考证了石峰堡起义中,回民军于“开斋节”这天毫无反抗,任由官军砍杀,“他们举意在尔德节圣洁的境界中飞向没有迫害侮辱的天堂”。这个情节与《你往何处去》中野兽撕咬基督徒一节何其相似。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描写了1897年巴西腹地卡奴杜斯农民起义,传教士“劝世者”是其精神领袖,他周围的3000多贫苦农民与政府6000名正规军作战,最后全部牺牲,小说中最后的战场上相拼一节与《心灵史》华林山义军拼死一战、全部牺牲的情景,也是何其相似。
总之,《心灵史》在形式上是对一个教派历史的叙述,它的主题却是通过宗教题材弘扬了人道精神,并描写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牺牲精神。就像作家多次说过的那样,他不是在写宗教本身,而是以宗教来体现人性,《心灵史》第五门“八大家”部分,他写道:“宗教是世界观更是人、人性和人的感情的产物。不仅在中国,在任何文化和任何宗教中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人的本性。”有研究者如刘复生就非常准确地认识到张承志宗教题材小说的意义:“正如《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作品显示的那样:现实苦难决不是升入天国的阶梯,而是异端存在的理由。由此,张承志的宗教写作洋溢着一种异端的气质和对体制的对抗色彩,所谓牺牲之美,所谓‘舍西德’(复数形式为束海达依,即为伊斯兰圣教牺牲)、圣战,完全不能在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它们所要捍卫的不是宗教的神圣原则,而是被压迫者的心灵自由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以及对维护和再生产不公正、不义的体制权力的永远的异端姿态。”[11]
[1]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10.
[2]谭桂林,龚敏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2006:66,72.
[3]张承志.荒芜英雄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294.
[4]敏春芳.文明的关键词——伊斯兰文化常用术语疏证[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44.
[5]张承志.清洁的精神(修订本)[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49.
[6]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03,304—305.
[7]张承志.绿风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179.
[8]旷新年.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J].读书,2006,(11).
[9]王安忆.《心灵史》的世界(第三讲)[J].小说界,1997,(3).
[10]丁东,陈坪,刑小群,谢泳.在信仰的档案里——漫谈张承志的《心灵史》[J].黄河,1993,(1).
[11]刘复生.另类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