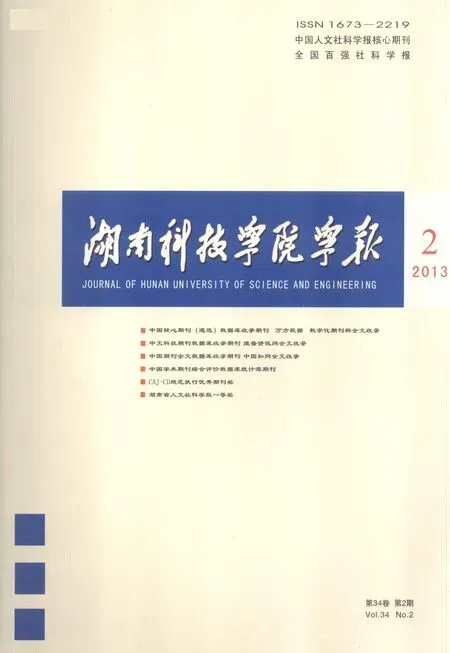历史精神的诗化显现——曹操诗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之关系
2013-04-07刘伟安
刘伟安
(昭通学院 中文系,云南 昭通 657000)
曹操是东汉末年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由于曹操的诗歌不重藻饰,缺乏丹采,曾经被《诗品》的作者钟嵘评为了下品。曹操本非舞文弄墨的文人,也未必有足够的闲暇与心思去雕章琢句,惨淡经营,其诗歌不以辞藻见长也在情理之中。钟嵘对曹操诗歌之艺术特点的把握应当说是相当准确的,但将其列为下品实属不当。所幸的是,不少后代诗人、诗评家和读者对此提出了强烈异议。如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三云:“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清人陈沆《诗比兴笺》云:“曹公苍莽,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翻看中国诗歌评论史即可知,认为曹操诗歌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上品的观点在后代诗人、诗评家和读者中已经形成了共识。应当说,虽然钟嵘将曹操诗歌列为下品实属不当,但曹操诗歌不重藻饰,缺乏丹采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曹操诗歌之魅力究竟何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后人为其诗歌被列入下品鸣不平?
一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曹操的生平。曹操可以说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四海鼎沸的背景中崛起的一位旷世英雄。他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有着特殊的家世背景。父曹嵩,为宦官曹腾养子。曹操的家世与宦官集团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以至曾被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文人陈琳骂为“赘阉遗丑”(《为袁绍檄豫州》)。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但曾担任汉太尉的梁国名士桥玄却慧眼识英才,曾勉励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南阳名士何颙也曾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另一名士许劭评之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曹操以孝廉推举为郎,任洛阳北部尉。中平元年(184),曹操出任骑都尉,曾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后又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被诛灭后,群雄并起,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经过多年征战,削平了割据于北方各地的群雄,统一了北方。由于非凡的功绩,曹操被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
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说人是自由的是因为人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世界,创造历史;说人是不自由的是因为人可能在连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下被时代精神召唤出来,成为历史潮流的引领者,但在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又要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甚至是神秘天意的限制。无论一个人的才能多么杰出,在这个规律面前都不可能例外。本来,步入政治活动之后的曹操,最初志向不过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誉”,“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让县自明本志令》)而已。但历史的风云际会不容许曹操的理想停留于此,因为汉末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召唤着能够结束天下大乱之局面,臣服四海的英雄人物出现。谁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谁就是历史精神在人间的化身。刘劭《人物志·英雄篇》云:“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可以长世。”放眼汉末,这一英雄人物无疑非曹操莫属。于是,曹操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变成了如《秋胡行》中所说的:“万国率土,莫非王臣”。直到垂暮之年,曹操的这个完成历史使命的理想都未曾稍衰,就如《龟虽寿》所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理想,曹操既曾金戈铁马,亲冒矢石,又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善于广招天下智能之士为己所用,所以多次以寡胜众,以弱胜强,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曹操说:“汉未,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曹操非凡的才略和盖世的功绩。
相对于那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则不过是一个傀儡的汉献帝以及其他割据一方旋生旋灭,空有英雄之名的碌碌之辈如吕布、袁绍、袁术、刘表之流,曹操无疑是真正叱咤风云的旷世英雄。他曾不无自负地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尽管如此,在为统一天下而奋斗的过程中曹操依然遭遇过许多艰难险阻和挫折失败,其“万国率土,莫非王臣”的壮志直到去世时依然未能完全实现,“西有违命之蜀,南有不臣之吴”是一时难以撼动的既成事实,而且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惨状依然在延续。即使想改变这一切,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见,即使是曹操这位受到上苍眷顾的历史精神的代表者,也同样无法主宰历史的进程,依然犹如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历史往往是悲壮的、苍凉的,充满了惊涛骇浪,充满了人的主观愿望所不能把握的曲折性。毕竟,任何人都没有抗拒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
二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于悲剧性现实状况的冷静理性的审视,带给了曹操深沉而悲壮的生命体验。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的:“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1]P301在军务倥偬之余,曹操十分爱好文艺,“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袁环《宋书》卷十四)。“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可谓是“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张说《邺都引》)而曹操作为群雄领袖在创造历史过程中遭遇到的主观愿望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无法彻底克服的矛盾,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在其诗歌创作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于是国家的命运,民生的多艰,人生的苦短,功业的难就,成为了曹操诗歌反复吟咏的主题。
曹操非常羡慕太平盛世的生活,其《对酒》云:“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所以他为当时社会连年战乱导致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而“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正是在悯时伤乱情怀的激励下,他不辞辛劳,不避艰险,四处征战。如《苦寒行》,既描绘了严寒季节里将士们的征战之艰苦,又抒发了作者沉郁悲凉之情怀,更透露出一股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王国维先生曾指出:“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2]P312本诗就以其感情之真和观物之真长久地扣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弦。
同时,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就如《古诗十九首》中所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不论是旷世英雄还是凡夫俗子,都同样能感受到生命短促之悲。曹操也同样为岁月的流逝、生命的短促而悲怆不已。如《短歌行》,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起兴,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强烈而深沉的人生短促之悲。我们知道,岁月蹉跎而功业无成,会让人产生悲心,表现这种悲心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用汗牛充栋形容之。只不过曹操笔下的“人生如露”之悲不像一般文士那样染上了自怨自艾、消极颓唐之色彩,而是一种蕴含着历史意识的大悲。时不我待,他需要在有生之年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博大襟怀,实现“天下归心”的宏伟理想。为此他需要贤才的辅佐,因此象征着贤才的“青青子衿”便联结着“悠悠我心”,于是《短歌行》实际上也成了一曲“求贤歌”。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这首诗虽然充满了深沉厚重的忧叹,但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豪情,充分显示了曹操诗歌悲凉、沉雄的风格。
三
正统观念极强的宋代理学家朱熹曾针对《短歌行》之“周公吐哺”一语说曹操“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清人朱嘉徵也说:“余颇颂其歌诗所陈,未尝不悲其志,悯其劳也。但托喻周公,以西伯自处,举明辟付之后人,此为英雄欺人。”(《乐府广序》卷八)无疑,朱熹和朱嘉徵对曹操进行的是一种道德评价。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无数古圣先贤的崇高道德风范让后人高山仰止、钦敬不已,但道德高尚与否对于一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一个人的道德再高尚常常也无助于其达成某一历史使命,否则诸葛亮也就不会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的永恒遗憾了。历史使命的达成往往取决于一个时代最强者的行动,而最强者往往是不受过多道德律约束的。尤其是每当新旧朝代鼎革之交,上天赋予那个时代最强者的使命就是结束四海鼎沸,群雄逐鹿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恢复社会生产,让人民安居乐业。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一个政治家果真亦步亦趋地按照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准则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则根本不可能成为时代最强者,遑论纵横四海,成就盖世霸业,只怕是寸步难行矣。“因事设奇,谲敌制胜”才是动乱时代的政治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必须遵循的法则。否则,恐怕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此类例子,史不绝书。我们常常喟叹于在历史中常常是恶战胜了善,乃至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来自我解慰,但这其实体现了最真实的历史精神。就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言:“一切历史都不过是所谓世界伦理秩序的经验之反驳。”[3]P212即便一位政治家具有视民如伤的仁者情怀,也只有通过尔虞我诈、残酷无情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战胜对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由乱入治,救民倒悬的目标。这固然是一个悖论,但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曹操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说:“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其《求贤令》云:“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其《举贤勿拘品行令》云:“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固然,曹操曾被人称为“谲诈”,并且其重才轻德的用人方式导致了“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之《两汉风俗》条)的恶劣社会后果,但对于一个参与惊心动魄的现实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政治家来说,这几乎是自身的生存壮大所必须的。曹操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遭遇的对手们又何尝是儒家所推崇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的仁义君子呢?
何况曹操的个性中并非只有谲诈,明人谭元春在评价《蒿里行》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时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古诗归》卷七)征诸历史就可以发现,曹操在位期间,颁布了《抑兼并令》、《存恤令》、《给贷令》、《慎刑令》、《禁绝火令》等一系列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法令都给了在战乱、饥荒、瘟疫中苦苦挣扎的人民一丝苟延残喘乃至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些法令的颁布实施也说明了曹操并非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统治者,与董卓之流有着本质的区别。曹操在《军谯令》中云:“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考察曹操的生平事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收买人心的虚伪之辞,而确实是其肺腑之言。所以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虽不乏历史依据,但似乎过甚其辞了,而且也没有认识到曹操“贪残虐烈无道”之恶中蕴含有一种历史精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人们想用怀疑别人动机、诬蔑别人伪善的办法去剥夺别人可敬佩的成就,但必须注意,人诚然在个别事情上可以伪装,对许多东西可以隐藏,但却无法遮掩他全部的内心活动。在整个生活进程(decursus vitae)里任何人的内心也不可避免地必然要流露出来。”[4]P293所以黑格尔尖锐地指出某些实用主义历史学家“不满意于朴实地叙述世界史英雄所完成的伟大勋绩,并承认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的内容也足以与其勋业相符合,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为深刻。”[4]P293黑格尔坚定地指出:“为了反对这种学究式的小聪明,我们必须明白肯定地说,如果历史上的英雄仅单凭一些主观的形式的兴趣支配行为,那么他们将不会完成他们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重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伟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4]P294不论曹操如何“谲诈”,我们都必须承认,作为伟大人物的他确实“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如《观沧海》,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五中评论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另一位清人王夫之评论此诗则称:“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愁者。”(《船山古诗选评》卷一)试问此诗不是出自一位旷代英雄之手,能有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气象吗?如果不是一种博大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贯穿其中,能达到充塞八极无非愁者的境界吗?
同时,曹操晚年还作了一些游仙诗,如《秋胡行》(二首)、《气出唱》(三首)、《陌上桑》、《精列》等。且看《秋胡行》其二:“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关于曹操游仙诗的意蕴,学者们曾有过互相歧异,见仁见智的理解与分析,其中不少人曾认为这些游仙诗是作者消极思想的表现。这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论。实际上,与沉迷于成仙幻想屡屡见欺方士却至死不悟的秦皇汉武不同,曹操性不信天命,在《善哉行》就已经发出过“痛哉世人,见欺神仙”的感慨。固然,暮年的曹操深受“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的人生迟暮之感的纠缠,但这种人生迟暮之感的本质却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其一)。因此,与其说游仙诗表明了曹操相信神仙,不如说它们是一位进入了暮年的旷代英雄内心之悲怆的写照。纵然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犹在,其奈英雄迟暮何!所幸的是曹操也不乏后代知音,如清人陈祚明论《秋胡行》二首时说:“首章自升仙而归于时业,次章自时事而悼于人生,会味其旨,总归‘沉吟不决’四言而已。序述回曲转变,反复循环不穷,若不究其思端,殊类杂集。引绪观之,一意凄楚,成佳构矣。”(《采菽堂古诗选》)换言之,在大业未竟,英雄迟暮的现实情境下,曹操的游仙诗体现的并非浪漫的成仙之想,而同样是一种悲怆的历史精神。
明人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的《蒿里行》、《薤露》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在中国历史上,唐代大诗人杜甫也被后人公认为一代诗史,他以一枝包含悲悯的凌云健笔真实客观、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苦难的社会现实。但平心而论,始终沉沦下僚的杜甫既是历史事件的一个卓绝千古的记录者,其实又只是历史本身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旁观者而已,其悲愤的呼号丝毫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曹操则不同,他是“鞭挞宇内”的“超世之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论》),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且无可替代的角色,堪称历史精神的化身。我们知道,历史是残酷的,充满了合纵连横的阴谋、刀光剑影的血腥;历史是悲壮的,充满了沉浮不定的命运、成王败寇的法则;历史又是苍凉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正因为如此,历史使命承担者的情怀往往是悲悯的、深沉的。曹操的诗歌作品具有一种厚重、质朴、苍凉、悲怆而又深邃的精神气质以及如史诗般的深广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曹操诗歌的这种艺术特点也被后人认识到了,比如刘熙载就在其《艺概·诗概》中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5]P52而对曹操诗歌评价最高的学者当属方东树,他在《昭昧詹言》卷二中更将曹操推崇为“千古诗人第一之祖”。可以说,古直悲凉、缺乏丹采的曹操诗歌虽被《诗品》的作者钟嵘列为了下品,却最终未被时间长河湮灭,反而受到无数后人由衷的推崇,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1][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王国维.文学小言[A].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德]尼采.尼采全集(第 5 卷)快乐的知识[M].梵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4][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