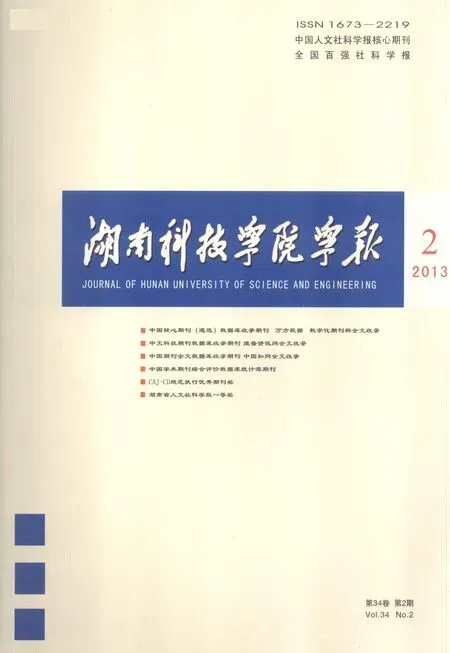哈斯宝对《红楼梦》“人情世态”主题的接受与阐释
2013-04-07胡明宝蒋艳柏
胡明宝 蒋艳柏
(1.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广西 桂林 541004;2.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4)
在《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史上,19世纪蒙古族杰出的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哈斯宝,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具体生卒年代目前尚不清楚。他自称“台吉”,属于蒙古族贵族阶层。他精通蒙汉两种文字,饱读汉文诗书典籍,博学多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多次慨叹“奸佞挡道”、“坎坷不遇”,以“隐没闲贤”自居,“是一个不得志的在野士绅”。[1]
哈斯宝的文学活动,据目前发现的文字资料推算,自1816年蒙译《今古奇观》,到1847年节译和评点《红楼梦》,长达30余年。他杰出的贡献是以我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将120回的《红楼梦》译成蒙古语,名为《新译红楼梦》(又称《小红楼梦》,共40回)。哈斯宝对曹雪芹的艺术才华赞赏备至。他说《红楼梦》“这部书的作者,文思之深有如大海之水,文章的微妙有如牛毛之细,络脉贯通,针线交织。”[2]21(以下只标注页码)他又云:“读此书,若探求文章的神灵微妙,便愈读愈得味,愈是入神。”[2]22哈斯宝自称是《红楼梦》“作者世后的知音”,他不仅节译了《红楼梦》,还为译著作批加评。哈斯宝的译、批都是用“古典蒙古语”写成的,文笔精炼优美,风格鲜明独特。除《新译红楼梦》外,哈斯宝还撰写了《序》《读法》和《总录》各一篇,《回批》40篇。这些都是哈斯宝文学翻译、小说批评与文学接受的代表作,也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翻译史、传播史、接受史与蒙汉文学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历来的接受者(评点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从脂砚斋到哈斯宝所生活的时代,这期间的评点家,或持大旨言情说,或持政治斗争说,或持盛衰说,或云隐演性理,或云宫闱秘史,或云发愤著书,等等,皆因评点者的人生经历、审美趣味、接受动机、期待视野不同而见仁见智、诸说纷呈。这种现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看,是十分寻常、不足为怪的。它恰恰显示了《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多义性与丰富性的特点,也说明接受者的任何一种理解诠释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哈斯宝对《红楼梦》的主题有其独特的认识与阐释,综观他的全部批评文字,我们将其梳理、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忠奸斗争说;二是人情世态说。关于忠奸斗争说笔者已有专文分析,本文仅就人情世态说做些梳理、评析。
一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世情小说”。世情小说,是指以描写世态人情——社会状况、人生百态、家庭生活、恋爱婚姻等为主,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世情,也就是世态人情。所谓世态,指的是整个现实社会状况、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和各阶层的众生相;所谓人情,包含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情感心理、理想、欲望、个性、意志等整个精神世界。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世情小说,是指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最早揭示《红楼梦》摹写世态人情、离合悲欢主题的是脂砚斋等人的评点,笔者已有专文探讨。于今,当我们梳理哈斯宝评点《红楼梦》的理论观点时,竟然发现哈斯宝也是一个与脂砚斋一样的“世态人情”论者。哈斯宝在揭示、阐释《红楼梦》忠奸、正邪、善恶矛盾斗争主题的同时,通过小说本文细读、情节分析、人物品评,发掘并诠释了《红楼梦》另一重要主旨:世态人情,即作者对宝黛真性情的赞美与讴歌、对人情冷暖、世态万象的关注。
哈斯宝始终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泄恨书愤”[2]22之作,其中“每个字都是抨击奸谄之徒的”。因此,他将批判的锋芒由贾府指向了其时的社会之恶与人生之丑。哈斯宝认为,《红楼梦》作者是“为世风堕落异常而悲号”。他指出“荣宁二府过失太多,已到了月亏水溢的地步”[2]87。又说《红楼梦》作者“写这部书,不仅写了人的性情,而且暗射了天时。看官请看,书中开始是暖,中间热,继而生凉,最后是寒,以天时比喻人的性情,怎会不写得淋漓尽致?”[2]28亦即《红楼梦》描写了人情冷暖、世态万象,揭示了“人的性情”的真假、社会与家族兴衰的命运。在哈斯宝看来,《红楼梦》中“人的性情”的主题的表现,既是与忠正、奸邪、善恶斗争的主题表现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又是各有侧重,各有所别,各有意蕴的。按照哈斯宝阐释的逻辑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其相互区别:当哈斯宝力图揭示《红楼梦》中忠奸正邪两大人物阵营的生死较量时,他是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俯瞰忠正与奸邪的搏杀,他着重表达的是对“残忍乖僻”的奸狡邪佞之徒人性中假恶丑本质的揭露、憎恶与抨击之情,对“清明灵秀”的忠正贤良之士人性中真善美品质的张扬、同情与赞美之情,以阐释贾府家族败落、封建社会衰亡的原因。当哈斯宝力图揭示宝黛爱情的发生、发展与毁灭的历程和红楼人生、爱情悲剧的原因时,他着重从人生、人性的角度洞释“神童慕才女,才女慕神童”的恋爱心理,以展示宝黛至真至纯的“人之本性”,诠释他们人生、爱情的理想及其追求,进而抒发对宝黛“千死万死也在所不辞”的纯洁无邪、坚贞不渝爱情的歌颂之情,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爱情理想。当然,哈斯宝的“写人的性情”,还包含了对形形色色人物的自然属性、个性、情感、品质的描写、褒贬,等等方面的内容,其所指较为宽泛。哈斯宝还强调,《红楼梦》“不仅写了人的性情,而且暗射了天时”,是“以天时比喻人的性情”。所谓“天时”似应指气候状况,即阴晴冷热的变化。“以天时比喻人的性情”,即是说作者用天气的阴晴冷暖变化比喻人的性情之真假冷热变换,意谓人的性情如同气候变化一样阴晴不定,冷热无常。
二
哈斯宝在《红楼梦》故事情节的设计和人物塑造的艺术世界里,发现了《红楼梦》写“人的性情”的主题,并对这一主题作了多方面的揭示与阐释。在哈斯宝看来,《红楼梦》关于“人的性情”主题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宝黛二人至真至纯的生死爱情及其超功利、超世俗的个性品质的刻画;通过封建末世中哪些沉迷于功名富贵与仕途、醉心于声色犬马与享乐、热衷于权势物欲与私利之徒的丑陋心理性格的描写和对红楼中人物人性真善美的赞美、对假恶丑的贬斥而实现的。故而,他在小说的环境透视、情节分析、人物品评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宝黛真挚纯真、生死不渝爱情、高尚品格、独立不移精神的礼赞与歌颂,对龌龊肮脏社会现实的愤恨与抨击,对奸诈、虚伪、丑陋之徒人格品行的暴露与针砭,进而揭示宝黛爱情悲剧、贾府家族衰亡悲剧的原因与审美价值。
首先,哈斯宝充分肯定了宝黛相互爱慕的知己之情,认为男女相互爱慕之情是人之本性,是人的正当、合理追求。在《红楼梦》作者的笔下,宝玉黛玉是“情痴、情种”,宝玉“情不情”,而又独钟黛玉;黛玉“情情”,坚贞不渝,挚爱宝玉,一往情深。哈斯宝在翻译“泪珠绢”一篇之后批道:“从此以后,我才相信宝玉是个神童,是个才子。从此以后,我才明白颦卿是才女,才认定她是佳人。……男大当婚,是先王所定之礼。神童慕才女,自是定理,但又敬慕先王,神童便可谓之才子。……才女慕神童,乃人之本性,但又敬畏古法,才女便可谓之佳人。……所以,才人爱佳人,若皆如宝玉之爱颦卿,佳人爱才子,若皆如颦卿之爱宝玉,即则使千死万死也在所不辞,只求把各死一方变成死在一处。将这等深广之章囊括在这篇简略之文中,岂非奇妙超绝。”[2]59哈斯宝所说的“礼”、“定理”的含义是什么呢?他引用哲人们的话作了诠释:“礼就是合理的事。”[2]88什么是“定理”呢?哈斯宝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并以此为喻,说“天将拂晓要昏暗一阵,火将灭时陡然旺起来,花木枯死的前一年必要盛开,病人垂危时要见好一时,这都是定理。”[2]88可见“定理”就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谓“男大当婚,是先王所定之礼”,指的是男女婚嫁是古先王定下的合理的规矩。童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之情是人的本性,是符合先王所定规矩的。在哈斯宝看来,宝黛这对神童才女、佳人才子的相互爱慕,是“人之本性”,是天经地义、符合先王定礼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这里,哈斯宝从人的自然属性、人之本性、先王定礼、事务发展定理等多角度充分肯定了宝黛爱情的合理性、必然性。虽然,哈斯宝为宝黛相互爱慕的自由爱情辩护时拉出了先王的大旗,未免有点迂腐,但还是坚定地表明了他对宝黛自由恋爱的赞同、对互相爱慕的知己恋情的肯定。这表明,他的爱情观与明清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所主张的“情理”观是一脉相承的。其可贵之处在于敢于理直气壮地认同“神童慕才女”、“才女慕神童”的爱情的合理性、正义性,这无疑是对封建爱情婚姻观念和宋明理学的有力反叛。
其次,哈斯宝十分赞赏宝黛真诚相知的爱情,热情地讴歌了宝黛至真至美的爱情。在《红楼梦》作者的笔下,宝玉之处处留心、钟情于黛玉,缘于宝玉对美的崇拜与执着,缘于他与黛玉心灵的相契、生死与共的挚爱。对宝玉黛玉而言,志趣相投的知己之爱,是生死相依、无法拆分的。故宝玉对于黛玉,深恨有男女之隔,不能朝夕共处、促膝并坐。哈斯宝评道:
宝玉爱潇湘,出于真诚,而潇湘总思量宝玉是否知道我对他爱之已极。潇湘爱宝玉,也出自真诚,而宝玉总思量潇湘是否知道我对她爱之己极。此语不逢出自宝玉之口,送入潇湘耳中的机会,犹如不逢出自潇湘之口,送入宝玉耳中的机会。如此则二人互不相知。爱之己极而互不相知,呵,还不如双双死去的好!亏得事有因,话有机,去看一对金麒麟,因为提到“金玉姻缘”,宝玉发急说了句“你放心”,黛玉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只有此时,潇湘才知道宝玉对己爱之已极。宝玉早己知道黛玉爱己已极,依他想来:你我相爱相知,心是一个。心一个,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我虽是一体,奈何身居两处!……你我心虽一个,却至终不能合在一起,这样活着勿宁死了的好!唉!又奈何死也不能在一起,现在只好面对而泣——这是何等的苦,何等的悲哀![2]83
宝黛这对神童才女知己的真诚之爱,并非世俗才子佳人之间的色相吸引,而是闺阁挚友灵犀相通、心心相印、性情志趣的契合。对于痴情、重情的宝黛而言,彼此一心,你我一体,互为对方唯一的知己、精神的家园、情感的寄托。因此,当无奈而不幸失去对方时,便觉得整个人生的意义与一切荡然无存,黛玉绝望而焚诗稿,宝玉则丧魂失魄,遁入空门。然而,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虽心为一体,却身居两处,“奈何死也不能在一起”,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与死后也不能结合的悲哀,又有谁能理会!对此,哈斯宝表达了无比的愤恨与同情。
在哈斯宝看来,宝玉与黛玉虽有潘安西子之貌,但他们迥异于此前文学作品中的才子佳人。哈斯宝在第十七回的回评中提到“上回中刘姥姥进潇湘馆,误说‘这必定是哪位哥儿的书房’,这一回误入怡红院,又说‘这是哪位小姐的绣房?’”[2]69他借刘姥姥对两玉住处环境、饰物的判断,以说明两玉的性情、气质不同于通常的“才子佳人”。他还说,“这个林黛玉,真是一位绝代佳人。”通常所说的佳人,无非是文君、莺莺之流,“她们首先就失去妇节,还算得上什么佳人。”在这里哈斯宝贬斥卓文君和崔莺莺,主要着眼点是她们的暗约私奔或偷香窃玉。在哈斯宝看来,这不过是“红粉女儿不安闺阁,寄情于路边蓬篙,置意于柳枝莺啼,恨春怨秋”[2]112怀春伤情的表现,是一种庸俗低级的追求,毫无真爱可言。哈斯宝认为,宝黛之间感情的可贵、感人之处,在于表现了男女知己间纯真无邪的爱情。“如今在花丛岩石之萌,湖水墙角之间,寂寥静悄之日,幽深无人之地,郎如潘安,女若西子,携手相会,谁人能说不致两朵鲜花开粉腮,三道浓霭落鸟云?可是严辞突然出口,邪行概未发生,呵,这全是何人之力?”[2]46“郎如潘安”的宝玉,“女若西子”的黛玉,“虽然也携手相会”,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已打破了世俗男女淫游私会的俗套。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纯洁无邪的心灵、至真至美的情操、一往情深的感情驱动力,因为彼此共同的爱情理想和反叛传统思想的力量。哈斯宝坚信“痴情”是宝黛情感表现的共同特征,是黛玉对红颜知己的爱情追求,也是宝玉对爱情的理想和希冀。对此,哈斯宝与宝黛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于是,便给予热情的讴歌与赞美。
第三,哈斯宝对宝黛人生追求、人生道路选择的肯定与钦羡。哈斯宝将《红楼梦》中各色人物的人生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分为两大类型。以贾母、王夫人、贾政、王熙凤、薛宝钗、袭人等为代表的是一种类型,他们是封建制度秩序、封建道德伦理的维护者、践行者,是功名利禄,仕途经济,富贵荣耀的追逐者。以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雨村之流为代表的是又一种类型,他们是醉生梦死、骄奢淫逸、贪婪无厌之徒,是权势、私利、物质的攫取者、道德伦理的破坏者。宝玉、黛玉、妙玉、晴雯等“清明灵秀”之人,他们的人生追求,既不是功名利禄,仕途经济,也不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而是迥异于上述两类人物的另途。这样哈斯宝就把宝黛的人生追求、人生道路的选择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那么,宝黛选择的究竟是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呢?哈斯宝以宝黛为自己心仪的偶像、人生的典范,我们只要看看哈斯宝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就可以明了宝黛的人生理想与人生道路的抉择。
哈斯宝十分厌恶“在众人面前炫耀德行,显赫一时,侍从载道,入仕为国家操劳,喜则慨颁赏赉,怒则刑罚加人”的人生道路,心驰神往的是“案上摆列墨砚,两边堆起笔纸,有兴则信手赋诗,厌倦则翻阅典籍,口诵心怡”[2]20的人生之路。他羡慕、向往超脱尘世,悟道参禅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贾宝玉最后人生的归宿。由此可见,哈斯宝为宝玉所规定的人生追求、人生道路的特定范围,不仅与他本人的人生道路,人生追求有相似之处,而且从中看不到与贾府家长们对宝玉的要求有钉点相同之处。宝玉不爱读书,尤其厌恶读四书五经;拒斥科举功名、仕途经济;不喜欢结交为官做宰的达官贵族,喜欢在内帏厮混;不论尊卑贫富,喜交三教九流,呵护体贴下人;自由恋爱,情钟黛玉;常吟诗作赋,喜看“淫词小说”;参禅悟道,等等,不胜枚举。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类似宝玉的人生实属罕见。所以,宝玉的行为举止被世俗之人视为“性情怪僻”、“愚顽”、“不肖”、“傻狂”、“痴呆”;被乃母王夫人视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其父贾政则以“酒色之徒”、“淫魔色鬼”看待。那么黛玉呢?在当时的社会里,像黛玉式的豪门闺秀、贵族千金,除了针黹女红之外,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但黛玉这个琼楼绣阁的“才女”却冲破了封建社会的闺阁的藩篱,大胆地选择了“吟诗弄赋”的读书人生活,她读“淫词艳曲”、葬花、弹琴,她与宝玉谈情说爱,且爱得死去活来。哈斯宝说:“潇湘临终的言语情态,即使铁石心肠的汉子也要为之神伤心碎。明窗净几,时而翻阅古今,时而吟诗弄赋,这不是读书人的行止么?为何又生此缠绵之意?深闺绣楼,或持针绣花,或执笔绘画,这不是红粉之业么?为何又生此伤感之情?”[2]112封建时代的女子居然特立独行的选择了读书人的生活方式,竟然常有“缠绵之意”,常生“伤感之情”,这在封建专制家长眼里分明就是大逆不道,世俗社会看来就是“性情怪僻”之举。显然,宝黛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封建家长的规定、期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据此,我们从二玉的人生道路的抉择上,看到了他们闪光的人格气质和人生理想,从哈斯宝对二玉叛逆思想行为推崇赞赏的情感倾向中,我们不难看出宝黛与哈斯宝对待人生、科举仕宦的态度何其相似!二玉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又恰恰是哈斯宝所选择的或实际所走的人生道路的写照,而这些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忍的“怪僻”、叛逆的行为,因此,二玉注定无法逃脱人生、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
第四,哈斯宝对两玉藐视封建伦理纲常“怪僻”言行的赞赏。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种种清规戒律,诸如“三纲五常”、“忠孝节悌”、“三从四德”、“忠烈名节”、“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赖以束缚、禁锢人们思想灵魂的枷锁。宝玉黛玉遵了那一“纲”,守了那一“常”,又何尝顺“从”过封建主子们的要求呢?对此哈斯宝有些矛盾、困惑、迷茫,所以,他只能用“怪僻”来诠释宝黛那些在封建家长看来离经叛道的“怪僻”行为。他说:
早就写出了一个性情怪僻的宝玉,已是怪僻之极。接着又写出了一个性情怪僻的黛玉,更是怪僻之极。这两玉心情不同,性情也不同,写了一个性情怪僻的宝玉,又写了一个性情怪僻的黛玉,已经是奇,都又慢慢研墨蘸笔,还写出了一个性情绝怪的妙玉,这一玉的心情、性情又与那两玉不同。[2]68
所谓“怪僻”即是反常、叛逆,不合正统、道统,不走正道。尽管哈斯宝内心深处认同儒家的纲常伦理,但他从宝黛反常、叛逆的种种思想行为中洞察到了他们与封建正统思想观念、尤其是假道学的格格不入、无法化解调和的激烈矛盾冲突,并通过宝黛“怪僻”的思想行为、人生追求与爱情理想等方面的分析,讴歌了宝黛叛逆的爱情,揭示了宝黛人生与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及其审美价值。
“哈斯宝的难能可贵处,在于他很是明确地指出了自己所推崇的宝黛爱情,与自己所推崇的孔孟学说之间矛盾的无法调和性。”[3]250“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你我在此不能任性,上无父母之命,下无媒妁之言,使得你我不能处在一起!你我心虽一个,却至终不能合在一起,这样活着勿宁死了的好!唉!又奈何死也不能在一起,现在只好面对而泣,这是何等的苦,何等的悲哀!才子佳人这副苦衷肠岂是淫夫荡妇能理会的!”“寄语锦绣才子诸公:诸君是否理会得这片苦衷肠?理会得的,我愿同他一起看这书,抄这书,评这书,议这书。若不理会,我就把书藏诸名山,引吭高歌,痛哭一通!”[2]83-84哈斯宝这段情理交融的批语,可谓一语中的。《红楼梦》中宝黛缠绵悱恻的爱情,自始至终伴随着泪水与痛苦。黛玉终年“眼空蓄泪泪空垂”,“抛珠滚玉只偷潸”,身陷“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境。这除了封建家长的严密的监控、无情的扼杀外,“情痴、情种”而又性情“怪僻”的宝黛,始终未能冲破孔孟学说的封建樊篱,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在那个时代,孟子的“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要恪守孔孟的圣条,宝黛绝无随心所欲、痛快淋漓地相亲相爱的自由。“可见,悲剧不仅来自环境,也来自相爱者的不能超越环境。哈斯宝还将这由孟子所言造成的,男女相爱却不能自由交往的痛苦,视为理解《红楼梦》故事的关键。”[4]251这就告诉我们,社会环境、人情世故、意识形态等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共犯”。
第五,哈斯宝认为《红楼梦》作者是“为世风堕落异常而悲号”,作者生动的描写了忠奸斗争、展示了龌龊社会环境中的世态百相和人情的冷暖炎凉。因此,他将二玉爱情的毁灭归因于黑暗腐朽社会的窒息与奸佞之徒的设计迫害,并将二玉爱情悲剧、人生悲剧、封建家族衰亡的悲剧同整个社会的悲剧紧密联系起来,所以他忠实地全译了《红楼梦》第四回,并将这一回作为全书故事发展的重要关节加以细察详评。在哈斯宝看来,“应天府”案对展开荣国府的兴衰史和金陵十二钗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来说是“一笔点睛”。“将薛家引入荣国府,不能没有这桩人命案。把英莲列入十二钗芳群,不能没有这起因缘。人命案起,因缘便结下了,一索两获,非常之妙。”[2]35哈斯宝所谓“一索两获,非常之妙”,既是指小说的艺术手法与艺术效果,也是指作者通过“应天府”案所展示的现实环境与世态人情,也是指导致红楼悲剧、社会悲剧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正是全书主题的点睛之笔。
哈斯宝还认为《红楼梦》故事框架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全书人物可分成正与邪两大阵营,整个故事就是在正与邪较量的历史过程中演绎终结的。在波澜起伏、峰回路转的各个阶段,正与邪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真与假、冷与热、虚与实、宾与主、阴与阳、喜与悲的激荡与冲撞,并且往往虚假掩盖真实、邪恶占据主导。因此,他认为,他的《新译红楼梦》“全四十回大纲便是真假二字。真,内热外冷;假,外热内冷。故开头都是冷,无一丝热处。后来贾家父子诸兄弟一出场,便写得炽热,一点冷也没有了。但是假的终究不长远,最后一旦返冷,便落得个破殴碎罐一般。”[2]28哈斯宝将真假冷热描写作为他译著的“大纲”,就是告诉读者,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冷暖、人性之真假是变幻莫测的,到头来都难逃悲剧的结局。这表明,哈斯宝不仅认识到了真假、冷热矛盾的双方互为对立统一,互相依存,有假才有真,有真才有假;还领悟到了在一定条件下,这相互对立的双方可以转化。真可以变假,假可以变真;热可以变冷,冷可以变热。哈斯宝在节译原著第87回之后,分析道:
此番潇湘馆景色何等凄凉。当初入园时,贾母重重钟爱,宝玉之情深上加深,姊妹之间谈笑欢乐,热闹非凡。而今老妖婆突然变卦,知心者廖廖,姊妹畸零,欢笑掩声,不堪回首。此时依门只有雪雁侧立,卧床只有紫鹃啼泣,暮闻栊翠庵钟声,晨听稻香村鸡鸣,凄凉之极,因何所致?我明白了。热极生凉,生凉则终有极寒。而今元、迎二春已去,春将终了,花谢莺啼,已到蝶去絮飞之时,还哪里去寻红火热闹?天时如此,何况人情。[2]97-98
他用辩证的观点剖析社会与贾府,洞释环境与人生,“热极生凉,生凉则终有极寒。”而今贾府“春将终了,花谢莺啼,已到蝶去絮飞之时”,衰败已是无可挽回了。更为糟糕的是在大势将去之时,整个贾府人情也像天时变化一样反复无常,真假难辨,阴阳颠倒,处在这种凄凉环境之中的黛玉“知心者廖廖,姊妹畸零,欢笑掩声,不堪回首”,必将“花落人亡”。哈斯宝进一步指出:“荣宁两公的子孙得为者不为,不得为者为之已甚,以至祠堂中发出叹息声,呵,这是何等可怖!”[2]88他认为贾府衰败的主要原因都是荣宁二府那些不肖子孙“闲居时专务不良无所不至之故”,[2]119“欲业使人迷于财色”,财色使人腐化堕落,腐化堕落导致大厦坍塌。哈斯宝指出:
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富贵是热,热则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贫贱是冷,冷则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不唯热冷二字可将真假颠倒到如此地步,且那热冷本身亦是无定的。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之真便成假,明日之假便成真。今日热而明日冷,则今日之真全是明日之假。咳,自来是欲业使人迷于财色,由财色生冷热,冷热搅乱真假。……所以一展卷便论真假,结尾又讲冷热。[2]134
因为欲壑难填、穷奢极欲的恣意攫取,导致统治阶级、封建大家庭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沦丧;因为令热无常、人情翻覆、真假颠倒,“假作真时真亦假”,从而造成封建末世乱象丛生、世风日下、社会衰败,以致灭亡。哈斯宝还说“天将拂晓,要昏暗一阵,火将灭时,陡然又旺起来,花木枯死的前一年,必然要盛开,病人垂危时要见好一些,这都是定理”,“衰极盛之兆,盛极衰之征”[2]86。据此,他认为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极盛,不过是衰亡前的回光返照,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最后必定要一败涂地。在哈斯宝看来,正是由于《红楼梦》中的各种矛盾的对立及其转化,才使情节波澜起伏,内蕴博大精深,而不像其他才子佳人小说那样一览无余。哈斯宝思想的光芒是对丑恶现实、炎凉世态、冷暖人情做了无情地批判,他在诅咒抨击这一切的同时,真诚讴歌他心目中的真善美。“哈斯宝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去俯瞰贾府的矛盾,使他的评论闪耀出哲学思想的光辉。”[4]
三
哈斯宝忧愤著书,欲“以墨水洗恨,以笔剑报仇”。他的译著与评点,融汇了满腔热情和爱憎分明的褒贬。哈斯宝对“人情世态”主题的接受与阐释,是其人生的艺术体悟;是其与《红楼梦》作者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是一位睿智的蒙古族思想家、卓越的小说批评家思想理论光华的折射。他的评点,作为一种审美接受与阐释活动,其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紧紧围绕小说中的相关情节、人物心理性格的精辟分析而透视险恶浑浊的现实、冷暖炎凉的人情世态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心理,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在他精彩、独特的《红楼梦》人物评论与阐释中,寄寓了他的社会理想和美好的人生诉求,鲜明地表达了他与《红楼梦》作者对真善美的真诚赞颂、对假恶丑的无情抨击与拒斥的鲜明情感倾向。毫无疑问,哈斯宝的世界观、审美观与《红楼梦》作者的世界观、审美观是有一定距离的;《红楼梦》与《小红楼梦》的艺术境界、艺术魅力无疑也是各有千秋、不可等量齐观的。然而,哈斯宝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独特的人生感悟融入到《红楼梦》的审美接受与阐释中,找到了只有他才能找到的东西,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东西。他通过翻译、评点成就了他的“另一部《红楼梦》”。“他对作品主题的把握与诠释,是他自身灵魂的写照和心路历程,是他所独具的对世界、人生存在方式的一种精神照亮和持存,一种审美掌握和艺术占有,是主体生命丰盈中的一种外在投射,一种人格力量的自我确证,一种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叠印认同。”[5]368-369虽然,哈斯宝对《红楼梦》之“人情世态”主题的诠释,有着进步思想与封建陈腐观念杂然并呈的矛盾,但他发扬了汉民族小说评点的传统,光大了蒙古族的审美理念与审美标准,彰显了本民族的特色和自己的个性。“他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点所做的分析,有许多是触到了问题的本质,也有不少自己的独特见解,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6]
[1]哈斯宝(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和他的译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2]哈斯宝(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3]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
[4]席永杰.论曹雪芹的后世知音哈斯宝[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8-12.
[5]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申晓亭.试评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1):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