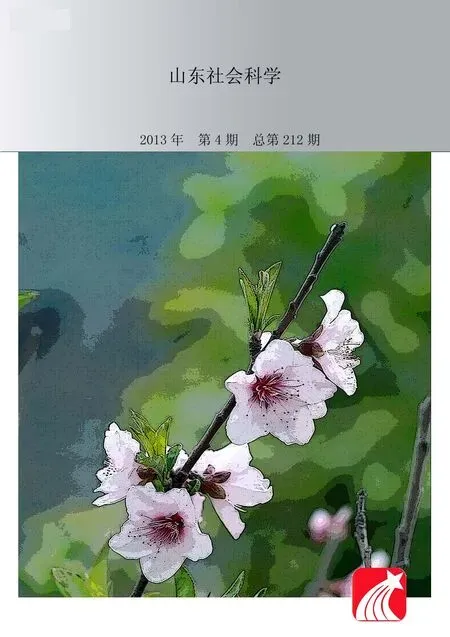南大德文专业的风流云散
——以若干人物为中心
2013-04-07叶隽
叶 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1950年代:南大德文专业的精英荟萃
1952年,借助院系调整的大势所趋,南京大学的德文学科似乎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天时地利”。于是乎,还仅是1947年建起德文学科的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央大学),一下子坐拥南方各主要大学的德文精英人物,一时间群贤毕至、荟萃英华。或许原有的学科底气多少决定了其发展的可能,令人遗憾的是,南大德文专业的合并式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昙花一现”的宿命。作为当事者的张威廉这样回忆道:
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卢姆,真可说是人材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1823年出版的《席勒全集》。①《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载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的外国语文系仅设俄文、英文两组。俄文组即原复旦大学外国语文系俄文组;英文组由复旦大学外国语文系英文组及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三校的外国语文系合组而成。可参见《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教育部档案1952年长期卷,卷14。转引自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这位布卢姆是一位德国女士,即朱白兰(德语原名KlaraBlum,拼音为DshuBailan,1904—1971)。1949年她重回北京,1952年担任复旦大学德语文学教授,同年9月转到南京大学任德文专业教授。关于朱白兰,可参见夏瑞春:《永远的陌生者——克拉拉·布鲁姆和她的中国遗作》,载印芝虹等主编:《中德文化对话》第1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0页。
以上诸君,再加上南大德文专业本来已有的商承祖、张威廉等人,真的是可谓“人才济济”,与北大德文专业相比,也是未遑多让(其时北大德文专业的领军人物为冯至,另有杨业治、田德望、严宝瑜等人)。就当时的德文学科格局来说,南北大学倒真的是名副其实,如果将专以外语语言教学为务、集中全力于培养实用性外语人才的北外排斥在外的话,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对峙,倒恰是形成学术性的德文学科的基本格局,这也符合中国现代学术史传统里的“南北对峙”②早在1917年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当其履新之初开始轰轰烈烈的北大改革之际,东南大学(南高师)就有与北大分庭抗礼的意味。而相对胡适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吴宓等在南方以东南大学为基地主张文化保守,虽然寂寞,但对文化史发展的意义来说却并不逊色。。这样一种状态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外国文学研究所。①这样说,主要是以德语文学研究为取舍的标志。就德语教学来看,到了1956年时,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分别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开始增设德语专业(与英语、法语同时);1954年成立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0年成立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都在外贸外语系下设有德语专业;1964年10月制定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大量增加英语学习人数、要适当增加法、西、阿(拉伯)、日、德语的人数。参见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4、77页。这些学院显然主要以培养实用性的德语人才为主,德语文学研究的学者当然也就仍主要集中在北大、南大这两所综合性大学。实事求是地说,这样一种借助政治权力运作而形成的“数花独放”,其实并不一定符合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事实上,同济、复旦、清华等校德文学科的消逝,也确实未曾换来南大、北大德文学科的“辉煌鼎盛”。按照张威廉的话来说,从人才鼎盛到“风流云散”,也不过十年间事耳。为什么竟会是这样的呢?
初时的制度设计并未调整,仍是德文组,只不过先由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德文组组成;同年,同济大学德语组亦并入。外来德文教师包括:陈铨、廖尚果、陈一荻、朱白兰、焦华甫等。这种叙述与张威廉的回忆是基本一致的。1955年,德国语言文学教研组成立。1956年,民主德国葛来福教授任教于德文专业;9月,高教部下通知,德、法、英、俄四专业从1956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改为五年制;实际上德、法二专业自1957年起入学新生方改为五年制;1956年德国文学方向招收研究生,导师为商承祖、陈铨、葛来福,学生为吴永年;1956—1957年德文组师资共11 人,学生77 人。②参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史纪事》,2002年。1957年,杨武能考入南大外文系,进入德文专业就读,他给我们留下了自己如何由学俄语而转为学德语、由重庆而南京的求学历程:“由于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不幸破裂,搞俄语的人在1957年突然多了,我不得不放弃俄语改学德语。于是离开故乡的俄文专科学校,从山城重庆顺江而下,千里迢迢地到了虎踞龙盘的石头城中,就读于南京大学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然而因祸得福,南大德语专业不仅素有做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传统,而且教我们的是商承祖、张威廉、叶逢植等一些当时在全国出类拔萃的学者、专家。从二年级开始,老师已陆续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文学名著,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正是大诗人歌德的一些代表作……”③《自序》,载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应该说,此期的南大德文专业师资的精英荟萃在学生眼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而且反之也确实在学生培养上得到一定的体现。至少,能够培养出杨武能这样的学生,就是一种证明,虽然其日后成就至少要提及其在社科院外文所师从冯至读研究生这一学术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1950年代末期作为本科生就已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译作④《自序》,载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当然,值得深入追问的,自然还是主事者的思路与策略。
二、作为主事者的商承祖与张威廉
就南大德文专业来说,商承祖(1899—1975,亦用名章孙)与张威廉(1902—2004)无疑是可以负起责任的人。⑤关于商承祖,参见叶隽:《出入高下穷烟霏——追念商承祖先生》,《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17 日;叶隽:《文章犹在未尽才——日耳曼学者商承祖的遗憾》,《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 日。关于其父商衍鎏,参见叶隽:《有时空望孤云高——念商衍鎏先生》,《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20 日;柏桦:《商衍鎏与德国汉学》,见http://www.chinulture.cn/forum-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951.html,下载于2011年3月10 日。关于张威廉,参见叶隽:《先生百龄,乘风而去》,《读书》2005年第2期;叶隽:《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因为在范存忠之后,商承祖曾长期担任南大外文系主任;而张威廉则是德语教研室主任。
这种制度性变化,是在1954年开始实行的。当时将德文组一分为二,即德国语言教研室(主任张威廉)、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陈铨)。德文专业课程与英、法、俄各专业一样设置为四类:1.政治理论;2.对象国文学语言技术训练;3.对象国文学语言理论;4.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汉语(重点是现代文学史和写作实习)。⑥参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史纪事》,2002年;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显然,在南大德文学科的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首推商承祖。作为现代早期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商氏家族与德国渊源颇深⑦也可以说商氏世家与福氏世家(福兰阁、傅吾康父子)都可算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家族,当然还可以加上卫氏世家(卫礼贤、卫德明父子)。商家的第三代,即商承祖长子商志馨(1923—1971)1953年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改名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德文编辑;女儿商志秀在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任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贸学院)德语教授,也都和德国有关。,而商承祖更是借得东风之便,能有少年留德之可能⑧按照其弟商承祚的记录:“1912年德国汉堡大学派员来华为该校东亚系招聘汉文教师,我父鉴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很乱,决定应聘出国,并携长兄承祖、二堂兄承谦去读中学。”参见商承祚:《我父商衍鎏先生传略》,载《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编:《商衍鎏、商承祚书正气歌》,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该书未标页码。,从此结下与德国的不解之缘。从13 岁留德到弱冠前后再归国,再到旋即就学北大新设的德国文学系,商承祖的德国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作为北大德文系开创者的德国学者欧尔克曾毫不吝惜地称赞商承祖是最好的学生,①Oehlke,W.:In Ostasien und Nordamerika als deutscher Professor:Reisebericht(1920-1926)(在东亚与北美做德国教授:旅行报告(1920-1926)).Darmstadt & Leipzig:E.Hofmann,1927.S.38.而商承祖显然也受乃师影响颇深,对莱辛、克莱斯特都颇有兴趣。商承祖可谓是早期具备跨学科条件的学者,因为他先后跨越了民族学、汉学、日耳曼学等多个学科,早年随父赴德时不过10 多岁的少年而已,自然打下了非常好的德语口语基础;日后入北大德文系,果然皎皎然不群于众。大概是在1930年代他再度赴德,在汉堡大学留学(1931—1933年注册),以《中国“巫”史研究》(Schang,Tschengtsu: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eine-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chen“wu”.Hamburg:o.V.Diss.phil.Hamburg,1934)的博士论文获民族学(Völkerkunde)博士学位。②参见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von1860 bis 1945(中国留德学生——1860 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Hamburg: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1999,S.468.但商与汉学关系也非浅,不仅是指他曾同时在汉堡大学任汉语讲师(LektorfürChinesisch),而是其论文也同时接受了汉学教授的指导,如他在论文后记中致谢的Jäger 与Forke,都是德国著名汉学家。③商承祖还曾与汉学家一起合作做人类学调查。1928年夏,他和严复礼到广西进行少数民族研究,在凌云县北部六个瑶族村寨考察一个月,翌年发表了《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他还曾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参见颜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1月;章学清、张佑中:《著名德国语言文学家商承祖教授》,见http://www.poetic.com.cn/go.asp?id=15841&ttt=,下载于2006年1月23 日。以这样的学术背景出长德文学科,自然易于开辟道路、有所规划。但遗憾的是,在很长时期之内,商承祖都是在中央大学教授公共德语。
张威廉1933年应陆军大学之聘教德语,陆大课多乃邀北大同学、时任教于中央大学的商承祖兼课;抗战爆发后,陆大、中大均内迁重庆,商承祖请张威廉兼课于中大。当时德语都是公共外语,时间约是1943年。由于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1903—1987)的战略思路,乃于1947年时建设了德语专业。按照张威廉的说法:“这个人很有眼光,要把德语作为一个专业搞起来。当时德文做公共课已讲了很长时间了。”④叶隽:《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范存忠这样阐述其担任学术行政职务间的作为:“从1931年回国起至1949年解放前夕为止,我一直在原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这期间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动乱时期,但中央大学文科各系科仍保持了相当的规模。我不搞宗派,因此,在任职期间,我主张兼容并包,从各方面罗致人才。当然,由于见识有限,也难免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⑤范存忠:《我的自述》,解楚兰记录整理,载王守仁、侯焕镠编:《雪林樵夫论中西——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所以,从总体来说,南大德文学科是在外国文学学科群的整体规划下建设起来的,范存忠是总设计师,而商承祖与张威廉是开辟者,也是同事,在学术组织和管理方面,前者的分量更重些。有论者在描述南大德文专业1952年合并后的盛况后,突出强调了系主任商承祖的功用:
……随着以后的各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就风流云散,盛况不再了。在此条件下,商先生认识到:培养年轻教师,使之迅速成长,已是当务之急。他就制订了一套翔实的科研计划:每周要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每位教师(包括他本人) 要选定一个题目(作家评论或作品分析) ,在认真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写出心得体会,在讨论会上宣读,听取意见后再整理成文。这对于年轻教师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迅速提高水平的措施。他还要求年轻教师根据各人的兴趣和特长开设选修课,如修辞学、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语言史、文学专题选读等。这一措施大大调动了年轻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特长,使得他们得以迅速成长。⑥章学清、张佑中:《著名德国语言文学家商承祖教授》,参见http://www.poetic.com.cn/go.asp?id=15841&ttt=,下载于2006年1月23日。但具体到德文专业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材料挖掘以及复杂的历史现场还原后才能深入推究分析。
从这段叙述来看,商承祖对学科发展是有一定意识的,他甚至试图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建设,譬如每周学术讨论会的设想。课程设置与教员兴趣的相结合,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而且既立足于实际工作之需要,同时也能将教师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更重要的是,可以迅速使之进入学术研究的状态和窥得学术门径。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主持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学术积养和高水准眼光。应该说,就教师培养来说,这种培养是有效果的,尤其是他自己课程的后续性方面,“对于他所亲自讲授的文学史和文学选读课,他也挑选了两位年轻教师给他们开小灶来精心培养,使他们能够接替他,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搞好整个外文系的工作。他是倾心竭力、手把手地扶助这两位年轻教师成长的:教材由他亲自打字后付印;参考资料由他首先阅读后用红笔将重点处划出;讲稿由年轻教师写成后由他亲自审阅;上课时他坐在后排听讲,课后由他提出修改意见后再由年轻教师整理成文。经过了这样几道关卡,他才放心地向年轻教师交班。”①章学清、张佑中:《著名德国语言文学家商承祖教授》,参见http://www.poetic.com.cn/go.asp?id=15841&ttt=,下载于2006年1月23日。应该说,这样一种师资传帮带的效果是不错的,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学者的杨武能如此回忆自己在南大德文专业老师引领下走近歌德的历程:“是啊,我永远忘不了在老师们带领下读歌德的情景:《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尽管在课堂上只能学几个片段,但却读了《五月之歌》、《漫游者的夜歌》、《普罗米修斯》和《神性》等为数不少的抒情诗,而且读得十分地专注、痴迷。跟敢于用自己的灵魂和魔鬼打赌的老博士浮士德一样,跟多愁善感、狂放不羁的维特一样,英雄的普罗米修斯也深深打动了我……诸如此类既铿锵有力而又洋溢着人道精神的诗句,都难以磨灭地铭刻在我心中,鼓舞着我在困顿重重的人生之路上前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②《自序》,载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应该说,此期的学生培养,也正是在商承祖的整体学科发展思路下而展开的,因为师资水平的提升就必然会带动学生质量之提高;而学生之桃李满天下,则反之又会提升学校和学科的声名。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我们更关心的,则还是学科史本身的问题,为什么1952年院系调整带来的群英荟萃的效应没有足够显现出来呢?
三、廖青主与陈铨的命运
祝彦(1926—)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说过,廖青主(廖尚果)与陈铨乃是南大的名教授。③祝彦教授给叶隽的信,时间不详,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祝彦简历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77268.htm,下载于2012年8月10日。可见,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廖青主、陈铨可谓是名声遐迩。南大有这样的名学者,应是一个学科和一个学校的骄傲,但遗憾的是,当他们从外校合并而来之际,德文学科似乎并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作用。
那么,我们关心的当然是,如果说陈铨因了政治因素而不得不“忍气吞声”,那么廖青主究竟是为什么要离开校园?1957年,廖青主向南大校方提出要求提前退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南京大学与系主任个人相处得不愉快有关”④廖乃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如此,南大德文学科于1950年代风流云散的学术史问题,可以浮出水面。当初访张威廉先生时,就觉得他对这段事情“语焉不详”,似乎不愿多说;⑤2004年我采访张威廉先生时,他曾约略提及南大外文系当时复杂的人事与社会背景,但基本属于语焉不详。本指望日后再有机会重访继续沟通,可惜的是张先生于当年即魂归道山,这段学术史看来很难通过当事人进行了解了。而日后尝试访问商氏之女商志秀(1928—),则又被回避。看来,作为1950年代南大外文系德语学科当事人的商承祖、张威廉、廖青主、陈铨等,都是不能忽略的关键人物。试图深入追问这一问题,乃是探讨学科史研究的必有之意。
廖青主(1893—1959)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修养也非常好,应是学科史值得关注的学者。在留意音乐之外,青主对德国精神文化也甚有修养,留学德国10年间,除顺利完成学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外,也大量涉猎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莱辛、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其中对海涅更是情有独钟,非常喜好。他对海涅的作品信手拈来:“Heine 说得好:我有一种极和平的意志。我的愿望是:‘……窗外有花,门外有树,如果天帝更要使我幸福不过,那末他应该使我得到这样的欢喜:把六个至七个我的敌人,吊死在这些大树底下。那时我便要把我的敌人生时对我所造的各种罪恶宽恕——是的,我们要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在还未曾把他们吊死之前,我们是不能够把他们宽恕。’——我并非要曲解前人的话,我现在只就Beethoven 来说,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敌人,不是要把他们吊死了之后,才把他们宽恕,那么,先前那一度惨烈不过的战争,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么?——Madame!外面又起了一片惨杀的枪声,全酒店里面的人们,都惊惶起来,但是,我们是用不着惊惶的,我们保留着我们的思想和爱。”⑥青主:《诗琴响了》(1930年),转引自廖乃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乐学院2008年版,第25页。其实何止如此,青主对德语语言学、文学都有相当深的研究和造诣,不乏洞烛之见:
Ein jeder kehrt vor seiner Tür!
这是Goethe 的一句话:每一个人要打扫他的门前。就表明上看来,好像和我们中国那句俗话:各人自扫门前雪,除了少一个雪字之外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意思是并不一样的,在德文是说各人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文是劝别人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
Die Haare stiegen ihmzu Berge 或Seine Haare richteten sich empor,或seine Haare standen zu Berge。
译成中文:他的头发竖立如山,或竖立起来。谁不想起我们中国怒发冲冠那句话呢? 但是它的意思并不一样,在德文是由于恐怖,在中文是由于愤怒,头发竖立起来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
由于上面举的那两句例句,我们可以见得:凡学习德文的字句都要探本穷源,决不宜只在字面上做工夫,即是说:我们要彻底明白它的意思。文字是用来表现人们的思想的,但是德国人拿文字表现思想的方式,往往是和中国人不同的,所以我们学习德文,要了解德国人用来表达他们思想的方式,决不可以拿我们中国人表现思想的方式来解释德文。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但是这并不是说:德国人表现思想的方式处处和中国人不同。有许多地方,他们和我们表现思想的方式是相同的,我们就拿头发来说吧!中国有“千钧一发”这个词,苏东坡论张子房,亦有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这样拿一根头发表示危险的程度,在德文亦是有的,比方说:
Sein Leben hing an einem Haar。
他的生命只系在一根头发之上。
Er hat mehr Schulden als Haare auf dem Kopf。
他的负债比头上的发还要多。
(这) 是用来象征众多的。如果用来象征稀少,亦可拿一根头发来做比喻: Ihm wurde kein H? rchen gekrümmt。没有弯曲到他的头发,亦即是中国话:没有动到他一根头发的意思。
我们学习德文,脑子里不要存有成见。中文和德文相同的表现思想的方面固然是很多,但是遇着不相同的地方,总不是强不同以为同,那便对了,根据这个理解,来学习德文的成语句,大约不会有什么错误了。①青主遗稿,转引自廖乃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153页。
如此不惜长篇引用,乃是为了说明廖青主的学养问题。虽然讨论的是语言词义的问题,但引用的例句有歌德之语,足见其对文学的熟悉,而中德比较引用的例证之佳、论述之清晰,更使其能从简单的语义学追问背后的文化成因,可见其学贯中西之学养厚重。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在大学执教以后,几乎没有一天,他不在思考他从事的专业与学识。他习惯于几乎每天总要数小时之久地伏在他那张古色古香的红木书桌上,面对着成堆的德文文法书和各种辞典进行德语与德意志文学的钻研”②廖乃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这样的学者,为什么竟会与南大德文学科有些格格不入呢?
陈铨(1903—1969)的命运似乎更可感慨,他早年可谓是才气横溢,是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在抗战时代扮演了文化场域的重要角色。即便就德文学科来说,他是中德比较文学学域的开辟者,能够出现陈铨这样的人物,当引为学科的骄傲。我曾当面问过作为当事者的张威廉先生,后者似乎有些含糊其词:“人很多的,他们都过来了,而且带了很多书和资料。象陈铨、廖尚果他们,陈是写剧本的,《野玫瑰》很有名,后来被打成右派。廖是搞音乐的,也很有才。但他们个性也比较强。”③叶隽:《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陈铨在这段时间,也并非完全停止了自己的学术活动,如他就撰写过《对张威廉先生〈泰尔报告〉的补充意见》(1955年),未刊稿,此文对张威廉关于席勒剧作《威廉·退尔》的报告,从时代问题、道德问题等方面提出商榷意见。季进等:《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张威廉关于此剧的思想,可参见《席勒剧本〈威廉·退尔〉、〈唐·卡洛斯〉和〈杜兰朵〉简介》,载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9页。陈铨对席勒是有研究的,但此时他的学术话语权利显然受到限制,有关论述都未能发表;但这种对自己学术意见的表达欲望和真诚,确实可以见出其作为德文学者的可贵一面。尽管比较隐约,但仍给我们留下了印照于史实、语境与时代背景进一步考察的可能性。实际上,像陈铨这样的人物,1949年之后的境遇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7年基本还可正常进行教学活动,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的大潮下,作为右派的陈铨处境则相当艰难。1952—1957年间,陈铨在被“发配”为外文系资料室管理员之前,④对这一点,时为南大德文专业学生的杨武能有回忆。参见杨武能:《“图书管理员”陈铨》,《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6 日。另相关叙述,也可参见杨武能:《圆梦初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还是有过5年为人师表的愉快生活的: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所热爱的德国文学与德语教学当中,他尝试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采用英语授德语课,让学生们轻松掌握和理解德语,同时又提高了学生的英语水平。他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戏剧课,除了课堂讲授,还利用业余时间,热心指导学生排练德国剧作家的名作,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陈铨甚至还可以和一些留在南大的德国人交往,相互之间就像中国人走亲访友一样无拘无束,还和一位德国教师一起编写了一本德文教材。教学写作之余,陈铨也会陪着子女家人去看看电影或戏曲演出。①季进与陈光琴(陈铨之女)访谈记录,载季进等:《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
然而,往事如风,即便曾经善待陈铨的南大,也挡不住政治运动爆发时的“山雨欲来”;虽然1961年他成为最早脱掉“右派”帽子的人员之一,但随即而来的文化大革命②陈铨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可参见季进等:《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页。,则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拖入另一重深渊。作为德文学者的陈铨自然也就很难展现其闪耀的光芒。陈铨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南大德文专业虽汇聚一代人才于一地,却为何最终得了个“风流云散”的结果的主要原因。陈铨的个体命运、南大德文专业的命运,不过都是时代风云的一角缩影而已。其实,何止是南大,又何止是德文专业,又何止是陈铨?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时代风云的历史诡谲之中。
1952年,如果说廖青主已经是年近花甲,那么陈铨尚未及知命。而此时的商承祖,才53 岁,正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年华,他若能够以一个学术领军者的眼光和睿智,将这些精兵强将用好,则不但是一个学校的振兴机会,对于整个德文学科史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树立“南方学统”的大好机缘。其实南大并不缺乏这个传统,早在民初时代,东南大学就以“南雍学术”之名而与北京大学相抗衡。③有论者提出“南雍学术”的概念,溯源历史,强调国子监是国家教育行政最高机构兼最高学府,并以明代南京、北京国子监并立的状况作比。认为在1910-1920年代,南雍具有新的含义,即特指当时南京的最高学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此皆今日南京大学之前身)等。并引述论证,或谓“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或谓东大与北大,“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参见王运来:《留洋学者与南雍学术》,载田正平、周谷平、徐小洲主编:《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在我看来,这一概念可以下沿,即由历史到现实中,均可以一种南北对峙的模式去考察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路径。在1950年代以前,由南高师到东大而中央大学的发展路径,借助政治因素,基本可以认为与北京大学形成南北鼎立的格局;在195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南方由于复旦大学(稍近还有浙江大学)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借上海的地利之便,使其渐有成为南方教育/学术中心之势,但总体而言,说南京大学代表了南方学术,仍不会有太大争议。而在文革结束之后,复任南大校长的匡亚明,以一种博大的气度排斥一切干扰而引进程千帆,为南大的文科振兴而请来大师。程千帆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意义,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这不仅是一个学派或学校的复兴,甚至攸关中国现代学术整体场域的学科兴废之关键。学术领袖的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之意义,或正在此。遗憾的是,作为边缘的德文学科,恐怕少为领导者所关注(如范存忠者毕竟是凤毛麟角,这与其学术养成和眼光有关),所以陈铨这样人物的命运自然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作为学生的杨武能曾经深深同情被安排到图书室做管理员的陈铨,因为作为一个具有敏锐学术感觉的学生,杨武能似乎已经感受到这位管理员老师的价值,他曾感叹“多亏南大外文系有一个藏书丰富而且对学生也开架借阅的图书室”,并且特别提及和他作为德文学生直接相关者——“其时管理德文图书的乃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学者陈铨,尽管他被视为不可接近的‘大右派’,学生有问题还是向他请教”④《自序》,载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铨作为学者仍可从学术薪火相传的断续香烟之中感受到的一点点温馨,毕竟还是有学生想要求知的。然而,陈铨的悲剧命运,却是那个大时代不得不然的结局。当然,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陈寅恪的情况,也是最后20年,相比较陈铨的近乎全面噤声,陈寅恪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说陈寅恪缺乏可比性的话,那么贺麟(1902—1992)总是可以的。当年曾同为清华弟子,日后又先后留学美、德,在1940年代显赫一时的战国策派运动中,陈、贺亦为其中核心人物。1950年代之后,彼此的命运既有近似之处,也不完全一样。贺麟终于作为哲学家而名世,并留下为数不少的著述,譬如煌煌的《精神现象学》译稿(和王玖兴合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而陈铨基本上在学术与文学上都保持了沉默,所存《精神现象学》译稿,只残留了一小部分。⑤我们鲜有人知道,陈铨是当初与其事者之一。《精神现象学》残稿,载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204页。对陈铨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最后的20年,他寂寞无声。我想他大概是不情愿如此的,作为一个学者和思者,思考总是必需的事情,读书也是必需的事情,没有读书如何来思考?没有思考如何来写作?没有写作如何来读书?这几者之间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陈铨的最后20年,确实是著述凋零。这固然首先是大背景的制约,但与他身在其中的南大德文学科与外文系的“小环境”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相比较作为外来人的廖青主和陈铨,商承祖对张威廉无疑是更信任的。像张威廉这样的人物,属于资质相对平平,为人亦锋芒不露者,且潜心学术与翻译,是大家都喜欢的好好先生,譬如廖青主就和张威廉有过学术交谊①廖青主“在南京这几年内除了授课讲解德意志文学以外,还进行了不少翻译工作。这应当感谢他的同事张威廉教授,是他主动向青主推荐民主德国安娜·西格尔斯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和他的名字》,说:如果青主愿意翻译,他可以拿去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吴朗西先生出版”。参见廖乃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2008年版,第153-154页。。而廖青主和陈铨就不同了,前者在音乐学方面卓有成绩,对文学也相当熟稔,更兼曾有革命元勋的政治资本,年岁亦高;陈铨更是才华横溢,不但在中德比较文学、德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都作出过开辟性的成果,而且更是一个享有声誉的作家和思想界风云人物。对于这样的同事,焉能心中没有半点提防?作为学科领导者的商承祖,或许难免受到这样的思路的影响。张威廉的朦胧说法或许也提供了某种印证,他说陈铨、廖尚果都很有名、很有才,“但他们个性也比较强”②叶隽:《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虽然他的话语焉未详,但其中表达的个体生性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冲突碰撞是清楚的。但如果仅将问题仅归结于人事的纠葛也是有局限的,实际上南大德文学科的发展问题,除了可能的“瑜亮情结”与“时代语境”之外,还有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也就是学术薪火承传的问题,这一点结合冯至门下的人才济济可能看得更清楚。如果说廖青主、陈铨是因为政治背景的关系,而不太可能有机会施展长才的话,那么商承祖、张威廉究竟出了怎样的弟子?虽然像吴永年、董祖祺等人可能偏重于语言学方面,但在文学领域确实是未出现能够比肩同侪的第三代学者。叶逢植(1929—1990年代,卒年不详)或许是另外一个可举的例子③叶逢植简历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268480.htm,下载于2012年8月10 日。,他大致该算是第2.5 代人,是杨武能的老师,但又是商承祖、张威廉他们那代人的小字辈,本可以作为承继者而别出手眼,可事实则大不然。作为学生的杨武能一方面强调其“多才多艺”,另一方面则指出其“未能在自己本行出类拔萃,一展长才的主要原因乃是“旁骛太多”④杨武能:《怀才不遇奈若何——怀念叶逢植老师》,《出版广角》2002年第2期;《多才多艺 可佩可叹——怀念恩师叶逢植》,载杨武能:《圆梦初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85页。。如此才华横溢的叶逢植都未能在学科史上赢得地位,更遑论其他人?南大德文学统的某种意义上的“断裂”,或许可以与北大德文学统的“传薪”形成一种对照。那么,我们要问的或许是,当商承祖晚年也遭到文革迫害、1975年因病去世之际,他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或者竟是,他已然认为,通过自己的精心规划,南大德文学科已可以薪尽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