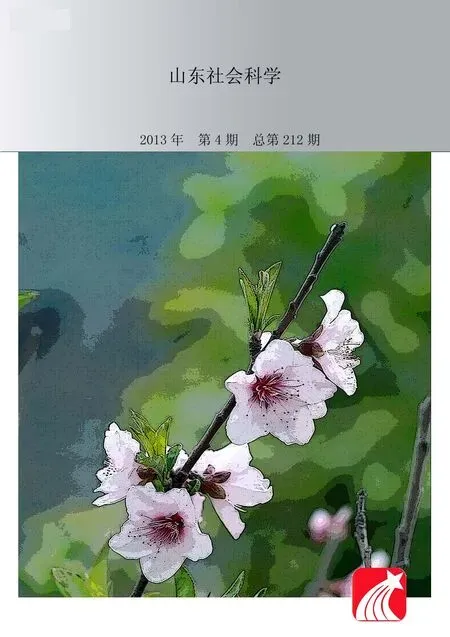文化、启蒙与理性
——论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
2013-04-07马欣
马 欣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开启者,学界较多关注他的“大众文化”(Massenkultur)批判。但本文将要说明,大众文化批判只是霍克海默文化理论中一个外显的层次,其背后的逻辑是启蒙和理性的批判。这无论是他1941年抨击艺术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取代,指责大众文化具有欺骗性和操控性的《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Neue Kunstund Massenkultur);还是1944年《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的概念》一文斥责启蒙退化为神话,被彻底启蒙的世界陷入了野蛮状态;抑或1946年《工具理性批判》中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理性的主观化倾向,认为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压制导致文化偏离了追求真理的轨道,都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故此本文将揭示,霍克海默的文化理论是一个逐层深入的体系,文化、启蒙、理性共同构筑了一个类似于同心圆的批判历程。
一
在讨论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德语语境中的文化概念,为理解霍克海默的文化概念作一下铺垫。在德语语境中,文化概念既包涵了文明的要素,又被作为一种自由的精神与文明相对举。霍克海默一方面受到康德以来文化与文明截然分立的观念的影响,同时又将文明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文化批判的视野当中,他的大众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正是基于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与固化的文明这个双重结构而提出的。
德语的Kultur(文化)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原意指耕作、培育,后被古罗马的西塞罗引申为心灵上的培育,“精神文化”(cultura animi)被他视为哲学的语汇。到了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倡导者普芬道夫(S.Pufendorf)才第一次将“Cultura”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化概念。他用“文化”的状态来对抗野蛮的“自然”的状态。这样,文化这个疑难概念就保留了像社会学这样的物质文明学的(ergologisch)要素。①Jachim Ritter,Karlfried Grueder.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and4:I-K).Schabe & Co.Verlag.Basel/Stuttgart,1976:1309.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von Herder,1744—1803)第一次阐述了现代的文化概念,将文化看作为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他将文化(kultur)和教养(kultiviert)赋予历史性的要素,文化作为一根链条,从一个民族传播至另一个民族,从人类之初到历史演进的每个阶段,都能看到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创造的踪迹,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习俗、规范等物质文明的成果。文化作为具有民族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与文明息息相关,这样一种理解文化的方式渗透到了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当中。大众文化批判,即是对处于历史当中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批判。
斯宾格勒(O.Spenglers,1880—1936)用生动的语言捕捉到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文化是体现和表达心灵的一种独立自足的现象,是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精神动向,每一种文化都会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他在《西方的没落》中拿“希腊的心灵”与“罗马的才智”来类比“文化”与“文明”。①[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6-54页。他认为,文明人不再拥有未来的文化,文明就是结束,它紧随着已经完成了的成长、已死的生命、凝固的发展……是文化的终结。②Jachim Ritter,Karlfried Grueder.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and4:I-K).Schabe & Co.Verlag.Basel/Stuttgart,1976:1319.其实在斯宾格勒之前,康德就已用更精练的语言在对立的意上使用文明与文化。他说:“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被高度的文明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范和礼貌方面,我们文明的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但要是以道德去衡量,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道德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的;但我们对这一观念的使用却仅限于名誉和外在礼节中那些类似德性的东西,而这些只不过是文明而已。”③I.KANT,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ergerlicher Absicht(1784).In:Gesammelte Schriften,Band.8.Berlich:Akademie Verlag,1784:26.显然,斯宾格勒与康德理解的文化在道德上高出文明许多,并且与文明是相对立的,对于人而言,文明是外表上的修饰,而文化则是内在的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这种将文化赋予创造性的、鲜活的精神内涵,而把文明作为外在的、固化的存在的观点,还在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和社会学家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 Weber 1868-1958)那里出现过。这样一种将文化和文明对立起来的传统影响了霍克海默的文化观,他在文化批判就是站在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的立场上去批判固化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具体表现为技术手段、道德教条和规范。
霍克海默继承了德语语境中关于文化的传统,首先,文化包涵着文明。1949-1969年间,他在一篇题名为《文化与尿壶》(Kultur und Nachttopf)的短札中说道:“‘文化’是人们共同生活当中的自然物的收纳(Hereinnahme)。它好比尿壶,小姑娘必须将尿壶清空,而尿壶表面上的印花和小姑娘则是最后的正在消逝的见证。”④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4:Nachgelassene Schriften1949-1972,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t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88:53.他将文化比为尿壶,尿壶中“自然物”便是文明的要素,虽然它日日须得清空,但总还有“小姑娘”与“印花”为证。其次,文明是文化批判的要素。他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中,将文明与反犹主义的屠杀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将极权主义与文明的发展相并列,“极权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机制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⑤[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他批评美国文化时使用了“文明”这个词:“美国的文明没能产生出一点新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思想也是无力的。”⑥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14:Nachgelassene Schriften1949-1972,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t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Verlag,1988:288.可见,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一种固化了的文明形态。
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其实是关注我们日常生活中价值的失落,它包括现代人只为金钱而奔忙的职业状况,沉溺于快感的休闲生活,艺术认知感的消弭……⑦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在霍克海默那里,大众文化既不是指一种由大众自发创造的文化,也不是指文化的大众性,“大众性从来不是由大众直接决定的,而往往是由大众在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决定的”。⑧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大众文化并不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一组概念,它指的是失去反思、创造以及批判性的文化机制。这一机制的可怕性在于,人们对它似乎只能顺从和适应,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创造力被压制了,只是沉醉于丰富的文化商品所带来的虚假满足之中。霍克海默以贝多芬的《英雄》在公演时与听众的互动为例,说明艺术在大众文化当中批判性、否定性的丧失,变成了像古董一样的东西,艺术曾作为对世界的表达、最后的判断,现在已变得完全中立了,充满趣味的艺术活动已经蜕化成了娱乐活动:“普通的音乐欣赏者已经不能了解它(Eroica 英雄)的客观意义。当他聆听演奏,为的是图解评论人对它所做的评语。在欣赏者那儿,一切变得黑白分明——道德的要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德国的现实,即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德国的精神生活,它不能够政治地表达,而只能在音乐和艺术中寻求出路的现实都已给出。这首音乐作品被物化了(ist verdinglicht),被弄成了一件博物馆里的作品,它的上演对于从属于社会组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闲暇活动、一个事件、一个对于明星登台或者一个必须参加的社交聚会的有益契机。但这里没有与艺术作品生动的交流,没有直接的,自发产生的对其作用的领悟,没有它作为一幅图画的整体的把握,也就是那被称之为真理的东西。”①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58-59.
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是在文化(自由精神)与文明(给定的机制)对立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发现大众在一种给定的机制下被操纵和愚弄,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对人的控制,实际上是对自由精神的压制,它本质上是反文化的。霍克海默以美国广播滑稽剧《you were present》为例,批判了娱乐工业的乏味性(Flachheit)②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4: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49-1972,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t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88:48-49.,此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Popularitaet)其实是被文化工业的管理者决定着,因而大众对流行文化的接受表面上看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是被有意操控的。
令霍克海默绝望是,由于进行艺术创造的私人领域不断受到文明科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干扰,社会中有一种大众文化日益取代艺术的倾向。比如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投资于每部电影的资金数目可观,因而要求迅速回收资金,因此好莱坞的经济关系不允许对艺术作品的内在逻辑——即艺术作品自律性进行追求。③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4:Schriften 1936—1941,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435-436.在霍克海默看来,好莱坞这个电影工厂无法创造出艺术,只能提供流行娱乐。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影响下,实际上很难找到纯粹的艺术形式,一切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而其本身实则是一个商业化的系统。
霍克海默并没有沉醉在文化的理想乌托邦里,他将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艺术失落的现实紧密联系,他所理解的艺术具有自律和创造的本性,与他对文化作为自由精神的理解相一致。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其实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消极性的揭露,这样一种批判根植于对启蒙的辩证思考,因而,大众文化批判是启蒙批判的前奏。
二
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是在努力反抗权威的过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为了权威,大众文化毋宁是这样一种权威统治下的产物。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④[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在康德看来,启蒙是人步入成熟所必须的精神指令,启蒙展现了人类心灵的独立、运用理性的自由和创造的勇气。但从人类历史上看,启蒙的结果不仅只有自由和独立,还有专制和屠杀。
启蒙与科学知识相关,在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中,启蒙一开始用人类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祛除了神话中的愚昧,但是当启蒙具有了足够的权力后,人类却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的状态。⑤[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前言1944/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即启蒙倒退成了神话,启蒙的倒退带来了两种后果:技术对人的控制和人对自然的压制。这说明,真正的启蒙还没有完成。霍克海默指出:“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⑥[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因而,启蒙文化自身包涵着自己的对立面,具有矛盾的双重性。
启蒙的第一重含义是指:一直在进程当中的进步精神,它跟神话相对立,反对一切原始遗存并旨在消除一切统治性文化,它永远在进程之中。第二重含义是指:具有神话般极权性质的宰制性文化,它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这种启蒙已经实现它的目的,世界正笼罩在它所招致的灾难当中。正是启蒙的两重性导致了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自身的分裂,第二重意义上的启蒙在让人成为主宰者的同时,也确立了普遍的原则和规范,这些文明化的原则又反过来压制文化的自由发展,因此,我们说启蒙两重性之间的对立是文化与文明相对立的原因。
启蒙的极权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德国的纳粹统治。纳粹统治在霍克海默看来是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⑦[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是一种平等的非正义,启蒙思想一开始是祛除愚昧的进步文化,但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成了纳粹的屠宰场,这里的启蒙显然不是追求自由并致力于推翻统治权的第一重意义上的启蒙,而是确立人类极权统治权的第二重义上的启蒙。极权统治不但残酷地控制人,而且有计划、按步骤地“清除”所谓异己,暴戾至极如同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祭活动。
启蒙的极权性也体现在大众文化当中。“大众文化”在霍克海默那里具有特别的含义,它并不是指从大众当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文化,也不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式,甚至与艺术无甚瓜葛,而是指一种依照某些流行的标准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化,它是经济王国的派生物,一种自上而下的被管理的失去内在创造力的文化。他在《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中谈到,在大众文化中,“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服从于那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只允许他们作出单一反应的机制。他们那些尚未开掘出来的本性因素无法得到相应的表现”。①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由于启蒙的极权性,注定了它还要在进程中前行。第二重意义上的极权化的启蒙放弃了思考思想,它使科学、艺术都成为迎合世界的符号体系,失去了反思的维度。霍克海默在文章中提到的“彻底启蒙者”(restlos Aufgeklaerten),直译过来“完全被启蒙的人”实际上是需要被重新启蒙的个体。“启蒙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并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万物,进而作用于人的存在和意识。”②[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这里的启蒙是指第一重意义上代表着进步和批判的启蒙文化。霍克海默坚信通过启蒙对其自身的批判,协调好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可以扬弃自身,实现第一重含义上的启蒙,“即在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然被看做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③[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双重性既是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的依据,也是启蒙文化批判的立足点。首先,一旦知道了霍克海默是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启蒙概念,就会明了“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④[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这一表面看来令人迷惑的辩证观念。其次,霍克海默对启蒙概念进行批判,实乃对第二重含义上的启蒙的极权性进行批判,这也是大众文化的批判之根源,正是由于极权化的思想渗透在文化当中,才使文化成为了权威的附属物,从而丧失了追求真理的维度,变成了具有欺骗性和操控性的大众文化。最后,启蒙批判暗含了理性批判,因为启蒙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霍克海默说:“俄狄浦斯(Oedipus)对斯芬克斯之谜的回答:‘这就是人!’启蒙运动不变的原型。”⑤[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从中可以看出,人类通过自身来思考自然界,人的理性具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将自然界的散漫无序都整合成一个体系,由此产生了极权性及同一性倾向。因而,在《工具理性批判》中霍克海默直接跳跃到了理性概念,将理性作为文化批判的核心进行考察。
三
如上文所述,既然启蒙的分裂极权化倾向是由理性自身所导致的,那么理性作为一种文化,它又是如何成为盲目的非理性的呢?这就成了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问题。他首先将理性作了区分,理性具有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两个方面,主观理性是以计算、工具为手段,依照主观目的行事,它最终走向了形式化的理性即非理性,客观理性是以客观的标准、原则来行事,它以追求真理为至高目的。理性概念的双重性决定了它的辩证运动,主客两方,一方被压制、另一方占主导的状况轮番交替在理性发展的进程中。
在启蒙的背景下,理性的扭曲来自于主观理性“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力量的推动,正如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所指出的:“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⑥[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第一章“工具与目的”中分析了理性扭曲的整个过程:首先,主观理性(subjektive Vernunft)已经或多或少被人接受,因为它具有适于达成某种目标的智谋⑦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27.,实际上这种完全致力于个人目标的主观理性,只是出自于“自我持存”的考虑。然后,当这种理性在某个机构当中发挥作用,它的使用就带有逻辑的、计算的倾向。在主观主义者看来,理性自身没有目的,因此去讨论相对立的目的之优先性是毫无意义的。可能的讨论,仅存在于当两个目标服务于第三个或者更高的目标之时,这就意味着理性只是工具性的而非目的性的。⑧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29.最后,理性完全成了手段(Instrument),被主观化、形式化地用于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而忘记了理性在受到“自我持存”推动的同时,也还应该具有超越“自我持存”的力量,即客观理性的力量。
霍克海默认为,尽管主观理性在历史上一直都内含在理性概念之内,但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占主导的是“客观理性(objektive Vernunft)”,它作为一种超越自我持存的和解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也存在于客观的世界当中,存在于个人与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机构里、自然及其表象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和德国的理性主义,无一不是在理性的客观的理论之上奠基的。①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28.“客观理性”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学曾致力于的客观秩序(规则),它与包括个人兴趣和自我持存在内的人类存在相和解,如同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所说:“谁生活在客观理性的光照中,就同时生活在成功和幸福当中。”②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28.客观理性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行为及其目标的按部就班,而是致力于最高的善的理念(die Idee des hoechsten Gutes)、人类的终极目的问题以及通往最高目标的方式。
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压迫主要通过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来实现。合理化思想其实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中指出:“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了技术能力发展的强烈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在这本书中,韦伯努力寻求导致西方文化所独具的合理性主义的缘由,最终落脚到了西方的宗教伦理。霍克海默却将这一韦伯所肯定的“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轨道”作为了批判的对象,理由是,由主观理性带来的现代人思想中的“合理化”倾向,散布到了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导致理性的个体在“进步”的铁蹄下被取消,从而走向了盲目服从权威的非理性。
主观理性的合理化倾向最终导致现代文化的危机,在《工具理性批判》的前言中霍克海默提出要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反思:“有必要对作为一定文明观所折射的统治思想进行探讨。作者在这里所要做的,不是试图给出一个行动上的方案,相反,他认为现代的倾向是每种思想都被转化为行动,或者说当前文化危机(Kulturkrise)的征兆之一是在行动方面进行积极的节制:为了行动而行动决不会强于为了思想而思想,甚至远远比不上它。”③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26.现代人自以为正确的“合理化”倾向,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它缺少了真正的具有客观性内容的基础。
大众文化是现代的文化的危机的一种表现。霍克海默认为,在大众文化体系当中文化具有高下之别,那确认为“好的”“干净的”便受到追捧,其余的则被嫌恶,文化越来越倒退为古老的禁忌,旧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表面下燃烧着,它为失去信念的现代人提供着热量。④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91:54.霍克海默带领我们反思现代生活中意义的缺失,实现目标代替了寻求真理,人的消遣和爱好作为内在化的生活业已消失,人们被带到休闲活动、社会交际等广泛的娱乐项目当中,文化作为自由精神的超越的维度几乎被大众文化所喧嚣覆盖。现代社会中那些与娱乐相关的文化商品,实际上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变质的需要,它与具有创造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相分离。
纵观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历程,从文化到启蒙最后到理性,一路都在追寻文化陷落的真正原因,正如他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指出的:“人类的未来有赖于批判行为的存在,它当然包含在传统理论的要素以及正在流逝的文化的要素当中。”⑤Max Horkheimer,Traditionell und kritische Theorie,In: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4:Schriften 1936-1941,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88:216.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的要素中找到了启蒙文化的极权主义倾向,在人类理性的觉醒中看到了主观化、工具化的一面,对理性的合理化倾向进行了批判。文化、启蒙与理性层层深入的批判历程,一方面使启蒙的主体具有了反思的意识;另一方面启示了哈贝马斯从而提出交往理性;同时,这一从概念内部展开批判的方法及其文化批判的多层次探究,值得当今的文化研究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