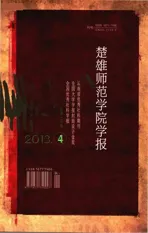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权意识*——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说起
2013-04-02蔡银强
蔡银强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对所有稍微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早已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即文化的变革。不过历来对“五四”的评价都存在分歧,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指责“五四”者认为那些主将及其追随者们对传统过于激进地否定,对西方又过于推崇;自认为继承“五四”的学人,则仍以坚韧的精神在文学革新和文化变革的路径上不断探索和研究。美国华裔学者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以下简称《跨语际实践》)一书以女性主义的视角,从翻译的等值性、国家与个人关系、现代文学话语模式的合法性、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对“五四”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了解构式的论述。比如“国民性”和文学经典的生成问题在刘禾那里,前者只是一个神话,而后者更是在经纪人要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编辑个人好恶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跨语际实践》一书里,刘禾对男权权威体制的女性主义解读,使“五四”的文学抒写以及文化呈现中显现出现代性的某种虚妄性。然而正如王德威论述的那样:“我们若将梅贻慈与刘禾的研究并列,可以发现一有趣的对话。刘禾指出中国女性从来只是父权文化象征系统中的空洞符号,而梅却看到中国男性也好不了多少。他 (她)们同样在历史洪流里,捞取材料,填充空虚的自我。也许所谓的父权体系不如许多女性主义所见,为一森森然的霸权实体。它可能根本是一架空的权威机制,而其中的男性成员一样也是流动的符号,不断寻求意义的依归。”[1](P367)在这一比较中,我们发现,被刘禾以为的“五四”现代性的实质即所谓的男权体制,也不过是一个虚妄的存在,那么,“五四”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
回到刘禾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不管她采取什么视角和叙述策略,都没有跃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那几个范畴,即中西之间、现代与非现代之间、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而从这些关系的表述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意义的趋向中心,即话语权归属问题。这里的话语权不只是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或者男性权威的视角问题,也不只是文学流变中传统与现代的成分问题,更不只是民族、国家和个人在现代性中谁才是意义中心的问题,它意味着文学研究先前就存在着的一个前提,即中西文化的交流、比较、碰撞与融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霸权意识。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五四”的权威性在于它所体现的理所当然的现代性,而这现代性的理所当然之处又必须以西方话语为理论支撑点。正如刘禾自己所论述的那样:“在中国,以及在后来的海外汉学界,对白话文学和通俗形式的倡导耗去了20世纪学者的大量精力,他们按照自己时代对欧洲现代文学形式和体裁的理解 (尽管这种理解经过了重重中介),实际上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重写。虽然我们对这些成果应当给予充分的信赖,但人们容易忘记的是,不论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发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不可能摆脱一种总是有欧洲文学参与的学术史和合法化过程。”[2](P333)
这种话语言说方式必然免不了民族主义的抵制,并且这种抵制是深广的,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华人学者的潜意识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正是中西文化交流中话语霸权意识的根源。笔者希望通过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范畴,对在西方话语逼迫下、受民族主义孕育的文学和文化的话语权意识,做一管窥蠡测的论述。
一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形下被国人认识到的,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交织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就像危机必须在西方的侵略下才称其为危机,救亡与启蒙也是以西方为参照。而这一西方的在场,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始终纠缠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和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时而平静、时而紧张的关系中。在这里,笔者不打算论述现代化本身的合法性,或者说传统文化何以不能维系时代发展并提供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而只就以上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范畴,在众声喧哗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理出自认为的关键所在,即话语权问题。
现代化的第一要义是民族的现代化,在民族前途的大义下所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是为了器物上能与西方相抗衡,而自觉不自觉地改变我们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到底是以何种身份在与西方对抗?我们西化的目的是要保持中国民族、种族的存在,而作为向西方看齐的一个种族,我们拿着从西方泊来的理论武器与西方抗衡,作为一个内在趋向西方化的中国人与西方文化对抗,又是否失去了对抗的话语基础?保族、保种、保教虽然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人大声疾呼,但是“复兴中华文化”这一相当有吸引力的呼喊,又何尝不是上述口号的代言,又何尝不是当今所谓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下寻求话语权的某种漂亮文饰!
而关于现代性批评话语本身的思考,我们也许不禁会问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非现代的?如果我们并不知道是用现代的还是非现代的语言在探索和描述我们的过去与现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历史做出恰当的述说?现代性问题本身也许不是伪命题,但是现代性问题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却有其虚妄性,因为你可能用一种连自己也不知道是现代还是非现代的语言,在做着关于现代的美妙的言说。在这一迷雾式的言说里,其消解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现代性得以合法化的西方话语基础。一如有学者主张:“传统的文论话语已随着过去的生活向历史深处走去。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及其文学显然已不是传统的,正如它也显然不是西方的。我们正在从传统出走的中途。这里生活和文学都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亦即‘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最坚实的地基。”[3](P385)这正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逻辑圈里,述说重建本民族学术话语权威的必要性和途径。以民族主义的煽情性和某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于抵消西方话语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权威性,来诉求在今天文化热的浪潮中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或许正是这种言说方式的话外之音和题外之旨。其实,我们在对于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思考方式中,始终存在着民族文化认同的身份意识,这种意识既是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中弱势文化心理的因袭,也是当下全球化过程中对文化殖民和学术殖民的反抗姿态——但只是一种姿态。
二
在有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论辩背后,无不舞动着民族主义的幽灵,对这种民族主义产生和生长的环境及其影响,张灏都有精当的论述,但他并没有加以简单地否定或肯定。他在论述到民族情结在当下的作用时指出:“今天我们虽已置身于所谓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代,但谁也不能否认,帝国主义的心态与行为仍然不时出现在国际关系中,同时,经济上的全球化趋势与文化上‘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仍然未能取消民族国家之间的畛域。民族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新世纪国际现实的一个主趋。因此今天评价民族主义,不能否认在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它有其重要的正面功能与意义。”[4](P173)但是当 “民族”而为一种“主义”时,就值得警惕了。张灏将近现代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分为政治的激进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进而指出,潜藏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之中的“汉族文化霸权意识”、 “大我心态”和“华夏情结”,与民主化和现代化是相抵牾的。确实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由这两种心态所激化的情绪让国家在独立和富强的名义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义和团运动,又比如“文革”。
关于话语权的转移,首先主要体现在华人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抒写方式中。以“重写文学史”为例,重写文学史这一热潮,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审美领域的学人们有关文学研究的言说方式变革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也代表着由过去政治宰制下的审美话语向纯文学的审美话语的转变,这其中有知识分子对于文学、文化及政治的理解和追求。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钱理群、温儒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些著作实际上以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隐藏其背后的是基于文化走向上的对民族、国家的关怀。而在这一关怀中,话语权通过言说者的言说方式悄悄地转移了。虽然话语权主要体现在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的阐释中,但是或许我们的视野要更大一些,我们的最终指向应在于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方式上的阐释权;如果没有这个终极的指向,我们的言说就不免显得气短。
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西方的言说方式早已深耕于我们的思维中,而情感上,在与西方话语对话过程中,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层面上,华裔学者恐怕都难免有相当的落差感和“矮化”意识。我们对这一矮化状况的不能接受,在刘禾的论述中也是可以得其一窥的,她希望民族认同的同一性建立在自我文化的基础上。刘禾论述道:“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这种区别能使我们了解主体作用的意义吗?它又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所陷入的深深的困境呢?这种困境的实质在于中国人企图利用非中国的或中国以外的东西来建构中国人的同一性,从而使自己从矛盾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矛盾既支持又损害了他们那种前所未有的举动,即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成为世界民族文学和文化之一员的努力。”[2](P334)的确,在与西方对话过程中,我们还存在一股凄凉气息,这一气息是民族优越感、崇高感和自信在对话开始时就瞬间消解所体现出来的,这似乎是中国学人很难避免和逃避的。
由此可见,我们真正在乎的或许不是我们的文学领域成为外国理论的操练场,而是不能直视经过百年的发展后,我们所期望的国家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这样的霸权心理是隐藏至深的,或者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依然无法实现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上的凄凉,甚至连这种情绪体验我们都不愿承认。笔者以为,我们面对的困境或许可以从詹明信的言说中得到说明。在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化研究或许是对第三世界文化反抗的消解。当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处于第一世界包围中诉求自己文化的话语方式和权力时,作为一种反应,一种自然而然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性,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如詹明信者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他们以一种似乎毋庸置疑的口吻述说着他们的话语,即他们对第三世界文化和文本的解读话语。其实,文化和文本的解读不在于由第三世界学人或第一世界学者来解读,而在于这种解读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内核周围进行,因为学术殖民就是在这一解读过程中发生的。而第一世界式的解读必然导致第三世界反抗内劲的消解,或找不到反抗的对象,或发现反抗的对象里竟然包括了在文化上已经西化了的自己,这的确是一个可悲的结局,然而似乎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话语权的诉求这一心态或许可以看作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相当自信的时候,谋求建立以汉语的语言特征为基础的话语霸权!这样的话语权诉求在当下并不乏追随者,“无论是历史寻根的,还是中西比较的,或是文化对话的,其方法论背后均隐含获得权力认同的合法性诉求问题”。我们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用什么意识去改写文明史包括‘文学史’,是当前重建面对21世纪民族话语权的关键。”[5]民族主义的特征在类似的论述中并不罕见,我们似乎总是在给自己设定的民族主义的逻辑圈里徘徊。
当我们在乎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不是言说者所言说的意义在场,而是言说者自己以某种身份在场,即话语权的基础固然需要文论意义上的强势,但最看重的还在于言说者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在身份认同之上的集体荣誉感。那么,我们今天在争夺学术话语权时,如果不对民族主义加以省察和反思,它固有的保守性和偏激性极有可能把我们带向所期望的目标的反面,即由文化保守主义导致的话语独裁。到那时,历史其实只是又上演了一幕滑稽的闹剧,而真正深受其苦的是始作俑者——我们自己。所以,当文化霸权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在目标的时候,所谓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过是那些图谋霸权者的故作姿态罢了。
三
诚然,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在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都贯穿着民族、国家和个人尊严的意味,并且个人似乎总是在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也有汉学家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个事件本身,而是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6](P39)然而,走出现代文学研究中在民族主义催生下的话语权意识,我们也许更能看清现代性的真正旨归,即人的权利和尊严。由此可见,国民性并不是所谓的“神话”,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早期呈现方式笔者认为可以追溯到林纾。如李欧梵在论述到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时说道:“我认为林纾对妓女的个人态度超越了传统的规范:林纾有意无意地尝试把儒家学者、官员传统上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一个是以正确道德操守为基础,在社会及政治上以效忠国家为己任的世界,一个是讲求艺术文化、暂时回归自然、不拘礼节、随便与歌女交往的比较轻松的世界。换句话说,林纾这个着重道德观念的儒家弟子,尝试以自己对道德操守的认真态度来对待感情事,填补道德观和感情观之间的空隙。”[7](P44)可见,在西方文学、文化的浸染下,守旧者林纾也开始对人的问题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在西方各方面的冲击下,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传统文化的失范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一无是处。而对于学术研究,我们固然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要警惕以传统为名义的保守的民族中心主义;还要反对那些玩弄新名称者对于我们思想的操纵的企图。我们需要的是种种理论的内涵能为我们的经验所认可的东西,这样的目的在于去除认知上的蒙昧,从而避免因思维的人为遮蔽而导致的某种激进、愚蠢和危险的人云亦云,因此,启蒙或许在当下还是有意义的。
总之,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必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社会意义。文化的健康发展首先是对我们的学术话语加以辨析,并且我们内在的自信必须基于细微而内化的自我省察。基于这样的前提,传统与现代不必你死我活,中国和西方的论域也不必你争我夺。我们可以遵从鲁迅的拿来主义的精神,从人的角度出发,对凡是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能体现和维护人的尊严和自信的中外文化都加以吸收、容纳,而不必强分你我,自我设限,自我拘囿;只有在人类的普世情怀中审视自己的文化,在多元对比中完善它,才能不断解决我们在生存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谐。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话语权,不在于各种对立的关系所生成的意义,也不在于民族主义的“大义”,更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无关,而是在于有关人的生存的终极旨归。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刘禾.跨语际实践 [M].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3]曹顺庆.比较文学论 [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4]张灏.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A].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杨小清.走向“文化”的文学话语权—— “审美权力假设及其合法性问题”续论 [J].文艺争鸣,2000,(5).
[6]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