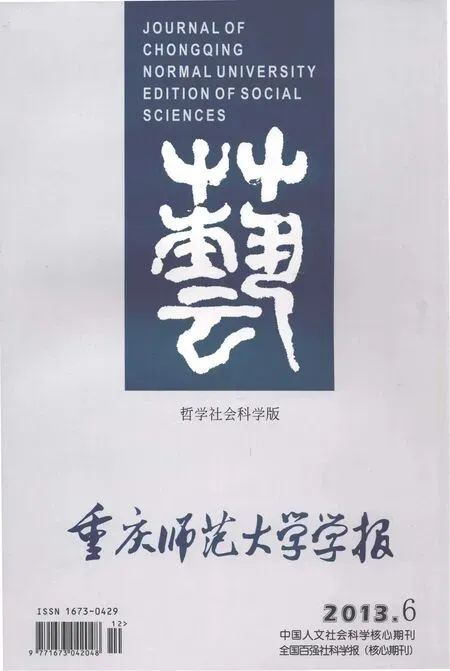从绍兴四年朝臣奏疏看南宋朝廷的对敌之策
2013-04-02陈忻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绍兴四年可以说是南宋朝廷初步扭转时局的一年,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引吕中《大事记》即称:“自绍兴四年赵鼎为相,伪齐与金分道入犯,鼎决亲征之议。于是,(韩)世忠进屯扬州,流星庚牌之计一行,遂捷于大仪镇,而金、伪俱遁矣。鼎又荐(张)浚可当大事,以枢府视师江上,将士见浚来,勇气百倍,而军声大作矣。”绍兴四年九月,伪齐刘豫遣其知枢密院事卢伟卿见金主晟,惑之以“货财子女”,因求“假兵五万下两淮,南逐五百里,则吴越又将弃而失之,不求而得,然后择金国贤王或有德者立为淮王,王盱眙,使山东唇齿之势成,晏然无南顾之忧,则两河自定矣”。于是,金“以宗辅权左副元帅、右监军昌权右副元帥,调渤海汉儿军五万人以应豫。”“又以左都监宗弼尝过江,知地险易,使将前军。宗辅下令燕云诸路汉军并令亲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伪诸路大总管、尚书左丞相、梁国公麟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合兵来寇。”对于这次大事变,朝廷从一开始的“谍报至,举朝震恐。或劝上它幸,议散百司”[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2册,119)到“士气大振,捷音日闻”,[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戊午条,2册,148)“将士致勇争先,至于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1](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乙未条,2册,162)最终于绍兴十二月挫败金与伪齐联军,“庚子,金人退师。”“金军已去,乃遣人谕刘麟及其弟猊。于是麟等弃辎重遁去,昼夜兼行二百余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1](卷八十三,绍兴四年十二月庚子条,2册,164)从绍兴四年九月到十二月,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只是战事的进程,而在此前后朝廷所采取的对伪齐和金人的不同策略,则对战争的结局走向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结合绍兴四年朝臣的奏疏,从切割金齐、观时俟衅等方面对南宋朝廷的对敌之策进行探讨,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宋齐、宋金力量的逐步转化过程。
一、先擒刘豫,则金人自定
建炎四年七月,金人册封刘豫为伪齐皇帝,刘豫于九月即伪位之后,就依仗金人,从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针对南宋的破坏性工作。
就外交上看,伪齐为巩固其境土及地位,极力倚靠金人,与南宋朝廷争夺利益。本来,高宗自即位以来,多次遣使入金无果,直到绍兴三年十二月才等到金人遣李永寿、王翊作为使人入宋:“自上即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尝报聘。至是,左副元帥宗维始遣安州团练使李永寿、职方郎中王翊等九人与(韩)肖胄偕来。”南宋朝廷对于金人的来使寄予期望,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诏刑部员外郎潘致尧、浙西兵马都监高公绘接伴,而兵部侍郎赵子画、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提举台州崇道观杨应诚馆之。所至诸郡守贰出城送迎。”[1](卷70,绍兴三年十有一月甲子条,2册,14)但是,金使的到来更主要是因为刘豫而起,故其主要议题也是涉及到伪齐的利益:“永寿请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且欲画江以益刘豫。”[1](卷71,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条,2册,26)伪齐的要求是南宋无法接受的,所以,作为回应,南宋朝廷于绍兴四年正月派出龙图阁学士枢密都承旨章誼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给事中孙近副之,“时金所议事朝廷皆不从,乃遣谊等请还两宫及河南地”。[1](卷72,绍兴四年正月乙卯条,2册,28)南宋朝廷的所为是对刘豫企图的正面回击,所以绍兴四年九月,在刘豫所下南犯的伪诏中也表现出对南宋的极端仇视之情:
朕受命数年,治颇有叙。永惟吴、蜀、江、湖皆定议一统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为请于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赵氏之祀。大金以元议绝灭,但欲终其伐功,力请逾坚,方见听许。岂期蔑弃大德,乃敢伪遣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会大金元帅,大兵直捣僭磊,务使六合混一。[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2册,120)
刘豫一则声称“吴、蜀、江、湖皆定议一统之地”,二则狂言“欲割地封之,使保赵氏之祀”,三则斥南宋朝廷遣使请还河南地的行为是“伪遣使聘,密期吞噬”。可以说,充斥于刘豫诏书中的是深刻的仇恨和极度的蔑视。除公然挑衅南宋之外,伪齐还接受其侍御史卢载扬结南蛮,扰川、广之策,南通交趾,结连溪洞,“遣通判齐州傅维永及募进士宋囦等五十余人,自登州泛海入交趾,册交趾郡王李阳焕为广王,且结连诸溪洞酋长。“俾财赋不入于二浙”。伪齐种种针对南宋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务使南宋“穷且迫”,“必鱼烂而亡”。[1](卷68,绍兴三年九月乙卯条,1册,877)
从政治和军事上看,刘豫自即位之日起,便以张邦昌伪楚傀儡政权灭亡、张邦昌被赐死为前车之鉴,所谓“北面奉符玺,退而复辟,犹且为齑粉”,[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丁丑条,2册,97)由此而选择了与南宋朝廷对抗到底的路线。所以“博州判官刘长孺以书劝豫反正,豫囚之。”“沧州进士邢希载上书刘豫,“乞通宋朝,豫杀希载。”进士薛笻“勉豫早图反正,庶或全宗,孰与他日并妻子磔东市?豫怒,欲兵之。”“国信副使宋汝为以吕颐浩书勉豫忠义,豫曰:‘独不见张邦昌乎?业已然,尚何言哉?’”“直徽猷阁凌唐佐、尚书郎李亘、国信副使宋汝为留伪庭久,谋疏豫虚实蜡书以闻,事泄,豫杀唐佐,亘亦遇害。”[2](卷475,刘豫传,13795)为与南宋抗衡,刘豫一方面紧紧依恃金人,建言金人“择金国贤王或有德者立为淮王,王盱眙,使山东唇齿之势成,晏然无南顾之忧,则两河自定矣。”[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2册,119)这一图谋无疑是对南宋的致命打击。假如金人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那对于国土日蹙的南宋来说,必定造成根本性的大灾难。另一方面,刘豫又连结南宋内部的叛乱分子,利用其力量给南宋朝廷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李成本来就是起于江淮的群盗之一,“绍兴元年,帝(高宗)至会稽,时金人残乱之余,孔彦舟据武陵、张用据襄汉、李成尤悍,强据江、淮、湖湘十余州,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意。多造符谶蛊惑中外,围江州久未解,时方患之。范宗尹请遣将致讨,(张)俊慨然请行,遂改江、淮路招讨使。”“俊亲冒矢石,帅众攻险,贼众数万俱溃,马进为追兵所杀,成北走降刘豫。”[2](卷369,张俊传,11472-11473)其后,“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2](卷365,岳飞传,11381-11382)关于刘豫接纳南宋叛降军队、阴结南方之背宋者,以扩张势力范围,掠取南宋土地、威胁南宋朝廷的事例比比皆是:
( 绍兴)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2](卷475,刘豫传,13795)
(绍兴二年三月)河南镇抚使霍兴屯伊阳山,豫患之,使人招兴,许以王爵。兴焚伪诏并戳其使。豫乃阴结兴麾下杨伟图之。伟杀兴,持兴首降豫。[2](卷475,刘豫传,13796)
( 绍兴二年)六月,蕲黄镇抚使孔彦舟叛降豫。[2](卷475,刘豫传,13796)
(绍兴三年四月)明州守将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军四千余人浮海抵盐城,输款于豫。文言沿海无备,二浙可袭取。豫大喜。以文知莱州,益海舰二十,俾寇通、泰间。[2](卷475,刘豫传,13797)
(绍兴三年)十月己亥,贼将李成陷邓州,以齐安守之;癸卯,陷襄阳,李横奔荆南,知随州李道弃城走。成据襄阳,以王嵩知随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简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贼将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寿春,将窥江南。[2](卷475,刘豫传,13797)
(绍兴四年正月)秦州观察使、熙河兰廓路马步军总管关师古叛降伪齐。时师古自武都率选锋军统制李进、前军统制戴钺求粮于伪地,袭大潭县,掩骨谷城,叛将慕容洧拔寨遁去,师古深入至石要岭,忽遇敌兵,与战,大败。师古旋师大潭,内怀惭惧,遂单骑降贼。自此失洮岷之地,但余阶成而已。[1](卷72,绍兴四年正月乙卯条,2册,34)
( 绍兴四年)五月,知寿春府罗兴叛降豫。[2](卷475,刘豫传,13798)
在宋金对峙中,“刘豫介然处于其中,势不两立,必求援于金”,[1](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丁卯引张浚言,2册,50)伪齐对南宋进行的不间断地挑衅和破坏,已超出了南宋朝廷的容忍限度。从南宋朝臣的奏疏中,可以看到伪齐很可能有介入并破坏宋金议和的行为:
臣观近者金人议和,托言刘豫所请。虽敌情叵信,然而中原残破,民力困瘁,不堪驱役,豫、麟父子特倚金人为重,以拒王师。如闻敌自有故,且倦于南牧,则议出于豫欲欵?吾问罪之举,延旦夕之命,理亦或然。今敌人遣使先至豫所乃来,而所持书辄有封疆之画,其为豫计无疑。陛下灼见其情,报书曲折,事理详尽,固应夺其狡谋,破其奸胆,不复敢肆桀骜,庶能听顺以定和约。[3](卷28,《面对第一劄子》)
綦崇礼所上奏疏是基于绍兴三年十二月,金人李永寿、王翊入宋,“请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且欲画江以益刘豫”[1](卷71,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条,2册,26)的事实。綦崇礼分析敌情,认为金人所议事既然“其为豫计无疑”,则南宋朝廷对于刘豫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为不得不作防备,因为和约只能建立在对伪齐“夺其狡谋,破其奸胆,不复敢肆桀骜”的基础之上:
然而犹可虑者,万一负恃强敌尚怀逆图,必欲窥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敌骑以来邀胁,则吾可以不为之备乎?今已过防秋,且远近传闻通使,人情恐便舒缓。臣愚欲望圣慈申戒沿江将帅,明远斥候,防扼险要,选练士卒,日讨于师,常如遇敌,以为先事之备,庶无后悔。苟和议遂成,亦未可以弛备,况今日耶?[3](卷28,《面对第一劄子》)
綦崇礼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那就是对于伪齐的绝对不信任,以及对其“奸胆”“桀骜”的必予讨伐之的激愤。这种情绪即使是在绍兴四年十二月金齐联合入侵将告失败之际也未曾改变。绍兴四年十二月,当尚书吏部员外郎魏良臣、阁門宣赞舍人王绘出使金国,“自金国军前还,入见”之时,侍御史魏矼即奏云:
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继有报聘,礼意周旋,信言可考,顷复专使寻好,未有衅隙。兹乃伪刘父子造兵端,本谋窥江,初无和意。使人未见国相,报书来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辙未远。[1](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条,2册,156)
魏矼所称“三遣和使”、“专使寻好”乃是指“王伦归,言金人要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尧等行。洎还,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韩(肖胄)、胡(松年)二枢密往。寻金使李永寿、王翊来聘,所需三事,故以章(谊)尚书、孙(近)侍郎往。及还,所议互有可否,独疆界一事未定”。[1](卷80,绍兴四年九月癸丑条引王绘言,2册,115)魏矼认为刘豫父子勾引金人所发动的南侵之战是对和议的根本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一切议和都是全然不可信的。同样的见解甚至来自于奉南宋朝廷之命出使金国的朝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一之绍兴四年十月辛巳条记载,“持国书物录,取天长路星夜前去”金国的通问使魏良臣于出发之际,“亦遣书状官梁植持禀目遗辅臣”,其云:
和议本为淮甸,今既进兵,百端恳请,终恐无益。况临难解纷,世无此理。自古两国议和,皆以势力相埒,不能相下,于是有议和修睦之请,息兵安民之议,未闻以弱和强。彼初无畏惮、曲意定和者也。澶渊之役规模宏远,昭然可见。比年诸将蓄锐练兵,志气思奋,百倍于前日,第以朝廷方笃信诈和之请,断然不疑,敛兵不动,以示诚意,遂遣使命,淹延岁月,堕欲奋之士气,乖违附之民心。今和议未定,敌兵已集。窃闻宣抚韩开府奋袂怒发,遂统全军绝江伺便,以进其行,踊跃如赴私仇,议者谓必能成功。独念建康控扼之地,闻朝廷已遣张太尉提兵迎敌,敌已压境,此行似不可缓。仍命刘开府相与应援,以破逆贼三不救之说。将和兵奋,敌气自慑,则衔命以往,宣国威灵,庶乎其有济矣。苟不知出此,止为退懦之计,效尤前辙,示之以怯,使吾军士气不扬,乘舆再动,社稷阽危,万一敌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扰,迟以岁月,人心苟安,则大事将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驰入不测之廷,是犹以羊委虎,至则靡尔,何功之有?
绍兴九月乙丑,伪齐诱金人大举进兵,分道渡淮,刘豫下伪诏南犯:“遣皇子麟会大金元帅,大兵直捣僭磊,务使六合混一。”[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刘豫伪诏,2册,120)庚午,通问使魏良臣等得国书,辞行,“至秀州则闻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1](卷80,绍兴四年九月庚午条,2册,123)魏良臣等既已在金齐入侵之际出使,则对“止为退懦之计”,“百端恳请,终恐无益”的认识更为透彻,所以语言也就更为激烈,以至视出使为“以羊委虎,至则靡尔”。
事实上,对于伪齐长期占据中原及其有利资源,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对南宋形成遏制之势,并图谋取而代之的图谋,南宋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明确,这也是南宋必须切割金齐,并坚决铲除伪齐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个问题,监广州寘口场盐税吴伸的分析可谓深透:
臣闻之,中原者譬如国朝之心,西蜀者譬如国朝之腹。中原既割据于伪齐,西蜀复几陷于勍敌,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国家之难止于安危,今也国家之难系之存亡。何哉?东南之地不过百郡,土地日削,形势日卑,于天下无三分之二,其地狭,一也;地倾而人众,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贫,二也;其土地薄而不厚,其水清而不深,无兴王之气,非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虽陛下谦德自保于全吴,至仁不争于天下,而百万之师坐糜廪禄,一岁之间国用不貲。设有旱干水溢之年,将如之何?又况土地日削,则财赋日少。财赋日少,则何以给士卒之费乎?臣窃谓,中原不取,则帝业不恢,中兴无期,危亡有兆。何则?金人虽强,实不足虑,刘豫虽微,其祻可忧。且如金人其来有时,其居不久,来则避之,去则复业,此不足虑也明矣。且如刘豫以臣窃国,因敌僭君,素无人望,唯多诈谋。彼以一旅之众当孤危之时,不一平之,设有大于刘豫,复据一方,将何以处之?呜呼!晋室之乱起于元海,继踵僭窃,终不能平,没晋之世不复故疆。今刘豫恃金人之势,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与我圣宋必不两立,势无俱存。彼若以利害痛诱金人进屯淮右,虽不交兵,纵未南渡,无所不脩,无所不寡,两军相持,积之岁月,必有存亡,将何所逃? 臣以谓先擒刘豫,则金人自定。[4](卷87,《经国》)
吴伸认为中原既为“国朝之心”,却为伪齐所占据,则其对南宋的威胁正可谓生死攸关。与之相对,吴氏更对南宋所据有的东南之地的“地狭”、“人贫”、“财赋日少”等涉及国家生存发展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中原不取,则帝业不恢,中兴无期,危亡有兆”的结论。吴伸还对金人南犯“其来有时,其居不久”与伪齐刘豫“以臣窃国,因敌僭君”的特点进行对比,提出“金人虽强,实不足虑,刘豫虽微,其祻可忧”的观点,并由此而引古证今,以“晋室之乱起于元海,继踵僭窃,终不能平,没晋之世不复故疆”与“今刘豫恃金人之势,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与我圣宋必不两立,势无俱存”作类比,以警示南宋朝廷,若不先灭刘豫,则南宋形势危矣。更何况“设有大于刘豫,复据一方,将何以处之”。正是从这样的忧虑出发,所以,当伪齐倚靠金人,步步紧逼以对抗南宋之际,吴伸认为,此时所应选择的对应策略便是“先擒刘豫,则金人自定。”
绍兴九月乙丑,伪齐勾结金人发动南犯赵宋的军事行动,南宋已经再无退路,所谓“避将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脱”,[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张浚言,2册,121)“豫父子逆乱如此……今乃挟强敌之兵,复入为寇,此安可容忍”绍兴四年十一月,高宗亲下手诏讨伐刘豫,宣言亲征:“叛臣刘豫惧祸及身,造为事端,间谍和好。签我赤子,胁使征行,涉地称兵,操戈犯顺,大逆不道,一至于斯。警奏既闻,神人共愤,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以俱生。”“念祖宗在天之灵,共刷国家累岁之耻,殪彼逆党,成此隽功。”[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2册,145)由此开启了南宋正面地、大规模地讨伐伪齐的战事。在宰相赵鼎、张浚等人全面运筹协调各方的努力下,南宋取得了“士气大振,捷音日闻”,[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戊午条,2册,148)的大好局面。绍兴四年十二月,金与伪齐退师,“金军已去,乃遣人谕刘麟及其弟猊。于是麟等弃辎重遁去,昼夜兼行二百余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1](卷八十三,绍兴四年十二月庚子条,2册,164)这就为金人最终废弃刘豫的伪齐奠定了必备的基础。“挫败伪齐与金人的联兵入侵,是南宋初期的大事件,无论是对南宋稳定地立足江南,还是最终与金人达成绍兴和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5](22)
二、和议乃权时之宜,以济艰难
赵宋朝廷自仓皇南渡,就一直处于金人的强势压力之下。靖康二年,金人废宋帝时即宣称“宜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以王兹土”,“赵氏宗人不预此议”。[6](《靖康要录》卷11,二年二月六日条)诚如王夫之所云:“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明州,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祜太后,南至虔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寄散地,而莫能自坚。”[7](《宋论》卷10《高宗》,177)从欲战而不敌,欲和而不能的危境发展到绍兴四年,应当说,南宋已经逐步改变了完全被动的局面,特别是在西部川陕一带与金人的争夺战中,南宋已经显示出不可小觑的实力。绍兴四年二月辛丑,“金右都监宗弼自宝鸡入犯,攻仙人关”,“与其陜西经略使萨里罕、伪四川招抚使刘夔率十万骑入犯”,[1](卷73,绍兴四年二月辛丑条,2册,41)在敌人的汹汹气焰下,南宋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及其部下奋力血战,击退敌人的进攻,“敌自是不敢犯蜀矣”。[1](卷七十四之绍兴四年三月辛亥条所引吕中《大事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绍兴四年三月辛亥朔条中对这次西部战事记载甚详:
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败敌于仙人关。初,金右都监宗弼与玠连战未决,玠遥与宗弼相见,且遣人谓曰:“赵氏已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谢曰:“已事赵氏,不敢有貳。”敌遣生兵万余击玠营之左,玠分兵击却之。贼怒,拥众乘城,玠遣统制官杨政以刀枪手深入。统制官吴璘以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敢退者斩。”敌分为二阵,宗弼阵于东,将军韩常阵于西。我军苦战久,遂退屯第二隘。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则形胜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吾度此敌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此地为蜀扼塞,死不可失,当守以强弩,彼不敢舍此而犯关。”玠从之。敌进攻第二隘,人被两铠,铁刃相连,鱼贯而上,璘督士死战,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莎里罕驻马四视,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诸军并力攻营之西北楼。统领官陇干姚仲登楼死战,楼已倾,仲以帛為绳,曳使复正。敌以火焚搂柱,仲取酒击灭之。玠又遣政与统领官田晟出锐兵,持长刀大斧击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随之。壬子夜,磊中大出兵,遣右军同统领王喜及王武等诸将分紫白旗入敌营,敌惊溃,将军韩常为官军射损左目。敌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军统制张彦劫敌横山寨,斩千余级。玠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是举也,敌决意入蜀,自莎里罕已下,皆尽室以来,既不得志,遂还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
文中不仅记载了吴玠等将士的忠勇义烈,更将“是举也,敌决意入蜀”的预期与“自是不复轻动”的结果相对比,以示这次战役对金人图谋的重创,同时也为南宋朝廷摆脱长期以来在西南地区的被动局面奠定了基础。在中部,绍兴四年五月,江西制置使岳飞先后收复郢州、襄阳、唐州,六月复随州,八月复邓州,自此,“襄汉悉平,川陕贡赋纲马道路,至是始通行无阻焉”。[8](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六,257)在东南,绍兴四年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所部自镇江进屯扬州,“邀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五军旗与敌旗杂出,敌军乱,弓刀无所施,而我师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捎马足,敌全装陷泥淖,人马俱毙,遂擒托卜嘉通赞远孙也。”[1](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2册,133)大仪镇之捷“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2](卷364,韩世忠传,11364)一方面是南宋“自敌骑蹂践中原,未尝有与之战者。今诸将争先用命,此成功之秋”;[1](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条引沈与求言,2册,134)另一方面则是金人“今士无斗志,过江不叛者独(韩)常尔,他未可保也”。[1](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庚子引韩常谓宗弼言,2册,164)南宋军队作战力的提高为宋金的抗衡奠定了基础,而宋金和议的权宜之策也因此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把和议建立在权宜之上,这就意味着和议的暂时性和不确定性,而其最终指向还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图谋恢复,正如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所言:“和议乃权时之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歩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1](卷66,绍兴三年六月丁亥条,1册,853)当然,以权宜为对策,必须以南宋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力量的实际改善和增长作为必备的基础。对此,翰林学士兼侍读綦崇礼的《面对第二劄子》论述最为详尽:
陛下神圣之资,英武之略,内有拨乱之志,而乃郁郁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请好,岂得已哉?徒以事势未竞,国步未夷,生民未安,故为计出此……非谓旧事可忘,中国可弃,敌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则约和之后,便欲高枕而卧,得乎?仰惟圣志,固将大有所为,兴起庶政,观时俟恤,期复旧业,不唯苟纾目前之急而已。臣愿陛下坚坐薪尝胆之志,励宵衣旰食之勤,深诏大臣,简贤能,慎名器,明殿最,严赏罚,申飭百执事之列,下至州县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媮堕,革因循之弊,去苟且之习,要使人人公心为国,诚意在民,而无养资尸禄,计日待迁之患,则众治举矣。于是生财积谷,缮甲治兵,啬用度,宽赋敛,以实民力,汰冗弱,精选练,以作士气。日伸月长,假以岁年,一旦起而用之,则大计可图,成功可必也。顾惟今日权宜之议,所利在此。昔周宣复古,盖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越之报吴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兹非往事之明验,而陛下之所熟闻者乎……臣愚窃以为,今日之议论规模宜不出三者:恢复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无所为,下也。语其上,则今之力诚未可为;守其下,则吾之势不可复立;惟度时量力,就其中者为之。中者既成,则其上可驯而致。苟止于下,则虽志于中者,有不可得矣。臣愚欲望陛下发自圣志,明诏大臣,无取高言以害实治,毋偷苟安以玩岁月,议论审其可用,规模定其适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责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间,治功不成,未之见也。[3](卷二十八)
与韩肖胄的意见一样,綦崇礼也是基于“非谓旧事可忘,中国可弃,敌情可信,能恃以久安”的认识,把“事势未竞,国步未夷,生民未安”作为权宜之策的立足点,因为以当时朝廷的实力,欲“恢复中原,以成再造之功”,则“今之力诚未可为”;若“苟目前之安而无所为”,则“吾之势不可复立”,所以,度时量力,惟以“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为致力之处,但这绝非最终目的,与之相对,“坚坐薪尝胆之志,励宵衣旰食之勤”的真正指向还在于“日伸月长,假以岁年,一旦起而用之,则大计可图,成功可必也。”事实上,綦崇礼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朝臣的议论,因为从当时南宋的总体形势来看,“今士气未振,难以议战,但当谨守封疆,如沿江一带,自襄阳、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诸郡如合肥、寿春、盱眙、广陵等处,各屯军马,西与四川形势联接,使上下有备,表里如一,庶几可以抗御,虽未剪去凶逆,南北之势成矣”。[1](卷77,绍兴四年六月丙午条引吕祉《东南防守利便》,2册,86)然而,要实施这一计划,还需要朝廷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方略,这也就是綦崇礼提出的“议论审其可用,规模定其适中”的内涵,其中包含着诸如亟待解决的大小官员因循苟且之弊、将帅不能彼此支持配合、整顿军队纪律等一系列问题。在当时,这些问题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必须根治的痼疾。
高宗对官员的不任责现象十分不满。他一方面“留意人物,固欲得贤士大夫协力以济国家之难。”[1](卷81,绍兴四年十月癸未条,2册,129)另一方面则指斥朝堂苟且之习:“数年以来,庙堂玩习虚文而不明实效,侍从、台谏搜剔細务而不知大体,故未能靖祸乱、济艰难。”[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戊申条,2册,144)针对“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责,每事取决”的现状,高宗谕朱胜非曰:“自今宜专责长贰,毋得循习苟且。卿等当进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图恢复之计,繁文末节,非所以委付大臣者。”[1](卷76,绍兴四年五月壬申条,2册,74)但是被高宗寄予期望的宰辅重臣却未能尽如人意:“赵氏自播迁之后,所与谋事者不过六七辈。吕颐浩横议狂直,失大臣风,兼有私门之僻,常为利所移。朱胜非虽老臣,然守法具位,怯于图大事。秦桧智小而谋大,翟汝文才有余而量不足。赵鼎虽大器,然孤立在外,进不容于朝。至于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顾行,又无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闒茸士,非宰相才也。况复互为朋党,此入彼出,视相府如传舍,一旦仓卒,其君惸惸于上,百官泛泛于下,无有任其责者。”[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丁丑条引伪奉议郎罗诱所言,2册,,98)虽然这样的评价出于敌人之口,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朝廷重臣的难任其责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朝廷之外,主兵的将帅乃国家安危利害所系,但彼此之间又交恶不已,这也是金齐无所忌惮的原因之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四,绍兴五年正月丁未条曾记载参知政事沈与求所言:“臣闻谍者言,刘豫诱金人,以我诸大将有不和者,故拥众南来,直欲渡江。”其实,对于将帅的不和,朝中大臣早有论议,祠部员外郎范同就曾专章议论此事云:
师克在和,大抵刚果豪键之士以气相高,始由小嫌,寖成大衅。然古之贤将急公家,弃私仇,舍怨忘愤,终成令名者,盖不乏人。陛下拔用才杰,礼遇勋贤,备极荣宠,固将凭藉忠力,扫除氛祲,一清寰宇,恢复祖宗之业。而道途窃议,以为将帅忘辑睦之义,记纤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轧已,或恃勋劳而排抑新进。审如是,他日必有重贻圣虑者。[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乙卯条,2册,,90)
范同所言乃是事出有因,当时朝廷倚重的大将中,“刘光世、韩世忠久不协,而岳飞自列校拔起,颇为世忠与张俊所忌”。[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乙夘条,2册,90)事实上,对将帅不和的担忧已经是当时朝臣的共识。殿中侍御史常同所上专章中所称大将“蒙陛下厚恩,不思协心报国,一旦有急,其肯相援”[1](卷76,绍兴四年五月辛酉条,2册,73)的忧虑很快就在绍兴四年十月抗击金与伪齐联兵入侵的关口显现出来:
时光世军马家渡,俊军采石矶。上命趣二人往援韩世忠,而光世等军权相敌,且持私隙,莫肯协心。(侍御史魏)矼至光世军中,谕之曰:“敌众我寡,合力犹惧不支,况军自为心,将何以战? 为诸公计,当灭怨隙,不独可以报国,身亦有利。”[1](卷81,绍兴四年十月甲午条,2册,137)
将帅不和固然关系到国家安危,而士卒无纪又成为影响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南宋的主要军力来源多为盗寇,“绍兴诸大帅所用之兵,皆群盗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后,弱甚矣。张浚、岳飞受招讨之命,韩、刘继之。于是而范汝为、邵青、曹成、杨幺之众皆降而充伍,乃以复振。”但是,这样的军力,其素质堪忧,所谓“不以败为忧,不以走为耻,不以旦此夕彼为疑。进之务有所卤获以饱众,退之知不可敌而急去以全其军。”“欲使之争封疆于尺寸,贸身首以立功,未有能胜者也。”[7](王夫之《宋论》卷十之七,182)绍兴三年正月,襄阳鎮抚使李横破颖顺军,败伪齐兵于长葛县,紧接着复颍昌府。二月,传檄诸军,收复东京,其形势可谓大好,以致刘豫急遣使诣金左副元帅宗维求援。但是,“横等军本群盗,虽勇而无纪律,见敌所遗子女金帛,乃纵掠数日,置酒高会。敌闻而易之,豫遣其将李成以二万人迎敌,金遣左都监宗弼援之,败皋于京城西北牟駞冈。横等军无甲,皆败走”,“颍昌复陷。”[1](卷63,绍兴三年二月己巳条,1册,828)绍兴四年十一月,和州为金所破,左朝议大夫知和州皇甫彦率军民据守麻湖水寨。“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遣摧锋军统制赵秉渊、统领官杨贵将其军民乘舟南归。秉渊等因纵火大掠,士民仓猝引避,水阔舟小,沉溺甚众。彦之金帛妓女皆为所夺”。[1](卷八十二,绍兴四年十一月辛未条,2册,154)类似的事例在绍兴年间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胡松年提出:“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岂能成功邪?”[1](卷七十九,绍兴四年八月癸未条,2册,,103)应当说,将帅间的不能相互配合、军队纪律的亟待改善都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也成为南宋朝廷不可能在绍兴四年之后乘胜北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面对诸多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朝臣们提出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下,南宋朝廷所采取的谨守封疆,“兴起庶政,观时俟恤”的权宜之策,所执行的“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的方针,应当说是务实的、现实的态度。
以上结合南宋朝臣的奏疏,从绍兴四年的军事、政治状况入手,探讨了南宋朝廷的对伪齐、对金所实施的不同策略。由此可以看到,和议的背后并非简单的“软弱”二字可以概括,其中包含着各种繁复的因素,这是上至高宗,下至朝臣都必须考虑的。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宋史[M].中华书局,1985.
[3]綦崇礼.北海集[M].四库全书本.
[4]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Z].四库全书本.
[5]陈忻.从绍兴四年高宗手诏看其进取之志[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3,(4).
[6]《靖康要录》[Z].四库全书本.
[7]王夫之.宋论[M].中华书局,1964.
[8]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編续编校注》[Z].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