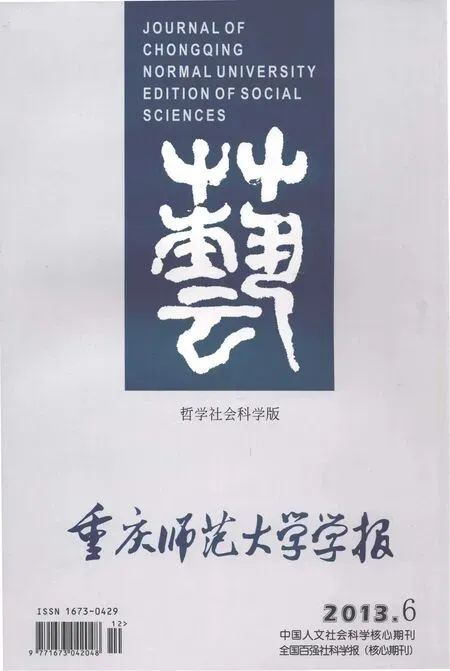“隐秀”与《文心雕龙》的文学形象特征论
2013-04-02王少良
王少良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具有严谨的系统性,书中围绕着文学的基本问题形成了系列的阐述,但其中是否有关于文学形象特征的专论,学界以往并没有确认其具体的篇目,这主要是由于对《隐秀》的篇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所致。“隐秀”的概念为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首次提出,作为古典文艺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隐秀”概括了“以少总多”、“言近旨远”的形象特点,揭示出了抒情性文学形象一般性的审美特质,为我们理解古典文学形象特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途径。
一、“隐秀”与文学形象的特质
对“隐秀”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在理解方面,主要有风格论、鉴赏论和修辞论等不同角度,其中影响较大的一说认为《隐秀》篇谈的是“含蓄”和“警策”两种修辞方法。清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云:“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清纪昀评《文心雕龙》把陆机《文赋》立警策文句和“秀句”联系了起来,认为陆机《文赋》所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就是刘勰所说的秀句。[1](333)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以炼章法为隐,炼字句为秀。秀而不隐,是犹百琲明珠,而无一线穿也。”近人刘师培认为“有警策而文采杰出,即《隐秀》之所谓秀”[2](148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提出:“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3](633)今人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认为隐指婉曲,秀指精警,“隐秀”分别讲修辞学上的婉曲和精警。上述评语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都认为“隐”指篇中文辞的隐意,“秀”是篇中秀出的警句。总结《隐秀》篇题旨,前人提出了“隐篇秀句”的说法。《隐秀》篇称:“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补文中亦云:“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如欲辨秀,亦惟摘句。”这恐怕就是这种说法的依据。
从文章修辞技巧上来理解“隐秀”,固然能体现作家创造形象的表现手法,但最终还没有从形象创造的整体性上来看问题。人们常谓《文心雕龙》是“泛论文体”的文章学著作,它的文体涵盖面是很宽的,这种认识固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看《隐秀》篇包括补文在内的文字,皆“论诗而不论文”,这说明《隐秀》篇在《文心雕龙》中是一个专属篇目,它探讨的对象是诗体文学或文学的诗性特征,具体来说就是文学形象的构成和艺术表现特征的问题。有的论者认为“隐秀”与《春秋》的“微言大义”笔法有联系,这在《隐秀》篇里是找不到根据的。张少康先生《文心雕龙新探》(齐鲁书社,1987)一书中,曾提出“隐秀”范畴为《文心雕龙》的文学形象特征论。这一学术新见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正确理解《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构成,但其中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的形象中,隐与秀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单独解释“隐”或“秀”的修辞效果并不能完整地理解和评价作品的形象。《隐秀》篇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指出:“夫文以致曲为贵,故一义可以包馀,辞以得当为先,故片言可以居要。盖言不尽意,必含馀义以成巧,意不称物,宜资要言以助明。言含馀义,则谓之隐,意资要言,则谓之秀。隐者,语具于此,而义存乎彼;秀者,理有所致,而辞效其功。”这里是就言辞而论,但没有离开篇意。接下来又说:“然则隐以复意为公,而纤旨存乎文外,秀以卓绝为巧,而精语峙乎篇中……大则成篇,小则片语,皆可为隐,或状物色,或附情理,皆可为秀。”[4](195-196)这里论及篇意,但没有舍弃篇辞。黄侃的观点是将隐秀放在成篇与成辞的统一关系上来看待,所以我们觉得并不是单纯的论修辞技巧。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评论说:“文家言外之旨,往往即在文中警策处,读者逆志,亦即从此处而入。隐处即秀处也。”[5](141)这里的观点可谓深得艺术形象之奥妙。“隐”的表达方式在于形象的寄托,借助形象描写或情景的烘托传达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只有透过全篇的寓意才能领略得到。“秀”乃为秀丽、秀逸之态,它是文学欣赏“披文入情”的着眼点。在文学性描写中,作品的秀颍之处一般是不能用某一个精炼的语句概括出来的,隐义和显象的融合才能构成独特的形象。例如《隐秀》篇举出的秀句“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诗句出自晋人王赞的《杂诗》:“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夕往仓庚鸣,今来蟋蟀吟。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这首诗感情真挚,不事雕琢,流露出怀乡之愁,故刘勰评其为“羁旅之怨曲”。显然这个评语是对全诗的整体评价,单从辞句上看,诗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力,而且还有多处模拟《诗经》和古诗的痕迹。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评诗十分注重作品通体华美的效果。《隐秀》篇提出:“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隐秀》篇补文云:“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秾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显然,《隐秀》篇这样大段的文字都是对文学形象审美特征的具体揭示,如果脱离了作品的形象,这样的效果是不能单单从文词或句意中产生出来的。
“隐秀”论是成熟的文学形象论,隐秀范畴的提出与我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结合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来考察,谈到先秦至唐前文学的艺术性和形象性,首先应注意的是形象的抒情表意性特征,这一点与西方古代文艺思想有显在的区别。西方文学理论奠基在史诗和戏剧文学的叙事性特点之上,因此,情节、结构、典型等概念是其核心。亚里士多德《诗学》就有了文学典型理论的萌芽,他指出诗和历史不同,“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6](29)本于艺术摹仿观念来认识文艺特征,《诗学》观点认为文学不仅再现事物的外形,而且还要反映其内在的必然性和普遍规律,相应的手法就是典型概括和现实的描写。相对于欧洲文学,我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发展迟缓。六朝以前,以叙述情节和刻画人物形象为特征的叙事文学尚未成型,成熟的小说直到唐代才开始出现。在古代小说、戏曲获得发展成熟以后,相应的理论总结如人物性格刻画、典型塑造及情节的铺设等方面的阐述也相继出现,这已是明代以后的事情了。在刘勰所处时代,文学理论批评主要建立在诗论文评的基础上,谈文学的艺术特征,也主要着眼于抒情文学的特征,注重以“比兴”手法创造富有情感的艺术情境。陆机《文赋》称:“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隐秀》篇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上述两者的见解是相通的,他们对艺术形象的认识反映了文学自身固有的规律。文学是以形象反映生活和情感的艺术,鲜明的对象性描写,充沛的情感贯注,形成生动感人的艺术画面,这是文学的美感特征所在。对此,刘勰以“余味曲包”加以概括,要求文学创作除了字面的形象性描写之外,还要具有引人联想的可塑性和再造性。
二、“隐秀”论的哲学思想本原
“隐秀”是一对文艺理论范畴,也是一对哲学范畴。刘勰提出的“隐秀”论,是就文学形象和形象性来谈的,而“形象”与“艺术形象”的区分,就在于其中是否具有意义的关联。在我国古代,作为“寓意”之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的卦象。“隐秀”论的提出,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周易》的象征手法。《周易》被称为“托象以明义”的哲理之书,易卦的每一条爻辞一般都有“设象辞”,取象征手法“以象喻理”,由此形成象与意之间的包容关系,故《易传》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文心雕龙》对《周易》经传内容多有运用,全书各篇经常引据《周易》卦象,援用《周易》文辞,以说明文学的形象性特点。《原道》篇说:“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艰深。”《宗经》篇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征圣》篇说:“书契断绝以象《夬》,文章昭晰以效《离》”;“四象精义以曲隐”。这些地方都谈到了易象,标明刘勰从“宗经”的立场上确立了论文的标准。《系辞》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庄氏曰:“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为四象也。”钱钟书《管锥编》谈到:“‘象曰:天行健。’《正义》:‘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地中木升也;皆非虚言,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7](11)“象”在《周易》中是一个形象的象征体,而“四象”之不同即在于取喻方式的不同,这已切近文学形象的创造方法。古人论文早已揭明《周易》卦象与文学意象之间的关系。明代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说:“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隐秀》篇就“隐”的特点说到“爻象之变互体”,篇末赞曰:“辞生互体,有似变爻。”“互体”指在一个卦象之中又含有其它卦象的孕体,但它不是指体式的重复,而是指意蕴的复指性特点。《周易》的立象偏重于生活事象的描述,但其所立之象主要是写意,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去表现一定的生活哲理,这一点使《周易》这部哲学著作同时兼有文学特征。
《隐秀》是《文心雕龙》唯一的一个残篇,从现存的文字来看,篇中论“隐秀”征引的典籍仅有《易经》,取用爻象的构成和变化形式来比喻文学形象的特点,这实际上是一个玄学的话题,因此篇中论文的义脉也是本着玄学“言意”之辩的基本论题而展开的。我们知道《文心雕龙》的思想融合儒、道、释三家学说,体现了当时玄学思潮在文学理论上的摄入。玄学兴起于汉末,魏晋之际发展到极盛。《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易传·文言》“天玄而地黄”,这里都有幽微玄远的含义,为玄学命名所本。“有无本末”之辨是玄学的基本命题,而《周易》《老子》《庄子》三书被称为“三玄”,因此成为玄学谈辩所依据的文本。“道”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蕴含深邃的美学思想。道家哲学所称的“道”无具体规定性,应该从“有无”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其中自然与名教之辩涉及哲学本体的探求。“言意”之辩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王弼、嵇康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一是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言论”。两派观点各自成论,在玄论言辩所依据的经典中各能找出根据,这说明在玄学“言意之辨”的论题里,原本就存在着两个基本层面的理蕴。《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这代表了“言不尽意”的观点。《易传·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这表明言可尽意,不过言和意之间需要经过“象”来作为中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解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玄学论的这些思想用于文论,可以揭示文学写作思维内容与语辞概念的关系,利用语言与思想的非同一性,故意造成“言不尽意”,以产生含蓄的艺术效果,这对《文心雕龙》的“隐秀”论产生直接的影响。汤用彤先生说:“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两句:‘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当为《隐秀》之主旨。‘秀’谓‘得意’于言中,而‘隐’则‘得意’于言外也。自陆机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者’,至刘勰之‘文外曲致’,‘情在词外’,此实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所讨论之核心问题也,而刘彦和《隐秀》为此问题做一总结。”[8]对于“言意之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并没有简单地持取某一方面的观点,他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的统一论者。学界有观点认为刘勰的隐秀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言意之辩在文学理论中的反映,是“言不尽意”论与“言尽意论”两者的合题。[9]“隐秀”论暗含文学形象构成论的思想,它在哲学上沉积了魏晋玄学的主体特征,体现玄学所造成的美学意趣。庞朴先生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此之间还有一个“形而中”者谓之象。“道无象无形,但可以悬象或垂象;象有象无形,但可以示形;器无象有形,但形中寓象寓道,或者说,象是现而未形的道,器是形而成理的象,道是大而化之的器。”[10](231)《庄子·天地》篇讲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这则寓言通于文学形象的特点,“象罔”表征有形和无形、虚和实的结合。宗白华解释说:“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形象“非有非无,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象的象征作用。[11](71)文学作品的语象是表层空间,它的展现形态丰富多彩,含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而“象外之象”则具有意象的自我超越性。“语象”处于文本表象与深层含蕴的中间层面,只有准确地把握住它,才能由此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形象意蕴或思想意义。
三、“隐秀”与“神思”“比兴”的关系
《文心雕龙》书中的“隐秀”论不仅仅在于《隐秀》一篇,而是以《隐秀》篇为主论,此外《原道》《宗经》《征圣》《神思》《体性》《比兴》《情采》《物色》等篇目也与这一论题有关联。因此,解决“隐秀”问题就应该联系文学的创造思维和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来加以研究。刘勰谈文学形象的“隐秀”特征,不限于一般地探讨写作技巧,而是紧扣《神思》和《比兴》两论展开探讨,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活动的整体认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谈到:“然隐秀之原,存乎神思,意有所寄,言所不追,理具文中,神余象表,则隐生焉;意有所重,明以单辞,超越常音,独标苕颖,则秀生焉。”[4](195-196)“隐秀”是艺术形象的特点,也是作家“神思”创造的产物。陆机《文赋》说:“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隐秀》篇说:“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该篇补文中也说道:“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于佳丽之乡。”上述文中说到的“心术之动”,“驰心玄默之表”,都是指神思围绕意象而展开活动。《神思》篇有“烛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的说法,讲的是作家的心意之象在作品中的结成方式。篇中论及作家创作的思维过程说:“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王元化《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归结这一段文字指出:“作家往往在作品中对于某些应该让读者知道的东西略而不谈,或写而不尽,用极节省的笔法去点一点,暗示一下,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吝惜笔墨,而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想象活动。”[12](105-106)在《隐秀》篇中,“隐”乃是情感的内化形式,含蓄蕴籍而不直质,言有尽而意无穷,而“秀”则是它的外在肌肤。陆机《文赋》谈到“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刘勰在《体性》篇中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附外者也。”两者都是神思活动由隐到显的创作过程。《文心雕龙》创作论“剖情析采”二十篇,很多篇目之间都有相互勾连,其中《神思》《体性》是从创作规律和创作过程上来谈物我关系的,而《隐秀》《物色》等篇则谈出了物我关系在艺术形象中的结成方式。《比兴》篇云:“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物色》篇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里谈的就是艺术想象,作家在想象构思中,其思维活动并不舍弃“物”的具体感性特征,而是通过外物的感发产生联想,在对客观事物的体认当中熔铸意象。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谈到:赋、比、兴这组范畴涉及诗歌艺术中“意”和“象”之间以何种方式互相引发,并互相结合成统一的审美意象,而这种审美意象又以何种方式感发读者,它们涉及审美意象产生的方式与结构的特点。[13](76)《隐秀》与《比兴》有密切的关联,“隐秀”是就形象而论,“比兴”是就方法而论,方法的确立是通往形象结落形式的必要途径。《比兴》篇谈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比显兴隐”,这在创作上就会直接形成“隐秀”的特点。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有言:“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十六篇,首系之兴,风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颂二,注曰:‘兴也’。而比赋不称焉。盖谓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也。”“比”意是以直言的方式来比附,运用到篇中自然容易造成生动鲜明的形象。《物色》篇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刘勰用《诗经》作品为例,说明比法在能够对事物的描摹状溢目前。《比兴》篇解“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故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篇中用了“睹物起情”、“依微拟议”这样的字样,标明它采用暗示或象征等手段来兴起感情或委婉托讽,因此会产生含蓄蕴藉的效果。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区分“比兴”特点有一段很好的概括说明:“兴之为体,兴会所至,非即非离,词微旨远,假象于物,而或美或刺,皆见于兴中。比之为体,一正一喻,两相譬况,词决旨显,体物写志,而或美或刺,皆见于比中。故比兴二体,皆构造虚词,特兴隐而比显,兴婉而比直耳。”[2](1336-1337)
刘熙载《艺概·文概》称:“《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14](21)这段评语指出了“隐秀”论所具有的针对性和理论意义。《定势》篇论到“自近代辞人,率有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在刘勰的文学史评价中,汉代辞赋家和六朝诗人的“弃兴用比”,造成了当时文坛的新奇、华丽、轻绮之风,他们的作品缺乏深刻、深隐的思想感情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隐秀”论的提出具有扭转时代文风的作用,它是针对南朝文坛注重刻削雕琢风气而提出的。这在《文心雕龙》中有多处论及。《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情采》指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物色》篇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隐秀》说:“或有晦涩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刘勰对宋齐以来文坛创作风气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作品流于刻削雕琢,不能唤起读者的审美兴趣。在刘勰看来,自《诗经》作者直至战国的屈宋,在创作上都是兼取比兴,斟酌用之,使二者相济相生,所以要纠正这种偏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回归儒家经典,取法“志足言文”、“情信辞巧”的为文准则。
四、“隐秀”与“意境”的创造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提出:“夫隐秀之义,诠明极艰,彦和既立专篇,可知于文苑最要。”[4](195-196)谈“隐秀”问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话题,因为它是文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涉及的方面也十分广泛。“隐秀”范畴在《文心雕龙》的文论中之所以显得最为重要,是因为它属于文学的艺术表现论。依“隐秀”来论文学形象,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隐秀”不是形象本身,而是透过作品文辞所显现的形象性特征。《隐秀》篇围绕这一核心,广泛论及文学创作的手法和意境的构成等问题。就文学的意境创造而言,作品形象的构成有赖于情与景、意与象的交融统一,其中包含着形与神、隐与显等辩证关系的处理,最终要使形象获得意义的显现,体现“以少总多”、“辞约旨丰”的审美特质,这自然也涉及到“隐秀”论的创作手法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意境”概念最初为署名王昌龄的《诗格》提出。其中说到诗有三境:物境“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乐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明胡应麟《唐音癸签》记王昌龄语:“为诗在神之于心,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上,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神似。”事实上,就诗境“了然境象”的特点来说,刘勰在“隐秀”论中已对意境有了准确的把握,而且作了完整的理论概括,可以说“隐秀”论就是“意象”论和“意境”论的最初形态。《庄子·逍遥游》有言:“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在文艺审美上,人们说到文艺作品有意境或有境界,究其实质是指具有审美意义的想象空间。有研究者指出,刘勰《隐秀》篇所讲的隐和秀,其实就是讲的隐蔽与显现的关系。“文学艺术必具诗意,诗意的妙处就在于从‘目前’的(在场的)东西中想象到‘词外’的(不在场的)东西,令人感到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15]《隐秀》篇赞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很明确,这四句是说作品的形象意蕴曲折深厚,犹如卦爻变动而产生新的含义一样,咀嚼文辞的意味,就会有言意之外的体味。
刘勰论“隐秀”,联系到了形象意境的生成关系上,这表明他从文学的艺术构成上分析了形象的特质,对文学的艺术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征圣》篇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宗经》篇说儒家经典为后世文章的典范,其特点在于“根抵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刘勰认为儒家的经典是后世文章写作及文学创作的范本。基于宗经的观念,刘勰对儒家经典之文有偏于抬高的倾向,但他所总结的这种特点用在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上,就是对意境的最好揭示。
正是由于具备这样的意义,所以“隐秀”论对后来艺术领域的意境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唐殷璠《河岳英灵集》称赞王维的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皎然《诗式》卷一讲道:“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司空图论诗提出了“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和“味在酸咸之外”的观点,他在所著《诗品》中抓取风格外象来描述诗境,侧重欣赏含蓄蕴藉、冲淡清远的风格和境界。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圣俞的话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而语工,得前人所未道,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严羽《沧浪诗话》揭明诗歌的审美特征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些都是对文学的诗性审美特征的揭示,与“隐秀”论有渊源的关系。“隐秀”范畴是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揭示,这不仅在文学作品,而且还融汇到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批评中,成为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共同的美学旨趣。钱钟书先生对此曾有论述:“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曰‘取之象外’,曰‘略于形色’,曰‘隐’,曰‘含蓄’,曰‘景外之景’,曰‘余音异味’,说竖说横,百虑一致。”[16](1358)古人对书画艺术的评论,注重用笔含蓄、意韵远出的境界,可与刘勰的“隐秀”论相印证。朱光潜先生也推此意论及美术作品:“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17](69)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固然因凭借不同的物质媒介而形成手段上的区别,但它们在形象构思上也共同涉及到画面的结构与营造问题。文艺作品所容纳的情感不是直接呈示的,而是以形象来构成意义的比附,借以引发读者的想象、联想,生成实相之外的审美境界。
[1]纪晓岚评注文心雕龙[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2]詹 锳.文心雕龙义证(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黄 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中华书局,2007.
[6]亚里斯多德.诗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1979.
[8]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1).
[9]王锺陵.哲学上的“言意之辨”与文学上的“隐秀”论[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十四)[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庞 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海天出版社,1995.
[1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4]刘熙载.艺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张世英.艺术哲学的新方向[J].文艺研究,1999,(4).
[16]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中华书局,1979.
[17]朱光潜全集(第一卷)[Z].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