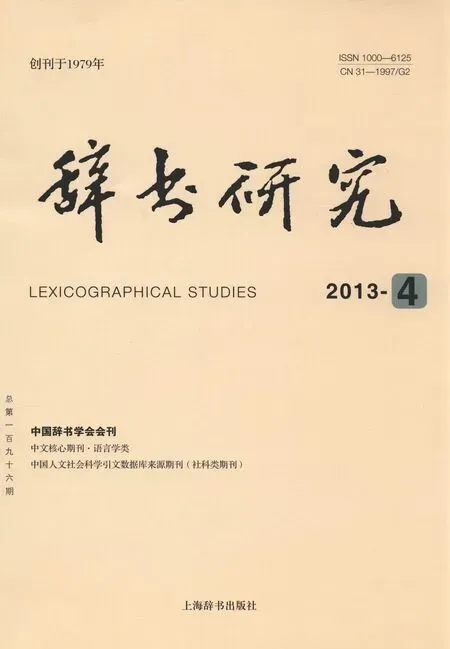近三十年英语词典编纂最新进展——*理论借鉴与实践反思
2013-04-02雍和明
雍和明 彭 敬
随着英美软硬实力在20世纪的延续性提升,英语作为主要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得到无可争议的认可。而作为英语语言重要载体的英语词典,借助19世纪的雄厚基础与厚积薄发的发展后劲,在20世纪最终成为国际词典领域中鹤立鸡群的一大家族。牛津英语系列词典和韦氏英语系列词典是这个家族中的杰出代表,引领着20世纪乃至新世纪英语词典的理论和编纂技艺的革新。当代语言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等崭新领域的陆续出现和逐渐成熟,使英语词典编纂与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催生了学习词典、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等新型词典和新型词典媒介,实现了英语词典与技术平台的革命性的整合。
回顾近三十年英语词典编纂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人们不禁惊叹其发展规模、速度、理论创新与技艺突破。其理论建树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性展示。(雍和明2000,2004,2010)从实践层面看,近三十年英语词典编纂给世人留下了众多富有开创性的技艺与方法。这里侧重探讨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已经产生广泛影响、具有应用推广价值、带有突破性甚至是革命性的词典编纂技术,以期对汉语词典编纂及其未来发展有所启迪。
近三十年来最具突破性的英语词典编纂技术非电子信息技术在语料库建设中的应用莫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语料库就不可能有近三十年来英语词典的繁荣。语料库最初是靠人工积累卡片创建的。运用人工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源于德国的语文学研究传统。生于德国、具有师生关系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Franz Boas、Edward Sapir等都强调语料获取的自然性和语料分析的客观性,重视使用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语言分析方法。
运用人工语料库编纂词典的最为经典的案例莫过于《牛津英语词典》,其早期编纂依靠人工收集语料,初版正文中400多万条引证全部依仗手工收集。1921年,美国教育家Edward Lee Thorndike建立了450万词左右的英语文章语料库,直接服务于语言研究、英语教育、词频统计和词典编纂。然而,利用卡片收集语料,效率低下、差错率高、检索麻烦、分类困难、携带不便等严重缺陷在所难免。
随着第一部计算机于1946年在美国诞生,以键盘录入方式创建的语料库开始出现,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BROWN语料库和70年代英国LOB语料库为先驱,实现了由手工语料收集向计算机语料库建设的转型。光学字符识别和机读文本技术的应用使计算机语料库再次转型升级,以80年代的COBUILD语料库和Longman/Lancaster语料库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90年代的英国国家语料库为代表的第三代语料库问世。世界上许多出版机构、研究部门、大学乃至个人都创建了规模不等的英语语料库,作为英语研究和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基础性工程。
目前最具国际性的语料库当数The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国际英语语料库,简称ICE),由Sidney Greenbaum于1988年提议建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赞比亚、肯尼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英语语料库。从20世纪后期开始,特别用途语料库,如英语用法语料库、方言调查语料库等专门用途的语料库陆续出现,近十年来通过因特网实现检索的在线语料库更是不胜枚举,规模高达50亿词次。有关专家预言,未来十年将出现1万亿词次的超级语料库。这些语料库以多元的语料题材、惊人的信息存储量、超强的可塑性、高超的反应技术、简易的分档归类、便利的检索导引、稳定的工作性能等特征,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英语词典编纂理念,使词典编纂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有了语料库,词典编者借助程序软件检索有关语词,统计使用频率,区别不同用法,了解语用信息,分析搭配情况,并借助有关信息编纂、补编和修订词典,开发和革新词典品种和类型,提高编纂效率,缩短修订再版周期,出现了牛津词典系列、朗文词典系列、柯林斯词典系列、钱伯斯词典系列、麦克米伦词典系列、韦伯斯特词典系列等依靠语料库开发的、传统编纂技艺无法企及的当代英美词典。
然而,汉语语料库,无论从技术、规模还是数量上看,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语语料库。目前,国外仅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历时汉语语料库——The Sheffield Corpus of Chinese(谢菲尔德汉语语料库,简称SCC,http:∥www.hrionline.ac.uk/scc/)、兰开斯特大学的共时汉语语料库——The Lancaster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兰开斯特汉语普通话语料库,简称 LCMC,http:∥bowland-files.lancs.ac.uk/corplang/lcmc/)等。
海外仅有台湾大学语言研究所的The Academia Sinica Ancient Chinese Corpus(台大古汉语语料库,简称 ASACC,http:∥corpus.ling.sinica.edu.tw/)和 The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台大现代汉语平行语料库,简称 Sinica Corpus,http:∥www.sinica.edu.tw/SinicaCorpus)、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 A Datab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s of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220—589)(魏晋南北朝古代汉语文本库,http:∥www.chineseupress.com/promotion/chant/weijin folder/weijin info.html)等。
大陆汉语语料库也是凤毛麟角,仅有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The Peking University Corpus(北京大学语料库,简称 PUC,http:∥ccl.pku.edu.cn.ccl corpus.jsearch.index.jsp?dir=gudai),教育部“教育振兴专项资助项目”支持建设的CCL语料库(简称 CCL,http:∥ccl.pku.edu.cn/yuliao contents.asp,含现代汉语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库、汉英双语语料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委员会主持建设的现代汉语书面语通用平衡样本语料库“国家现代汉语语料库”(简称CLR,http:∥www.clr.org.cn/productions.jsp)以及“古代汉语语料库”(简称 CNCORPUS,http:∥www.cncorpus.org/ACindex.aspx)等。
上述汉语语料库,除少数收录共时汉语语料之外,大多数是古代断代汉语文本的电子版,既没有根据文本类型或题材分类组织,也没有必要的功能标注,所选择的内容更没有全面涵盖所在历史时期的文本体裁,规模属于中小型,只有个别声称规模超过1亿字,对于历时语言分析和共时语言观察能有所帮助,但缺陷非常明显,用于词典编纂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一部真正基于汉语语料库开发的汉语词典。
语料库技术开发迟缓、语料库建设滞后、人才建设落后、文化强国意识薄弱等因素严重制约中国成为世界辞书强国,阻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大业,使中华文化、汉语语言和汉语教学潜在的软实力缺乏载体,难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彰显。所以,应该将建设超大型汉语语料库工作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整合国家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力量,从国家层面整体推进这项决定全局的基础性工作。
从词典编纂技术角度看,电子信息技术催生了新型载体词典。多媒体词典是计算机信息技术与词典编纂理论和实践融合的结晶。计算机技术在词典编纂和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给词典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使词典信息呈现媒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音像俱全的新型词典信息载体——多媒体词典,即袖珍电子词典、CD—ROM词典和网络词典,因携带方便、检索快捷、信息量大、功能面广等特点得到用户的普遍认可,受到越来越多开发商的重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自20世纪后期起非常热衷于多媒体词典的开发和营销,取得了巨大成功。英美英语词典基本上实现了所有版本的光盘化、电子化和网络化运行。目前,词典运行微型媒介化(如移动、Ipad、Ipod运行系统)在英美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
根据“在线词典索引大全”网站(www.yourdictionary.com)的关键词搜索统计,现在网络词典已经多达1700部,从普通型到专门型,从单语型到双语型,无所不包,涉及世界上230多种语言。“它们准确地反映了网络词典学发展的空间。”(Carr 1997)近年来,由于Ipad、Ipod和手机媒介的词典信息运行技术的开发,检索工具随处可见,随时可用。“移动系统”(Mobile Systems)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移动系统”在词典信息多媒介、跨平台移动开发领域当属先行者,已经成为个人移动生成软件的引领者。该公司开发的OfficeSuite Professional for Android是一款极具特色的移动办公软件,能够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装置生成、阅读和进行微软文字处理,运行Excel、PowerPoint文件和附件,查看PDF文本等,更可以通过手机界面查阅词典。目前,“移动系统”智能手机软件通过MSDict电子格式载入了一系列基于世界顶级出版机构(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柯林斯出版公司、杜登出版公司、McGraw-Hill出版公司等)出版的移动词典和参考书,如多个版本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The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Complete&Unabridged(《柯林斯全本英语词典》2011)、The Collins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柯林斯英语义类词典》2011)等都被囊括其中。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的移动版尤其受到手机用户的青睐。
反观汉语多媒体词典,袖珍电子词典和光盘词典在近一二十年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袖珍电子词典的开发,因国内庞大的用户市场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发展,用户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存在质量不高、技术水平落后、开发后劲不足、专业队伍不健全等妨碍良性发展的因素,一直处于低层次、粗放型的发展状态。而国内网络汉语词典和手机汉语词典的开发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与拥有三千余年词典文化、拥有亿万词典用户的国家现状格格不入。同样,应该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这一紧迫问题,组织精干力量,整合学术队伍,开发汉语网络词典和手机用户词典,否则将是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缺失,更是汉语文化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大缺陷。
“一部好的词典不仅应该是一部杰出的文化产品,也应该是一部精美的艺术作品。”(雍和明1997)无论从文化产品还是艺术作品的角度看,词典书稿一旦成为印刷品就具有商品的属性。国内词典界一直忌讳提及词典的商业化问题,不过,在英美国家,商业词典(commercial dictionary)(Barnhart 1962,Householder 1967)[注意不是“商贸用语词典”(business dictionary)]作为词典营销术语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而词典品牌意识则可以说从Cawdrey词典出现之日起即伴随着英语词典演进的脚步。中国出版界、汉语词典界乃至整个语言学界对待词典商业化和词典营销的消极态度(或者认识不足)是阻碍词典品牌打造的主要因素。
当代汉语词典要向更高层次迈进,铸造品牌是必由之路,在当代汉语国际化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之际更是如此。回顾英语词典的国际化发展,首先由英国萌发,随着英语的全球传播,继而在美国,再后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等国家不断发展,品牌意识和品牌营造是支撑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性环境要素,没有品牌拓展就不可能有今日英语词典广泛的国际认可度。当然,品牌背后是词典设计的科学规范、词典编纂的精益求精和词典的整体特色。
当代英语国家在词典项目启动之时就十分注重词典的后期推介和品牌营销工作,各种类型的编纂研讨、现场推介、媒体发布活动司空见惯。甚至早在19世纪,Webster就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开始编纂词典之前,就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咨询等方式进行大量的市场分析和研究工作,在编纂过程中也不失时机地在美国、欧洲大陆和英国向媒体、出版商、普通公众推介营销。这种词典品牌营销意识通过持续不断的营销活动不断积淀,久而久之,在用户心目中铸就自己的品牌形象,赢得用户的信任。
像英美生产的其他商品一样,英语词典拥有众多国际品牌。在英国,除了老牌的牛津英语词典系列之外,尚有柯林斯、朗文、剑桥、麦克米伦、钱伯斯等国际知名品牌。在美国,除了韦伯斯特和梅里亚姆-韦伯斯特英语词典之外,尚有芬克-瓦格纳尔、桑代克-巴恩哈特、兰登书屋、美国传统、世界图书等国际认可的品牌。甚至在非主要英语国家,英语词典品牌也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例如,《麦夸里词典》和《澳大利亚国家词典》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品牌经营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英语词典的两大支柱,不仅赢得了本国用户的尊重和赞誉,而且得到其他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英语学习者的信赖。
试想,人口仅仅2000余万、英国词典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澳大利亚在夹缝中获得自己民族词典的良性发展和国际声誉,在人口不足5000万的南非,“法罗斯词典”正在成为南非人心目中的民族品牌和非洲英语国家词典的楷模。而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泱泱大国却几乎没有自己的品牌词典,更不用说创建国际品牌,这是多么可悲啊。《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少数几个品种可能是汉语学习者说得出的屈指可数的几种汉语辞书。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比较流行的汉语和汉英双语词典基本上都是国外学者编纂的。《康熙字典》至今仍然颇受关注,享有极高的知名度,甚至被用作检索和学习的工具。这是昔日汉语词典的骄傲,更反映出当代汉语词典令人悲叹的现状,发人深思。
20世纪英语词典凭借品牌效应实现了系列化发展,这在牛津、朗文、韦伯斯特等国际大品牌的词典发展中显得尤其突出。品牌影响与引领是词典系列化的基石,否则系列词典难以持续发展,更不可能形成必要的品种规模和用户群。英语语文词典和学习词典的系列化是词典开发商的主攻方向和领域,这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用赘述。下面以英语词典家族中并不十分抢眼的义类词典系列化和新西兰英语词典系列化为案例,探究其演进的轨迹,展示系列化发展对词典兴盛的重要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义类词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Philo of Byblos是世界上第一部类似“同义词词林”的著作的编者。最早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英语义类词典当数《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1852),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呈现系列化发展态势,以柯林斯品牌为马前卒,牛津、朗文等品牌词典紧随其后。
柯林斯义类系列词典主要包括《柯林斯义类词典:按字母顺序编排》(1984)、《柯林斯小学生义类词典》(2005)、《柯林斯学生义类词典》(2009)、《柯林斯袖珍学生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9)、《柯林斯作家英语义类词典》(2010)、《柯林斯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组合》(2011)等。该系列基本满足各层次用户的语词检索需求。朗文义类词典则主要针对海外用户的需求,主要有《朗文当代英语分类词典》(1981)、《朗文联想活用词典》(1993)等。
与柯林斯义类词典相比,牛津系列义类词典种类更多,功能更全,规模更大,主要有《牛津义类词典》(1991)、《牛津简装义类词典》(1994)、《简明牛津义类词典》(1995)、《牛津压缩版义类词典》(1996)、《牛津美语案头义类词典》(1998)、《新编牛津英语义类词典》(2000)、Elizabeth Jewell编纂的 The Oxford American Desk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牛津案头美语词典与义类词典》2002)、The Compact Oxford Dictionary,Thesaurus,and Wordpower Guide(《牛津压缩版词典、义类词典和构词指南》2001)、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牛津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7)、The Historical Thesauru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历时牛津英语同义词词林》2009)、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English 2 Book Set(《牛津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2010)等。《牛津压缩版词典、义类词典和构词指南》分为上下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通用释义词典;后一部分则根据前一部分词目的义项序号有选择地列出同义词。此外,柯林斯和牛津品牌还开发了适应未来需要的在网络、手机、iPod、iPad等媒介上运行的移动义类词典,如《柯林斯英语义类词典手机系统》《超语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等。
新西兰是太平洋西南部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的岛国,面积只有27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43万。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外人看来词典市场并无多大潜力的岛国,英语词典的发展,尤其是根据用户需求精细分割市场的程度,令人难以相信。考虑到英国英语词典的传统因素和澳大利亚所编英语词典的渗透性因素的影响,新西兰出版英语词典的空间应该少之又少。不过,文献检索的结果让人大感意外。撇开新西兰出版的其他英语词典不谈,光是Oxford New Zealand Dictionaries(新西兰牛津系列词典)就足以构建自成体系的词典系列,多达十多个系列。
“新西兰牛津系列词典”大体上可以分“普通释义词典”“学生词典”“义类词典”“释义与义类复合词典”“俚语词典”“引语词典”“新西兰特有语词词典”等。词典用户需要的主要词典类型基本上都有反映,而且前三类词典都根据用户层次再做精细化市场分割。如“普通释义词典”有通用型词典,如The New Zealand Oxford Dictionary(《新西兰牛津词典》2004)、The New Zealand Oxford Paperback Dictionary(《新西兰简装牛津词典》2006)等,有袖珍型词典,如The New Zealand Little Oxford Dictionary(《新西兰小型牛津词典》2003)、The New Zealand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新西兰袖珍牛津词典》2005)、The New Zealand Oxford Minidictionary(《新西兰微型牛津词典》2006)等。
“学生词典”则分为通用型、小学型、初中型,甚至小学中级型,如The New Zealand Oxford School Dictionary(《新西兰学生牛津词典》2006)、New Zealand Oxford Primary School Dictionary(《新西兰小学牛津词典》2004)、New Zealand Oxford Junior Dictionary(《新西兰初中牛津词典》2011)、New Zealand Oxford Primary School Dictionary,Intermediate Level(《新西兰小学牛津词典—中级》2009)等。“义类词典”则有The New Zealand Mini Thesaurus(《新西兰牛津小型义类词典》2005)等,此外还有“释义与义类组合的词典”——The New Zealand Integrated Oxford Dictionary&Thesaurus(《新西兰牛津释义与义类词典》2008)。
其他类型的词典包括“俚语词典”(如A Dictionary of Modern New Zealand Slang,《当代新西兰俚语词典》1999)、“引语词典”(如A Dictionary of New Zealand Political Quotations,《新西兰政治引语词典》2000)、“新西兰特有语词词典”(如A Dictionary of MaoriWords in New Zealand English,《新西兰英语中毛利语词词典》2005)等。
在英语词典市场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义类词典的系列化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在人口和词典市场环境并不占优势的新西兰能有如此精细化的词典市场分割水准,这充分说明了系列化发展对满足不同层次用户需求、架构词典市场整体体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汉语词典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单本独打天下”的格局。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它们上游没有更大规模的词典与之相配,下游也没有形成满足中级、初级甚至幼儿层次用户的词典,在其左右更没有衍生出与之匹配的其他类型的词典。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此众多的用户必定存在教育层次、知识需求、功能设计、年龄分布、经济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没有像英语词典一样的系列化多元发展,要满足如此庞大的汉语词典市场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在国际汉语词典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强调汉语词典的系列化并非意味着齐头并进,均衡发展,恰恰相反,应该通过周密的规划,尤其是通过国家社科规划层面,按照轻重缓急分步推进,突出重点项目和重点类型。例如,英语学习词典目前占据中国英语学习用户市场的几乎全部份额,它们既是学习的工具,也是英语文化潜移默化的传播渠道。当前,配合中华文化推广的总体安排,可以优先考虑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发展。国内目前面向汉语非母语用户的“外向型”学习词典只有《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主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徐玉敏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主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等。
这些学习词典固然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优点,但是与英语学习词典相比,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需要什么,他们学习汉语的难点是什么、存在什么困难或者障碍,积极型与被动型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在设计上如何有针对性地差异化等问题的研究缺乏力度,没有充分做好汉语学习的比较分析和错误分析,没有深入国外学习环境中观察和了解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实际情况,更没有以外国汉语学习者的大量第一手语料作为分析基础,因而很难提升实用性,收到预期效果。《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之所以一鸣惊人,与其编者长期从事海外英语教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海外英语教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此外,出版时间久、内容陈旧、后续修订跟不上、信息重点不突出、缺乏外向针对性、没有开发新型运行载体(如发展光盘版、网络版、手机版)等,都是外向型汉语词典面临的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三十年英语词典的类型多元、范式变革、技艺创新、繁荣兴旺与其自19世纪起与语言研究成果紧密融合息息相关。从19世纪中叶启动的《牛津英语词典》,其编纂理念和原则源自欧洲传统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成果,为20世纪主要英语国家历时词典的蓬勃发展树立了范式。英语词典在20世纪的全面兴盛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代语言学的繁荣及对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应用。
20世纪初期,英语学习词典从描写主义、结构行为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等中吸取营养。20世纪60年代,描写主义原则伴随着《韦伯斯特第三版国际英语词典》的问世深深地扎根于英语词典编纂之中。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词汇学、语义学、文体学、语用学等的兴起以及语法教学最新成果的出现,英语词典的功能设计、词目选择、释义词汇控制、释义方式和模式变革、词条信息及其组织形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种基于描写主义、趋向认知主义、模拟用户词汇习得表征的全新词典设计范式应运而生,一种集光与电、音与像、编码与解码功能于一体的全新综合词典检索界面正式与世人见面。
近三十年英语词典编纂与当代语言学理论成果的有益结合能够为汉语词典,尤其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全面提升提供深刻的启示和效仿的样板。汉语词典的全面提升应该将普通型和学习型词典的提升作为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侧重在设计上创新、类型上多元和内涵上提升。在科学吸取当代语言学成果、系统反思以往汉语词典编纂得失和利用汉语语料库进行实证性分析的基础上,拓展编码与解码功能,强化其文化和社会功用,以普通型和学习型为主干驱动,着力推进其他类型词典的编纂。同时,在内涵上深化词性标注、义项划分、释义控制、引证筛选、语法编码、文体标注、语体引导、语用说明、用法注解、同义辨析等,使汉语词典真正显示出用户友好的特征。
最后强调词典使用与用户研究。词典编者不研究用户,就等于企业生产不研究市场和客户。没有对用户的深入了解就不可能编纂出受到词典市场欢迎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词典来,没有对用户语言认知特征和词典使用行为与习惯的研究就不可能存在对用户的深入了解。只有全面深化词典用户和词典使用研究,才能全面提升词典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持续性。
英语学习词典的空前成功有力地证明了词典用户和使用研究对词典编纂的支撑作用。汉语词典编纂应该及时借鉴当代语言理论(尤其是认知语言学)成果和汉语教学成果,消化吸收原形与范畴(prototype and categorization)、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概念隐喻(conceptualmetaphor)、相似性(iconicity)等认知语义学理论的合理实用元素,结合对词典用户和使用的实证研究,使之转变为词典编纂的创新活力。《麦克米伦高级英语学习词典》(2002)中的“概念隐喻专栏”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络词典WordNet(《词网》)都是系统探究用户语言认知机理、协力模拟词典使用表征、不失时机地吸收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创新英语词典范式、变革编纂思维和模式的榜样,值得汉语词典编者、汉语研究人员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共同深思和跟进。
1.陈伟.新词典学范式与数字化出版,中国图书评论,2008(10).
2.王仁强.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雍和明.词典与词典编纂中的美学原则.辞书研究,1997(1).
4.雍和明.从现代语言学看英汉语文词典的编纂.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4).
5.雍和明.语言·词典·词典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6.雍和明等.中国辞典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7.Barnhart C L.Problems in Editing Commercial Monolingual Dictionaries.∥Householder and Saporta(1967),1962.
8.Carr M.Internet Dictionaries and Lexic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1997(3).
9.Householder FW,Saporta S.(eds.)Problems in Lexicograph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67.
10.Cowie A P.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1.Meyer C.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2.Thagard P.Mind: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2nd ed.)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
13.Yong Heming,Peng Jing.Chinese Lexicography:A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