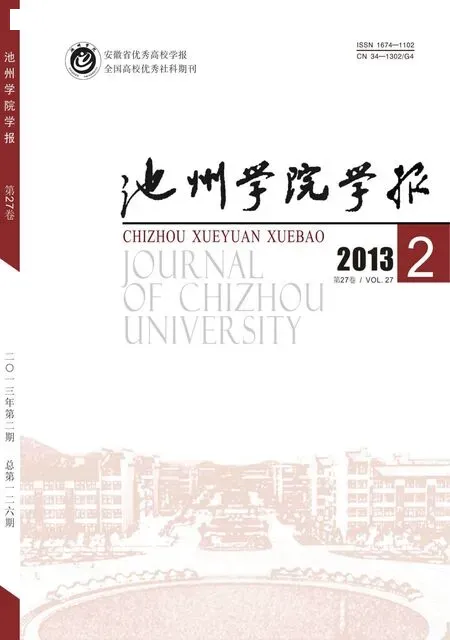二十世纪初到文革时期中国女性画家自画像的精神内在指向
2013-04-01王祎
王 祎
(民进开明书画院,安徽 池州 247000)
中国的女性绘画历史很悠久,相传绘画就起源于女性,绘画的鼻祖是上古时代舜的妹妹嫘,但史料上有确切纪录的女性画家却廖廖无几。画史中最早记载的女画家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绘画史——唐朝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此书记述的310位从传说时代至晚唐历代画家传记中,只有一位女性画家,三国时期吴国的赵夫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与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对女性的蔑视与束缚是紧密相关的。在传统的礼教中,在父权管理制度之下产生了性别等级和性别分工,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只能是处于某个具体家庭关系中,自始自终都是以男性的附属品出现,而非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对女子的教化驯服是维护这种社会宗法礼制的重要内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成为主流社会固有的意识形态,读书习画是为了让她们成为贤女贞妇,才艺对女性而言不但不是一件荣耀的天赋,反而成为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在清代汤漱玉所编辑的《玉台画史》集历代能画之妇女,此书把中国古代从事绘画的女性大致分为两类:出身官宦世家的闺秀与青楼名妓。因些,出身名门大家的闺秀们出于身份的考虑,往往耻于把自己的画作展示于众,画完之后即撕毁以免外流,而被混同于名妓。而且她们所涉及的创作题材最多的是花鸟,这完全是取决于她们被限制于传统划定的生活空间,局促的视野只能让她们寄情于闺房花园之内常见的花草鱼虫,墨竹,偶一为之山水,大多以此做为创作题材,极少涉及人物画。
直至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思想解放与新式学堂的兴办,“女性”一词的出现做为一个充满了反叛意味的符号,越来越多的闺阁名媛得以走出闺房,接受新式美术教育。但自幼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仍深刻地植入内心,使得她们的作品天然地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气质特点。尽管接受了新式教育,甚至有的远渡重洋长期学习生活于海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依然保持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典雅含蓄的气质,出现了如方君璧、孙多慈等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1 自画像中折射的东方意象
方君璧(1898-1986)出身名门望族,是五四时期这批女艺术家中起步最早的,年仅14岁时即跟随其姐方君瑛留学法国。她不但开创了作为第一位中国女学生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先河,而且也成为首例入选巴黎春季沙龙展的中国女画家。方君璧以肖像画成名,其作品都带有中国画的意象特征,她往往将人物置身于特定的情景中,力求古典雅致的诗意效果。从她的几幅自画像中都可以明确体会到这种特点。《寻梅》一画完全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学巨著《红楼梦》中黛玉这一形象的再现,她身着长氅踏雪寻梅,身姿绰约,典雅端庄,完全一派中国古典绘画的意境效果。《方君璧自画像》中她则身着黑色旗袍,斜斜地倚坐在一张太妃榻上,整幅画所流露出的一眼望之都是中国画的符号元素。再如 《拈花凝思》、1928年参加巴黎展览会上的自画像等等作品都洋溢着极其浓郁的中国韵味,她的自画像呈现给观者的感受是,既洋溢着时代新风尚同时又保留有传统遗韵的女性自我形象,具有一种温婉的东方闺秀气息。
相对于方君璧这位画坛前辈,孙多慈 (1912-1975)可以称做“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女性画家。虽然前后相隔了十数年的光阴,她们的绘画风格却在气质精神上有着某种神奇的契合。孙多慈又名孙韵君,与方君璧同样出身于书香世家,那种来自中国传统大家庭娴静、温润、优雅的闺秀气质在她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转而反映在她们的创作中。孙多慈1930年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师从徐悲鸿。短短数年时间,以她的天赋与勤奋在专业上获得了极佳的成绩,深为徐悲鸿所器重:“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1]。1935年,徐悲鸿亲自与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伯鸿协商,出版了《孙多慈描集》。这本画册的封面即是孙多慈的一张自画像,当时的画家正处于最好的青春时节,衣着打扮为典型的五四时期女学生的风范,长袍,短发,白色的围巾,她右手持着调色板,左手拿着画笔,神情温文尔雅。此画造型结构精确,色彩沉稳丰富,笔法细腻,侧光造型凝练微妙,充分显示了她娴熟的绘画技巧与深厚的人文修养。她的素描可说深得徐悲鸿之真传,无论是构图与笔意技法,均可看到徐悲鸿对她深刻的影响。画册中有一幅她的素描自画像,线条简洁肯定,寥寥数笔神情毕现。她一生留下多幅自画像,无论是素描还是油画,均形象秀美而意韵深远,她个人的从容与优雅的气质特征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体现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澹远宁静、端庄典雅的内在精神指向。
这些从闺阁深处走出的女性艺术家,以自画像记录着自己对艺术的追求,留下了一份以色彩与线条构成的历史的视觉图像资料,折射了当时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与精神状态的微妙变化,反映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紧密相联。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观看和被观看二者相互迭照的历史痕迹,显现了女性艺术家自我成长、自我进化的过程,这些图像所涵盖的微妙意味,是我们得以了解她们的信仰、审美、家庭等独特的意识的变化的切入途径。
2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娜拉”们的群像
每个时代女性形象都有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娜拉是“五四”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了的中国新女性的代名词。亨利克·约翰·易卜生也许没有想到,他的一部《玩偶之家》会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女性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剧中主人公娜拉会成为五四新女性群体的象征符号。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世纪交替中西文化大冲撞大交融的时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对于经历了上千年封建统治中国民众的意义不亚于文艺复兴之于欧洲。这是一场兴起于古老中国的“发现人”的运动,尤其是一场“发现女性”的运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方方面面,带给中国画坛的意义更为深远。在中西相融、新旧交替的阵痛之中,催生了一大批女画家。1924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此次展览会上,中国第一代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洗礼的女性画家,代表着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女性画家们以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艺术思维方式表达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女性的存在与情感际遇。
这批女性画家的创作题材多为肖像画,更多以自画像示人,反映了民国时期女性的初步觉醒,不甘再以男权的陪衬为代名词,自画像显示了她们对自我的关注,从中获得了自我生命的延展以及感情渲泄的途径,以一种平等的性别身份参与到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民国女画家的群体,她们的出身背景不同,人生经历迥异,绘画风格更是各有千秋,充分体现了她们整体的规模与实力,堪称中国女性绘画的一个高峰。
2.1 静穆的高贵与单纯——蔡威廉
在1929年4月的首届美展中,蔡威廉(1904-1939)以五幅肖像画参展,其中自画像占了两幅。当时的业内人士对这两幅自画像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试观她的两幅自像画,着色多么沉着,用笔多么简洁,线条多么单纯,而结构多么劲健!两幅之章法不同,表情也殊异。侧面斜视者似无求于世,玉立正视者若有渺茫之幻想。二者皆作家内心片时之形象而凝定于画幅之中遂成不易!”与同时代的潘玉良相较,蔡威廉的声名似较少为大众所知。事实上,她在艺术上的造诣完全不输于潘玉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教育家蔡元培之长女,她成长的教育环境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她幼年时即跟随父母出访游历于欧洲各国,1923年至1927年,蔡威廉先后就学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之后又独居巴黎专攻人体素描及艺术理论研究。数年海外磨砺,使她积淀了深厚扎实的绘画底蕴。蔡威廉虽然出身优越,又有美术科班背景,却生性不喜浮华喧嚣,完全没有当时某些新潮艺术青年的虚荣习气。沈从文曾有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蔡威廉的人格,“当时只听说她为人极忠厚老实,除教书外从不露面,在客人面前也少说话。很文静,毫无浮嚣气,有功夫。人如其画,同样给人一个有教养的好印象。试想想,在一个国立艺术学校教西洋画十年,除了学生,此外几乎无人知道,不是忠厚老实,办得到办不到?”“她样子很朴实,语言很少,正和她那画像相称。且以为朴实的人,朴实的工作,将来成就一定会大得多”[3]。沈从文对蔡威廉的这些描述从她存世的自画像中可以得到印证,画中的她朴实自在,表情平淡沉静,线条简洁大气,用色沉着稳健,呈现了这位系出名门的女画家含蓄沉默的个性特征。
从1929年到1939年她离世之前的十年时光中,她创作了多幅自画像,这些作品深含着她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是她的精神写真。因为她深厚的个人修养和低调平和的个性特点,其画风与潘玉良华丽肉感的画面抒情性相较,蔡威廉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的思想意图”,她的画风由于深受后印象派影响,没有被具象写实的学院画法所拘泥,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将关注点放在表现人物之神态、情绪和精神,善于表现人物的表相乃至性格特征,更为可贵的是她对于人物瞬间的心理情绪的准确把握。画面毫无脂粉气,更无媚俗气。1930年她开始尝试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佛像的笔法、色彩、线条创作自画像,揭示出隐藏在人物内心的最核心、最隐密的性格特征,与其个人超脱圣洁的精神气息不谋而合。
2.2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女性的自我审视——关紫兰
与蔡威廉截然不同,关紫兰(1903-1986)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无论是从个人性格还是到绘画风格都大相径庭。她与蔡威廉曾同为《良友》的封面人物,蔡威廉素面朝天,朴实无华,而关则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时尚前卫的女性形象,可谓是典型的引领时代潮流的摩登新女性。曾有人误把她的照片当成红极一时的名伶阮玲玉,她的时髦由此可见一斑。在她的自画像中,她总是身着各式时髦服饰,胸前环绕着长长的珍珠项链,显得极为精致优雅。其画风正如其她本人,色彩华丽、时尚,人物造型平面化,抽象化,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
她于1927年经老师陈抱一的介绍前往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画界受到新生的野兽派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代表人物是曾留学法国的有岛马生和中川纪元,他们以狂放热烈的色彩与大胆简约的笔触,强烈地冲击了当时的日本画坛。关紫兰与他们过从甚密并有机会得到了他们的指点,由此成为国内较早接触现代绘画的女画家,她的用笔自如率意,色彩华丽秀雅,极具形式感。从她的画作可以窥见马蒂斯的优雅和浪漫的情调,深得野兽派之精髓,她的画风也成型于这一时期。《L女士画像》作于1929年,有美术史学者推测画中人物正是画家本人。其色彩大胆浓烈,线条流畅洗练,笔意潇洒,女子的面目简略变异,却透出一种稚拙大气的美感。
关紫兰在日本的学画经历颇为一帆风顺,先后多次参加了诸如“二科”美术展这样最高级别的展览,并举行了个人画展。当时日本著名的艺术月刊《妇人——女士造型》杂志于1927年10月详细介绍了她及其画作,对于这位来自中国的女画家给予了高度的学术评价,她的油画作品《水仙花》被制成明信片在全日本公开发行,深为日本油画界所青睐,被称为“中国闺秀女油画家”,这对于一个初涉日本画坛不过数年的女性画家而言是非常罕有的。“关女士的画,富有色彩而不辨轮廓,完全用直觉去表现图象,所以在关女士的画风中,只有一种很简单的形式,就是,幽秀华丽,大方新鲜。她的用笔奇特的很,是近代的浪漫派,实在的内容,离我们目下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可是她是远处的一盏明灯”[4]。
20世纪上半叶,正是欧洲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等现代绘画流派风起云涌之时,其影响力波及了全世界,当时的中国画界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随着一批留学欧州,日本的画家归国,各类不同艺术主张的团体也相继成立,诸如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默社……女性画家大多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关紫兰做为默社创始人的陈抱一的学生,却一直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社团。一直保持着绘画创作的个人独立性,坚守着自我的内心,始于个人而终于个人,清晰呈现着女性微妙难言的日常经验。
出身城市小康人家,留学日本的学习经历更是强化了她对于城市人生的自我审美认知,将现代绘画形式与自我画像成功地结合,从而形成她特有的画面符号:率真的笔触,唯美的情调,表现主义的画面构成形式,这一切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新的城市女性自我形象。
2.3 身份转换中的自我追寻与肯定——潘玉良
民国时期的女画家中无法回避的必然是潘玉良(1895-1977),由于潘玉良本人跌宕起伏的人生,从一个青楼雏妓到旅法画家的身分转换,让大众关注其个人的传奇性远远大于关注其作品的艺术性。一般人对她的印象几乎都来自电影、电视剧当中那些女演员们刻意塑造的,或漂亮妩媚或风情万种。其实这与历史上真实的潘玉良大相径庭。目前为止所有表现她的影视剧中的美丽女子形象,只能说是导演善意的美化,或出于商业的需要而迎合大众的心理,为市场创造出的一个美女加才女。实际上,潘玉良不但谈不上漂亮,甚至还可以用丑来形容。这一点从当时她的很多友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可管窥之,“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潘玉良14岁不幸堕入勾栏之地,所幸得潘赞化不为世俗所牵绊纳为妾室,不但解决了她当时现实的生计问题,最重要的是还给予了她一个为社会规范所承认的身份定位。然而早年的际遇始终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她原名杨秀清,后被亲戚收养又又改名张玉良,被潘赞化赎身之后再随他姓潘,二次改名换姓,使她与同时代的女性而言其社会从属身份更为显著,也许正因如此,她才越发执着于以“自我”作为艺术表现对象。自学画伊始便不断地创作着自画像,并且忠实,毫无粉饰地表现着自我。纵观其一生,她的代表作多为各个时期的自画像。她以自我作为画面叙述的主题,自画像构成了其自我叙述的,谱写生命传奇的图式记录。从她的自画像中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她的艺术演绎的主线,年少时的跳脱与迷惑,少妇时期的忧郁与高傲,中年之后的落寞与练达……这个在世间除了 “我”几乎一无所有的女子,完全忠实于自我生命的体验,一直以“我”为题材,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叙述。早期她的自画像往往眉头紧锁,目光冷峻,表情执拗,画面色彩暗淡冷寂。这与她在国内所遭受的同行的攻击,身份尴尬的家庭生活,困于中国传统人伦定位不无关系。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中年之后的她越来越显得自信而豁达,她本身就是一个性格爽利,豪爽大方的人,从她后期的自画像可以看出她心绪的改变,色彩绚烂华丽,笔触洒脱流,她的面部表情越来越放松,不现紧锁眉峰,目光之中的冷峻与忧郁也被沉静与自信所取代。
从1921获得公费留学法国到1928年归国,接近十年的时间是潘玉良创作的高峰时期。在法国期间,思乡之情流露于她的画布笔端,她创作了多幅带有东方情调的自画像。在1940年的黑衣自画像中,她身穿装饰着金色花边的黑色旗袍,华丽的色彩与桌上绽放的花朵交相辉映,她姿态优雅,目光深沉饱含着忧郁,整幅画洋溢着中国式的古典气氛。此时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之中,此画寄托了她对于亲人的无限思念。1949年她创作了一幅女性自画像史上前所未见的作品,画面上的她坦胸露乳,正在自娱自乐地开怀畅饮。桌面上洋酒倾倒,烟蒂满缸,浓烈的明黄、纯蓝、粉绿交织挥洒,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整个构图异常放松,表现出对于传统道德与绘画模式的挑战。与她之前的自画像总是以正面面对受众不同,这里她不再关心是否与观众进行目光上的交流,她脸上的笑完全是为自己而绽放。
因为早年缺乏教育机会,可以说其文化程度近乎于文盲,这种没有因承的文化负担恰恰成全了她的绘画。她的画,没有被各种高深的理论所牵累,以我手写我心,完全出乎一片赤子之心。其笔触干脆俐落,色彩大胆主观,不柔媚,不纤巧,其形象也完全没有女性作为被观看的客体通常所有的那种低眉婉约的模式图样,她画笔下的自我不复是柔弱无依的中国传统式美人的形象,相反的表现出男性般的力量感。她自画像基调大约分为两类,一类阴郁、苦痛的;另一类则反其道而行,极其艳丽而绚烂,她的自画像就是她生命的镜像。观者从她的画作能感受她的豪放性格与艺术追求,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色彩里将她内心赤烈的情绪表露无遗,真实单纯而更显其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她早年在国内学习过中国画,从她的绘画风格可以看出中国水墨色线的技巧,油画的色彩,印象派的光影与线条共存,融入了自我的情感,自然地勾勒出明暗结构,虚实变化,与她所追求的“合中西于一治”的艺术主张相契合。
除去上述几位,这个时期活跃的女性画家还有郁风、麦绿之、翁元春、吴似鸿、梁亦坚、徐坚白等人,她们无一例外地都曾经画过自画像。就绘画的前卫性而言,丘堤(1906-1958)与关紫兰可以划归为同一类的画家。她原名丘碧珍,出身于福建霞浦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当时“五四”运动早已发生数年,但对于远离京津沪,偏居东南一隅的闭塞之地,文化环境与社会风俗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她刚烈率真的性格在入学之后就体现了出来,她率先剪掉了长发,以“五四”风靡一时做为新女性符号的短发示人。所谓画如其人,开放的思想与其后来前卫的画风当属一脉相承。她的画风受到后印象主义的影响,流露出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她具有良好的写实功底,却并未受制于具体外形结构的禁锢,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具象写实绘画保持了距离,强调表现性,平面化,装饰性的油画语言。
作为中国第一代女性画家群体中的后来者——郁风于1935年创作的自画像,完美地诠释了“五四”女性的精神风貌。整幅画最直击人心的就是画家那双炯然有神的双眼,明亮而聪慧,似乎有着勾魂摄魄的神奇力量,让观者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画中的她短发,浓眉,面部轮廓分明,没有通常女性的柔媚,反而看起来象个男孩子般犀利。与她的外在形象相吻合的。该画的表现手法,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概括与老辣,在这里她强调的是自我个性精神的表达,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精神独立群体性生存状态。
做为上个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女性画家,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画像做为记录时代的方式,构成了她们共同的自我表现方式。以自己为绘画的对象,与当时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紧密相联,潘玉良、关紫兰、孙多慈、丘堤、郁风、萧淑芳等人用自画像开拓了民国女性美术的新局面。这种自我表达方式不但是女性精神自立的宣言,记录了“小我”的成长,更成为寻求“大我”,勾勒了在风云激荡的年代她们的自我觉醒与自我进化的历程。
3 毛泽东时代女性自画像中隐匿的自我述求
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美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鼓励妇女走入社会,“男女平等”建国之初就被写入了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男女都一样”成为当时被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的社会风尚,以国家的名义弱化男女性别上的天然差异。女性的性别特征,心理差异,气质风貌被模糊,被掩盖。个体语言的自画像被集体语言合并、分解,所谓的“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唯一的女性符号。这种对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的颠覆矫枉过正,男女平权嬗变为一种被掩藏的对男权的迎合歪曲漠视女性,实际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性别歧视。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体制,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与弘扬个人主义的自画像格格不入,自画像的土壤几乎完全被铲除殆尽。艺术创作及艺术家本身被纳入体制化管理,使绘画方式与艺术观念由多元转向了单一,“五四”时期蓬勃发展的异彩纷呈的自画像艺术于此时悄无声息了。从民国走来的一大批女性艺术家,如李青萍、关紫兰、丘堤……或因当时被打入另册的家庭成分,或因自身思想没有紧跟上新的时代等等内因外因,已多数从公众视野中淡出。自画像除了做为美术院校学生练习基本造型技巧的偶然为之,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已经不再被主流所认可。进入50年代之后,情况越发恶化,所谓“搞臭个人主义”的口号,使以表现个人的自画像这一艺术形式进一步濒临绝境。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对于自我心灵的守护使即便是在个人被抛弃的时代,也仍然有一些女画家努力寻觅着冷酷政治体制的缝隙,以一种特殊的形态,迂回执着地找到自我表现的途径。这些画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从民国进入新时代的,如萧淑芳、郁风、徐坚白等人,强调自我情感的表现和内在自我精神的描绘;另一类则是成长于新中国的美术院校的女艺术家,如周思聪、王玉珏、邵晶坤……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造就了女性自我形象与他者的公众形象相分离的状况。但无论是哪种类型,“不管他表面上的主题是什么,画家所画的永远是他自己”[5]。所以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只要是进行艺术创作,自觉不自觉地艺术家笔下流露的都会有自己的影子。
3.1 时代更迭与政治环境对于自画像画面符号之影响
萧淑芳(1911-2005)做为跨越两个历史时代的人物,从1954—1955年间,她连续创作了三以滑冰为主题的作品:《北海溜冰》(油画)、《北京冬季的什刹海》、《北海溜冰》(国画),选择这个创作主题与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萧出身于世家,她与她的四个姐妹从小接受到良好的西方教育。她还热衷于各种时髦的运动,早在1921年,当时年仅18岁的萧淑芳获得了华北女子花样滑冰的冠军,当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生活类大型画报著名的《良友》杂志还曾以她做为封面人物。滑冰做为她终其一生的爱好,即使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并没有熄灭她的冰舞情结。《北海溜冰》这幅油画创作于1954年,是萧淑芳曾于1935年创作的同题作品的一次再创造,同一表现题材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虽然画面中仍旧是那座白塔下的冰场,中心人物依然是那两位姑娘翩翩身姿,可画面中出现的象征性符号——姑娘胸前的红领巾,却在明确地告诉观者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整幅画从表面上看来,完全合乎建国初期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美术做为颂歌式的宣传工具的要求,画面所营造的热烈欢庆的氛围象征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生机勃勃的,美好热烈的生活状况。而在画家歌颂新生活表象之下,蕴含着的其个人自我形象以及生活经验、心理体验的内容。1935年的《北海溜冰》是画家的自画像无疑,而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这组滑冰图,虽然画面的主角变为了两个小姑娘,但通过微小的细节仍然含蓄地表达了画家个人的印迹。“画中女孩子穿的白色溜冰鞋,就是外婆照着自己的溜冰鞋画的……”[6]画家用心良苦将画面与个人的标记符号隐蔽地联系在一起,谁还能否认这不是画家的“自画像”呢?如果说在《北海溜冰》画家还只是隐匿地表现自己的影像,《北京冬季的什刹海》中的女性形象,相信看过画的观众只要参照画家本人,就会完全认同处于画面视觉中心的黄衣女子就是萧淑芳个人的写真。除去这种隐晦的表现方式,即使是在“个人主义“被严厉批判的当时,萧淑芳仍然创作了数幅独立自画像。从画作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对艺术的影响力。人物的外在形态完全符合当时为官方所认可的所谓“红、光、亮”的形象,她面色红润,衣着朴素,眉目间可以察觉到画家内心的紧张。观者已经无法将此刻的萧淑芳与当初那位潇洒灵动的时代新女性联系起来了。臃肿土气的罩衣,紧张坚硬的姿态让她成功地把自己转变成了一个朴实茁壮的劳动妇女。同样的,在另一幅她的自画像中,她身着工装,头戴矿工的安全帽,从外形上完全消泯了女性的性特征,女性的内在气质被扭曲,表现女性天然具有的柔美,敏感以及妖娆的曲线都被归为小资产阶级情趣,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表现。所以画家只能以当时最光荣的工人形象而不是艺术家出现于公众视野之中,此时,艺术家的“本我”被隐藏于“他者”的着装之后,类似的例子几乎俯拾即是,诸如,王玉珏的 《山村医生》、《农场新兵》。前者创作于1958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大跃进的狂热浪潮中,提出了诸如“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不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被投入了这场令后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被视作半边天的女性也都自觉自愿地在生理上以及心理上抹杀掉自己女性的特征,以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铁姑娘”形象来要求自己。时代决定了绘画的艺术特征与隐喻指向,艺术家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创作了很多迎合当时审美情趣,只限于表现劳动人民高大全形象的肖像作品。
3.2 特殊时代中女性意识曲折的自我叙述
邵晶坤的《铁姑娘》即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然而即使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女性艺术家特有的细腻,敏感也会如磐石下的小草一般顽强地探出头来。这幅头像虽题为铁姑娘,穿着打扮乃至面部肤色都符合时代要求,却难掩画中人物秀丽的五官与双目中蕴涵着的柔情,那是一个女画家对于内心不能自已的流露,隐藏在所有政治符号之下的女画家自我形象几乎触手可及。
而王玉珏创作的《山村医生》所流露出的恬静温柔的气息,与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格格不入。排除画面中那些表明主人公身份——赤脚医生所列出的各种符号,她恬淡优美的姿态,美丽的麻花辫子,尤其是画面在上角的草帽上插着的一朵鲜艳夺目的红花,这种对于美的追求与赞美正是被官方所批判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含蓄表达。在她同年所作的另一幅代表作品 《农场新兵》中,体现了其一贯清新雅致的画面语境。处于画面视觉中心的女子除了发型的变化之外,其五官及形态特征与《山村医生》的主角极为肖似。这种巧合并不是出于偶然,参考王玉珏的生活照片可以看出,这两幅画中的女子其外貌形象与画家本人酷似,这种表象所蕴含的深意颇为耐人寻味。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可以视之为画家的自画像,是她们在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自我形象曲折的表达方式。
从二十世纪初到文革数十年间,中国的女性画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时代变迁、政治环境的挤压,但她们仍执著于自画像的创作与表达。正如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朱青生曾说过的,自画像最具价值的所在是通过画家的个人自我形象的描摹,反映出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时代背景,而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画自己。从建国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女性画家的自画像无一不映证了这种论点。
[1]孙多慈.孙多慈描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5.
[2]姚玳玫.自我画像蔡威廉与她的画作[J].读书,2010(2):131-137.
[3]沈从文.记蔡威廉女士[M]//沈从文.沈从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72-76.
[4]吕鸿.绘画的心理状态与感触[J].艺术广角,2001(2):56-57.
[5姚玳玫.自我画像 女性艺术在中国[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