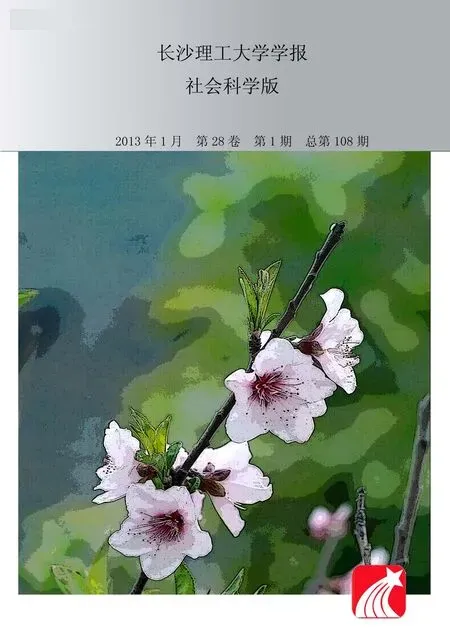“技术-性别-自然生态”问题探究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阈
2013-03-31易显飞
易显飞
(1.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732 ;2.长沙理工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114)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完成及其连续引发的几轮产业革命,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引发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种族问题是20世纪的关键问题,生态承载问题很可能是21世纪急需解决的问题”。[1]与此同时,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严肃地意识到:女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压迫女性”与“压迫自然”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联系,在这种背景之下,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ce Spretnak)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了当代社会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生育技术到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从有毒废弃物到新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2]本文简要梳理生态女性主义基本理论,并以蕾切尔·卡森对生物杀虫剂技术的分析为例,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技术—性别—生态问题进行整体探析。
一、生态女性主义:“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具有内在关联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F.奥波尼(Francoise d' Eaubonne)首次提出,她指出父权制或男性权利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认为女性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巨大,呼吁女性主义者发起一场颠覆男性权利的生态革命,目的在于建立男性与女性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并不是要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男性处于边缘的社会。[3]它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开端。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把自然所受的压迫和女性所受的压迫相结合,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探究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男性对自然的压迫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4]很显然,她是从性别-自然-文化的维度给生态女性主义下定义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场全球性运动,这种运动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暴力”。[5]美国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斯塔霍克(Starhowk)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一切带有统治意蕴的关系,它的斗争的价值目标不仅要改变掌握权利主体,而且要颠覆权利结构本身。”[6]“生态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采纳女性、贫穷人口、欠发达地区的人以及其他不同种族和文化意识背景的人的观点。 ”[7]斯特拉·金和斯塔霍克的概念已经突破了性别压迫与生态压迫的框架,认为对一切压迫和暴力的“突围”都是生态女性主义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珍妮斯·伯克岚(Janis Birkeland)认为,“以一种价值观,或一种实践,或一种社会运动存在的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分析框架,用这种框架拷问与反思了男性中心主义和生态环境破坏之间的内在关系”。[8]杰妮斯·伯克岚的定义强调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的“合二为一”。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把“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联合起来进行解决。卡伦·J·沃伦指出:“(1) 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两者之间有内在关联;(2) 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根本实质对于更充分全面理解女性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与剥削是关键且必要的;(3) 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运动实践理应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 生态问题的解决理应亦包含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视角。”[9]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和自然“同病相怜”,两者都是“客体”或“他者”被男性统治与压迫的对象。因此,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因而解决策略也是需要“打包”应对。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在一个继续以统治与被统治对立关系作为主要关系模式的社会,女性很难有自由(解放)可言,生态问题也不可能找到实实在在的解决途径。必须把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种种价值需求联立起来,创造和重建基本的社会与经济,重构现代工业社会基础的价值观”。[10]生态智慧、女性解放、基层民主、非暴力、非中心主义、尊重差异、可持续的发展都是生态女性主义追求的“联合目标”,因为这些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必须“联合解决”。
二、生态女性主义技术批判:以蕾切尔·卡森为例
蕾切尔·卡森(Rachel Karson),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海洋地理学家。1962年,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该书构思来自她收到的马萨诸塞州杜可斯波里一位名叫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的妇女的信,信中告诉卡森滴滴涕(DDT)正在杀死鸟类的事实[11]这说明,她虽身居要职,却善于倾听来自普通民众的心声。
蕾切尔·卡森认为,人类的出现,改变了自然的命运。她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就是生物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地球上生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环境塑造的。宏观而言,生物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力量一直是微乎其微的。但人类出现之后,生命具有了“异常”的能力改造周围环境。在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异常”的力量对环境的破坏产生了质变的程度。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都遭受到了致命的袭击和污染,并且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和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生物体的生存环境,也进入了生物体系的组织内部。[11](P5-6)
随着化工技术的发展,人工制造的化学物质越来越多,这改变了整个自然界原有的物质组成。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200多种化学制品通过化学工艺合成出来,用于杀死被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工技术制品的表现形态一般是这些喷雾药、粉剂和气雾剂,它们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各种场所所采用,但是,这些“未加选择”的化学药品同时具有杀死“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所以,卡森认为,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该称为“杀生剂”。 化学药品的使用,是一个无止境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DDT被使用以来,有毒化学物质的发明与创新在不断升级,昆虫在不断进化,抗药性在不断增强,出现了化学药品越来越“毒”与昆虫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强”的恶性循环。就在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人类整个生态环境已由这些有害物质所污染,并进入生物体内,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11](P8)
蕾切尔·卡森并不是一味的拒绝现代化工技术。她反对的是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任何区分,盲目大量且完全地交到技术使用者手中,而对它潜在的技术风险却全然不知。大量的人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这些毒物接触,甚至这种“不知情”是人为地造成的。[11](P8)在她看来,没对化学杀虫剂进行审慎的技术评估,公众对该技术知晓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使该技术不光彩的一面被“遮蔽”起来,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60年代化学杀虫剂技术至少是“不民主”的技术。
技术应该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技术应该是“人性化”的。技术应该能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需求,若技术带来人的生存危机,还大谈什么“人性”、“人道”、“价值”等,无异于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11](P46-48)但是,这种化学杀虫剂技术,却无孔不入地侵害着正常人的身体。卡森认为,具有巨大的生物效能的合成杀虫剂使人体的生理过程产生致命的负向变化,包括毁坏对身体起保护作用的酶,阻碍正常的氧化过程;阻碍了人体器官功能的正常发挥,等等。[11](P16)卡森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整个人类都暴露于动物实验已经证明极具毒性并且许多例证表明有积累毒效的化学药品的侵害。这种暴露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做法,这种暴露将会持续侵害现代人的一生。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可以作为指导” 。[11](P:X)
人类的技术,可以踏入太空,可以深入微观粒子,却无法让资源匮竭中止,无法使生态系统恶化缓解,资源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保护技术与其他技术体系在发展速度与品质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化学杀虫剂技术一方面,确实使农作物免于受到害虫的侵害,从而导致产量更高;另一方面,它却污染了我们水源、土壤、食物乃至整个地球。谈到对水源的污染,卡森认为,各种化学技术制品的使用,产生了大量的有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借助于雨水,肆意扩散,变成世界水体运动系统的一部分。谈到对土壤的污染,卡森认为,土壤生态学问题基本上被科学技术专家所忽视,而杀虫剂技术使用者则完全不理睬这一问题,当土壤中一些种类的生物由于使用杀虫剂的广泛而大量使用而减少时,土壤中另一些种类的生物就出现疯狂地增长,从而搅乱了生态链条的摄食关系。这样的变化造成土壤的新陈代谢紊乱,并影响到它的生产力。[11](P56-58)
技术非生态或者说“反自然”,都与人类没树立正确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有关,卡森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极端幼稚和狂妄的。“应用昆虫学”在相当程度上得归咎于科学技术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类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大地了,这真是我们巨大的不幸。[11](P295)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卡森的影响已超越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谈及问题的疆界。她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现代文明中已丧失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这个观念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融洽相处。[11](P:XVI)
卡森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她反对的是化学杀虫剂技术“非生态”的一面,主张对化学杀虫剂技术进行生态改造,用替代性的新技术来取代化学技术制品对昆虫的控制。[11](P:XV)但她和她的书仍遭遇到来自“污染获利者”的顽强抵制。几家大型化工技术公司都试图禁止《寂静的春天》公开出版。当该书摘录在《纽约客》杂志发表时,马上出现了反卡森的“大合唱”,指责她歇斯底里,是极端主义者。正像为该著作写“引言”的美国前总统阿尔·戈尔所指出的,对蕾切尔·卡森的攻击,可与当年对出版《物种起源》的达尔文的恶毒诽谤相“媲美”。甚而,由于卡森是一位女性,很多攻击者直接拿她的性别说事,称她“歇斯底里”,诬蔑她是“自然的女祭司”。她作为科学家的职业声誉也同样遭到攻击,她的对手“污染获利者”出资大搞宣传,污蔑与否定她的研究工作。[11](P:VI)阿尔·戈尔认为,卡森的研究工作也是为了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观念:即男人应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科学技术史基本就应是男人主导的历史,这几乎被看成是一个终极绝对状态。
基于卡森所唤起的生态意识和关怀,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去扭转杀虫剂污染剧增的潮流,其相关的科技政策包括三项原则:更严的技术标准,减少杀虫剂技术的使用,广泛推行可替代性生物技术制剂。[11](P:XIV)总体上,卡森提出的问题既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是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加以解决的。阿尔.戈尔认为,我们必须在以农药及农业社团为一边、以公众健康社团为另一边的文化沟壑上架一座桥梁。两边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只要他们隔着猜疑和嫉恨的鸿沟对峙,我们就很难改变一个生产和利润都和污染紧密相连的体系。有一条路可使我们看到结束这种体系的曙光——并开始缩小这种文化差异——那就是让基层的农业推广站去推行化学药物的替代品。另一办法是让生产食物和维护人类健康的机构彼此进行建设性的对话。[11](P:XV)
总体上,卡森提出的生态与技术问题,在阿尔·戈尔看来,它唤起了民众的注意,它也赋予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以拯救地球的责任。纵使政府不关心,消费者们(公众)的力量也会愈来愈强烈地反对农药技术使用导致的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含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食品促销手段,也同样正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必须行动起来,而公众作为新型的责任主体也要“当机立断”。[11](P:XV-XVI)
三、“技术—性别—自然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批判:悲观主义基调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西方认识论中的二元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二元结构将男性与理性、社会等同,将女性与情感、自然等同,构成了父权制统治的基础,并进而形成了男性占优势,女性居于劣势地位的社会心理。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世界中的技术是男性气质紧密关联,技术追求理性与效率,体现为操纵、控制和压迫,因此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并且,男性还与自然为敌,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男性通过技术强化对自然和女性的统治地位。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技术是典型的男性文化的象征。在男性文化中,内含着一个性别关系的隐喻,男性代表人类社会,女性代表自然,技术的目的就是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社会,自然和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男性居于统治地位。父权制文化导致“统治”逻辑的兴起,它解释与辩护了“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统治的合理性。
依据Karen Warren “统治的逻辑”的思考模式,女性是与自然、身体相联,而男性是与人和心智相联。男性和女性是两类不同群体,身体不如心灵高贵,自然不如人高贵,进而得出缺少优越感的女性群体应处于被统治地位,即从属地位,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主要缘于父权制文化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批判父权制世界观,并对这一文化背景下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进行了类比思考。她们提出了关于军事技术、工业技术和生育医学技术与女性关系的新观点,呼吁反对父权制文化,解放女性和自然,倡导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为女性从边缘走向核心,进行自我拯救和解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父权制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技术将无法避免地打上男性统治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烙印与偏见。因此,父权制社会的技术发展价值取向将不可避免地呈现男性优势。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女性与自然之间联系及其演化的考察,揭示出科学技术的统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她们认为,男性通过科学技术不断强化其统治和控制,女性和自然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为了逆转这一趋势,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以下假设:女性的本质不同于男性;女性的特殊性在于她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男性文化承载着“统治和压迫”使其劣于女性文化。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崇尚和平与抚育后代方面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存在价值。基于此,她们和文化女性主义一样,主张发展出男性化特质偏弱的技术,发展民主的、人性化的以生活为导向的“生活技术”而不是以工作和权力为中心的“非生活技术”。
对于技术导致的生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遍持猛烈的批判态度。卡森对农药技术的反思,麦茜特对自然技术化导致的“自然之死”的批判,都是基于生态维度来对技术进行人文主义的批判。在她们看来,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对技术进行生态控制与对生态进行技术控制应该是协同进行的。前者是对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进行生态规约,这是一个社会规范问题或者“技术与社会”问题;后者是基于“解铃还须系铃人”运用“更好的”技术来控制由原来的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这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人类与自然对立、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对立的二元论思想,突出了重新理解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意义,为从二元思维向非二元思维方式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她们提出要以多元代替二元,男性、女性、自然等所有存在者都有其生存的权力,应该在一种多元平衡的关系中发展。在此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者还对技术进行了有力的,甚至于有些偏激的批判。他们的关注焦点除了女性地位的改变,还关注技术发展与生态环境危机,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使她们能从更宽阔的视角,更大的背景来考虑女性解放问题。生态女性主义视界中的技术整体上是悲观主义的,她们不赞成发展现代技术,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现代技术甚至回到始技术时代(The Eotechnic Phase),因为技术是父权制下的产物,即对男性发展有利,体现着男性的统治功能,是男性无限制追求权力的产物,而女性只是牺牲品,是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受害者。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只是在生物学基础上探讨女性的特征,而没有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或者说从本质的意义上揭示出女性的特质,她们只是在感性的意义上探讨女性的本质、力量和美德,而没有从理性的意义上,或者更深的哲学意义上反思女性与技术。其次,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无意投身于社会变革,或者说,不是行动主义者,因此,也不能在更深层次上变革传统的女性文化、变革生态和变革技术。再次,生态女性主义者没有打开技术的“黑箱”,把技术看成是一个整体,并把技术与社会相等同,并因此而认为可以通过对父权制社会的解释来解释父权制的技术,这在一定意义上暗含了技术的经验研究的否定。
[参考文献]
[1]Lawrence Buell. The Ecocritical Insurgenc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30) ,1999:701.
[2]Charlence Spretnak.Ecofeminism: Our Roots and Flowering, in Woman and Power(9),1998:8.
[3]Francoised Eaubonne.Feminism or Death, in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 An antholog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81:64.
[4]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Gaia and God: 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 Healing.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2:2.
[5]Ynestra King.Healing the wounds: Feminism, Ecology and Nature / Culture Dualism, in Alison Jaggar and Susan Bordo. eds. Gender / Body /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ing and Knowing.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20.
[6]Starhawk.Power, Authority and Mystery: Ecofeminism and Earth - Based Spirituality, in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eds.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77.
[7]Starhawk,Power, Authority and Mystery: Ecofeminism and Earth - Based Spirituality, in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eds.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83.
[8]Janis Birkeland. Ecofeminism: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Ibid. P.18.
[9]郑湘萍.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
[10]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an/ 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NewYork: Seabury Press, 1975.204.
[11][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