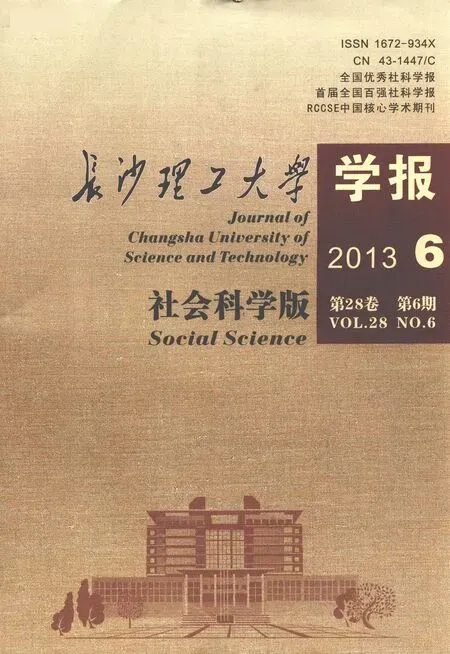经验的符码:历史镜像与缺席之物
——对孙文波《十四行诗》的总体性阅读
2013-03-31张伟栋
张伟栋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经验的符码:历史镜像与缺席之物
——对孙文波《十四行诗》的总体性阅读
张伟栋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将孙文波的诗作《十四行诗》放置在其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当中全面的阅读,从而对其创作内核给以较为清晰的认知,这个内核是围绕三个关键词来展开的:经验的符码、历史镜像和缺席之物。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致解读来理解这个内核的具体含义。
《十四行诗》;经验的符码;历史镜像;缺席之物
对于一位写诗将近三十年的诗人而言,如果诗歌没有将他带入自我突围的绝境,那么他的写作则极为可疑,写作应有的含义,也在敦促诗人:写,最终是对伟大事物的抵达。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当下,写作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它要求一种总体性的视角,将我们可疑和可怖的生活,带往相对安全和幸运的线路,因此,写作的困境,要远大于生活本身的困境。我也因此对巴丢的一个判断,抱有认同感:“我们生活于其上的世界是一个脆弱的风雨飘摇的世界。它决不是位于历史统一内部的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决不能允许让全球性接受自由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现象掩盖20世纪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暴力而脆弱的世界这样一个事实。其物质的、意识形态的和知识的基础都是相异的、分裂的、大多矛盾的。这个世界没有宣告一种线性发展的安宁,反倒宣告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文集和相互矛盾的事件。”[1]而这样的世界也有权向诗歌提出要求。
相对于一些较早形成自我风格,而陷入自我复制、模仿的诗人,孙文波的写作显得更为自觉和刻意,近三十年的创作画出了一条不断自我突围的轨迹。《地图上的旅行》(工人出版社,1997)、《给小蓓的骊歌》(文化艺术出版,1998)、《孙文波的诗》(人民文学出版,2002)、《与无关有关》(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新山水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等诗集的出版,则彰显了这条轨迹的突围路线。这样一条突围路线的刻画,必然承担着诗人自我设定的写作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诗人不断完成和修改的写作内核,以及依靠这样的内核,如何发明我们的当下和未来,进而建立一种成熟的诗歌模型。我将以三个可以把握的关键词:经验的符码、历史的镜像和缺席之物,来对这一内核进行描述,以期待对孙文波的写作以及当代诗的问题意识有着更好的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是通过对孙文波早期的一首《十四行诗》的总体性阅读来完成的。
一、经验的符码
八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西郊的一家工厂上班的孙文波开始了他的诗歌写作,整个文学大环境的激发和诱惑,使得他最早的写作带有与经典诗人对话和强烈的自我书写的特征。我们能读到孙文波最早的作品,是他发表在《1986—1988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上的一首名为《十四行诗》的诗歌。这首诗没有被收入诗人的任何一本诗集,原因显而易见,是因为诗人并不满意这首诗所取得的艺术份额,但我之所以着重强调这首诗,是因为一个诗人初期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定风格,往往会成为贯穿其整个创作的重要底色,将这样一首诗放置在诗人的写作进程中,在其前后的关联性中,而展开的总体性阅读,是我们理解诗人具有独特风格和复杂主题的切实角度。
初读这首诗,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被赋予了一个戏剧化的角色,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错位中,带有某种坚定的使命。在这首诗中,夜晚、苦难、鲜血、死亡和灵车,编织起一个暴力的世界,它是抒情主人公内心的镜像,也是其理想世界的对立物,因而诗人所表明的:“他被迫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一首诗”,其实更多是对重构美好现实的历史法则的探讨,这样的一条线索,在孙文波后来的写作当中,愈来愈清晰,也构成他诗歌写作的一个核心元素。在这方面王敖对孙文波的判断非常准确,“孙文波的诗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道德拥有诗的形式感,他无疑是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当代诗人。在他的作品里,政治和美学的拉锯经常为内心的独白伴奏,节拍强劲,音色粗粝。”[2]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读到的是,在这首诗中,抒情的色调在组织词语的节奏和语义的转换,使得整首诗带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句法特征和主观自我的表现形式,在第二节中,我们甚至可以辨认出雪莱的影子。我想,从孙文波后来的作品来看,他对这首诗最不满意的地方应该是在这种抒情的语调中,审慎地观察和内省没能冲破自我抒发的激情,在诗歌中取得应有的比重,因为个人经验被包裹在象征的结构和词语中,而无法获得明确的现实和历史的含义,正如我们在这首诗的结尾所读到的,“走进每一座石头坚固的庭院”,实际上是一种太软弱的写法。
他被迫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一首诗
那里夜晚与夜晚紧密相连
苦难和鲜血辉光闪耀,那里
在无数建筑中,死亡一再发生
缓缓走过的灵车压倒了异性的容貌
他不是去迎接西风的英雄
血液里没有风暴、火和神赐予的力量
一只鸟儿也比他更自由
飞翔,在高空歌唱,穿过岁月
声音和影子
到达永恒居留的处所……只有他
走进每一座石头坚固的庭院
——《十四行诗》[3]
这首《十四行诗》中的象征结构,比如,“夜晚与夜晚紧密相连”对应着现实之中的黑暗状态,“迎接西风的英雄”对应超历史的个人等等,在孙文波接下来的写作中,几乎被全盘推翻,而抒情的语调被保留下来,得以改造,通过对个人经验和历史镜像的完整书写,而获得与现实具体而有效的关联感。这种具体的关联感是与某种诗歌模型的接受有关系的,像他在访谈中所说:“其实一直以来感兴趣的是以经验主义为背景的英语诗歌写作方法,自觉当时受到的影响亦是来自于从玄学派到叶芝、奥登这样的,在细节描述上非常落实,带有叙述色彩的诗歌。”[4]因而这种语调也不再是对现实的应激性反应,而是以个人的视角对现实有力的阐释,正如艾里克·海勒对里尔克的诗歌所做的分析:“在欧洲传统的伟大诗歌中,情感并不阐释什么,它们只是对被阐释了的世界作出反应。在里尔克成熟的诗歌中,情感会对世界加以阐释,然后又对自己的阐释作出反应。”[5]这也是九十年代诗歌叙事的一个基本态度,孙文波后来的写作,所寻求的以情感阐释世界,确切地讲,是从1989年之后开始的,诗人对诗歌中的单纯抒情性的警觉与现实叙述的自觉,使得他加入朦胧诗之后最重要的诗歌转型运动之中。通过这首《十四行诗》,我所关注的是,这种现实叙述,是以何种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个人的经验以何种方式被编码,从而编织成一首诗的叙述。这种对经验编码的原则,我将之称为经验的符码,是我们理解一首诗成诗过程的关键。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我们所看到的诗歌中的“世界”,并不是像地图一样,通过对现实进行比例的调节而完成的,恰恰相反,诗歌中的“世界”无一例外地是对现实的重写,而这种重写的方式取决于诗人所依赖或所创造的诗歌模型,想象一下,一个以荷尔德林为榜样的诗人写下“你们死之于诸神”这样的句子,对于熟知荷尔德林的诗歌模型的读者来说,并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一种诗歌模型,会大致圈定诗人的语调、修辞、诗人对现实的想象和重构的尺度,甚至诗人的全部世界观,一个初学诗歌的年轻人,即使写下“我深深懂得谋杀者是多么怯懦”,也不见得这位年轻人有多么惊人的思想,因为这句诗不过是对艾吕雅的改写,它的力量来自于原作的独创。我们常常会听到,某某诗人被称赞写的很好,但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会发现不过是二流的作品,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卞之琳认做一流诗人的原因。一种伟大的诗歌模型,像是精良的捕兽器,把世界囊括其中,因为它发明了“一个全面的、堪称正确的视角,以观察世界和人对世界的安排”,[6]而“经验的符码”就是这个捕兽器的开关。“九十年代”诗歌和“朦胧诗”的明显不同,就在于这种经验编码方式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两种诗歌模型的差异。
经验的符码之所以是这样一个开关,在于其组织起叙述的同时,也结构了诗歌的肌体,不同的符码会决定诗歌的模型的不同,比如一首关于乡村的抒情诗的写作,布罗茨基曾详细描述这种经验的编码方式,他说:“你一开始要描写你看到的一切,从土地开始,再抬起身来,一直写到树冠。这样你就获得了崇高。需要习惯看到整体画面……没有整体部分是不存在的。应该最后考虑各个组成部分。韵脚,最后来考虑,比喻,最后来考虑。音步似乎是一开始就出现了,是不依赖于意志的。”[7]我们当然无需将布罗茨基的诗歌方式当成典范来接受,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例子,而考虑其具有的结构性含义。布罗茨基所描述的编码方式,具有技艺的功能。在我们的诗歌语境中,诗歌的技艺,往往得到了不公正的理解,赞同的人,认为技艺是使得诗歌高超起来的方法,而反对的人,认为技艺是对诗歌的雕琢,是对真实情感的回避,对于这个词,我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技艺“意味着一种知道方式”,[8]意味着提前知道,比如“哀歌”这种形式的技艺掌握,就意味着我们要熟悉此前关于“哀歌”的写作,而这种以技艺为指导的经验编码方式,是每个诗人都逃脱不掉的。关于另外一种通行的符码,我想使用荷尔德林的例子,在著名的《饼和葡萄酒》一诗中,诸神的远离构成了荷尔德林思考和情感的起点,全诗以神性的法则来计算我们生活的困厄,以及未来之神的踪迹,伽达默尔的一个判断极为精准地说出了这首诗中的诗歌法则,他说:“昼与夜的对立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描述了荷尔德林的历史意识,作为诸神远离的困厄,希腊生活就是相反的图像,是充满神行的白昼。这是十分明晰的经验,荷尔德林在图像与反图像中构造的就是这种经验。”[9]我将荷尔德林的这种诗歌法则,称之为“历史对位法”,[10]这是一种现实的计算法则,它要求对现实的清点,在“图像与反图像”的构造中重新发明现实和未来的尺度,罗兰·巴特所说的肉身与语言之间的秘密方程式,也与此相关。
我在孙文波的《十四行诗》中所读到的经验编码方式,虽然这些经验的符码被包裹在重叠的象征结构当中,但是通过与其后来作品的对照,其实可以清晰地概括:历史镜像和缺席之物。这并不是要以此来总结孙文波的写作,他的写作远比我这篇文章中所谈论的要丰富得多,而是要借此一看其叙述中的内核。在这首诗中,缺席之物随处可见,来指认现实的残缺,最终被归结在“永恒的居留处所”之中,而历史的镜像则表现为对现实的计算法则,这种法则的具体含义,则需要进一步的补充阅读,才可以明晰。
二、历史镜像
九十年代初,《散步》、《地图上的旅行》、《还乡》、《八里庄的夜晚》、《在无名的小镇上》、《在西安的士兵生涯》等一系列组诗的发表,使得孙文波的写作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在这一系列组诗当中,现实经验从单纯的象征意味和抒情尺度中解放出来,而赋予其文字以丰富的肉身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场景的叠加、画面的铺陈、空间的转换、舞台的戏剧等原素成为其诗歌中的主导,因而在文字的弥漫之处,我们尽可以感受到伦理和政治的张力,这两者也成为了孙文波后来的诗歌写作中一以贯之的诗歌主题。
进一步讲,伦理和政治的张力所切中的人、事、物的存在尺度以及时空的流转,对应的则是对历史镜像的铸造和表现,这构成了孙文波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坚定的内核。所谓历史的镜像,从孙文波的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将当代的生存经验放置在历史的尺度中加以叙述,去寻找和反思那些操控我们生活的力量,进而得以指出我们何以谋划当下的未来,因而,当下就是历史,个人的经验即是历史的见证,这样的构想与泰德·休斯所宣扬的信念颇为相似,泰德·休斯说:“如果诗歌不是来自于那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内部原初的受难和决断的一种陈述,那它就不是一首诗。”[11]另一方面是,它要求对现存的制度、法则和历史处境给以诗歌的尺度,诗歌在对经验进行解码和重新编码,从而将经验所构成的历史编织到诗歌的尺度中,诗歌与历史在政治、伦理的美学原则中获得同一性。
让我们来读一首孙文波写于1990年的作品《还乡》,[12]这首诗所确立的诗歌元素,虽然也被诗人不断地修正,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诗歌中历史镜像的构造方式。
在不断晃动的火车上,我被安排在窄小的乘务室里,
它不比一个墓穴大,也不比一个墓穴小。
就像一册书一样翻动。地名。历史。
这一切都显得缺乏真实。我问道:“我置身于其中吗?”
没有谁来回答。“过程是不存在的。”
我知道这是公元前的一个夏天,面对
在胜利的凯旋中回到家乡的士兵,一位哲人
是说出的话。我知道我必须关注的不是
行进。我知道我已经被一个关于蛇的箴言缠绕。
这首《还乡》是由十节诗组成的长篇组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开篇的第一节诗,在如墓穴一般的火车乘务室里,诗人开始了还乡之旅,大地上的风景和火车的行进重叠在一起,被诗歌的过滤器改造成认识性的装置,而涌向对真实的审视,诗人说:“这一切都显得缺乏真实”。在这里,来自于我们内部的受难和决断的陈述,透过这种虚无的语调,指向了缺席的存在。因而这首诗当中,还乡并不是重点,还乡只是这首诗的形式,它给予了叙述以必要的经验和境况,诗人在作为结尾的第十节诗中写道:“‘从成都到华阴,或者从华阴到成都。这旅途/使我看到的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必须回到什么地方?”缺席的存在在这里完成了对整首诗的主权的构造,所以构成了整首诗的主题。正如在开篇中诗人所写:“透过双层玻璃的窗户,我看见大地”,而大地上的一切都“恍如隔世之梦”,众多的景象,如秋天的气流、山坡和沟谷的模样、通往墓地的小路、孤单的桤树,被一一的拣选计算,这计算的法则来自于对死亡、幸福、正义、尊严、欢乐的秘密书写,缺席之物则紧紧地围绕在这秘密书写的节奏里。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还乡的途中,所有的事物都被剥离了自身的秩序和想象的可能,被放置在现实的尺度中,被放置在诗人发问的语气里,就像诗人在第五节中所写:“工业是人貌似进步的现象。有两台拖拉机/你们就进入高级的生活吗?……这是被像马尔萨斯这样的人物们计算过多次的公式/依照这样的公式,我听到/‘生命就是消耗一切。到达未来的到来已经消失!’”这些发问和随之而来的决然判断,以及对现实的定义,帮助诗人完成对当下历史的叙述,这是孙文波九十年代写作非常热衷的一种形式,他这个时期的写作基本上是以这种形式来完成对历史镜像的处理。
在以“六十年代的自行车”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诗歌当中,诗人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直接书写重新定义现实,确认我们的当下,个人的经验在为历史作见证的同时,也迂回地指认了仍残存在我们现实中的无法和解之物,就像《一九六六年夏天》中所写:“她在我记忆的波浪和漩涡中上下翻滚”。这种自觉和刻意的筹划,在《“文革”镜像》一诗中,尤为显著。
一场武斗之后,二十几辆卡车
放下挡板,载着尸体在街上缓缓前进。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站在街角,
加入观望的人群,听人们谈论
子弹钻进人体如何像花一样炸开。
我眼前出现幻景:一朵朵花
从人的头顶、胸前、背部绽放。
我还注意到:在一辆车上,
从包裹的尸布露出的脚,一只穿着鞋,
另一只袜子烂着洞,露出脚趾。
它使我想起爷爷又一次告诉
我的话:人死时穿着什么,
到了阴曹地府,会一直那样穿戴。
这首诗的细节极具感染力,配合着诗人的出席见证,而将历史还给了现实,其含义也不言自明。正如孙文波在《我怎么成为了我自己》中所言明的:“真正使我最终明确自己面对诗歌应该写什么和怎么的,是一九八九年发生在天安门,并波及到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巨大政治事变。不管今后的历史学家怎样看待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但它的出现的确改变了我这一代不少人对政治的含义、国家和个人命运的看法。”[13]这段文字今天读来,含义丰富,事实上,诗人在追认自己写作经历的同时,也在确认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传统,今天对杜甫诗歌的热切阅读,使得这一传统不断地得到追认,归根结底包含着对某种道统的体认。1930年后而盛大的左翼诗歌也从属于这一大传统,作为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这个大传统是其接受的最直接的诗歌教育,在众多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诗人那里,如北岛、多多、王家新等,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传统的种种变形。八十年代以人道主义话语为开端而兴起的种种价值取向所塑造的“个人”,在重新定义历史含义的同时,也帮助诗人重返杜甫的“诗史”传统,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旨趣在于:个人对历史的承担,诗人在其具有自传倾向的诗句也传达了这一观念:“我是最后一个他们的见证人/用诗的韵律,把他们/写进文字的历史”(《曲城》)。
《“文革”镜像》这首诗作为一个例子被单独展示,在于这首诗典型的构成方式。我们可以简略地将此诗分成两个部分:前十行为一个部分,是对历史的追认和承担,这种承担在于诗中所嵌入的一个当代人的视角,通过“我”所执行的功能,而将历史重新带回现实;后三行为一个部分,诗歌的尺度在此突然出现,它进行评判,也直截了当地将历史钉在我们眼前。这种方式在孙文波近几年的写作当中,几乎随处可见,并且极力将其推进到当代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褶皱一般起伏的细部,而将我们放置在现实的陡坡之上,比如这首《迎春辞》。
我写迎春花开在坡上;柳树,
河边垂下细枝;新建水泥桥,
蓝油漆栏杆阳光下鲜艳夺目;
指路的箭头朝向一片苹果林
——不过,我还写语言像风在电线中
飘荡,而我得到消息晚了,再去寻找,
赤裸美人已杳无踪影,只有法律
狼犬一样守着一扇扇打开的视窗。
这就是现实?它成就想象,
让人的脑袋成为毛片工厂。更多故事被叙述。
人的秘密中最不秘密的是:每个人不论外表
如何光鲜都只是动物。或者一切都像政治,
只能放在台上,如果在台下,所有主张
都流氓——想想也无趣。但,这不就是美?
正是它构成欲望的动力,让我们
看到,叙述的扩张粉碎掉不少人的梦想,
生成更多人的梦想。是啊!它们
让我写不自然的句子:我坐在水坝上,
望着远处羊群,眼睛里一片灯红酒绿
的场景。民族的奢糜正进入叙事。
相对于《“文革”镜像》来说,这首诗隐晦而更加曲折,历史的镜像以碎片的方式,通过情感的粘合剂而聚拢,相互问答与回应,但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还原到更全面的现实当中去,也更加争锋相对。因此,他这一时期的诗歌,雄辩、开阔,在经验的扭结处急冲冲地奔向历史的缺口,从而使得生存的正义在词语的深处浮现。诗歌在对经验进行解码,从而将经验所构成的历史编织到诗歌的尺度中。
三、缺席之物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再来回望《十四行诗》,其中的经验符码和问题意识,就再清楚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的镜像并未带来一个“将来之神”,而处处在显露现实的破败与虚无,而将一个没有到场的缺席之物,提交到前台,实际上也是将诗歌落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褶皱与历史的曲线当中,诗歌的发声器官从呼喊的喉咙转变为沉吟、争辩、反驳的内心,这是理解九十年代诗歌的一条重要线索,表面看来是,经验叙述在对抒情进行纠正和革新,骨子里却是试图以超然的激情对历史的临界点进行致命一跳的诗歌不得不直面它的当下。
那么,缺席之物或缺席的存在到底是什么?诗人并没有明确地指明,我们只是能在诗人对现实的偏移和对虚无的强调的语调中感受到,我们之所以如此,之所以虚无和“独自承担痛苦和罪孽”,都是由于那缺席之物的不在场,历史的运转把我们抛掷在这个钢铁的时代,像诗人在《还乡》中所写:“这是一个钢铁的时代,水泥的和众多规则的时代。”在臧棣主编的诗歌民刊《诗东西》第一期,我读到了由诗人明迪和Neil Aitken翻译的孙文波的一首诗歌,《“自由”是一个孤独的词》,这首诗被翻译成英文后效果很好,我仔细通读了几遍,发现译者虽然在语气和节奏上有所调整,但基本上忠实于对其历史镜像的表现和传达。诗歌的不可翻译,已经成为翻译界的一个共识,因为诗歌语言中的气味、语调、韵律和修辞的精微之处在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往往会被损失掉,这也是好多当代诗人的诗歌被转译成英语时,会显得浅白和乏力的原因。而对一个诗人诗歌写作中的内核的翻译,往往可以让我们把握其写作的整体状态和成就,汉语中对米沃什、洛威尔、普拉斯等人的翻译就是如此。那么对照孙文波诗歌的英译,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历史镜像所指向的缺席之物。
Remembering you is remembering loneliness;
A word wanders in the mountains of my brain,
Over the steep cliffs and down the cold ravines.
It moves quickly leaving no trace behind
Like a leopardess tormented by hunger.
A word tells me:it doesn’t want to disappear into emptiness
As if never existed.It wants me to see it and track it down
Like a hunter,finding it in the memory
And saying it out loud.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place it.Oh word!How can I put you
Into this world,it’s not even my word.
在这首英文译诗当中,几乎是以直陈的方式来展开对“自由”这个词的追踪,诗人将这个词放置在历史的镜像中来审视其缺席的现实处境,我所引用的是该诗的1—11行,通过其中的关键词来分析这种缺席的含义。我们看到,这个词Freedom(自由)被放置Lonliness(孤独)、Emptiness(虚无)的语境当中,word(词语)和world(世界)因此成了可以相互对峙和相互否定的两个词,原因是这个词无法被安放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被商人和政客所把持,买卖是唯一的游戏规则,在这里,自由就是缺席之物,孤独和虚无中所想象和追认的事物,都是缺席之物,这是一望即知的。但最真实的状况是,world (世界)比word(词语)多出了一个字母L,最终被以Lonliness(孤独)的状态来把握,最终造成了Emptiness(虚空)的情境,也就是说,真正的缺席之物在这首诗当中并未到场,它显露了痕迹,但却像是“物自体”一样不可知。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永远存在着“黑暗状态”和不到场的“缺席之物”,诗歌中的历史镜像正是据此来发明当下和对未来的想象,诗歌也因此使得那个“缺席之物”自行到场,但不是从历史当中请回一个已经被磨损和消耗掉的残缺之物,而是重新发明一个“将来之神”。因此,我们愈加严肃地审视着“缺席之物”,我们就愈加接近其中的“神学”维度,这不意味着,我们要眼望上苍,追随天堂之光,而将大地废弃,恰恰相反,是要我们在大地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事件当中寻找解救的可能,它最终要推翻焦灼的虚空感和孤独感,这是诗歌与世界所签订的契约关系之一,它也因而得到授权去想象和发明新的世界。现代主义诗歌,一开始就无力去发明这个“缺席之物”,而更多地表现出在这种无力感中的震惊和恐慌,正如我在开篇提到的,今天的世界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前提就是要终结现代主义诗歌的逻辑,而向古典诗歌求助。
在孙文波新近出版的诗集《新山水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系列以山水为主题的诗歌,诗人在这批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努力,也力图在与古典诗歌建立某种勾连感,正如诗人自己在后记当中所坦诚的:“书中所有以‘山水’为对象的诗,并非将着力点放在状述山水,也非单纯地如古人‘借景抒情’,而是把更深入地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仍然是要达到对生命的理解,再之则是由此进入与文化传统的勾连。”[14]我们在其具体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勾连,仍是以历史镜像为核心,去编织我们的种种处境,缺席之物在这些处境里开始出场,虽然并未严格地确证自身。
……只是一切都在加速。语言的归宿,
犹如香烟盒上的警告。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让它指向要描写的事物;日常的行为,
面对气候异常,人们需要从内心做出的反思。
我不想像他那样再神话它们。
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
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
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
表面上仅仅是自然现象。隐含的难道不是
法律问题?法律,不应该是制度的玫瑰。
它应该是荆棘吗?也许应该是教育,
告诉我们,天空和大地实际上有自己秘密的尊严。
肯定不是征服。不是……,而是尊重。
我的努力与炼金术士改变物质的结构一样。
通过变异的语言,能够在里面
看到我和山峦、河流、花草、野兽一起和平。
这首《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应该算是孙文波近年来最好的作品之一,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较,语调和着力点都有所改变,最重要的是,诗人更自觉地去瞄准当代诗中的症结。结尾处出现的意愿,在重塑全诗的品格的同时,也在指认即将到来的缺席之物,“我的努力与炼金术士改变物质的结构一样。/通过变异的语言,能够在里面看/到我和山峦、河流、花草、野兽一起和平。”这种努力力图通过变异的语言,而使之装配上古典的韵律。
在这样的线索里,《十四行诗》的整体内容便清楚无疑,它只是展开了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所包含的三个内容:经验符码、历史镜像和缺席之物。经过诗人其余作品的填充,才可以被完整地解读,而这样的阅读方式,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孙文波的写作内核。我想,这也是理解当代诗的一个重要线索。
[1]阿兰·巴丢.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4.
[2]孙文波.与无关有关[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封底.
[3]1986-1988现代主义诗群大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9:373.
[4]孙文波.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回答张伟栋[J].中国南方艺术网http://www.zgnfys.com/a/nfrw-33932.shtml.
[5]奥登.诗人与城市[J].薛华,译.译文,2007(2).
[6]朗佩特.尼采的使命[M].李致远,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
[7]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M].刘文飞,译,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9:125.
[8]海德格尔.致小岛武彦的信[M]//同一与差异[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9.
[9]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M]//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M].吴建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4.
[10]“历史对位法”是理解荷尔德林诗歌的关键,也是诗歌的重要法则,作者(张伟栋)将在“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一文中,给以详细地解释和探讨.
[11]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M].吴德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10.
[12]孙文波.地图上的旅行[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34-38.
[13]孙文波.我怎么成为了我自己[M]//新诗(第十辑)[M].蒋浩,主编.“孙文波小辑与无关有关”,129.
[14]孙文波.新山水诗(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陈浩凯]
Empirical Code:Historic Mirror Image and the Object of Absence——a general review of Sun Wenbo's Sonnets
ZHANG Wei-d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158,China)
A general overview of Sun Wenbo's Sonnets in the context of his writing experience in the recent 30 years,brings into light a cognitive clarity of the inner core of his writing.This inner core involves three key words:empirical code,historic mirror image and the object of absence.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of his poetic works,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of the inner core may be revealed.
Sonnets;empirical codes;historical mirror image;objects of absence
I207.22
A
1672-934X(2013)06-0056-07
2013-09-23
张伟栋(1979-),男,哈尔滨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