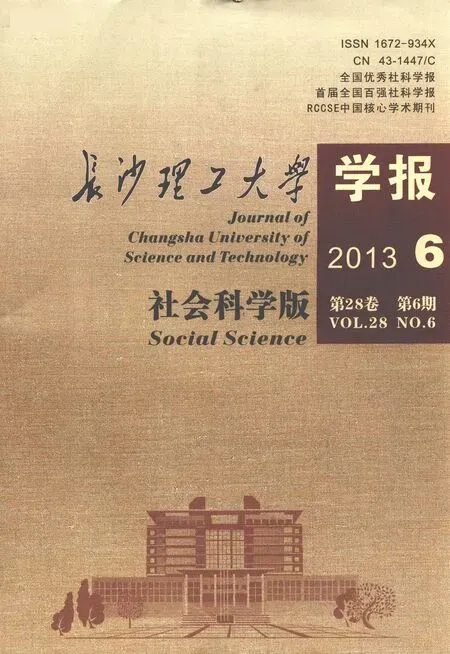德鲁克论技术本质与技术创新
2013-03-31黄欣荣祝龙珠
黄欣荣,祝龙珠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德鲁克论技术本质与技术创新
黄欣荣,祝龙珠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德鲁克以国际管理教父而著称,但同时也是一位地道的技术哲学家,他对技术的本质、社会作用以及技术创新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德鲁克把技术看作是人类作用在具体事物上并与人类劳动相关的综合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他认为评价技术的测度是其绩效,创新是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德鲁克的技术哲学思想补充了传统西方技术哲学对技术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的不足。
德鲁克;技术本质;技术动力;技术创新
说起德鲁克,大家几乎马上就能想到,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开创者,被尊为“管理大师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德鲁克对技术及其哲学问题也做过不少的思考。他在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技术的本质,对技术推动社会的进步做出肯定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其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对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此,我们将德鲁克称为技术哲学家似乎也并不为过,系统探讨其技术哲学思想更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从技术哲学视野看德鲁克
德鲁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不过他为全世界最熟知的还是管理学教父的光环。但因该光环太过耀眼,故遮盖了德鲁克其他方面的卓越贡献,其中他对技术及其哲学的思考就是被人忽略的领域之一。
一位管理学家,或者说管理哲学家为什么会涉及技术与技术哲学呢?我们说德鲁克也是一位技术哲学家是否有依据呢?德鲁克自称为“社会生态学家”,并用生态学的视野和方法对社会这个大系统进行生态学考察。在社会生态的生成演化中,技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技术是社会生态极其重要的生态因子,因此为了全面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态,德鲁克对技术这个重要生态因子必须有所观察和论述。
德鲁克有关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著作写作或发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期他对技术史、技术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对其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担任过美国技术史学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也是德鲁克一生中担任过的唯一一个学术性的职务,由此可见他对技术史、技术哲学的重视。因此,探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不是毫无缘由的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足够的理由和根据。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论述技术本质的四种解读时,承认德鲁克是技术哲学家,将他作为技术过程论的代表性人物,并将其《技术、管理与社会》一书列入技术哲学的基本文献中。[1](P328)
德鲁克的技术哲学著作不太多,代表性论文有发表在《技术与文化》杂志上的三篇论文:《劳动与工具》(1959年),系统论述了技术、工具与劳动的关系,回答了技术的本质问题;《第一次技术革命及其教训》(1966年),分析了五千年前的灌溉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影响;《技术革命:关于技术、科学与文化关系的注记》,系统论述了技术、科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还有第一次发表在M.Kranzberg和C.W. Pursell主编的《西方文明中的技术》第2卷中的两篇论文:《20世纪的技术趋向》和《20世纪的技术与社会》,这两篇论文系统论述了20世纪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强大社会影响。1970年,德鲁克将上述文章与其他文章一起结集出版,取名《技术、管理与社会》。[2]除了这些纯技术史或技术哲学论文外,德鲁克在论述社会、经济与管理时,将技术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而对技术进行过阐述,不过论述没有这么系统。在对技术史和技术哲学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3]一书于1985年震撼出版。该专著虽然似乎主要论述企业家创新、创业问题,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十足的论述技术创新的原创性著作,因此可以说是一部技术哲学文献。
二、技术是社会生态的构成要素
技术的定义及其本质问题一直是技术哲学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工程技术哲学还是人文技术哲学,针对这个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德鲁克对技术及其哲学思考也必然涉及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技术哲学中,技术的定义是一个难题,无论是西方技术哲学界还是中国技术哲学界对此都争论了数十年之久,至今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大部分技术哲学家一般都是就技术来论技术,因此很难给技术以一个确切的界定,而德鲁克则另辟蹊径,从社会生态的视野来界定技术的定义问题。他自始至终都把技术看作是社会生态的一个影响因子,而不是就技术论技术。他说:“虽然我曾经做过技术史学会的主席,但我始终没有单纯地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我对技术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技术没有被融入社会研究中。”[4]
从社会生态视野来看,技术究竟是什么呢?德鲁克首先不同意把技术看成纯粹的工具或者说把技术当作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人类发展技术是为了克服自身的局限,以便营造一个适宜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技术来提高人类自身的生态承载能力,因此是人类自身的主动进化。他说:“人类发展给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态承载力,而且改变不是通过进化过程中的随机基因变异导致的,而是人类主观通过技术刻意提升自己的能力。”[5](P90)这就是说,德鲁克把技术上升到人类自身进化的高度,正因如此,他才不同意将技术等同于工具的看法。他认为,技术与人类的劳动相关,而与工具、过程和产品等具体事物无关。为什么将技术与人类劳动关联起来呢?因为人类劳动是一种综合的行为,是使社会生态发生变化的人类行为,是人类特有的有目的的活动,其他动物仅仅是适应自然环境,而人类却不仅适应,而且能够根据自身的目的而改变环境来为自己服务。他认为,已有的工具和技术不仅会极大地影响到可以从事什么劳动(或工作),而且还会影响到劳动方式。反过来,劳动的结构、组织和观念也会影响工具和技术及其发展,而且影响甚大。他强调,为了理解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首先明白工具、技术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为此德鲁克把技术定义为:“技术是人类作用在具体事物上的抽象行为,或者是为人类服务的具体事物。”“技术研究的主题都是与人类劳动相关联的。”[5](P91)
技术与社会生态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网络。德鲁克正是从这样一种系统思维来理解技术之本质的。他说:“技术必须被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相互关联和互通的单元和行为的集合体。”[5](P97)作为社会生态的一个重要因子,技术影响了社会生态的态势,同时它也受社会生态中其他各种因子的影响,例如经济、法律制度、政治机构、社会价值、抽象哲学、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等等。德鲁克把社会生态当作一个大系统,应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来观察、分析技术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系统内的各种力量和因素相互制约,最终会呈现一个清晰的效果。当我们开始关注这些时,才有可能研究和理解技术这个系统。工具、流程和产品显然没有能力提供对这个被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复杂系统的理解和关注。但人类劳动可能提供这样的关注,可能提供对所有这些具有相互依存关系但又是自主变量的整合。人类的劳动可能提供一个统一的理念,这些理念能让我们既从技术本身又从技术所处的角色,既从知识又从信仰,既从个体又从社会各个角度理解技术的地位和影响。
德鲁克在其《劳动与工具》一文的最后说,历史并不是储存破烂古董的库房。真正的历史以帮助人类了解和塑造自身为己任。正如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是政府,艺术史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是艺术一样,我们也期冀技术史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是技术。可是,当技术史学家了解的只是一堆具体的工具而不是抽象的技术概念时,他怎么可能带领我们理解技术史,进而理解技术本身呢?退一步说,当技术史学家关注工具而不是劳动,他怎么可能提取出抽象的技术概念呢?德鲁克坚称技术的本质与其说是“事物是如何被做或制作的”,不如说是“人们如何做或制作的”。[5](P90)对德鲁克来说,技术不仅包含成功的制作以及人类(有意或无意)的制作、使用工具的劳动,而且还包括失败的一切。因此,技术应该与制品、发明物、经济、政治和科学等因素相关联,而不仅仅只指器物性的工具。[1](P200)更有甚者,他还将管理活动纳入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他会选择技术、管理与社会几个关键词来做他技术史与技术哲学文集的名字。
德鲁克还认真地探讨了20世纪技术的变化及其新特点。[2](P48-63)德鲁克认为,20世纪以来的技术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它在结构、方法和范围诸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从结构上来说,技术活动走向了职业化、专业化和建制化。整个19世纪的技术活动几乎仍然是按照工匠时代的模式进行的,它通过个人的实践来实现,往往是孤军奋战,并且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到了20世纪中叶,技术活动已经完全变成了基于大学专业训练的职业,并且由此产生了技术活动的特殊机构——研究实验室(特别是工业研究实验室),以便专门从事技术创新。从方法上来说,技术与科学之间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并涌现出系统化的研究方法。之前的技术发明或创新都是基于工匠的经验,没有多少理论的支持。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新技术都是来自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基于科学的技术,也就是说,新技术几乎都是先有科学理论,然后走向技术开发。也就是说,先前的新技术是靠发明家发明出来的,而20世纪是靠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根据科学理论联合开发出来的,因此它被称为“技术创新”,而不是“发明”。从范围来说,由于超出了原来的发明这一传统概念,走向了创新这一新概念,因此20世纪以后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从前,已经走向了规模化、系统化和产业化,由此技术的威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带来了产业革命,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20世纪技术发展的特点更加揭示了技术的本质,更加揭示出它是社会生态的制约因子,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三、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仅仅从技术的定义还很难看出德鲁克眼中的技术,他除了从社会生态来定义技术之外,更多地是从技术对社会生态的影响来观察技术的本质,从技术革命的分析中观察、研究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从总体来说,德鲁克眼中的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
在人文技术哲学流派中,哲学家们往往都是技术的门外汉,他们从技术的社会影响看技术,而对技术内部及其本质的理解比较肤浅。人文技术哲学家们眼中看到的往往都是技术的负面影响,都是技术对自然、社会、人类消极的一面。他们很少理性地思考、分析技术,对技术给出客观实在的评价,而是夸大负面影响以达到否定技术、复归原始的目的。例如,德鲁克的老朋友刘易斯·芒福德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彻底否定机器的神话;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比喻为构架,人被技术所困;埃吕尔更是通过技术的自主性分析来强调技术摆脱了人的控制,按照自身的规律自我发展,因而发出了“狼来了”的呐喊。[6]
德鲁克与上述人文技术哲学家不同,他不但对技术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甚至可以说热情地讴歌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重要,他在人文技术哲学家中属于少有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德鲁克曾经高度赞扬过技术对人类的巨大作用:技术让人这种没有鳞片、鱼鳍和翅膀的陆生两足动物上能入天,下能潜水;技术让身体保护层不佳的这个“亚热带动物”能在各种气候区域里生活;技术让灵长类里最脆弱和缓慢的动物拥有大象和牛的力量、马的速度;技术让人20年的“自然”寿命延长到70年;技术让人远离了捕食者、疾病、饥饿、事故等“自然原因”导致的死亡。[5](P90)人文技术哲学家经常批判技术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更多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例如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但德鲁克并不赞同这种过分夸大负面影响的评价,认为人类技术的发展给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态承载力,而且改变不是通过进化过程中的随机基因变异导致的,而是人类主观通过技术刻意提升自己的能力。
德鲁克主要是通过分析技术革命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来揭示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早在1961年发表的《技术、科学与文化》一文中,他通过分析技术、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来充分肯定了技术革命的作用与影响。他说:“技术革命产生了亘古未有的影响,诞生了统一的世界文明,并正在侵蚀和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不管它们有多么古老、多么发达、多么被人们珍惜和热爱,都挡不住技术革命的脚步。”[5](P108)他认为,技术革命赋予技术以强大的力量,而以往的学科(无论是农业、机械还是医学)都不曾有过对人类思想产生这么大的影响。[5](P108)
技术革命为什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如此强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技术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德鲁克认为,技术革命背后是知识的意义和本质的改变,以及我们对知识态度的变化。“技术革命是工艺和工具、手工和机械发明长期积累的结果,包含着缓慢而痛苦的发展过程,以及瞬间、迅速扩散的双重特性。”[5](P109)他认为,技术革命是历史的转折点,无论是在知识、政治、文化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在知识、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历史的传统驱动力是制度、权力和宗教,但如今已被技术所取代。[5](P109)技术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认为是因为它将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了,将人类的精神发展和自然属性连接在一起。[5](P110)
德鲁克详细回顾和分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及其经验教训以及20世纪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通过这两个案例来分析技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认为七千年前人类的第一个文明史——农业灌溉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分析这次技术革命对个人的影响和对自由、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影响,最后他归纳总结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
技术革命创造了社会和政治创新的客观需要。它们也判定了相关领域里需要哪些新制度,而哪些旧制度已经过时。
新制度必须适应具体特殊的新需要。对技术来说,社会和政治制度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社会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新技术所决定的。只有正确的制度安排才能满足技术发展的需要。
这些制度试图实现的价值蕴含着人类和社会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各种目标的重点还相互冲突。但这些价值大部分都是由人类掌控的。社会的骨架是由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所决定的。但一个社会的气质却掌握在人们手中,是一个“该怎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P124)
人类进入20世纪后,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它重塑了社会的建制、让人类进入了一个人造的环境中,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德鲁克论述道,20世纪的现代技术已经使人们重新思考过去的观念,诸如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重新塑造了工作、教育、福利等基本的制度,并让技术发达国家的大量人口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脑力劳动者。现代技术让人类的自然环境变成了人造的大城市,更有甚者是改变了人们的视野。在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共享知识、信息、希望和恐惧的紧密联系的社区的同时,现代技术也将人类直接带到了外层空间。[2](P65)德鲁克说:“人们对技术本身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是物的东西,而是同样要关心人自身。这种新观念的结果是,我们开始认识到,技术不再像其父辈相信的那样,它是能够让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消失的神奇魔棒。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技术的潜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巨大。”[2](P67)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技术革命的时代,因此需要不断关注技术革命对个人的影响,以及技术革命对自由、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影响。技术曾许诺能够将人类引入乌托邦,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此提出了警告。技术可能正在奴役人类,正在使人类疏远自己和社会,正在破坏全人类及其政治价值观。所以,德鲁克也提醒我们,作为人类创造的技术也会像其创造者一样,会出现问题,会有矛盾,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需要我们对技术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因此,“真正的技术革命时代,不是狂欢的时代,也不是沮丧的年代,而是工作和责任感的时代。”[5](P125)
四、创新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动力
技术为什么会越来越进步?为什么会向前发展?技术发展的动力问题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技术哲学最难研究的问题。科学哲学对科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格外关注,而且各个学派对此都做出了详细的研究和明确的回答。技术哲学家们对该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鲁克提出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应该说是最全面的技术发展动力理论。
从原动力来看,科学因为求真,道德因为向善,艺术因为唯美,那么技术应该是因为什么呢?德鲁克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把管理也纳入广义的技术之中,认为管理也是一门技术,而他在论述管理之时,其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卓有成效,也就是“绩效”,一切技术都是在追求绩效,一切技术也必须用绩效来测度。[7]追求绩效其实就是要不断地优化,不断地好中再好,优中选优,因此择优这个追求绩效的过程应该是技术发展的真正最终动力,由此技术要不断地创新,不断进步,以满足越来越优的要求。正因如此,德鲁克把技术择优问题转换为技术创新问题,从创新的角度来探索技术进步的原动力。
为了满足技术不断优化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创新。那么什么是创新?德鲁克认为,技术创新是20世纪所出现的新现象。他认为,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发明的世纪,那么20世纪是技术创新的世纪。[2](P63)技术发明是比较个性化的事情,而技术创新则先提出目标,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并通过组织化来共同努力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例如,为了登上月球,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类技术来共同完成这个目标。“在技术创新中,技术被用来作为一种手段,它能够带来经济、社会、教育、福利等方面的变化。”[2](P59)所以,技术发明一般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技术创新是一个各种技术综合应用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有时并不仅仅因为技术的原因而开展技术研究工作,它也会为了经济、社会或军事等非技术的因素而进行。
技术发明当然是创新,但德鲁克认为,创新不一定是一种新发明,将一种旧技术用在新的领域也是创新,例如把货车车厢去掉车轮就变成了“集装箱”。他说:“创新活动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力,使它能创造财富。事实上,创新活动本身就创造了资源”。[3](P27)“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创新就是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3](P30)所以,发明之类的活动创造了完全原来不存在的新东西是一种创新,将已有的东西重新赋予新用途并产生新财富,也是一种创新。
大约在1880年以前,技术发明或创新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19世纪早期的书籍不断地谈到“灵光乍现”(flash of genius)。发明家则被描述为一个既浪漫又荒谬的人物,他不食人间烟火,独自躲在孤寂的阁楼里苦思冥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发明”已逐渐变成了“研究”,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经过精心策划与组织,无论是在所达到的目标还是在可获得的成果方面都有高度的可预测性。”[3](P31)正因如此,德鲁克认为技术创新并不神秘,而是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以开展系统化的创新。
我们如何进行系统化的创新?绝大多数成功的创新都是利用技术系统内、外在环境的变化来实现的。“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寻找变化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本身可能提供的经济或社会创新的机遇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中。”[3](P31)系统化的创新就是指关注创新机遇的来源。根据技术系统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德鲁克将来源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技术系统内部,例如意外事件、不协调的事件、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产业结构或市场结构的变化;另一类来自于系统外部环境,例如人口的变动、认知的变化、新知识的出现。[3](P31)。
要抓住这些机遇来实现技术创新,德鲁克认为还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他认为,创新必须遵循如下五个原则:1)有目的、有系统的创新始于对机遇的分析,而对机遇的分析则始于对机遇的来源进行彻底思考;2)创新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3)创新若要行之有效就必须简单明了,目标明确;4)有效的创新都是从不起眼处开始的;5)成功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取得主导地位。[3](P120-121)
德鲁克通过分析各种机遇的不同来源,以及抓住机遇的方法原则来论述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基本动力。由此,德鲁克无意之中为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找到了一条分析技术发展动力机制的途径,为技术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结语
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德鲁克主要从技术系统外部,甚至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技术对社会、人类的影响,只把技术看作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生态因素,或者说是生态因子。因此从技术哲学流派的分类来看,德鲁克的技术哲学应该属于人文技术哲学流派,但德鲁克不像其他人文技术哲学家那样把技术当作毒蛇猛兽而猛加批判,他对技术的态度比较理性和客观,除了指出技术的负面影响之外,更多的是肯定技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充分肯定技术的正面影响,认为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特别是20世纪以来技术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子。他还通过技术创新重点探讨了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补充了西方技术哲学对技术发展动力研究的不足。德鲁克的技术观介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属于对技术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客观主义。在人文技术哲学家中,德鲁克是一位难得的不属于技术悲观主义的西方学者。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M].陈凡,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Drucker P F.Technology,Management and Society[M].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0.
[3]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4]Drucker P F.The Ecological Vision[M].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446.
[5]德鲁克.变革中的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6]黄欣荣.现代西方技术哲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7]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87.
[责任编辑 陈浩凯]
Drucker on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UANG Xin-rong,ZHU Long-zhu
(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anchang,Jiangxi 330013,China)
Known as the godfather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Drucker is also a real philosopher of technology,who has carried out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social function as well as technology innovation.Drucker views technology as the synthesis of human effect upon concrete objects in combination with relative human labor,and regards technology as a major impetus to drive forth social progress.He thinks that measurement to assess technology is its performance,and that innovation is the motive power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His thought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complements the defec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by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technology philosophy.
Drucker;nature of technology;technology power;technology innovation
N02
A
1672-934X(2013)06-0020-06
2013-09-06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技术设计的哲学探究(13B133)
黄欣荣(1962-),江西赣州人,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性科学与哲学、技术哲学、管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