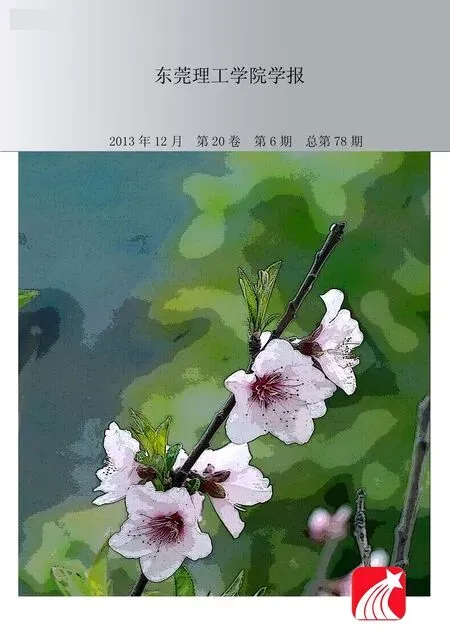故乡风景与“怀乡人”面相
——基于鲁迅《故乡》与莫言《白狗秋千架》的比较分析
2013-03-28郑上保
郑上保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白狗秋千架》已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农村成长史的微缩胶卷。他个人的文学才华早已尽藏其中”[1]。被视为莫言创作根据地——高密东北乡的开辟之作,《白狗秋千架》写于1984年,这部体量薄弱的作品在字数上仅七千余字,而且似乎故事上也了无新意,全然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归乡叙事”*“归乡”模式的说法借用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的说法。见该著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传统,唯一的“新鲜在于故事的残忍”[1]。这“残忍”也并非新鲜,因为在“归乡叙事”的开创者鲁迅处,《故乡》、《祝福》等篇中闰土和祥林嫂等人命运的凄惨似乎也丝毫不弱于《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和哑巴。鉴于这种在故事模式、人物形象以及精神内核的相似和延续,本文拟对鲁迅《故乡》以及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进行文本比较细读,在考察小说产生时不同的历史语境的同时,分析两篇小说中所构筑的作为“还乡人”形象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图谱以及“故乡风景”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变奏*关于莫言和鲁迅的比较在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比如孙郁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的《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和葛红兵发表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的《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从鲁迅、莫言对语言的态度说开去》。在某些具体的母题上,比如“复仇”、“看客”,学界有单篇作品之间的比较,如张磊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的《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等。,冀求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进入莫言早期创作世界,获得其与历史和当下的回响和共鸣。
一、故乡风景的建立
日本评论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有关于“风景”的论述:“所谓的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风景一旦成为可视的,便仿佛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似的……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因为写实主义所描写的虽然是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的人,但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必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2]。在这一段话中,柄谷行人不无洞见地指出了风景生成的内在机制,同时亦将风景的范畴进行了泛化的扩展,将“平凡的人”也纳入“风景”之中,使得“风景”不再局限于“一定地域内由山水、花草、树木、建筑物以及某些自然现象(如雨、雪)形成的可供人观赏的景象”[3]。与柄谷行人借“风景”来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相似,英国学者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l)也在专著《风景的阴暗面》(TheDarkSideoftheLandscape),通过“穷人之景”来揭示在18 世纪的风景画和诗歌中,“风景”如何将乡村的贫苦形塑为自然而然。“唯有穷人劳作的画面,方能被用来再现他们的生活现状;描绘他们休息的方式则是将其感伤化或牧歌化”[4]。
尽管在当下中国,关于“风景”的论述还相对破碎*在过往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从写实主义的层面,关注现当代小说中“风景”描写的功能意义,比如烘托氛围、过渡情节、调解叙事等。其中,曹文轩的研究相对较为系统,他在专著《小说门》中单辟一章“风景”予以论述。此外亦有人关注现当代作家的风景叙事,比如张夏放的博士论文《旗帜上的风景》就对现代作家的风景写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并不妨碍我们引用上述学理对鲁迅和莫言笔下的“风景”进行一番剖析。通过描写和生产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人,昭示写作者自身内在的情感和想象,不仅成为日本和英国的现代文学“起源”之处,实际上也是鲁迅和莫言对建构故土乡村的取径。
归乡小说所构建的凋敝、落后的乡村,其生成第一步无疑是对乡村现实图景的刻画。在《故乡》中,鲁迅对鲁镇的风景描写非常节制:“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5]在这里,村是萧索的荒村,屋是长满断草的老屋,青山迫近黄昏,“模糊”不可见。尤其在写到作为“风景的平凡人”——“豆腐西施”和闰土时,“凸颧骨,薄嘴唇”,“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脸色灰黄,“浑身瑟索”,双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整个人“仿佛石像一般”。
“现代的风景不是美,而是不愉快的对象”[2],这样萧索灰暗、苍老衰败的故乡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人,无疑构成乡村落后衰败的第一步表征,尤其当这些现实的风景与回忆中的风景——“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及勇武的少年闰土相比照时,故乡的不堪和衰败更是越发明显。
同样的风景似乎在《白狗秋千架》中复活。在小说的伊始,便写立在“颓败的石桥”前头的老狗,“垂头丧气”,眼睛“浑浊”,“神色遥远荒凉”,而空气中尘土飞扬,让人难受。小说中间“我”出门寻访暖,“一过石桥,看到太阳很红地从高粱棵里冒出来,河里躺着一根粗大的红光柱,鲜艳地染遍了河水。太阳红得有些古怪,周围似乎还环绕着一些黑气”[6]。此处莫言笔下的故乡,燥热浑浊,太阳如血,似有不祥之景;狗则疲倦无力,而作为“风景中的人”暖在贫苦的劳作中,身体近乎变形;残缺的面目因为感伤更是“凄凉古怪”。简单的几个描写,即勾勒出一个凋敝、贫苦的故乡景象。
不过,莫言的“风景”已出现突破衰败和凋敝的迹象,展示了当时乡村的多种面相。究其然,主要有三点。其一,小说中描述了许多中性,甚至是优美的乡村风景。比如篇头对狗的安静喝水和撒尿等场景的描写和“我”所看到的“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6]。这些平实的描绘赋予小说更为真实的品格,是对乡村生活场景的本真还原。小说最后,写到暖在高粱地中,“压倒了一边高粱,辟出了一块高间,四周的高粱壁立着,如同屏风。看我进来,她从包袱里抽出黄布,展开在压倒的高粱上。一大片斑驳的暗影在她脸上晃动着。白狗趴到一边去,把头伏在平伸的前爪上,‘哈达哈达’地喘气”[6]。高粱地、暖和白狗构成了一副静谧、美好的电影画面。其二,劳作场面重返乡村,成为了风景的重要部分。小说中出现几处暖劳作的场景,“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她用一只手按着搭在肩头的背棍的下头,另一只手从颈后绕过去,把着背棍的上头。阳光照着她的颈子上和头皮上亮晶晶的汗水。高粱叶子葱绿、新鲜。她一步步挪着,终于上了桥”[6]。这些色调冷峻的描写,极为细致地还原了劳作的每一个步骤,践行了约翰?巴瑞尔的论述——劳动场面是乡村的重要风景。其三,看风景的姿态发生的逆转——从俯视到被窥探。以往的“归乡”小说中,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以审视的姿态出现。但在莫言处,知识分子哑语、被围观,被窥探则成为常态。小说的开头出现几处“狗眼看人”: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两只浑浊的狗眼;
白狗又回头望褐色的土路,又仰脸看我,狗眼依然浑浊。
狗卷起尾巴,抬起脸,冷冷地瞅我一眼,一步步走上桥头去。
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6]
苍老、呆滞的白狗无异于一个审判者,用“浑浊的狗眼”、“冷冷地瞅我、瞥着我”,在这里,作为启蒙者天生的优越感丧失殆尽。这样的观看与反观看的角力,既是对启蒙者观看权力和俯视姿态的消解,又是乡村狂野、原始面目的还原。此时的乡村风景不再是沉默的被观看主体,它开始以与现代城市文明尖锐对立的眼光呈现自己的主体性。
二、精神灵魂的侧面显现
在西方,风景隐然有阶级的身份,这一身份,促成了“风景政治学”的诞生。美国学者米歇尔(W.J. T. Mitchell)将风景从它所隶属的社会阶层中抽离出来,加以重新形塑,认为风景有证实社会身份与捍卫权力关系的功能。“风景并非‘是什么’或者说‘意味着什么’,而是‘做了什么’,如何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而运作。我们认为,风景不仅仅意味或象征着权力关系,而且是文化权力的生产装置,也许还是权力的代理”[7]。在归乡小说中,作者往往会寻找故乡的风景形象代言人,通过与其对话以及对其人生故事的追溯还原,从而折射和挖掘出乡村的精神图谱。比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这些或麻木痛苦,或天真烂漫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故乡在作家笔下人格化的体现,指向故乡秉格的丰盈或匮乏,换言之,故乡中人的社会身份、精神世界与故乡风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互为表征。
在《故乡》中,闰土便是鲁迅所要寻找和戮力塑造的故乡代言人。记忆中闰土的蜕变,实际上也是故乡在鲁迅视野中的蜕变,小说中开始所写到的没有活气、苍黄萧索的荒村图景,以及“我”的悲悯:“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5]与下文“我”与闰土的相见在文本上形成了互文关系。相见时的闰土早已不是年少时期充满活力的模样,而是“浑身瑟索着”,双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不仅如此,年长的闰土早已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所异化,成为彻底的奴隶,他一改儿时与“我”的亲近,以“老爷”这一恭敬称呼唤“我”,在挑选东西带走时,要的是“崇拜偶像”的香炉和灶台。可以说,由外及内,从躯体到精神内核,故乡的衰败与闰土的老朽麻木构成一种对话和关联,他们在文本中的主体性产生了挪动和转移,进而外延扩张转化,被吸收成为一种更为广阔衰败的乡土面貌图谱。不仅是闰土,这一愚昧、衰败的故乡精神图谱在杨二嫂的身上也得到强化。杨二嫂在小说中的性格是尖酸刻薄、好事泼辣、贪图便宜,不外乎是“忠厚老实”的乡民中的另外一个群体的代表。但是愚昧老朽如闰土也好,尖酸刻薄如杨二嫂也好,实际上都未能逃离鲁迅审视者的眼光。他们作为风景的形象和作为精神镜像的内心世界映衬出衰败残缺的乡村灵魂和停滞毫无生机的生命力。
在《白狗秋千架》中,暖是最为适合的故乡形象代言人。与闰土一样,暖残缺、被过度的劳动挤压到变形的躯体,无疑与故乡贫瘠的风景形成了呼应。但是在小说中,“我”与暖的对话和角力,在展示暖多面性格的同时,也呈现出乡土灵魂的丰富内核。这里的“我”再也不是被人恭敬相对的老爷,而是充满忏悔,被暖“冷语”相对的知识分子。当“我”语塞半天后,说出想念家乡时,暖竟然用尖酸的语言回应“我”:“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X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6]。暖背柴离开时,“我”讨好地想上前帮忙,却被一句“不敢用”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在“我”的面前,她还恍无旁人地搽脸洗身,袒露出自己变形的躯体。如果说在小说前半部分两人相见时,暖的“尖酸”、“嘲讽”的语言和不雅的举动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赌气和故意为之,那么小说的最后,暖大胆而坚定地向“我”求种,则更多地表现出两人身份和主体意识上的平等和交流,甚至显示出暖极端强势的一面。实际上,这亦可视之为故乡生命力在现代城市文明形态的询唤之下一次主体确立和意识复苏。尽管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故和打击,但她仍然未被彻底摧垮,不幸的命运可以改变她的容颜,扭曲她的性格,但并不能改变她对“纯种”、对健康生命的执着和向往,她不甘于沉默无力的人生,这是她生存的动力,推而广之,也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得以繁衍和延续的根本。“暖的‘求种’行为还承载着象征的意味,不仅意味着农村企图摆脱封建、落后的现状,急欲向以‘我’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明‘求种’的现实;同时,也意味着深受城市文明侵润的‘我’,在‘藏污纳垢’的乡村,从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自身业已丧失、超乎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的原始生命力”[8]。
同时,由于哑巴的存在,故乡原始的生命力和不安的灵魂得到更深层次的张扬。从他与我相见时“用翘起的小拇指表示着对我的轻蔑和憎恶”到粗暴地强迫暖吃下“我”带来的糖果,到“我”与他喝酒同寝他自在狂野的日常姿态的自然流露,再到与“我”分别时,血气十足地赠“我”以刀。哑巴对待现代都市文明的蔑视和无知,对人群的粗鲁和不拘礼节,一一可视作是乡村旺盛的生命力的集体复活。
可以说,在莫言的笔下,一个迥异于鲁迅笔下“破败之乡”的故乡,一个虽然衰败,但是自在、拥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故乡得以通过对暖和哑巴等人物的刻画构建完成。暖和哑巴的出现改写了鲁迅笔下故乡沉默无力、令人惋惜的生命状态。莫言用叙述主体“我”的卑微和“审视”对象的强大和粗野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故乡的破败之景已经不能全然指向于或者表征它羸弱无知的生命力和精神世界,相反,精神力量的狂野和执拗使得故乡面目得以突破“苍老”、“衰败”、“愚昧”、“无知”的重围,浮出历史的地表。
三、浮出历史地表的“怀乡人”面目
在柄谷行人看来,风景是一种中心透视法的视觉呈现,它在创造“外面的风景”的同时,也创造了“内面的人”。风景的创造是一种外化,本质上是创造者自身的一种折射。因此,在比较《故乡》与《白狗秋千架》中对于风景的不同叙述之中,我们无疑可以窥见彼时的乡村面貌,更可以检阅“我”这个“怀乡人”之于故乡的复杂心态与紧张关系。正如程光炜在解读《白狗秋千架》时所谈及,阅读当代小说应该将其放置于历史的坐标之中,“社会学知识能够给你一个认识世界的“结构方式”,而且能够给你一种立体感,让当代中国社会更为多层化。小说,不过是当代中国社会多层化结构中的一个部分。没有这个多层结构,就不会有这个模样的“当代小说”[1]。
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小说中,我们能读到彼时中国大地上的真实状况。祖屋在寒风中招摇落败;少年时期英勇活泼的闰土却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像“木偶人”,“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5]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关于“故乡”的种种陈述均指向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形态和乡土宗法制度溃败;人们逃离故土进入城市;军阀乱战,民不聊生等中国社会“民生风景”*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一书中将“民生风景”纳入风景之中:“构成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变化世界中的人的景观,这些人包括旅行者、移民、难民、背井离乡者、外出劳工、以及其他流动群体和个人,迄今为止,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景象,并且影响着国家和国际间政治。”。国之将倾,大厦不存。但此时故土上的人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愚昧和家国的沦丧,相反习惯于“做惯了奴隶”的姿态,或如杨二嫂一般沉迷于蝇头小利的争夺,或如闰土一般在盘剥之下沉默,恪守着封建迷信作为自身信仰。
一方面,《故乡》中“我”眼里的风景和作为风景的平凡人的苍老衰败与愚昧麻木,折射出作为“怀乡人”的知识分子在伦理认知上的优越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故乡本无所谓自己的衰老和荒芜,而觉得“日子过得很苦”的闰土想必不会注意到自己“又粗又笨而且开裂”的双手;乡民对人外貌的形容,决然也不会用到一个半是幽默半是讽刺的外来词汇——“圆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启蒙话语之下的审视必定无法全然囊括“怀乡人”的复杂心态。“叙述故乡的丧失”[9]34或是“知识阶级回乡而离乡的故事”[9]193之下既是“怀乡人”对故乡丧失的痛心,又指向自己行走于寻找与漂泊、回返与告别的精神路途中的被动、焦虑和迷茫。小说最后关于希望的论述看似为故乡的未来和自我身份的寻找提供一条道路,但是青山背景的模糊以及“怀乡人”近乎无力的语气,为这条道路添加了几分迷雾。丁帆将《故乡》称之为“虽然不缺乏理性的烛光但更显得消极被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10],可谓是较严厉的批判。
相比于《故乡》,莫言写于1984年的《白狗秋千架》有更为强烈和鲜明的历史印记。自行车等时代奢侈品已经风行;“读书无用论”已逐步开始渗入乡村(其中以八叔对“我”的嘲弄为代表);对于尚是新生事物的牛仔裤,乡民抱以强烈的厌恶;糖果和精美的折叠伞则引来孩子们垂涎。《白狗秋千架》中所展示的这些现实的生活图景,隐然指向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所发生的变迁。1982年,中共中央转批《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主张经济改革从农村入手,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乡村,集中了全国的关注目光。但仅仅两年后的1984年,这目光就从乡村转向了城市——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沿海城市的陆续开放,乡村短暂光辉之后再度遭遇失落。
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占有了传统乡村的资源和权利,更榨取了乡村的血气和劳动力,无形中将乡村置身于进化历史之外,暖“尖酸”和“嘲讽”的语气与白狗、老人对我的“窥探”和“蔑视”,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乡村被“遗弃”,从 “中心”失落时的愤懑不安心态。乡土和城市之间的这一微妙的关系内化到小说之中,成为“怀乡人”内心忏悔和不安的精神来源。小说中“我”不再“启蒙”,“向民间撤退”,并且呈现出对传统乡土伦理的认同和回归。小说中写到“我”一开始与暖相认,出现了称谓和语气上的渐变:
“暖。”我喊了一声。
“暖,小姑。”我注解性地又喊了一声。
“小姑,”我发窘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6]
如果说“发窘”和“嗫嚅”指向城市回望故土的暧昧,那么“我”多次急盼的呼唤更像是并不坚定的内心世界的一次确证。从“暖”到具有宗族身份意味的“小姑”,称呼上的转换,正表明“我”在离开故乡十多年后,自身身份认证仍需回归传统的乡土伦理之中,无从逃遁。
莫言曾谈到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他在离开故乡时,将故乡定位为“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的土地,对其抱以“刻骨的仇恨”[11],恨不得永远不回来;可其又多次坦承对故乡的巨大依恋,“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的祖先灵骨的那片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12]。莫言本身的农民身份使得他并没显示出过高的启蒙姿态,他无意于为故乡的走向指路,尽管现实证明,故乡还将以更快更猛的速度坠入历史的底层,以自身的“空巢”形塑出城市的丰满。相反,深深的忏悔掩饰了,甚至是美化和野化了其落后的故乡“风景”,他以自身的谦卑和无力,乃至愧疚感,还原出自己另一番的“还乡人”面相。
四、结语
20世纪以来的归乡小说始终绕不开对故乡风景和人事的追忆与批判,并急于加入“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总主题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一总主题在《白狗秋千架》却上演了一出变奏:伴随乡村风景面目的多变,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灵魂的震醒、高大与渺小、观看与“被观看”,相互之间出现了暧昧不清的转化。
毫无疑问,莫言在创作上有着鲁迅的痕迹。“鲁迅对故乡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他长期身居在外乡而类乎赌气不返乡的做法,都是可以打开莫言故乡之门的金钥匙”[13]。所幸,在这一重的影响焦虑之下,《白狗秋千架》中的莫言虽然在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上师法鲁迅,但是他赋予了故乡风景新的面貌,也勾勒出在其历史语境下,“还乡人”复杂、忏悔而又暧昧的精神面相。
参 考 文 献
[1]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8):10-19.
[2]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 John Barrell.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92.
[5] 鲁迅.故乡[M]//鲁迅.呐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25.
[6] 莫言.白狗秋千架[M]//莫言.白狗秋千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244-258.
[7] Mitchell W J T. Landscape and Power[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1.
[8] 康林.莫言与川端康成:以小说《白狗秋千架》和《雪国》为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11(3):129-137.
[9]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M].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2 .
[10] 丁帆.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8.
[11]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2):37-39.
[12] 莫言.超越故乡[M]//莫言.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26.
[13] 叶开.莫言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