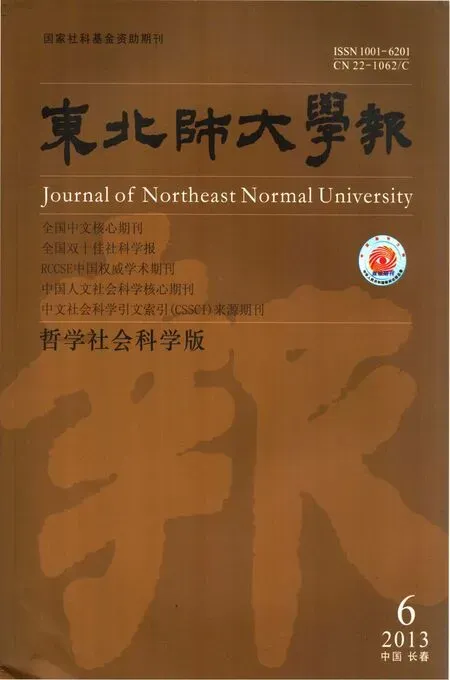野蛮与文明的融合变奏——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的蛮族文化传统与英国文化精神
2013-03-24王春雨
王春雨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形成而言,文化因子的构成与相互作用极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文化的形态,更加影响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重构。文化因子及其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式和形态更是千变万化。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可捉摸,相反,认清一个文化的源流对于认识这一文化的内核至关重要,人类诸多学科的努力也正是让这种厘清成为可能。来源于日耳曼口传文学形式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长期以来不仅被当作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在英国文学史中大放异彩,更是在诸多的日耳曼史及英国史中作为反映盎格鲁-撒克逊部族的重要参考史料屡次出现。这不仅因为现存的反映日耳曼早期历史的资料非常鲜见,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学界对《贝奥武甫》折射出了日耳曼蛮族文化因子及其对后世文化精神形成所产生的作用的认同。“关于蛮族人的文化与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被此前的国内学者们所忽略。我们耳熟能详的看法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是由‘二希’文化哺育的结果。这种看法,其实只说出了问题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看法是,没有蛮族人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贡献,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乃至后来的欧洲文化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1]这一点对于英国尤为适用,英国“自诺曼征服往上追溯,种族混合史约占千年之长。”[2]蛮族文化因子对英国文化精神形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是有了蛮族的入侵,英国的历史才充满了冲突,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冲突正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冲突中的融合是英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这也是“英国模式”形成的基础。如果说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里呈现的正是英国历史文化中的野蛮与文明融合的独特景观。
一
作为文学和历史共有属性的英雄史诗无疑是各民族的重要的文化遗产,“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3]《贝奥武甫》正是这种基于口头诗歌创作的英雄史诗。作为英雄史诗,与文学作品之于历史的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在文化史、精神史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使命和作用。
历来认为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翻开中外任何一本英国文学史著作,大部分都是这样表述的,连较为权威的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也不例外。但这并不代表着没有质疑,因为在史诗的创作及传播方面还有很多空白,这造成了人们的猜测及质问。在新的史料出现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同意这样的事实:“故事背景虽然是在北欧,其中所反映的精神却正好代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英国人的远祖正是来自北欧。所以这部北欧气味浓厚的史诗亦无妨称之为英国史诗。”[4]不管史诗故事发生地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如何认为,这都改变不了英国人的日耳曼蛮族血统。这种血统促使了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的形成及流传,更加促使了其英伦风格的改造及认同。
据有关史料证实,历史上确实有贝奥武甫其人,但记载甚少,如果我们把《贝奥武甫》单纯地看作是一部文学文本的话,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因为文学作品重视的是想像和情感,作品主人公的历史真实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正如“文学批评不去关心《启示录》的作者是谁,却可以欢迎以《启示录》为背景的超现实诠释”[5]。但如果我们把英雄史诗的“史”的属性扩大的话,也并不妨碍其“史料”作用的发挥。我们知道,史诗的具体作者虽不可考,但至少有两类人参与了史诗的创作,一类是日耳曼民族的游吟诗人们,一类是10世纪左右不列颠岛上某个修道院的僧侣们。游吟诗人以吟诗为生,所以吟唱的内容取决于听众的反映,《贝奥武甫》被口传吟唱了近5个世纪不仅仅是因为故事的离奇动人,更为重要的是让听众产生的强烈的认同与共鸣,这种认同来源于本民族共有的价值内核。这种价值内核一直延续到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观的10世纪左右的英国。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与神迹故事众多,为何还要选取远祖口传的异教故事来做为加工改造的对象呢?这里不排除僧侣们对祖先英雄故事的感情,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故事中传达的价值观在当时也有强烈的社会认同感。
共同的价值观一定是民族融合发展的产物,英国民族历来非常热衷于幻想,这种热衷于幻想的情愫造就了优良的文学创作与欣赏的传统,一直以来大量的英国文学精品在世界文学宝库中闪着耀眼的光芒。然而在这种丰富而独特的幻想背后,最为重要的精神实质是对自由的标榜与推崇,这是英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核心。对自由的标榜来源于民族形成之初的经历与记忆,自由精神贯穿于英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无论是和平时代,还是争战时期。
除崇尚自由外,更为重要的就是对真诚的追求和向往了,日耳曼这个词语本身就包含着真诚的含义,而绝非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是野蛮的同义语。而在英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真诚精神无处不在,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商业运作。真诚体现在英国民族非常重视自身和他人信誉上,更体现在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要究其真相,论清根本方面。总之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很多特质,他们对财富的追求毫不掩饰,他们奔放而又理性,他们郁闷但不伤感,他们意志坚强又恪守规则,这些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在英雄贝奥武甫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二
在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观以及对伦理、道德的基本认识,这些认识基本上都来源于被罗马人称为蛮族的传统。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认为蛮族对于欧洲中世纪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消极的,尤其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被罗马人称为三大蛮族之一(三大蛮族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野蛮行径,更是因为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迁徙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正确地对待蛮族文化的作用是正确还原中世纪历史文化原貌的前提。
就英国历史的发端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英格兰的历史开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那不仅因为这些新到来的日耳曼人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现在通用的名字,更因为英格兰民族的主体也是由他们的后裔所组成的。”[6]9这就注定了英国历史中拥有无法抹去的蛮族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一直影响着英国历史的走向和英国文化精神的形成。作为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主要人物就是日耳曼蛮族的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就是日耳曼蛮族所追求和向往的最高理想,我们通过细读作品可以梳理出史诗中呈现的蛮族文化的精神内核。
(一)仇杀和掠夺是蛮族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知道日耳曼民族长期处于以血缘维系的氏族部落时代,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是掠夺他人以获取战利品,可以说蛮族民族大迁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这也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强取豪夺必然以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部落之间或结盟或对立,所以仇杀时常发生。仇杀实质是以一种看似正义的理由为掩饰进行的更加血腥和残忍的掠夺,这是整个日耳曼民族崇尚的精神,也是史诗《贝奥武甫》故事发生的前提和内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仇杀是日耳曼民族极为重要的传统,这在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里有突出的表现。可以说,不明白这种仇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贝奥武甫》。”[7]
通过史诗我们可以知道,贝奥武甫之所以冒着巨大的危险来到丹麦,除了显示其是一位人人崇拜的英雄之外,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报仇。他为谁报仇呢?表面上看是为了丹麦国王赫罗斯加和其子民,而实际上是为了他的父亲艾克塞奥。根据史诗描述,“贝奥武甫的父亲曾经惹过一桩祸事,他亲手杀死了威尔芬人希塞拉夫。希尔德子孙则以金钱化解了那桩血仇,所以贝奥武甫的父亲从此与赫罗斯加起誓结盟。”[6]35由此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贝奥武甫的父亲与丹麦人已经结盟,贝奥武甫必须与丹麦人站在同一阵营,这是一种契约,也是建立自己信誉的保障。
当英雄贝奥武甫打败了恶魔格兰道尔,新一轮的仇杀又开始了。格兰道尔的母亲为死去的儿子进行了更加凶残的复仇:“她迅速抓住一位武士,然后即刻返回她的沼泽地。被抓走的是一位光荣的战士,四海之内,在所有的扈从中最受赫罗斯加国王的恩宠。”[6]67鹿厅再次陷入悲伤之中,随后,英雄贝奥武甫再次出场,他对丹麦国王说道:“请不必悲伤,智慧的国王!与其哀悼朋友,不如为他报仇。我们马上出发勘探妖母的行踪,我向你保证:不管她逃到哪里,无论她钻入地下,还是躲进深山,抑或潜入海底,都要把她找出来。”[6]71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相互之间的仇杀反复地进行着,尽管又一次成就了英雄的威名,但双方都损失惨重,英雄的事迹随着复仇的成功而被广泛赞颂。
(二)勇敢和忠诚是蛮族文化的方式和途径
仇杀和掠夺固然是日耳曼民族日常生活的常态,但人们尊崇的品格却是勇敢和忠诚,这是完成仇杀成就英雄的唯一途径,也是后来被基督教所接受的异族精神。史诗中处处都在赞颂这种优秀的品格,贝奥武甫就是勇敢的化身,他为了报恩为丹麦人复仇,杀死恶魔格兰道尔和其母亲凶狠的女妖;他为了保护王国的利益,年迈之年不顾自身安危与火龙搏斗,恶龙被杀,自己也受重伤而死。在整个过程中,他都表现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在与恶魔格兰道尔的斗争中,他“使劲反而将恶魔的手臂紧紧抓住。作恶多端的魔鬼很快发现,在世间,在这广袤的大地上,他从未遇见有谁的臂力与他比匹相当。”[6]46在与格兰道尔的母亲女妖搏斗时“只见他一剑击中女妖的脖颈,砍断她的肩骨。锋利的刀刃刺穿那具该死的躯体,她轰然倒下。”[6]78在与火龙决斗时,“贝奥武甫最后一次发出他的豪言壮语,我年轻时就曾身经百战,如今年事已高,但作为人民的庇护者,只要作恶者胆敢从地洞里爬出,我就一定向他挑战,让我的英名千古流传。”[6]115因为勇敢,他才受人崇敬,因为勇敢,人们才拥戴他为国王,从而也说明在日耳曼民族中,勇敢是人们推崇的第一品格。可见,为同盟复仇,只身犯险是人们崇尚和鼓励的,人们明知道远赴丹麦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极有可能有去无还,他们也极有可能失去本族的一位能征善战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将会成为自己部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贝奥武甫在族内威望很高,深受族人爱戴,但即使这样,大家都鼓励他去。这说明在日耳曼部族那里,信誉远比生命更为重要。
除勇敢外,忠诚则是日耳曼蛮族崇尚的另一品格,史诗里表现了个人对集体、对盟友的忠诚,亲兵、随从武士对主人的忠诚,武士对国王的忠诚等,这是日耳曼部族中最为崇尚的上下级关系。当贝奥武甫决定远赴丹麦直面巨大的危险时,他选择了十四位武士与他同行,从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四位武士对贝奥武甫表现的极为忠诚,“武士们争先恐后登上甲板,潮水汹涌激荡,冲击着沙滩,勇敢的武士们把闪光的盔甲、珍贵的兵器搬进船舱,然后船儿被推进深水,武士们登上了备受祝福的航程。”[6]25当贝奥武甫在深潭中与妖母搏斗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时,很多丹麦武士都以为贝奥武甫一定是遇害了,但高特武士们却不愿离开。“时间已是下午三点。英勇的丹麦人开始撤出山岗。武士们的朋友回到自己的王宫。但高特的武士心情沮丧,依然守望着水面。他们希望——明知这希望渺茫——再见到他们敬爱的领袖。”除此之外,史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王与下属之间相互平等共处的关系,王被称为“恩主”、“部族的保护人”、“财富的分发者”等,这种忠诚、平等、服从等观念都是血缘维系下部族关系的典型特征,“蛮族的忠诚的观念和服从的意识以及其他意识,毕竟是家族血缘联系中产生和积累下来的,因此,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文化观和文化意识,而不是自觉的或自为的创造的结果。所以,说到底,它依然是其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产物。”[6]69
(三)冲突和融合是蛮族文化的实质与归宿
蛮族文化中好勇斗狠的特性促使他们不断地入侵和掠夺,与被掠夺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地发生与加剧。但我们还要看到,蛮族文化中固有的一些优良品质使得他们的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在征服的途中与当地文化并非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很多时候蛮族文化与当地文化,尤其是与当时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进行了有机的融合,这一点在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文化痕迹历来受到多方质疑,基督教和日耳曼传统在诗中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的重点。这样的争论一直继续,因为史诗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均无法准确地界定,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史诗发生在约5世纪的瑞典和丹麦,根据基督教的传播情况和日耳曼人的发展历史,故事发生时和基督教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人物和事件都是属于异教的。而且史诗一直处于口传文学状态,当被征服者带到不列颠时,基督教已经在岛上传播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因此把一部异教的口传文学变为书面文学时基督教的因素一定是人为加入的。但问题的重点是这种异教故事与基督教的思想观念能够共存在书面文学的《贝奥武甫》中并且被人接受,这不能不说是文化融合的结果。阅读《贝奥武甫》时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史诗中多次让英雄处于上帝的关怀之下,贝奥武甫对氏族部落和王国的忠诚转化成了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忠诚。史诗对基督教正统地位的肯定以及对异教行为的斥责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奥武甫是代表上帝去和恶魔格兰道尔征战的,他的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上帝的荣耀。
虽然我们不得不说,从史诗的行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基督教思想的融入有些生硬,但这里我们看到了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融合趋势,一个异教的民族英雄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护教者的形象,但又保留了日耳曼民族的独特性格特征,这本身就能说明到了8世纪至10世纪,英国文化已经融合成了一种新的形态,不同于日耳曼民族传统文化,也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传统直接决定了未来英国历史的面貌。
三
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在英雄故事的背后实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文化的发展结构,即侵入——冲突——融合。这种文化发展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蛮族的文化特性,用基佐的话说就是一种情操、一个事实:“个人独立的快乐;在世事和人生的种种机遇中,生气勃勃地、自由地享受人生的那种快乐;有活动而无需劳作的那种快乐;对充满不可靠性、不平等性和危险的冒险事业的爱好。这些便是野蛮状态的主要的情操,也就是驱动这些人群的精神欲望。”[8]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蛮族文化因素前提,当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时,独立、快乐、自由、冒险、忠诚这些文化特征都会发生作用,而不会出现断裂。
纵观《贝奥武甫》中的前后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贝奥武甫经历了两个转化,一是从氏族部落英雄向封建王国英雄的转化,二是由异教英雄向基督教英雄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知道当盎格鲁-撒克逊人以蛮族入侵的方式占有英格兰之后,武力争斗就不那么重要了,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实用的信仰依托,需要有利的制度来保护家庭生活和各项权利。同时,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权也需要规范和保护。在这种现实需要的推动下,基督教融入人们的生活便是一种历史必然。这种文化融合的现象在英国历史中成为主流,形成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在英国,由于种偶然或必然的因素,冲突却常常以融合而告终,斗争的过程可能很激烈,融合的经历可能很漫长,但结局却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方都被改造又都被保留。被改造的双方其实是互相吸取的,由此产生一个新事物”,所以“英国的道路——和平、渐进、改革之路,其秘诀正在这里,在其中,冲突与融合缺一不可,斗争与妥协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9]。
冲突和融合出现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各个时期,无论是罗马统治,还是诺曼征服,无论是蛮族入侵,还是丹麦掠夺,一次次的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英国民族共同的记忆,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形成了民族的文化。融合之后的文化形态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民主制度与王权形式共存,保守政治与自由精神共存,野蛮殖民与绅士风度共存,古堡庄园与现代建筑共存等等。在英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处,传统与变革是一种常态思维方式,这种创造性与包容性共同作用的精神结构使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着与其它国家民族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比如他们对宗教既注重其普适性,又注重其独特性,既看到了基督教中的善,又能够勇于追求基督教中的真,所以英国的宗教形态是明显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也是为什么《贝奥武甫》能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被改造和接受的原因。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野蛮与文明不仅是文学中的诗行,更是历史与现实的镜像。
[1]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0:63.
[2]屈勒味林.英国史[M].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
[3]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M].王亚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
[4]梁实秋.英国文学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9.
[5]叶君,柳博赟.论圣经研究的范式转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15.
[6]陈才宇译.贝奥武甫.世界英雄史诗译丛[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7]肖明翰.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8]基佐.欧洲文明史[M].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7.
[9]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