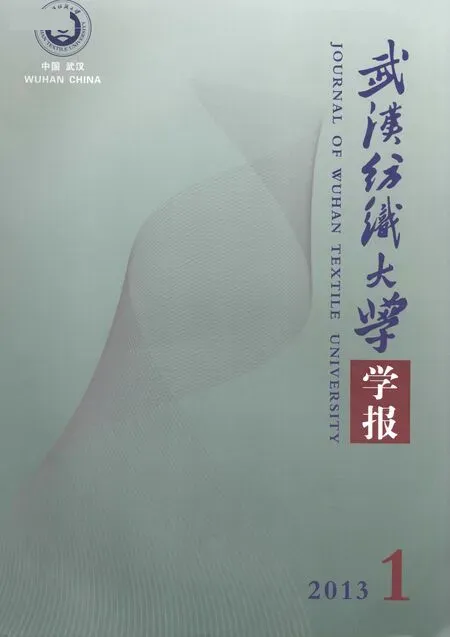村规民约溯源及当代价值
2013-03-19杨程
杨 程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再度复兴使人们对它的关注不断扩增。诸多学者对村规民约进行了不同视角、语境及程度的考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村规民约被置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中进行个案研究。综合地讲,对于村规民约的多维度探索,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治理,为了完善基层民主的建设,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二者关系的良性互动。因此,村规民约作为一种制度,如何充分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形塑乡村社会秩序,就显得异常重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村规民约逐步演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活着的传统。然则,在这种生生不息的传统演化进程中,村规民约的内涵也变得交织错杂,形如迷雾。为了使村规民约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则必须首先厘清村规民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认识它与其他规范、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一、村规民约溯源: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
村规民约,古已有之。要探明村规民约这种制度,首先需要考察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之间的关系。根据董建辉对明清时期乡约的考察:传统中国社会,不仅乡规民约的历史比乡约要悠久,而且从内涵和性质上比较,乡规民约也不等于乡约[1]。持同样见解的还有卞利,他在分析明清徽州的乡规民约和乡约时,就采用两个章节分别论述,予以表示二者的不同[2]。然则,有区分必然就会有混同,例如: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黄珺主编的《云南乡规民约大观》,就清晰的表明:“乡规民约不仅包括我国古代乡约制度下产生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现代政府主导下制定‘乡’(村)规民约,还包括社会成员为调整彼此利益关系而制定的或官方调解民间纠纷而制定、认可的各种规则”。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牛铭实,他在《中国历代乡约》中,将“村规民约与当代村民自治”这一章编纂在“乡约导读”部分。与此同时,但凡认同乡规民约滥觞于北宋《吕氏乡约》的,基本上都是将乡规民约与乡约等同视之。
但是,正如董建辉所指出的:“从学术的层面看,虽然乡约与乡规民约之间的确有许多的联系和共通之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仅其内涵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1]笔者认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讲,首先要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规民约《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劵》以及最早的乡约《吕氏乡约》进行分析、对比。由于《吕氏乡约》一直以来讨论诸多且基本历史脉络清晰,因此,笔者在文章只对其进行简要的梳理。但对于《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劵》的分析由于学界主要停留文史考据层面上,对于其作为一种民间规约的规范层面考察较为薄弱,因此笔者着重分析这则规约。
《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劵》从规范角度看,它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标题中的“僤”和“里父老”指的是民间组织及其管理者。“此僤是以一定地缘为本的民间组织,其成员局限于侍廷里的范围。”[3]“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管理者,“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物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祀,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起到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4]结合该劵文来看,“僤”这个民间组织组建的目的是为了给管理这 25户公共事务的里父老予以经济上补助,即由立此约的25个人名所代表的25户人家集资买田,使田上的收益用于补给和奖励里父老。其次,劵文向我们交代了这则规约中的两个重要领导人物,即“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祭尊、主疏在该僤中分别是列位第一和第二的领导,是这 25户人家的代表者和核心管理者。在这则规约的落款处,我们看到“于姓”在规约中占了10户人家,拥有其强大的家族势力,所以由于季作为第一领导人合乎民间社会的规则运作。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于季虽然是该僤的第一领导人,但是却不代表他是该僤中的“里父老”。因为该劵文规定只有具备一定经济条件——訾次,才能成为“里父老”。主疏一职是从事文书工作,也就是说左巨可能是这所有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他主要负责书写记录工作。再次,卷文展现了一个民间完整规范。于季等25户人家共同集资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亩,将田地提供给父老,用于补给父老在承担公共事务中的经济损失。这八十亩田是此僤的集体财产,由此僤享有所有权,父老只有使用权,并且后代对此田的继承权利也只享有其使用权。当集体利益需要时,可以将其田予以出租获得孳息,作为集体经费所有。
通过上述劵文分析,我们可以对古代乡规民约与现代村规民约的关系进行几点小结:第一,从它控制或约束的地方范围来看,大致限于“一里”,相当于今天我们一个村的地域范围。所以,这类规约也被称为“乡里民约”,今天我们普遍称为“村规民约”以表达它约束的地域空间。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指出,古代乡规民约和现代村规民约主要是基于地缘关系而设置的规约,它古已有之,可追溯到东汉建初2年。第二,从它制定的主体来看,形式上仍然是参与该规约的全体乡民,从实质上看,主要是由发起人来草拟规约文本。担任主要发起人的人选大致需要符合两种条件:其一,大户姓氏中要派出一个代表,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家族的权威和利益;其二,在这些乡民中选出具备相当文化水准或教育程度的代表,负责书写和辅助起草规约。今天的村规民约从制定主体来说,虽然已经基本确立为村民大会,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然保留上述分析的传统做法。第三,从它制定的目的来讲(此处目的作功能解释),着重体现“管理”这一基本功能,即管理事务的含义。该劵文通过补给或奖励这种手段,让里父老更好地替乡民们服务,帮助全体乡民管理乡间的公共事务。因此,从功能上说,主要体现“管理”,今天的村规民约延续了古代乡规民约的这一主要的社会功能。当然,这一点也是笔者认为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主要区别的地方之一,因为乡约的功能重在体现“教化”,而非“管理”。
作为乡约的历史源头,《吕氏乡约》最有代表性,将“儒家精神的感化”体现的淋漓尽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无一不体现中国古代“礼”的要求,可以说,“礼的主张是乡约制度的根本”[5]。乡约这一传统的体现和它的主要发起人吕大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吕大钧,在礼学上有过人的造诣,作《吕氏乡约》,是为了实现自己知行合一的理想,使乡约能感化乡民、淳化风俗。“杨开道认为,吕氏乡约与古礼的关系有两处。一是它的根本原则与《周礼》十二教的教化精神一致。二是它继承发展了《礼记》的乡饮酒礼。”[5]
乡约的社会功能,目的体现为维风导俗。[6]当然,乡约的属性和职能也不是一直未变,正如董建辉所指出:“明清乡约是宋代乡约的历史发展,其属性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乡约由一种民间教化组织转变为官治的工具,它的职责也相应地从社会教化与救助,转向同时承担基层的行政和司法事务。”[1]但是乡约的主要功能并未随着属性和职能的变迁而发生实质变化:都是“以儒教的精神感化为其运作的核心功能。”[7]
如果对乡约进行整体考察,把乡约作为一种民间基层组织,有学者归纳其特征:其一,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二,有定期的聚会;其三,有比较固定的活动场所,称“约所”或“乡约所”;其四,有一套繁琐的读约仪式;其五,乡民入约,往往要缴纳一定的会费[1]。
那么传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到底有哪些区别与联系?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不同之处:第一,古代乡规民约在功能上侧重于“社会管理”,乡约在功能上侧重于“社会教化”。第二,古代乡规民约在精神上侧重于“能者当政”,乡约在精神上侧重于“人人皆为尧舜”。第三,古代乡规民约在表达上侧重于“平铺直叙”,乡约在表达上侧重于“意蕴悠远”。相同之处:第一,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都属于民间规约,均是民间智识行为的结晶。第二,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均体现民间规约“私”的性质,即它们都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作后盾,而主要依民间契约的约束力做保障。第三,古代乡规民约与乡约主要运作人均是地方精英,这两种制度的运行都要依靠民间有贤德、有资历、有訾次的人物操作。今天的村规民约与上述特征均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可谓一脉相承。
二、村规民约的生存现状:村民自治章程与村规民约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村规民约古以有之,它发端于古代乡规民约和乡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化,现在广泛存在于广大农村,成为现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手段。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即村民自治章程是否是村规民约变迁的产物呢?
如果将1987年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视为村民自治章程的开端,那么我们看到,“山东省章丘县(1992年改为章丘市)是全国最早制定村民自治章程的地方[8]。”“1991年6月7日,埠西村召开第三届村民代表会议,79名村民代表一致通过了《埠西村村民自治章程》[8]。”该文本成为现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史上的第一部村民自治章程。该文本共分五章。“第一章“总则”有五条,主要内容是制定该章程的依据、开展村民自治的目的和全体村民的要求。第二章为“村民组织”,这是该章程的重点,它总共有5节15条。这5节分别是:第一节,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第二节,村民委员会;第三节,村民小组;第四节,村民;第五节,村干部。第三章的内容是经济管理,共六节,分别为劳动积累、土地管理、承包费的收取使用、生产服务、财产管理和大力发展村办企业。第四章是对社会秩序的规定,其中第一节社会治安,第二节为村风民俗,第三节为邻里关系,第四节为婚姻家庭,第五节为计划生育,第六节为村民档案[8]。”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部内容涉及村庄的各项大小事务、规范完整的章程清晰地向我们证明它的村庄“小宪法”地位。可以说,20多年过去了,今天许多的村庄在制定村民自治章程上仍然沿用着这一套固定的模板。就笔者调研的恩施州利川市南坪乡营上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而言,其文本共为五章。第一章总则,共4条。第二章村民组织,共4节17条,这四节内容分别为: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第三章经济管理,共2节6条,这两节内容分别为:土地管理和财务管理。第四章社会秩序管理,共7节36条,这七节内容分别为社会治安、村风民俗、邻里关系、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村民档案。第五章附则,共3条。我们对比这两个不同村庄的村民自治章程,就可以发现,他们从形式和内容上基本保持一致,不同的是有些章节涉及的内容会有所增减,这是根据不同村庄的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而变化。
但是,如果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作为村民自治章程的开端,这种理解难免会让我们失去对它的全貌认识。因为有史料显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Sidney.D.Gamble在1908-1932年间曾四次来到中国进行调研访问。尤其是他对中国北方农村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一份研究报告,1963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了这份报告,题目为《华北乡村:1933年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郎友兴从这份资料中节选了山东一个村庄的四份村规民约,旨在为村民自治提供一个历史背景[9]。这四个村规民约是有关村务的规程:第一份是1930年6月28日制定的“村(保)会议条例”,里面规定了村民会议的职能、与会形式、参与人员的资格问题等。类似于我们今天村民自治章程的第二章村民组织这个部分,是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规约,因为在1930年,村(保)民会议组织的权力与责任相当于立法机构。第二份是“村公所规则”,村公所是村级的执行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民委员会。第三份是“村官员选举规程”,相当于今天村干部的选举程序。通过这份规约我们可以看到:“村级领导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K村的选举规程就说明近代农村已有民主选举了[9]。”第四份是“村民守则”,相当于今天的“村规民约”(此处作狭义的理解)规定的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民自治章程”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社会产物,也不是在《村民委会会组织法》下冒然而生的催生品,而是在历史传统中存留下来的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制度。是对历史经验中的村规民约的一种提升、扩展和总结,是一种历史传统的承接,是现代村规民约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今天,因村民自治章程由地方政府主导,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在现代语境中使用往往指针对特定事项的规范,使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章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那么现代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章程有何种区别联系呢?其一,从规范内容来说,村民自治章程是村级自治的总章程,内容较为抽象和系统;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具体规约,内容涉猎具体而多元。其二,从规范地位来说,国家法并未确定二者的位阶关系,但从大量的民间实践中已经彰显村民自治章程略高于村规民约的地位,事实上这有可能是因为村民自治章程被誉为“小宪法”的原因。就二者实质的关系而言,他们之间是互相的补充和延伸的。其三,从规范的效力而言,由于国家法没有承认这二者的制裁效力,使得其无法与其他法律规范和制度有效对接,因而在其实效性上大打折扣,不同地方的村规民约执行差异较大。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者否认村规民约的生存价值的根本原因。
三、村规民约的制度价值:活着的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是一种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那种延续性的意识,是现代的过去,更是现代的未来基础。我们在不断地界定村规规约这一概念的过程中,缩小和狭隘了事物的发展空间和未来,我们区分它(乡规民约与乡约、村民自治章程与村规民约)不是为了各自画地为牢,而是为了实现它吸纳不同语境下使用的村规民约(广义),扩充它的范畴,丰富它的知识结构,使之更加多元,为新的延续提供更为广阔的伸展空间,成为真正活着的传统。
为什么村规民约成为一种活着的传统,这源于几千年来,中国治理边缘地区的大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村规民约始终都是村民实现自治的智识结晶,古有“父老僤”、“吕氏乡约”,今有“村民自治章程”、各种“公约”等,无一不是村民们通过习得而获得地方性知识。但仅有这种自生自发的传承也不足以使之延绵下去,因此我们也看到了政府的强制命令对村规民约的控制和干预,尽管它引发了村规民约在自治效力上的危机,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插足使村规民约有力量存活至今。
“维风导俗”,是历史经验中的村规民约留给我们的宝贵价值。今天,民法的基本原则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指的也就是要维护善良风俗。因此村规民约也成为村民们实现公平正义的一道标尺,是具有中国式的正义衡平标准。这种特性使得村规民约有着独立存在的空间和价值,是它为之可以传承重要因素。那么它发展中的短板在哪?那便是国家、政府对它的控制、干预,不承认其制裁效力。穆尔很早就指出:“国家既没有垄断有效的制裁,也没有垄断产生拘束性规则的权能[10]。”但为何村规民约的实效性受到如此冲击,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与其他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制度进行有效的对接,使受之统治的村民无法利用其规则与外界规则(如国家法)进行良好的沟通,最后成为谁也不买帐的“鸡肋”。
现实中,我们总是无法逾越国家法与习惯法二元对立的鸿沟,总是试图超越,但总怯于失去自己固有的位置。国家法的中心主义、习惯法的边缘地位使社会在自我控制、自我调适过程中总是显得力不从心,而唯有“半自治社会领域”中的潜规则发挥着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深受各种潜规则的迫害,却又不得不遵循这些潜规则行事。我们没有有效的法律利器,因此也无法平衡各种纷争,于是我们被规则中的规则循环反复地操控。这些应该收场了,因为我们需要法治。那么,法治如何可得?
在基层农村,就需要我们重构村规民约,扩展村规民约的制度价值,重塑其社会功能。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了它的优势,也在历史中看到了它的劣势,但我们更应该在现实中看到它从来不拘一格的存在方式。它从来不强调自己的社会位置,所属领域,只是不断地调适着自己。这就为我们协调和沟通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搭建了重要载体。它被多次论证中,证实了其传统的价值性,也披露出许多与国家法相互冲突的现实问题。但冲突的开始不代表消极的结束。事实上,村规民约一直积极地与国家法进行对接,只是在对接中存在诸多的人为因素,使它抵触了国家法度,成了众人眼中国家法与习惯法不和的事实证明。但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它既然有意对接国家法,我们为何不给它送去橄榄枝,搭上疏通与国家法对接的桥呢?(这一技术性的制度空间拓展有待另文详论)。需要予以说明的是,这种拓展过程中,难免会被人再度扣上“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帽子,但我们需要客观地讲,这不是一种中心主义,而是一种让村规民约纳入到更为多元的知识体系中,在这种新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使之求得共同的发展。
[1]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2]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3]张金光.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2003,(10).
[4]马新.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J].东岳论丛,2005,(6).[5]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6]王崇峻.维风导俗——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变迁与乡约制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7]杨念群.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J].清史研究, 1993,(3).
[8]罗平汉.村民自治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9]郎友兴.对七十二年前山东一个村庄村规民约的简要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3,(2).
[10]李婉琳.社会变迁中的法律——穆尔法人类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