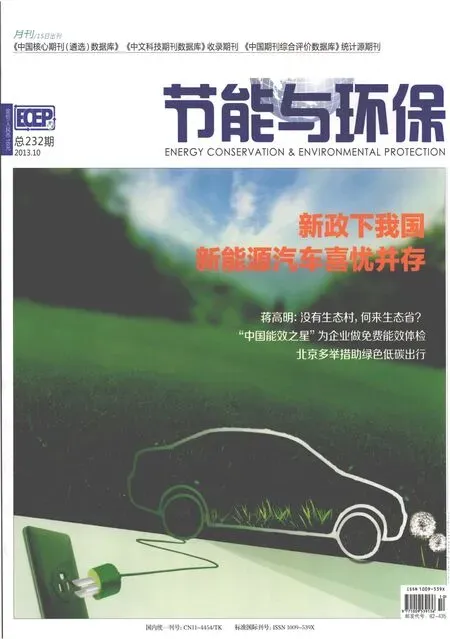蒋高明:没有生态村,何来生态省?
2013-03-12陈向国
文 / 本刊记者 陈向国
中共十八大后,生态文明建设升格为“五位一体”的国家战略。在这之前的中共十七大,强调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2008年确立了要在2020年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目标。
是年1月15日,国家环保部主办的《绿叶》杂志上刊登了题为《农业需要一场生态学的绿色革命》的文章。该文呼吁,农业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逐步摆脱大化肥、大农药和转基因等现代农业技术束缚,从循环农业入手,促进粮食安全、食物安全和环境保护多赢。那时,该文章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教授已经在为这场农业生态学的绿色革命而躬身实践了;那时,蒋高明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蒋家庄创建的弘毅生态农场已经3岁了。弘毅生态农场租用的是村里曾经的建筑垃圾堆放地、土层只有20厘米的低产田。在这块土地上,蒋高明坚持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他用农家肥提高土壤有机质从而生产出高产有机粮。开始的两三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每亩收才1000来斤,到了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吨粮田,并且产量连续平稳——超出周围农田亩产一倍多。
弘毅农场是如何做到的?该农场充分利用了农场内外的一切生态要素,让各种元素循环起来发挥作用,实现有机循环,实现有机粮吨粮田。弘毅农场用实践证明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以搞,可以像依赖现代农业技术——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获得高产一样,获得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高产——不低于依赖现代农业技术的现代农业的收获。更重要的是,生态农业因为不依靠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等现代农业技术,从源头上减轻甚至消灭了对土壤的污染、对水的污染、对空气的污染。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表示:“生态农业是实现中国两型农业的发展方向,弘毅农场用现实证明了生态农业不是理想中的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
但,实现生态农业要抛弃原来的利益格局,要停止争论,让实践检验真理。
近几年,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生态文明火了,生态农业火了。如雨后春笋般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应运而生。对于此,蒋高明表示:“据我所知,中国目前尚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村,但官方宣布的生态省就有十几个。”是蒋高明在唱反调吗?“这不是唱反调,是客观事实。我实地调查了很多早期的生态村,发现那些富裕起来的生态村,走的都是工业化路子。很多地方打造生态市、生态省,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农业依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热带地区也铺农膜,除草剂更是大量使用。生态村都没有,哪里来的生态省?”
蒋高明说:“我理解许多地方打的是生态概念,这是可以的,但既然打造生态村或生态省,就必须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让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各项元素循环起来。遗憾的是,真正这样做的不多。”在蒋高明看来,生态文明必须扎扎实实从生态村做起,而非一纸文书、一个只有在专家层面理解的自上而下的、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生态文明。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常年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生态农业的研究和实践,热心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身体力行支持开展保护中国生态环境的活动。其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创建的弘毅生态农场,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的情况下,已将低产试验田变成稳定的有机吨粮田。
为何是农村?
农村已经成为污染严重的地区。污染一方面来自现代工业的废水、废气、废渣;另一方面就是工业化农业造成的对土壤、河流、空气的污染。这些污染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食物、人们的健康。工业化农业对农村的污染已经恶迹昭著。
化肥、农药过分使用使农村充满杀机
记者:化肥使农作物增产,但化肥的过量使用会导致环境污染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吗?
蒋高明:中国每公顷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为434.3千克,是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60%的化肥中氮磷随水流失到河流或地下水中。河流因为过多的氮磷而出现富营养化。不久前,我到河北沽源去考察,滦河的发源地闪电河就在那里,而今闪电河的变化令我吃惊。20年前,我曾在闪电河做科研项目。那时的闪电河河水清澈,岸边风光优美。可如今,由于富营养化,苔藓、蓝藻疯长,往日风光已经不再。原因就在于当地要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为了增加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化肥残留通过雨水流到河里造成富氧。而实际上,闪电河是当地重要的水源。这样的情况很普遍。
记者:在弘毅农场除虫不用农药,这是为什么?
蒋高明:使用农药除虫,同一种农药的效果会越用越差,只能用毒性更大的农药才能起到效果。而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药越用越毒,害虫抗药性越来越强,最终害虫无法根治。目前,中国每公顷耕地农药平均施用量为13.4千克,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农药残留和化肥残留汇集到河中,河水就会受到污染,鱼虾逐渐减少,甚至绝迹。可以说,现在的农村是充满了杀机的“杀场”。弘毅农场采用生态防虫法,可以实现有效控虫,捕获的虫子用来喂鸡,生产有机鸡肉、鸡蛋,形成有机良性循环。
“白色恐怖”造成双重危害
记者:农膜残留问题越来越受关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如何?
蒋高明:白色污染问题不得不令人忧心忡忡。十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农村调研,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对粮食生产大省河南、河北、山东、吉林、辽宁、黑龙江、四川、湖南、湖北农村去过多次。总的情况是污染越演越烈。北方耕地几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所覆盖,从空中俯视北方乡村,大地白茫茫一片,仿佛来到了一个“白色恐怖”世界。即使在热量条件非常好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种地也覆膜,只不过由白色变成黑色。
记者:农膜残留有哪些危害?
蒋高明: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残留在15~20厘米的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很明显,影响作物生长。其二,农膜回收难、利用价值不大,绝大部分会被烧掉。而这一烧,却带来了更直接、更厉害的污染。
记者:更直接、更厉害的污染是什么?
蒋高明:农膜焚烧会产生不少于5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主要是毒杀芬、六氯代苯、二恶英、呋喃、多氯联二苯。这些物质是2004年生效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首批公布、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对人类危害极大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在自然界中长期存在,最长可在第七代人体中检测出。这些物质毒性极强,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受损、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农膜虽然实现了反季节蔬菜生产和提前上市,但代价惨重。由于长期生产反季节蔬菜,大量化肥、农药、农膜污染,导致以蔬菜产业闻名的华北某市农民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需要花钱到上游的县买水喝。而这种模式,还在无节制的推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不用直接回答了。
秸秆焚烧污染空气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记者:国家一直鼓励秸秆的综合利用,但烧秸秆的问题却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请介绍一下,我国秸秆的使用情况。
蒋高明:国家要求在2015年之前对秸秆要做到80%以上的综合利用率,这肯定达不到,我个人认为能达到50%就是理想状况。我的研究生曾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秸秆利用的文章,其中显示,我国秸秆中23%被牲口直接吃掉;4%用于工业原料;0.5%用于生产沼气。这三项加起来一共是27.5%。有约37%被直接烧掉,其他在收获、运输中、在农户家中自然损失。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被焚烧了。尽管政府严令禁止焚烧,但屡禁不止,而且有越演越烈的态势。焚烧秸秆不止污染当地空气,污染物还会随风排到其他地方的上空,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率已经刻不容缓。
农村除了上述问题,还有滥用添加剂、激素的问题,这也是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被滥用添加剂、激素的畜禽、水产对人们的健康只能做减法。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就会造成在农民本身受害的同时,城里人也难幸免于难:城里人再有钱,也难以买到健康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农民生产的各种食品,难以买到洁净的空气和健康,只好将钱投向医院和医药。生态文明只能也必须从农村抓起,没有生态农村,就没有生态省,也就不会有生态文明的中国。
应对能源危机的需要
“十二五”规划中说,到2015年末,要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准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副所长李俊峰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如何实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落实。有专家表示,41亿吨的控制目标没有考虑到农村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换言之,如果要实现41亿吨标准煤的控制目标,得先把农村的增量控制住。“一旦农村的能源需求爆发,将使国家本就紧张的能源供给形势雪上加霜。”蒋高明坦言。
农村用能:弃传统能源亲化石能源
记者:农村用能呈现哪些特征?
蒋高明: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商业化能源的普及,农民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生物质能源,即秸秆的利用,转而利用煤炭、液化气等化石能源或化石能源发出的电能。尽管我国在全国推广了很多农村小沼气工程,但由于“空心村”的出现,出料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加之,农民嫌麻烦,沼气废弃现象很多。这就造成优质的生物质能源被浪费,同时也加大了国家能源供应的难度。
记者:请把沼气废弃的原因再展开些。
蒋高明:必须肯定,在农村发展沼气,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下去。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废弃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能源转型原因,在推广沼气的时候采用政府免费修建,农户自己管理使用的方式也是原因之一。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让农户无偿使用,往往是开始的一段时间使用好,但之后由于漏气、出料等问题的出现,由于农户不愿投入、日常管理不到位导致最后废弃。在这点上,需要改变重建设、轻管理;建有钱、管没钱的现状,聘请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一定要普及和巩固并重,否则,建的越多,废弃的越多,造成资源的二次浪费。
发展沼气:工业、资本都要进入
记者:在您看来应如何发展沼气?
蒋高明:大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只有老弱病残留守的“空心村”的大量出现,客观上决定了农村在管理沼气技术上,劳动力严重缺乏。外出打工者很容易获得大大超出土地收入的报酬,他们不愿意伺候又脏又累、一年用不了多少的沼气。我觉得发展沼气,可以换个思路:走工业化道路。现在我们技术没问题,冬天出气也能保证。在山东已经建了很多汽车加气站加天然气。如果把沼气提纯就会变成天然气,可以作为清洁燃料,而且可以做到廉价,这样的话在汽车正在普及的农村肯定大有市场。瑞典、瑞士已经这么做了。还可以将沼气装罐保证农村生活用能。产业化之后,公司有利润,出料有保证,大量的有机肥料可以肥田,改善因过量使用化肥导致的土壤酸化、板结、生产力下降的现象。这样的话,农民就可以利用家门口的能源,远离煤炭、天然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对环境、空气的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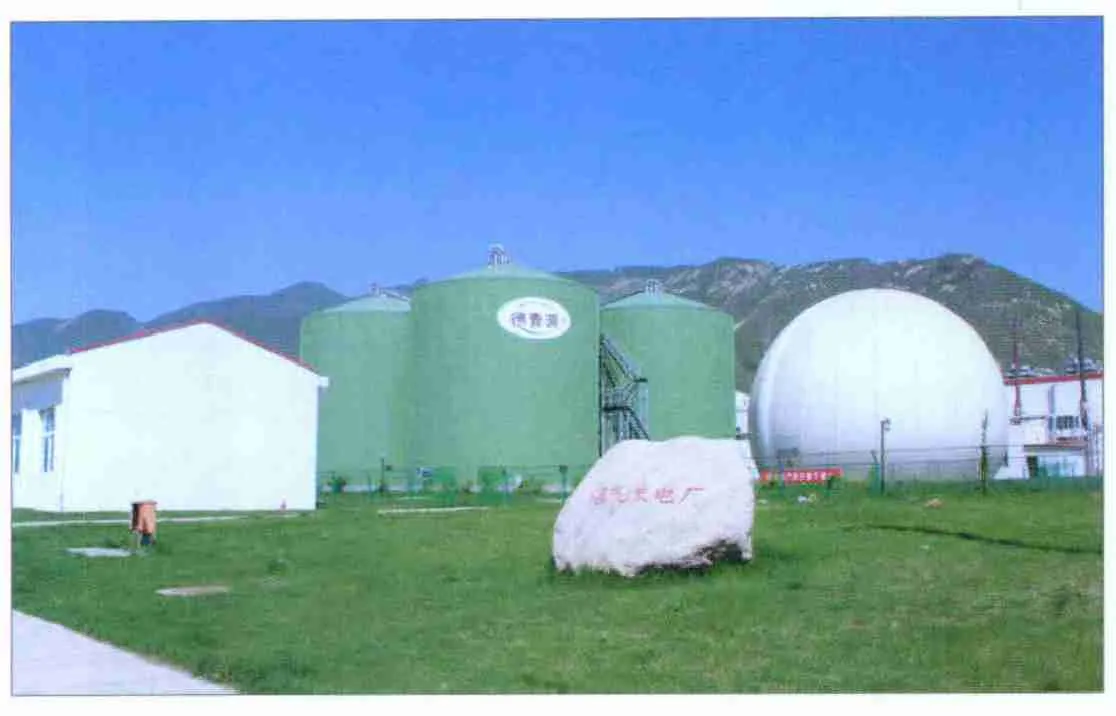
沼气发电厂
邯郸学步贻害无穷
一味模仿别人,非但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倒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谓之邯郸学步。中国的农业发展近些年来尤其崇拜美国的工业化农业发展模式。大农药、大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农膜、添加剂和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种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和农村资源资本化的现象被联合国专家批为邯郸学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盲目跟风,导致中国农业单位面积的化学化程度蹿升至世界第一,导致农业、农村成为中国面源污染最为严重的领域。
美国工业化农业真的那么“牛”吗?
记者:美国的工业领跑世界多年,在农业方面也是这样吗?
蒋高明:的确,有人说我们应该走美国那样的农业工业化路子,让2%的人口来种植98%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过美国式的现代文明生活。那样的话,我们将需要106.6亿亩耕地,可我们只有18亿亩耕地,且这些耕地还在受城市化的严重冲击。
记者:我们自然资源无法和美国比,那美国的生产效率是不是很高呢?
蒋高明:让我们来看基本的事实。美国用29亿亩耕地和数百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才生产出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差不多一半的土地(18亿亩耕地中的约15亿亩)和不到一半的补贴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效率,中国仍然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美国的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记者:我们的单位面积产出率最高,但人均产出率却低得多。我们可以获得像美国那样的个人产出率吗?
蒋高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我国像美国那样的平原性耕地大约6亿亩,只有人家的1/5左右。与此对应的是我国的农业人口是美国总人口的数倍。假如像美国一样一两个、两三个人经营1000亩地,那剩下的人去干什么?上世纪50年代,我们搞机械化,最后的结果怎样?60年代全国就挨饿了。有人会认为,那样的话可以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产生人口红利。的确,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创出了“中国制造”的牌子,但也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漂泊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和近6000万的留守儿童。如今在很多农村,经营土地的多半是老人、妇女,这些提供给人们最根本的生存物资的留守农民,收获的是低微的盈余和地位的降低。
记者:现在国家不是努力在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的尊严吗?
蒋高明: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承受几十年的剪刀差实现的。尽管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但农民收入依旧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悬殊。前两年的4万亿投入,又继续拉大了这种差距。在民间有这样的说法,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农民的辈份一降再降:建国初期是农民爷爷,改革开放前后降为农民伯伯,现在再降一辈,变成农民兄弟了。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戏谑味道,但农民地位的低微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直接相连的就是真正务农的农民采用各种手段保产量。因此农村难免不成为环境污染的重地。
记者:弘毅农场所在的蒋家庄是怎样的情况?
蒋高明:现在蒋家庄有三四百人伺候一千亩地。真的变成二三人的话,粮食品质肯定会降低,品种肯定会减少:五谷丰登的情况会难以见到。
记者:还有其他原因说明我国不适合美国的经营模式吗?
蒋高明:美国的经营模式适合高度的城市化完成率,在缺乏充足劳动力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在拥有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可以为之。美国98%的人口在城市,它必然也必须走集约化经营模式,这是适合美国国情的。而我国的城市化率充其量为51.2%,还有专家说可能高估了10%,就算是51.2%,我国仍有几亿人口在农村,如果强行走美国模式将有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隐患。我认为,起码在目前阶段,搞美国模式为时尚早。而且,美国的模式是可持续的吗?看看他们的做法吧:他们将污染的企业转移到了他国,农药化肥也都是在别的国家生产。土地、环境的污染总有超出承载力的时候;另外,有几个国家可以有美国那样的高投入?那样的霸权?总之,我不看好美国工业化的农业模式。
搞生态农业比生产牛仔裤强
城乡发展的极不平衡造成城乡收益相差悬殊,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经营土地的多为老人、妇女。为了省事、获得较高的眼前利益,依靠像美国一样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工业化农业经营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当然,这也离不开说话有分量的专家、官员的极力推介。在蒋高明看来,这是杀鸡取卵式农业模式,只顾眼前几十年而对之后的事不加考虑,“与污染的企业挣钱快、容易一样,污染的农业挣钱也快。”蒋高明认为,我国发展生态农业既符合国情又有竞争力。
生产牛仔裤赚得那点钱太不值
记者:我国发展生态农业与美国相比有哪些优势?
蒋高明:首先,我国有充足的懂得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劳动力,美国这方面恰恰是软肋,劳动力缺乏导致只能依靠工业化集约经营模式;其二,我国地理条件多样性,气候带也较欧美丰富,这就使农作物多样性成为可能。像美国,气候条件相对单一,作物田是大平原,想在多样性上做文章都难;其三,我国耕地多较零散,大型机器不能施展手脚,这看似是劣势,但也是极大的优势:这些耕地主要靠手工,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生态元素生产出高品质的作物,而这样的高品质是可以在高产的情况下实现的。弘毅农场的经验可以佐证。
记者:国外对中国的传统农业模式如何看?

生态型农业园区
蒋高明:中国古代先民自7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蚕和种植野生稻,并逐渐形成传统农业。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兼业化、立体循环的土地经营模式。100年前,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到中国调研小农村社制经济,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在切实有效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而美国的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破坏了资源环境,最终发明了一种更加不可持续的转基因技术,继续沿着工业化农业的错误路线走下去。100年前,美国的那位博士将这些所见、对比结果、感悟写在了《四千年的农夫》一书中。这本书在发达国家和在除了我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了近百年。这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农业自身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我个人觉得,改革、借鉴都是必要的,但不能不加辨别的照搬,不能剔除糟粕的同时也扔了自己的精华。
记者:如何让中国的农业体现竞争力?
蒋高明:要走生态农业的路子。工业化农业的模式把中国的优势损失殆尽。比如生产、加工牛仔裤。从原料棉花生产开始,就要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大化肥、大农药等等环境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转基因技术则使农药、除草剂的应用进一步升级走向恶性循环。这样生产出来的棉花不仅让环境遭受破坏,还隐藏着对健康的威胁。而这在纺织、印染阶段依然在继续。品牌的溢价是人家国外的。中国只得到了可怜的加工费——是在把环境污染一溜够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挣到多少钱?一亿条裤子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如果我们发展生态农业,生产高品质的食物、原料,则可以跳出污染环境只赚廉价加工费的怪圈。生态农业模式下,农民同样的劳动获得的回报高多了,对于生态环境并没有多大影响。
如何发展我国的生态农业?
记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生态农业?
蒋高明:从农村做起,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让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各项元素循环起来。应该在不适合集约化经营的地方且劳动力有保证的省的农村如云、贵、川、渝、湖、广、鲁一带的山区先发展起来,在不影响国家粮食供应格局的前提下,先争取10%的耕地(低产田)实现生态农业经营方式,最终低产田搞成高品质的中、高产田。
记者:生态、有机农业炒得很火,实际的情况怎样?
蒋高明:我国生态、有机农业走的是市场的路子。主要靠有机认证等市场手段。如果从认证的数量看,耕地量可能会超过1%,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真正按生态、有机要求去做的肯定达不到。发达国家有机食品的消费量高达20%到40%,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一步步来,先实现1%的目标,再实现10%的目标。中国有10%的耕地,全部的草原和全部的森林,保持在健康的状态,这些土地告别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就是保护了 62%的国土,带动了2亿多农民和农业大学生就业,而只要有1%的人群消费这些有机产品就实现了农业的增值。
记者:具体应采取哪些措施?
蒋高明:其一,政府得支持,同时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像有机认证,一年一次,每次费用一万多元;这还不说,认证就是填一大堆表格,这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易事。要认证就从源头认认真真认证,防止以有机之名行工业化农业之实。能不能认证免费?能不能在标准上不搞一刀切?希望政府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决策。其二,想办法让农民愿意从事生态农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得提高农民的收入。我粗略计算过,如果有机粮价达到3元/斤,就会有80%的青壮年回家务农。因为这样的话,按照一家5口人5亩地,其纯收入近三万元,而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去掉各种开支,也就剩下二三万。我曾经对山东、河南的农民做过调查,他们表示,如果能在家里挣二三万,肯定就不出去了。
记者:您希望将政府每年的2.5万亿农业补贴直接用在生态农业上。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希望?
蒋高明:每年国家的大量补贴都给了粮食生产的中间环节,到了农民手里很少,直接到农民手中也就是每亩八九十元。5亩地的话,也就四五百块,农民也不在乎这点钱。如果都直接补在生态农业上,直接高价收购粮,低价卖给城里人,那样的话粮价就在每斤3元以上了。那农民的积极性就上来了。
记者:这样做的阻力在哪里?
蒋高明:主要阻力在于中间环节太多,有利益冲突。如农药、化肥、农膜的生产商、供应商会反对;直补到农民头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管理部门也因得不到好处,而不愿积极推动。还有,以农业单项技术为研究对象或有利益冲突的农业科学家也会反对。
记者:您觉得我国生态农业的前景如何?
蒋高明:会很不容易,但环境、能源供给的压力、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压力使之成为大势所趋。它毕竟是朝阳产业。希望政府对生态农业实施政策倾斜,引导生态文明在农村、在农业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