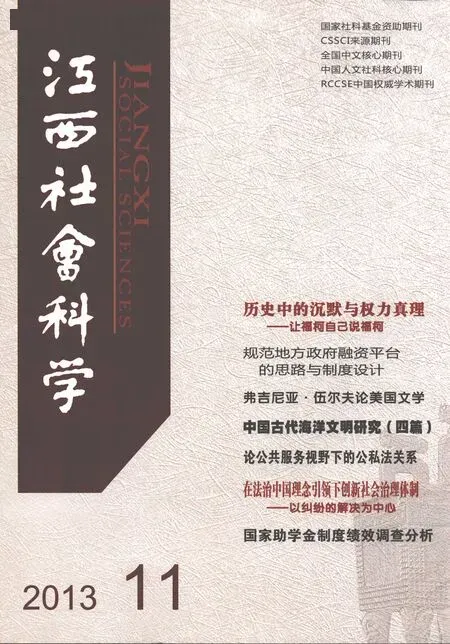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2013-02-19刘松来
杨 群 刘松来
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杨 群 刘松来
元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性张扬的时代,元代的艺术作品体现出与前代迥异的审美理念。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新儒学息息相关。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元代士人对以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接受和改造,发展和完善了“心境说”、“性情说”等审美范畴,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元代艺术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基本范型。
新儒学;艺术精神;散曲;文人画
杨 群,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刘松来,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22)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元代的艺术精神充满矛盾又极富灵性。以政治文化背景而论,蒙古贵族入统中原、游牧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彼此冲突,作为当时艺术创作主体的士人集团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生存状态极其压抑。以艺术创作而言,元代又是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元杂剧横空出世、感天动地,散曲清新动人、畅达明快,文人画更是名家辈出、盛况空前。以下试从元代士人的思想背景入手,探析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轨迹。
一、元代艺术审美理念的突破与创新
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代表,元代艺术在继承、总结前人美学成果的基础上展现了鲜明的创新精神。画论家汤麟指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思想桎梏在艺术上有两次大反抗。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对文学功能的再认识,一次就是元代以文人画成熟为标志的审美观念的突破。”[1](P9)这一突破既以文人画为标志,也同样体现在以散曲、杂剧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上。与前代尤其是宋代相比,元代审美理念的创新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求天趣、尚自然的审美追求
两宋是程朱理学从发端到昌盛的时期,其在美学观念上的直接反映就是宋人热衷理趣,化盛唐的热情为含蓄,乃至喜好“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一风气到了元代却彻底为之一变:绘画方面,文人画家们以逸品为高,热衷表现自然山水,寥寥数笔、不事雕琢而气韵全出;文学创作方面则呈现为题材贴近生活、语言清新明快,以自然质朴为美,以明朗酣畅为趣。
以文人画“元四家”之一的倪瓒为例,他的创作多取材于江南小景,尺幅之上往往只有一抹平湖远山、三两疏林枯树。其代表作《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秋亭嘉树图》等,虽然将自然物象简练到极致,没有任何人为的夸饰,却传达出地老天荒般的荒寒、寂寞,彰显着隽永、简逸的美。就像陈传席评价《秋亭嘉树图》时所指出的:“整个画面简淡萧疏幽逸,如洞庭月色万籁无声,毫无热闹尘俗之风。反映了一个人思想的纯净清雅、无欲无为、淡泊自守的情怀。 ”[2](P297-298)
又如以下两首散曲作品。马致远 《双调·寿阳曲·潇湘八景》写渔家生活:“鸣榔罢,闪暮光。绿杨堤数声渔唱。挂柴门几家闲晒网,都撮在捕鱼网上。”[3](P150)冯子振《正宫·鹦鹉曲·野渡新晴》写雨后春游:“孤村三两人家住,终日对野叟田父。说今朝绿水平桥,昨日溪南新雨。”[3](P183)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白描手法实写日常情状,不论生活琐事还是周遭景物无不流露出天然之美,令人如临其境。这种清风扑面般的艺术风格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王国维赞为:“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4](P101)
从本质上说,求天趣、尚自然的审美追求彰显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力,体现的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元代美学所倡导的清气、逸格相关审美范畴,都是由此衍生而出。
(二)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
对于自然美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元代艺术家只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摹写。相反,在元代艺术作品中,观者往往能感觉到浓郁的情感意绪,这正是元代审美理念的又一重要突破。以山水画而论,经过元代画家精神世界的改造,自然山水仿佛拥有自身的生命,每每令观者为之感染,久久不能释怀。诚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所言:“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5](P730)美国学者高居翰就此对于宋、元两代山水画审美理念的流变做了非常精当的比较分析:“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成为体现宇宙宏观的主题。山水画大师们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特有地形,经营出各成一家的表现形式。……元代,地域派别式微,绘画上追求主观情感的表达,发展出本质上已抽象且理想化的山水类型,画家们刻意或无意识的选择以形写心中山水,来取代对客观山水的描写。”[6](P191)
在元代文学作品中,这种主观情感色彩则突出表现为情与景的交融。试看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主人公长亭作别之后的桥段:“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3](P592)以常理而论,青山不可能“送行”,疏林无所谓“做美”。但是,作者有意将人物情感渗透进场景描写之中,乃至于何处是情、何处是景已经无法分开了。又如张养浩的 《双调·折桂令·中秋》:“一轮飞镜谁磨?照彻乾坤,印透山河。玉露泠泠,洗秋空银汉无波,比常夜清光更多,尽无碍桂影婆婆娑。老子高歌,为问嫦娥,良夜恹恹,不醉如何? ”[7](P180)虽然吟咏的是唐宋诗歌中很常见的中秋主题,但是诗人跳上前台与嫦娥对话,纯是元人口吻,从而以强烈的主观色彩赋予古老的题材以全新的审美意义。
(三)审美旨归在于自娱而非教化
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儒家美学传统中的诗教理念在元代开始动摇,以自娱为初衷的个性化表达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审美的新趋势。如元代中后期的文人领袖杨维桢将元代盛行的散曲称为今乐府,意在有别于前代以温柔敦厚为旨归的传统诗歌,并认为,“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8](第41册,P308)。 王国维分析其原因认为:“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4](P101)绘画领域同样如此,文人取代画工成为绘画艺术的创作主体,他们不再承担宋代院体画服务于宫廷的任务,以笔墨游戏为特征的自娱精神贯穿于创作的始终。正如倪瓒在《答张仲藻书》中所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5](P706)
自娱精神意味着元代艺术家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在这种精神主导下,艺术无须迎合官方的教化需要,而是成为艺术家抒发性灵的渠道,这正是元代艺术重要的活力之源。柳贯在《自题钟陵稿后》说出了元代士人的普遍心声:“余之诗,出诸余心,宣诸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 ……以足吾之所好而已。 ”[8](第25册,P180)
二、新儒学与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
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总是离不开主导这一时代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文化背景,元代艺术审美理念的突破当然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由于外族入统中原,传统思想文化和社会格局受到强烈冲击,相对之前的时代,元代艺术的主要创作主体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面貌较为复杂,呈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向,即倪瓒总结的“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8](第46册,P551)。 不过,正如“据于儒”中“据”所揭示的,儒学仍为元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根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代士人所接受的儒学是经过两宋学者重新诠释的 “新儒学”,主要包括程朱理学和象山心学两大学派。新儒学与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之间的紧密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观照:
(一)元代艺术家对新儒学美学观念的接受
从哲学发展史看,理学虽然始于宋代,但是它的广泛传播和成为官学并逐步确立其在全国学术思想中的统治地位是在元代。一方面,蒙古贵族为了巩固其统治,有利用儒家思想的一面。孔子被元代统治者奉为至圣先师,朱熹被尊为圣人,科举考试仍然在“四书”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更是从来没有丢掉儒家传统。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宋代程朱理学与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在元代的进一步发展。而陆象山的心学则在元代中后期开始广为文人士大夫接受,新儒学的发展出现和合朱陆的趋势。
以程朱理学与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吸收了老庄哲学和禅宗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结合了儒、释、道思想的安身立命之学。元代士人凭此进之可荣登朝堂,退之可明哲保身,纾解内心苦闷压抑,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所以,新儒学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对于处于外族统治下的元代士人来说,尤其具有特殊意义。赵孟、朱德润、范德机等艺术名家均崇尚新儒学,他们自己研读新儒学经典,并与虞集、袁桷等学术名家相互切磋交流。与此同时,虞集、袁桷等人本身也是书画家和文学家,他们对于新儒学的研究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美学观念,并自觉应用于艺术创作之中。就连倪瓒等寄情山水、不问世事的隐逸画家也有着深厚的新儒学学术背景①,元代中后期的文坛领袖杨维桢更是明确自称“吾心学者也”[8](第41册,P366)。 当然,元代艺术家对于新儒学美学的接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结合创作实践进行了诸多大胆的创新。正是在对新儒学美学的接受和改造中,元代艺术精神体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二)儒家隐逸文化与元代艺术的审美风尚
由于元代统治者阻绝了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的进仕之路,普通士人经世报国的理想无法实现,只能退而修身。隐逸于野取代出仕于朝,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风尚。需要指出的是,元代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思想并不等同于老庄之学的避世思想,而是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韦宾指出:“隐逸文化背后的哲学可分为两种境界,曰孔颜之乐的境界,曰庄子哲学的境界。孔颜之乐的本质在于,士之如何处其身的问题。实际上是‘士’如何在逆境中自处其身,自守其节,如何于中求道、味道的问题。 这是一种高境界的隐逸哲学。 ”[9](P144)
宋代理学家十分重视“孔颜之乐”的追求,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氏兄弟曾回忆导师周敦颐的教诲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10](P27)能否体验到孔颜之乐,成为衡量理学家修养功夫的一个重要标尺。在元代特定的历史人文条件下,新儒学对于“孔颜之乐”的推崇又直接推动了士人隐逸之风的传播。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们在隐逸生活中,为了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纾解内心的苦闷压抑,往往遁迹到艺术创作之中以寻求心灵的平衡,在残酷的现实中发展出艺术化的人生态度。
试看张养浩的散曲《中吕·普天乐》:“楚《离骚》,谁能解?就中之意,日月明白。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11](P548)拒绝无谓的入世“胡来”,寻求自然的“无涯”快乐,正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暂时抛开尘世烦恼的隐逸生活中,他们得到了新的审美体验和心灵纾解。
与元代的文学家们一样,元代的文人画家们不仅主动寻求隐逸江湖的生活方式,而且将这种生活方式作为了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山水画在元代文人画中的突出地位正是他们对于自己隐逸生活的真实写照,与之相关的一些题材也被文人画家赋予了隐逸文化的象征意义而受到画家们的青睐。例如,几乎所有的元代文人画家都曾经创作过“渔父”主题的作品。吴镇在《渔父图》卷轴中题诗说“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12](P259),这正是那一时代文人画家们的心理写照。同时,除了“渔隐”之外,带有隐逸文化符号性质的“松竹梅兰”也成为元代艺术家热衷的表现对象,“四君子画”由此盛极一时,并对明清花鸟画发展影响深远。
(三)程朱理学“性情说”在元代的美学转化
“性情说”原本出自先秦儒家思想,《诗大序》第一次在诗学领域提出“吟咏情性”的说法。就《诗大序》看,“情性”主要不是指诗人个体的感情而是社会的情志,“吟咏情性”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和政治干预意识。到了宋代,程朱理学非常重视有关“情”、“性”的讨论,并赋予其严格的伦理学意义。程颐说:“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散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10](P368)朱熹在《答徐景光》一文中进一步阐发道:“心之所得于天之理则谓之性(仁、义、礼、智是也),性之所感于物而动则谓之情(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是也)。 ”[13](第24册,P3991)总的来说,程朱理学所谓“吟咏性情”乃是将圣人的德性、气度、胸襟、情怀通过诗歌,表现为一种气象。
而元代士人普遍好以性情论诗,但是他们所说的“性情”已经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概念。如元初诗人刘将孙提出:“诗本出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后之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恶远而变化非矣。”[8](第20册,P151)这里的“情性”实际上与程朱理学所指的德性、修养无涉,而是直指文艺创作中的个人性情。元末杨维祯更进一步在《李仲虞诗集序》中提出:“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8](第41册,P240)元代士人通过“性情说”倡导个性化的创作,反对盲目崇拜古人。
(四)心学美学与元代艺术生命意识的传达
除了程朱理学,陆象山创立的心学是受到元代文人士大夫推崇的另一新儒学思想。陆象山的心学讲究发明本心、从顿悟中领会天地之理。虽然象山心学在宋代受到程朱理学信奉者的排斥,但是进入元代之后,陆象山的本心思想为元代士人修养心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因而被广泛吸纳,从而形成了和合朱陆的趋势。心学思想在美学上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吴功正指出:“宋、元时代理学盛行,理学进而发展为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精微深细的说明和体认,使得人的体认基点和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审美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14](P510)
早在元初,思想家郝经就对传统的审美体认论进行了重新解构,提出“内游”的概念。郝经强调主体的自主功能,以此达到“因吾之心,见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游,见天地鬼神之游”[8](第4册,P463)的效果。 郝经之后的诗人、学者方回则进一步阐发了郝经的心学美学思想,他的《心境记》对心与境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从陶渊明的 “心远地自偏”开始探讨,分析了“顾我之境与人同,而我之所以为境,则存乎方寸之间,与人有不同焉者耳”的审美现象,并得出“心即境也”的结论。“心境”说的提出实际上将“心”作为审美的出发点和核心点,进一步强调了审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
在元代的新儒学美学思想体系背景下,艺术家们往往将自己的主观精神注入客观世界,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创造出李泽厚所说的“标准的‘有我之境’”[15](P263)。元代文人画家对于笔下自然风物的主观改造与文学家对于心境的营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们的笔下,一山一木、一水一石都仿佛具有了活生生的生命。不论是倪瓒的荒寒、黄公望的清隽、吴镇的苍茫、王蒙的圆润,这种种意境都不是西方风景画家那样对大自然的忠实再现,而是他们用心所看到的世界。
自称“心学者”的杨维桢在《无声诗序》中对元代艺术的这种心学倾向有着非常精辟的概括:“诗者心声,画者心画。 ”[8](第41册,P314)元代艺术家们以心赋诗、以心作画,从心灵出发感知世间万物,然后又回归心灵,诉之以艺术的表达,强烈的生命意识由此成为元代艺术精神的典型特征。
三、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价值拓展
如前所述,新儒学是元代艺术家们的主要思想根基,它为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艺术家们从新儒学及其美学思想出发,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对原有的艺术门类进行了大胆创新,实现了元代艺术精神的重大拓展。
(一)抒性情而任自然、不拘一格的艺术表现手法
相对而言,在唐宋文学家最擅长的诗、文领域,元代艺术并没有突出的成就,而元人所独擅的散曲和杂剧创作则充分拓展了元代艺术精神的价值。在“性情说”、“心境说”等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元代的散曲和杂剧作家们摆脱了前代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以率真的表达方式、百无禁忌的语言风格展现离愁别绪、市井百态,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历史人物都可以成为他们表现的对象,表现的手法和角度更是别具个性。
如兰楚芳《南吕·四块玉·风情》写道:“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3](P497)这段独特的爱情独白就是放在今天也是饶有新意,兴味盎然的。这一时代,艺术家们不再将“含蓄蕴藉”奉为至尊宝典,不再回避一些前人的禁区,而是敢于彰显个人情怀和时代精神。在他们的笔下,贵如天子也不过是一介无赖,“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3](P253)。甚至于对天地至尊也不惮质问:“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3](P519)
透过这些富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元代文学家们摈弃了前人的矫揉造作,热忱地讴歌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同时敢于冒犯神圣、嘲弄自我。品读元代的艺术作品,不难发现:其实不管是俗也好、丑也好,并非是对原有审美标准的颠覆;相反,它是对审美领域的一种大胆开拓,从而在全新的事物中发现更多样性的美。
(二)打通艺术门径,确立诗、书、画一律的审美传统
元代出现了大量的题画诗,文人画成为诗、书、画三位一体的艺术精品,这也成为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从表面上看,它是不同艺术形式间的融合,但从更深层次看,它标志着元代艺术精神已经拓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即在艺术的本质层面上确立了中国古典艺术诗、书、画一律的思想。
元代的艺术共通性思想首先体现在书法与绘画两门艺术的创作上。赵孟指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应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5](P1069)杨维桢更直接提出:“士大夫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8](第41册,P315)书画一律的艺术观念直接导致了元代文人画家对笔墨的突出强调,将中国古代“线”的艺术推向了最高阶段。
元代艺术家有关艺术门类相通之处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笔墨技法的实践层面。元初学者王恽在《玉堂嘉话序》中指出,书、画之所以能互通,根本原因在于创作主体的“自得”性:“书与画同一关纽。昔人谓学书者苟非自得,虽夺真妙墨,终为奴书。余于画亦然。”[8](第6册,P220)所谓“自得”,即体味出艺术的真谛所在,且这种真谛并不拘泥于具体的艺术门类。循着这一思路,元代艺术家进一步将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并举,黄筆的《唐子华诗集序》总结道:“人知诗之非色,画之非声,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诗中之画焉,有画中之诗焉,声色不能拘也。……盖其诗即画,画即诗,同一自得之妙也。”[8](第29册,P103)
正是基于诗、书、画同属于“自得之妙”的体认,元人明确提出了“写意”理论。汤蠷《古今画鉴》认为:“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画者当以意写之,初不在形似耳。 ”[5](P1071)这里的“写”既可理解为书法的写字之写,亦可理解为赋诗的写作之写。“写”与“画”一字之差,已足以显示元人对艺术精神的理解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始终与元代士人对新儒学的接受和改造息息相关。从中国古代美学发展来看,元代在中国古典文人艺术范型的确立过程中处于关键的时间节点。元代的艺术家们以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创新了新儒学美学,在艺术题材、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地突破创新,向前承接了唐宋艺术的优良传统,向后则开启了明清的浪漫主义洪流。通过元代士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以抒情文学与文人画为典型代表的元代艺术集中诠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与精髓,其作品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美学境界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欣赏,成为中国艺术的典型代表。
注释:
①倪瓒在《秋水轩诗序》中明确表达了对程朱理学的崇奉:“子朱子谓:‘陶韦冲淡之旨得吟咏性情之正,足为学之助矣。’”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13页。
[1]汤麟.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元代卷)[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2]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3]贺新辉,李德身.元曲精品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5]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6](美)高居翰.气势撼人[M].李佩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7]薛祥生,孔繁信.张养浩诗文选[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
[8]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9]韦宾.宋元画学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1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蒋星煜,齐森华,叶长海.元曲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12]薛永年,邵彦.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3](宋)朱熹.朱子全书[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吴功正.宋代美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15]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彭民权】
I206.2
A
1004-518X(2013)11-0084-05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