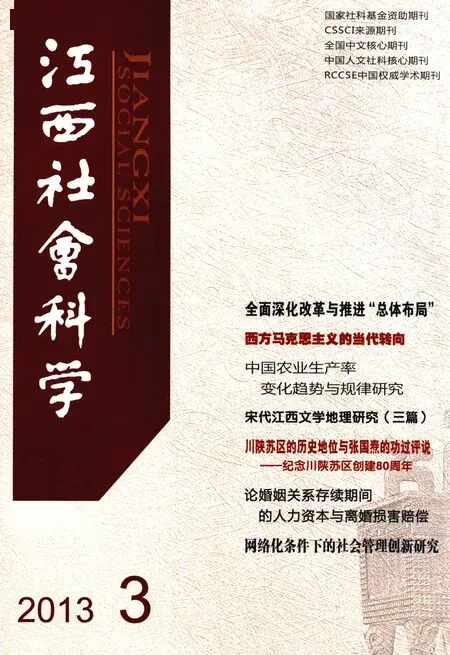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解构与重塑
2013-02-18■吴琦
■吴 琦
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确立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弥补了该领域的法律空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此项制度的设计缺陷与不足逐步地暴露,理论界和司法界开始反思这一制度。因此,从根本上探寻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价值,积极重塑法律制度设计,将有助于此项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司法高效,促进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一、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家务劳动价值论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务劳动是人类维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且必要的手段。虽然家务劳动随着家庭出现就已经产生,但是有关家务劳动价值的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有关全职妇女家务劳动价值的研究。
(一)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
一直以来,家务劳动被看做是一种对家庭应担的责任和应有的奉献,被认为是无偿的劳动。“家务劳动通常被理解为为了维持家庭而进行的没有报酬、没有交换价值的无偿劳动,它既不是流动的货币,也不是固定资产,更不能生产出特定的商品,而是被限定在某种特定的关系(如血缘、婚姻)下的活动。”[1]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创立劳动创造价值理论,马克思是第一次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依此为基础建立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从实体上解决了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价值的问题。另外,恩格斯认为,生产本身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类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具体说来,前类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后类指劳动力的生产。人类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女性的生育活动,二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恩格斯所指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则是指:“人们每天都能回到工作中,并使工作能够代代相传的过程。狭义地讲,即以物质和服务的消费支撑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广义地讲,还包括许多看似与经济、生产无关的过程,如家务劳动。”[1](P103)所以,日常的家务劳动琐事,包括扫地、烧饭、买菜等,本质上也是社会生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应当作为经济基础结构的一部分。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的,是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家务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劳动是能够创造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务劳动的社会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功能就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一经济形式下,社会生产在广泛而细致的社会分工体系中进行,而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就有专门为一些家庭提供家务劳动的第三产业的家庭保姆、钟点工一族。这种劳动的社会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2]由此可见,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体制下,家务劳动因此而具备了社会劳动属性,并且是可参照同类社会劳动来计算价值的。
(二)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意义
长期以来,因受制于西方“公与私”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家务劳动对家庭的贡献和隐含的社会价值被蒙蔽,造成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地位不高。在西方的哲学理论体系中,他们认为,公与私是可以截然分开、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公领域指公共事务领域,而私领域仅指私人事务领域。“当公领域和男人、理性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女人、感性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3]男性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创造的劳动价值被社会承认,且可通过赋予相应报酬来评价,而女性在私人事务领域中的家务劳动则被认为是当然之义务或家庭责任,无视其价值含义,且不被赋予报酬。男女两性在公与私两个领域里的劳动价值的巨大差异加剧了两性的不平等。因此,有学者认为对家务贡献予以补偿,有利于男女性别平等和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转变传统的性别认知与社会分工模式。
在我国,受制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思维定式影响,家务劳动的大部分是由妇女完成,虽然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对社会发展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家务劳动者的贡献往往被家务劳动的无报酬性所掩盖,而社会对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也存在一定的歧视。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确实有助于正确地评价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另外,男女双方在家务分配上的合理与否会直接影响夫妻的感情,以及对婚姻的满意程度。法律制度对家务劳动价值给予确认可以有效地协调和保护家庭分工,同时成为夫妻关系稳定和家庭和谐的重要保证。[4]
综上所述,家务劳动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应该被确认为有偿劳动,法律对此给予保护,对提高妇女地位,保证协调的家庭分工,促进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重要意义。
二、对我国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现实解构
家务贡献补偿制度,一般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对方予以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我国《婚姻法》第40条明确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法律规定,是我国在婚姻家庭法中首次加入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体现,这无疑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
我国设立家务贡献补偿制度之初,目的在于在离婚当事人适用分别财产制情况下,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离婚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从而保证其社会地位,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概括来说,此条法律的适用隐含以下六个的条件:第一,适用前提限定于采用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家庭;第二,只能在离婚时才能提出请求;第三,平等适用于男女双方;第四,行使请求权的主体是对家务贡献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第五,家务贡献的内容具体包括照料老人、抚育子女、协助配偶另一方工作等;第六,补偿的形式为财产或物质补偿。
然而,十余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项制度虽在婚姻家庭立法建设上弥补了空白,但因没有充分的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观念,存在设计上的不足与缺陷,导致立法目的无法真正实现。
(一)法律适用的前提过于狭窄
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普遍与夫妻财产制相结合。适用前提只限定在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一般外国立法例为避免复杂的算定手续,都将妻之家事劳动与夫之职业劳动同等评价,而使家事劳动之评价与夫妻财产制相结合。”[5]我国夫妻财产制度采取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两种形式。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一方离婚当事人行使补偿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也就是财产归各自所有。在司法实践中,离婚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没有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实行法定的共同财产制,那么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则丧失补偿请求权。再假如夫妻双方约定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共同所有,部分归各自所有,那么依据此前提条件,仍然不能请求经济补偿权的法律适用。[6]
按照发生根据标准,我国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现实生活中,由于受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影响,我国绝大部分的家庭并未选择约定分别财产制。全国妇联曾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过“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众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42.6%,持反对意见的占57.4%。[7]而这仅是一个观念的调查,回到现实的生活中,选择约定比较明晰的财产归属的做法更显得有悖常理。笔者对江西省南昌市的 1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发现,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仅有1%,而这个家庭也仅仅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在司法实践中,提起家务贡献补偿的案件少之又少,即使有个别当事人有此意愿,可是终因没有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而不能进行法律适用。综合来看,家务贡献补偿作为离婚救济的手段之一,因其适用的前提过窄,并没有产生应有的立法之意。
(二)法律适用范围过于片面
我国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只适用于婚姻关系解除时。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无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有学者调查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7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家务劳动应主要由女性承担,男性持该观点的这一比例更高,高出女性近10个百分点。而从实际的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来看,多数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在1~2小时之间,而多数男性的家务劳动的时间少于1小时。女性每天家务劳动超过2小时的人数占被调查女性总数的30%左右,而相应的男性只占总数的20%。”[1](P106)由此可见,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数家庭中的女方把人生中大好年华、精力和体力和情感奉献给家庭。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必然影响她们的知识更新、工作晋升、事业发展等,从而失去市场竞争力,甚至是身体健康。而对方却因此可以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和提升的机会。如果婚姻关系破裂,由于受到适用前提和适用范围的制约,家务贡献补偿无法落到实处。尤其是对家庭主妇而言,“唯于主妇婚姻之场合,即夫于外从事职业活动,以其收入维持家计,而妻于家庭内操持家务时,采取分别财产制未必即能保护家庭主妇之利益。因为以夫妻分别财产为原则时,夫对于职业收入保有所有权,而未从事职业活动之妻,则一无所有。妻于婚姻关系存续中,须依存于夫之经济能力,若一旦婚姻发生破绽,则将身无分文被逐出家门”。[5](P155)如能扩大适用范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可请求家务贡献补偿,或许可弥补此制度不足。
(三)计量方法不明确
家务劳动虽然获得了与社会劳动同样的价值评价,但家务劳动的具体价值确难以估算,在我国的立法例中没有相关具体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有人提出家务贡献补偿请求,法官也难以适用法律。我国有经济学家做过测算,如果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曾提出:“妇女非市场劳动的被承认并赋予相应的价值,是一个比社会公正问题更加复杂的事,它关系到妇女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假如更多的人类活动被看做是以工资形式的市场交易,并由此获取庞大的货币价值,粗略估计数字可达16万亿元……上述估计包括了妇女和男人所做的无偿劳动以及妇女在市场形式下所赋予的不平等低价。在所说的16万亿美元中,其中11万亿美元是妇女以非货币形式、看不见的贡献。”[1](P102)另外,在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同时,有学者认为:“家务劳动不仅有劳动的强度和质量为表征,而且有亲属的情感和精神的投入。家务劳动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报酬来计算,家务贡献补偿也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来对待。”[7]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重塑
家务劳动能够获得和社会劳动同等的价值评价,是社会文明和法治进步的极大体现。为达到立法者的立法应有之意,我国的家务贡献补偿制度或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重塑。
(一)家务贡献补偿应扩大适用前提于夫妻共同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将家务贡献补偿制度限定适用于夫妻分别财产制。适用分别财产制的离婚当事人一方应从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出发,对作出贡献或贡献较大的另一方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似乎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要实现家务贡献的补偿比较困难,救济无门。有些国家的家务贡献补偿,则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为适用前提。比如,1969年前《苏俄婚姻家庭法典》第20条规定:家事劳动视为相当于生产劳动,从而,夫妻对家中之财产有所有、收益、处分之平等权利。1995年《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34条规定:“在婚姻期间从事家务、照管子女或者由于其他正当原因而没有独立收入的夫妻一方也享有夫妻财产共有权。”1986年《越南婚姻家庭法》第42条规定:“因与家庭各成员共同生活以致无法确定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根据受分割方对于维护和发展家庭共同财产所作的贡献,以及对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贡献,从家庭的共同财产中分割出夫或妻的财产份额。家务劳动视同生产劳动。”[8](P83)
(二)家务贡献补偿应适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国外立法例已有相似规定,比如《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一)料理家务、照顾子女或协助对方从事其职业或行业的夫妻一方,享有定期从对方获得合理数额的由其自由支配的财产的权利。(二)在确定个人自由支配的财产的数量时,必须考虑有权获得该项权利的夫妻一方的个人收入及其为家庭、事业及行业的未来作适当准备的责任。”[7]除上述规定外,《瑞士民法典》第165条还对夫妻一方的特别贡献予以补偿,即“夫妻一方为夫妻他方所从事的事业或行业所作的贡献已大大超过其维持家庭应尽的义务时,该方有权获得合理补偿”。“但如果夫妻一方所作的特别贡献,是基于雇佣合同、贷款合同及任何典型的合伙协议或其他合法职业关系,则该方不能请求补偿。”[9](P296)从各国的补偿机制来看,他们把家务贡献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而赋予作出贡献的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能获得定期的、合理数额的财产权利,这样做有利于夫妻双方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合理分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有助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
(三)明确简单易行的计量方法
20世纪后期,国际上有关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的计量方面提出过几种解决方法。一是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从事家庭外的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二是将家务劳动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三是将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都列出,然后在市场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运用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
在我国,有学者从补偿性工资角度对单个家庭的家务劳动应付报酬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计量方法,从这种动态的方法出发,也有人结合统计知识原理,提出了产出法、投入法、机会成本法、行业替代费用法、综合替代费用法、补偿性工资法等计量方法。然而这些方法若引入司法实践,或不具有现实性与可操作性而难以运用。
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具体补偿的方法,可参考夫妻双方的收入差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以及相应贡献等因素。简单的补偿方法应为:家务贡献补偿=(夫妻双方的年收入差÷2)×婚姻关系存续年限。[8](P84)笔者认为此计算方法也不完全具有现实操作性。在此计算公式中,夫妻双方的年收入是个变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每年的收入差就可能不一样,那依据此公式是无法算出家务贡献补偿价值的。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较详细的论述了家务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家务劳动应该和社会劳动一样被平等评价,据此,家务贡献补偿可以采用家政服务小时工的工资来计算,并依据每年的家政服务的工资标准来计算,然后计算总和。这样的计算方法,简单易行,也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家务贡献的价值,体现法律的权利义务统一原则,维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我国的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已建立十余年,但终因我国传统观念、文化价值以及本身的计量困难,而导致此制度束之高阁,没有实现其立法初衷,此制度的重构还有待于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逐步完善。
[1]黄春晓.城市女性社会空间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2]李永新.浅谈家务劳动创造价值的功能[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7).
[3]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王歌雅.离婚救济制度:实践与反思[J].法学论坛,2011,(2).
[5]林秀雄.夫妻财产制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薛宁兰,许莉.我国夫妻财产制理发若干问题探讨[J].法学论坛,2011,(2).
[7]商越.聚焦新《婚姻法》:婚前财产公证引爆观念之战 [EB/OL].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 -08 - 09/115657.htm1.
[8]王歌雅.家务贡献补偿:适用冲突与制度反思[J].求是学刊,2011,(9).
[9]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