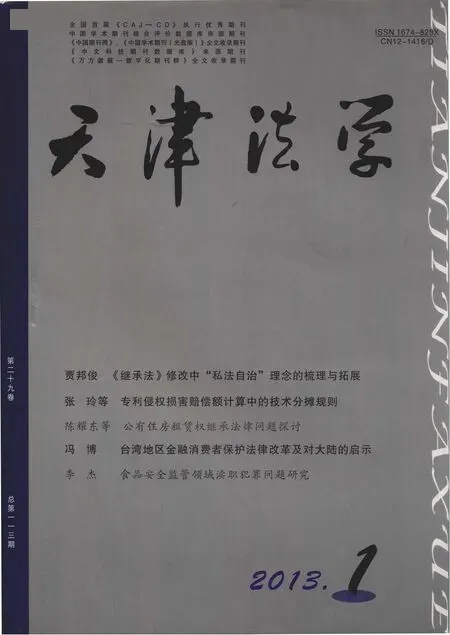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的技术分摊规则
2013-02-15张玲,张楠
张 玲,张 楠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1)
技术分摊规则是指按照专利因素对产品利润的贡献比率来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具体而言,就是在专利权人实施专利技术的产品的所失利润总额或侵权人的侵权产品获利总额中,扣除不是由专利因素贡献的利润。我国专利法中没有规定技术分摊规则,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释[2009]21号中给予了确认(第十六条),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适用的案例。但不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司法实践经验,均处于初期的粗放阶段,亟待深入研究。
一、技术分摊规则的必要性
(一)技术分摊规则与全部市场价值规则之争
在发生专利侵权后,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是专利法领域的世界难题。究竟应该以全部市场价值规则,还是以技术分摊规则为基础确定赔偿额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全部市场价值规则是以涉案专利产品的全部市场价值计算赔偿额,技术分摊规则是以涉案专利在整个产品中的贡献率计算赔偿额。
美国最高法院在1884年Garretson案中阐明了技术分摊规则。19世纪后期,美国法院对技术分摊问题给予了极大重视。据统计,自1853年到1915年间,最高法院在至少35起专利赔偿的判决中提及分摊问题。但是,技术分摊始终是困扰当事人和法院的一个难题。1922年美国专利法修改增加了合理许可费计算方式。由此,原告在无法完成技术分摊的举证责任时,法院可以按照合理许可费进行判决。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院对技术分摊规则产生了怀疑。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技术分摊的不可能性命题,主张一项专利技术特征对整个产品的贡献比例是难以量化的,即使量化了也未必符合市场的评价。1946年美国专利法修改取消了侵权人非法获利计算方式。美国众议院专利委员会对此的解释:一是侵权人所获利益在多大比例上是由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往往难以准确地认定;二是侵权人非法获利赔偿往往造成诉讼上的附带支出和迟延。因此,技术分摊难题是美国取消侵权人获利计算方法的主要原因[1]。20世纪后半期,美国法院逐渐抛弃了以技术特征决定因果关系的做法,代之以市场价值决定因果关系。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阿罗案中提出了“若非”标准:假设侵权人没有侵权,专利权人会获利多少?之后,许多法院认为已经不再需要技术分摊规则。由此,全部市场价值规则取而代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广泛适用[2]。美国法院采用全部市场价值规则,判决支持原告高额的赔偿金,对于威慑侵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不断刷新的天价赔偿额,也逐渐受到业界、学者的质疑。在朗讯诉微软案[3]中,加利福尼亚联邦地区法院一审适用全部市场价值规则裁定了赔偿金。微软提出上诉,Apple、Yahoo等十二家公司联名支持微软,认为:陪审团以Outlook软件的总成本,而不是Date—Picker专利功能的成本为基点计算赔偿额是极其不妥的。要求法院禁止陪审团以产品的总成本作为计算损害赔偿金的基础。而应以侵权诉讼涉及到的专利技术的功能价值作为判定损害赔偿金的唯一依据。针对微软及其盟友的诉求,3M、Exxon Mobil等十三家公司表明支持朗讯[4]。
我国专利法只是规定了专利侵权赔偿的计算方式,没有具体涉及技术分摊规则或全部市场价值规则。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1号),对专利侵权赔偿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定。其中第20条第2款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第3款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据此,全部市场价值规则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法院依据全部市场价值规则裁决了一些纠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等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一审法院将施耐德公司销售全部产品的平均营业利润率认定为侵权产品的营业利润率,然后乘以侵权产品的销售额,得出侵权产品的营业利润为3.559亿元。该数额大于原告的请求额3.348亿元,因此,一审判决施耐德公司赔偿3.348亿元。二审双方达成协议:施耐德公司支付补偿金1.575亿元。①该案创造了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最高补偿额,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并入选浙江法院2009年知识产权诉讼十大案例以及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但是,该案的过度赔偿也成为全部市场价值规则的转折点。
(二)技术分摊规则的合理性
在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推动下,现代技术孕育的产品已不再是对单一专利实施的成果,绝大多数产品集合了若干专利技术或现有技术。特别是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一个产品可能会包含成百上千的专利,形成了“专利丛林”。当这种涵盖“专利丛林”的产品发生侵权时,如果被告仅侵犯了众多技术特征中的某一项或几项专利技术,那么在大多数情形下,原告获得由众多技术特征共同决定的整个产品的利润就显失公平。将非由系争专利技术产生的收益排除在损害赔偿之外,方符合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因为,专利的价值体现在实施了该专利的产品因此而增长的利润上,当侵权发生时,权利人受到的损失正是由其专利技术带来的增利[5]。因此,专利侵权赔偿的应是权利人因侵权而丧失的或侵权人因侵权而获得的增利。
从产品的利润构成角度分析,对于被侵权产品来说,其市场价值一般归因于两部分技术特征,一为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另一部分则是非涉案专利技术特征。对于前者,由于专利权人对该技术特征拥有排他性权利,因此由它创造的价值,理应属于专利权人所有。如果因专利侵权行为导致专利权人未获得由该涉案专利技术特征带来的利润,那么专利权人当然应就此获得赔偿。而对于后者,由于其并未处在专利权人排他性权利覆盖的范围之内,因此其产生的价值,专利权人无权获取。所以,“若涉案专利仅为相关产品的部件或该专利对相关产品而言是改进专利,在计算侵权赔偿数额时,与专利构成整个产品是不同的。如果专利侵权仅仅涉及所售产品的一部分,那么赔偿也应当和必须地被课以相应的限制”[6]。我们可以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来对此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假设某汽车生产商拥有十项专利技术,另有十个汽车制造商未经许可分别将其中一项专利使用在自己制造的汽车上。如果专利权人可以对每一个侵权人都要求整车利润赔偿的话,将导致原告获得十次整车利润赔偿;反之,对于侵权人来说,假如其生产的某一型号汽车侵犯了十个分属于不同主体的专利,如果每个专利权人都可以向其主张整车利润赔偿,该侵权人将对十个专利权人分别承担整车的所失利润或侵权获利赔偿,这会引发对侵权人的过度惩罚,也将导致专利权人获得额外的不当利益,这无疑是有失公正的。因此,赔偿数额的确定,无论是采用所失利润还是侵权获利的计算方式,都必须考虑技术分摊的问题。
从不同专利类型来看,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中,大多数情况下,原告据以计算所失利润的产品往往只是某一部分实施了专利技术,或者被告侵犯原告专利权的仅仅是据以计算被告侵权获利的产品上的某一个部件,那么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该部分在整体中所起的作用,“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的一般部件应当参照该部件的价值和在实现整个产品利润中所起的作用来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才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本意;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技术分摊的需要就更为迫切。消费者完全基于产品外观而做出购买决定的现象十分少见,尤其是高端、价值额较大的物品或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购买者极少会有完全出于对一部电脑、一辆汽车或者一条生产线的外观的偏爱,而决定购买的。因此,对权利人使用该外观设计专利生产的产品的利润损失全部给予赔偿,或者让侵权人将其销售侵犯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利润所得全部返还给权利人,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外观设计专利仅仅作为产品包装物时,如钦料瓶,如果按照原告瓶装饮料的整体利润损失确定赔偿金非常不妥,一般应“参照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7],而且,当包装物在影响整体产品销售中的作用并不显著时,应单纯以包装物的利润计算赔偿数额,方为合理。
综上所述,由于专利构成的复杂性,进而决定了产品市场价值的多样化,因此,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理应考虑专利因素对产品整体市场价值的贡献率,将产品利润在专利技术特征与非专利技术特征之间进行分摊。
二、技术分摊规则的比较法考察
技术分摊规则是两大法系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均采用的规则,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的日本,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司法运用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许多阐述技术分摊规则的经典判词和理论学说,颇具借鉴意义。
(一)技术分摊规则在美国
在美国的专利侵权诉讼中,专利权人应首先证明被告所侵犯的专利技术是构成该产品市场需求、形成产品利润的核心之所在,此时技术分摊比例为100%,即适用全面市场价值规则,专利权人不仅对实施该专利的部件所应获的利益能够得到赔偿,其对整个产品,甚至对独立于专利实施物之外的、与专利实施物通常一同销售的非专利实施物的利润,也可主张赔偿。
在Eimco Corporation v.Peterson Filters and Engineering Company一案中,涉案专利是一个用于排污设施和工业领域的过滤传送带,属于旋转式过滤机器的一部分。第十巡回上诉法庭认为:过滤传送带优化了整个产品的性能,对于过滤设备的市场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侵权人应当赔偿权利人过滤器的全部利润,而非仅赔偿传送带的价值[8]。在Bendix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案中,原告的专利能够根据发动机运转速度、大气压力和气体循环产生的温度来监测燃料用量的燃料测量仪表控制装置。Woodward GovernorCompany,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等企业未经许可,将涉案专利用于为政府采购而制造的涡轮式发动机等设备上。法院认为政府采购的发动机如果未安装原告的燃料控制装置就不能发挥其功能,无法满足政府采购该发动机的特定使用需要,即未安装专利产品的发动机设备对于政府这一购买者来说毫无价值,因此专利设备决定了整个发动机的功能,故对原告的损害赔偿金应当按照安装有该燃料控制装置的、包含与之不可分割的所有连接器的整套发动机的全部价值计算[9]。在Paper Converting Machine Company v.Magna-Graphics Corporation案中,涉案专利是用于卫生纸重绕生产线的卫生纸高密度自动缠绕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了地区法院作出的赔偿权利人整个卫生纸生产线所失利润的判决。其理由是,虽然该部件可以单独销售并独立计算利润,但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在该产业中,为使销售企业对整个生产线承担质量责任,生产企业的采购惯例是购买整条生产线,而不是单独购买自动缠绕机。自动缠绕机是整个生产线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原告的所失利润应当按照整个生产线的利润来计算[10]。在LeesonaCorporation v.the Unite States案中专利技术是一种通过更换电池阳极片来实现充电的电池,法院在判决中不仅要求被告赔偿了原告电池的所失利润,同时也支持了原告“赔偿用于更换的电池阳极片的所失利润”的请求,因为法院认为,如果不是作为专利产品的必要配件,消费者购买电池阳极片将毫无用处,而将阳极片与电池相分离是该专利最为显著的技术特征,该电池的市场营销优势在于其充电的便利性,在实现该功能的过程中,阳极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阳极片虽然未为专利技术特征所覆盖,但其利润损失也应纳入赔偿范围[11]。
但是,当原告无法达到全面市场价值规则的证明标准时,法院将考虑涉案专利本身所带来的利润或特别贡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产品整体价值,并进一步区分被控侵权产品的哪些价值是由侵权人自身的研发所增加的价值或是自身的改进所提升的利润[12]。美国法院在进行技术分摊时,不仅仅局限于对技术特征本身的分析上,还注重从市场的角度进行考察。专利因素对消费者选购的影响程度、专利特征给权利人市场收益做出的贡献度是美国法院决定技术分摊比例的主要因素。
1884年最高法院在Garretson v.Clark and others案中,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技术分摊规则。原告拥有一项拖把头的改进专利,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拖把头的技术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拖把的价值,最后仅获得名义赔偿。最高法院认为,专利权人“必须在每个案件中提供证据,在专利特征与非专利特征之间,来分摊被告的获利与专利权人损害赔偿,而且这样的证据必须是可信的和令人满意的,而不能是推测的或想象的;或者他必须以同样可信的和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由于作为商品的整个机器的全部价值适当地和合法地归因于专利技术特征,因此利润和赔偿按整个机器来计算”[13]。在1886年的Dobson v.Hartford Carpet Corporation案中,最高法院再次论述了技术分摊问题。该案涉及一种地毯外观设计专利,初审法院推定被告制造、销售的地毯造成原告的销售流失,并按原告整个地毯的边际利润乘以被告地毯销量计算所失利润。最高法院否定了该判决,认为,“对编织或印在地毯上的装饰图案的外观设计专利,我们从来没有确定这样的规则,即允许将制造、销售地毯的全部利润——包括梳理、纺纱、染色、编织而产生的利润——作为损害赔偿,因为这样的规则意味着地毯的全部利润是由于图案样式所产生的;当然,如果原告能够提供可靠证据证明全部利润是由图案样式所产生的,则可以按全部利润计算损害赔偿。对于发明专利也采取同样的原则。证明责任在于原告,如果他不能提供必要证据而只是凭借推测和估计,他必将由于缺少证据而败诉”[14]在。Hughes Tool Company v.G.W.Murphy Industries Inc.一案中,原告的专利是用于岩位间的轴承密封件,而侵权产品几乎与原告的专利实施物完全相同,但第五巡回法院认为“显然,专利部分不是决定整个产品销售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侵权者不应当为超出专利部分的价值承担责任”[15]。在Medtronic Inc.v.Catalyst Research Corporation案中,专利是心脏起搏器的电池,但原告据以主张计算赔偿数额的利润却是整个心脏起搏器的利润,法院认为“起搏器的全部市场价值并非由电池决定,故将起搏器的整体利润认定为赔偿数额不够合理”,应当分别确定心脏起搏器各部件的利润情况,进而确定赔偿金额[16]。
综上可见,美国法院是从技术和市场双视角来确定技术分摊比例。如果未实施专利的产品毫无价值,或者当涉案专利的价值达到了能够决定整个产品的市场价值或决定性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时,权利人可以按照整个产品利润要求赔偿,否则将按照专利技术在产品市场盈利中所占的比例来确定赔偿数额[17]。
(二)技术分摊规则在日本
在日本,专利侵权赔偿计算方式的规范经历了一个由民法到专利法的发展过程。1959年,日本在参考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对专利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成为现行法的基础。此次修订中增加了专利侵权民事救济的条款。此后,为了解决赔偿额过低,减轻权利人对侵权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困难,使专利权人获得充分而有效的救济,日本对专利侵权救济条款又进行了修改,1998年侧重于实体规范[18],1999年侧重于程序规范[19]。形成了现行专利法第102条关于专利侵权赔偿计算方式的规定。其中第1款是权利人损失计算方式;第2款是侵权人获利计算方式;第3款是许可使用费计算方式。在此之外,第105条第3款规定了“相当损害额的认定”,即法官自由裁量酌定赔偿额。由于日本第102条设计的基点是民法第709条,有着浓厚的民法理念蕴含其中。按照填平原则计算赔偿额符合侵权责任法的实质。侵权人侵犯专利权实际上是侵犯了专利权人本应独占的市场份额,因此,应该将份额对应的利益归还给权利人。所以,作为控制赔偿数额的有效手段,技术分摊规则在日本专利保护中有着广泛的适用,称为“专利寄与率”,即专利在整个产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介绍,如日本经济产业省官方网站上对专利侵权救济手续的介绍中几乎每一项都提到了寄与率问题;而在日本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几乎都倾向于在判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时考虑寄与率。据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统计,在1998年至2007年间,无论是按照权利人损失、侵权者获益还是许可费的损失计算,都有当事人主张考虑寄与率并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例[20]。
与美国法院考察技术因素对产品市场价值的影响时首先考虑全面市场价值规则的做法不同,日本法院是先考虑寄与率,全面市场价值规则是寄与率适用的例外。大多数案件中,都会在10%—95%之间确定一个比例,只有在充足证据证明,虽然专利技术特征仅构成涉案产品的一部分,但却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决定性因素时,才将寄与率确定为100%。不过,不同于美国法院在每份判决中都会详尽表述确定技术分摊比例的理由,大多日本法院只是简单地阐释专利技术对整个产品的影响,而后直接确定一个比例。例如,东京地方法院在一个关于液体灌装设备喷嘴专利侵权的案件中,认为原告的专利所涉及的喷嘴角度有利于液体的灌装,其对整个设备灌装能力的提高作出的贡献约为20%,应以此计算损害赔偿额;随后,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此案的上诉判决中认为专利仅是液体灌装设备的部件,因此不宜以整个设备的价格来计算,而是应当考虑喷嘴对整个设备的贡献度,以10%的比例来计算为妥[21]。
三、技术分摊规则在中国
我国专利司法保护中,赔偿数额低、计算缺乏科学性、法定赔偿适用过多等,一直广受诟病。为了克服上述弊端,更加合理地计算侵权赔偿数额,技术分摊规则正在逐渐受到重视。
首先,从裁判规则层面看,一些高级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出台司法文件明确要求在计算赔偿数额时要考虑专利因素。2005年江苏高院在《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适用定额赔偿办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②中规定,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应区分起辅助作用的一般部件和体现产品技术功能的关键部件,对前者应参照部件价值和在实现产品利润中的作用确定赔偿数额,对后者则可以按产品整体利润计算赔偿金。2007年重庆高院也做出了类似规定③。2009年最高法院在地方法院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认可了技术分摊规则。《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号)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专利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应当限于侵权人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因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应当合理扣除。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零部件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成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为包装物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从裁判实践层面看,在一些具体案件审理中,法官运用了技术分摊规则,如上海中院在本田诉宗申“小型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的判决主文中就指出,应考虑“专利占整个产品的价值比重”确定法定赔偿金额。④在金童公司诉金鹿日化“蚊香盒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中,虽然原告坚持认为被告的获利应为整个产品的利润,但浙江高院在判决中认为“被告侵权产品的利润包括了蚊香盒及蚊香两部分,应排除蚊香盒中所包含的蚊香利润比例确定被告侵权获利”。⑤在所失利润计算中,法院同样考虑技术分摊规则。例如在中集通华专用车公司与环达汽车装配公司“车辆运输车上层踏板举升机构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中,原告主张按照自己销售运输车的利润乘以被告侵权运输车的506辆的销量计算其所失利润,北京一中院认可了该计算方法,但同时指出由于涉案专利产品并非运输车,而是运输车上装置的上层踏板举升机构,所以在计算赔偿额时“要考虑本专利产品在整个车辆运输车中所占的价值比例”,进而根据“涉案专利在实现车辆运输车用途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安装本专利产品的车辆运输车相对于其他车辆运输车而言具有的市场竞争优势”,确定因安装涉案专利产品“所增加的利润”占运输车利润的三分之一。⑥
综上,我国司法实务界在专利侵权审判实践中已经对技术分摊规则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过于简单随意,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还“没有实现具体化和规则化”[22]。绝大多数法院的做法“不是确定一个可以量化的数字比例,而仅仅是在判决中提及曾考虑此因素”[23],即便是上述北京一中院的判决,虽然确定了三分之一的比例,但却是法官基于技术分摊规则的考虑,径行裁量出的一个比例,既未要求当事人举证,同时也缺乏具体的说理论证。因此,司法实务中技术分摊规则的具体适用亟待规范。
四、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
我国司法实践已经引入了技术分摊规则,但是在操作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应当尽快建立契合该规则本身特点并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适用规范。
(一)以市场分析法确定技术分摊比例
技术分摊规则有其合理性,但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也是不可回避的。单纯从技术角度确定一项专利对某个产品的贡献比例非常困难,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要计算出被侵权专利在侵权产品全部利润中所占的比例,是一件非常棘手甚至无法完成的事情”[24]。美国的汉德法官也曾在判决书中指出,由于技术分摊并不能依据权利要求的文本加以确定,因而“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任意的”,“所有的发明都是一种改进,都是站在过去知识的肩膀上作出的,很难说它为现有知识增加了百分之几的新贡献”,“也许某种改进在结构上是可分的,使技术分摊的量化成为可能,但这仍难保证利润也按这一比例分摊就是准确的”[25]。
应当承认,单纯依靠对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的分析来确定技术分摊比例是不可取的,因为很难确定在一个产品所涉及的若干项技术之中,专利在技术价值方面占有一个多大的比例,而且它还可能导致专利申请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的投机行为,因为只要在措辞上下足功夫,将必要技术特征表述的更为独特和包容,权利人在日后的侵权诉讼中就很容易按照权利要求书的记载,主张涉案专利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产品技术水平提升上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技术特征分析法变得不合理和不可能的情况下,直接面向市场,用市场分析法确定技术分摊比例才是合理的选择和科学的出路。即从专利技术对消费者购买选择的影响、对专利实施物市场价值的提升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专利技术在整个产品价值中的比重。比如在前述的中集通华专用车公司与环达汽车装配公司“车辆运输车上层踏板举升机构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中,原告如果能够证明506辆侵权运输车的购买者不会选择购买没有安装原告专利“上层踏板举升机构”的车辆,或者证明市场上其他经营运输车的商家,由于未安装“上层踏板举升机构”而惨淡经营,那么原告就有理由按照整个运输车的利润来计算其损失,而无需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技术分摊。而被告也可以证明,即便没有其侵权行为,这506辆运输车的购买者中的一定比例会转向购买其他未使用“上层踏板举升机构”的运输车,而非购买原告的车辆,从而降低自己的赔偿数额。
(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基于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较低这一现实,从利益平衡原则出发,可以考虑将技术分摊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由侵权人提出技术分摊的请求并证明在多大的比例范围内进行分摊。同时,为了提高技术分摊规则适用的科学性,应当广泛引入专家证人制度,以其专业知识协助确定分摊比例。
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由其证明涉案专利对原告的专利产品或被告的侵权产品利润的贡献比例。具体来说,被告应证明原告的专利只是产品上的一个零部件,或该专利为改进专利,或是其外观设计专利仅为产品的外包装物等等,进而证明该专利因素在多大比例上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在产品整体利润的实现中发挥了多大比例的作用。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虽然专利覆盖了整个产品,但被告在其侵权产品中另外又增加了某些有价值的改进,不论这种改进是专利技术还是非专利技术,此时如果采用“侵权获利”的计算方式,那么赔偿金额的确定也需要对被告利润进行分摊。此种情况与前一种有所不同,前者是原告专利技术对产品利润的贡献比率,而此处的贡献比率,则是侵权人的技术的贡献比。法院应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增加的有价值改进对其利润所做贡献的比例。如果举证不能,可以借鉴美国做法:“根据信托原理,被告将自己财产与由原告专利产生的信托财产混同,将承担赔偿全部混同财产的责任”[26],即将被告全部利润计为侵权获利赔偿。例如,某专利为制造灯丝的技术,专利权人生产由灯丝专利技术及其他技术组成的灯泡。如果侵权人也生产灯泡,则其应举证灯丝专利在灯泡的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专利为灯泡,侵权人在生产时增加了灯罩,而且灯罩对侵权人利润有所贡献,则侵权人应对灯罩在其利润中所占的分摊比例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完成了该举证责任,则按照其证明的比例进行技术分摊。当然,此时原告可以提出反证证明被告主张的技术分摊比例过低或者证明产品的全部市场价值是出自涉案专利,要求按更高的比例进行分摊或是按全部利润计算赔偿金额。
(三)技术分摊规则的具体操作流程
总体上,技术分摊规则应为:首先计算出侵权人的销售利润总额或权利人因侵权所失的全部利润,而后,乘以专利技术对产品利润的贡献比率,得出侵权人的赔偿数额。具体而言,对于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应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技术分摊规则适用的整体思路是,如果涉案专利仅为产品零部件或仅是改进专利,应当按照该部件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整个产品利润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技术分摊比例;如果是外包装物侵犯外观设计专利的案件,则应当按照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技术分摊比例。
如果涉案专利技术特征覆盖了整个产品或者虽未完全覆盖但却对实现产品的全部市场价值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应按照产品的整体利润计算赔偿金额;对于包装物,只有在该包装系吸引多数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主要因素,且与产品在销售时不可分离时,方可以参照产品的整体利润确定赔偿数额。适用全部市场价值规则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专利技术特征必须构成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基础;(2)专利权人必须合理地期望将非专利部件连同专利部件一起销售;(3)非专利部件与专利部件的功能密切关联,在发挥作用时相互依赖。
其次,如果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确定技术分摊比例,其理应承担不利后果,但是此时如果将全部产品利润均赔偿给原告,显然是对被告一种严苛的惩罚,而且原告获得非由其专利创造的利润也没有合理依据,会造成原告的不当得利,因此法院应当根据原被告双方既已提供的证据,裁量一个比例,但是法院在裁量中应考虑到被告举证不力的事实,采用相对宽松的标准,在裁量中略向原告倾斜,在其确定的实际分摊比例上做适当的提高。无论是当事人举证并经法院确认的技术分摊比例,还是法院自行裁量的比例,都应当要求法院在判决中对该比例的确定,做出尽量详细的阐述,以最大限度的防止技术分摊规则适用的随意性。
结 语
从我国目前专利保护的司法实践来看,专利作为技术程度高、复杂性强的一种知识产权,长期处于一种赔偿水平低下的状态。据统计,2007—2008年度,即使在我国专利保护水平较高的京、沪、粤、江、浙五省市,专利平均赔偿数额也仅在十万元左右[27],“十赔九不足”是企业界对专利司法保护的评价。因此,在我国当前专利赔偿水平较低的背景之下,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应当更加规范化。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技术分摊限制了赔偿数额,就摒弃对专利贡献度的考虑,因为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符合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被侵权人因损害赔偿而不当获利;另一方面,我国应当通过对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经验的借鉴,合理优化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
技术分摊的证明是复杂而困难的,按照分摊比例计算出的赔偿数额也难以做到绝对精确。但是如果不考虑技术分摊比例,那么赔偿数额就一定是不准确的。所以,即便复杂、困难、无法达到绝对精确,也不可因噎废食否认技术分摊规则的适用。实践中应当做到的是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法官据此确定一个尽量合理的比例。
注 释:
①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温民三初字第135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07)浙民三终字第276号.
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适用定额赔偿办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第十一条.
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八条、第九条.
④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1号判决.
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浙民三终字第150号判决.
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初字第8857号判决.
[1]和育东.美国专利侵权救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40.
[2]和育东.专利侵权赔偿中的技术分摊难题——从美国废除专利侵权“非法获利”赔偿说起[J].法律科学,2009,(3).
[3]Lucentv.Gateway etal,509 F.Supp.2d 912(2007).
[4]Erik R.Puknys.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朗讯诉微软案为例[J].电子知识产权,2009,(5).
[5]周琪.技术与市场综合分析法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应用.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研究2009[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342.
[6]Philp v.Nock,84U.S.460,462(1873).
[7]管育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判定中专利贡献度问题探讨[J].人民司法,2010,(23).
[8]Eimco Corporation v.Peterson Filtersand Engineering Company,406 F.2d 431,160U.S.P.Q.182(1969).
[9]Bendix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676 F.2d 606(1982).
[10]PaperConverting Machine Companyv.Magna-Graphics Corporation,745F.2d11,223U.S.P.Q.591(1984).
[11]Leesona Corporation v.the Unite States,599 F.2d 958(1979).
[12]周琪.技术与市场综合分析法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应用.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研究2009[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340.
[13]Garretson v.Clark and others,111U.S.120(1884).
[14]和育东.美国专利侵权救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15]Hughes Tool Company v.G.W.Murphy Industries Inc.,491 F.2d 923,180u.s.p.q.353(1974).
[16]Medtronic Inc.v.Catalyst Research Corporation,547 F.Supp.401(1982).
[17]管育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判定中专利贡献度问题探讨[J].人民司法,2010,(23).
[18](日)特部工所有制度改正室.平成10年改正:工所有法の解』.明会,1999,10.
[19](日)特部工所有制度改正室.平成10年改正:工所有法の解』.明会会,2000,40.
[20]管育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判定中专利贡献度问题探讨[J].人民司法,2010,(23).
[21]管育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判定中专利贡献度问题探讨[J].人民司法,2010,(23).引自:京地裁判决平成14年(ワ)第3237号,平成17年9月29日;知 高裁判决平成17年(ネ)第10006号.
[22]戴建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9.
[23]和育东.专利侵权赔偿中的技术分摊难题——从美国废除专利侵权“非法获利”赔偿说起[J].法律科学,2009,(3).
[24]廖志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5]和育东.专利侵权赔偿中的技术分摊难题——从美国废除专利侵权“非法获利”赔偿说起[J].法律科学,2009,(3).
[26]和育东.美国专利侵权救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38.
[27]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法律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专利与商标,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