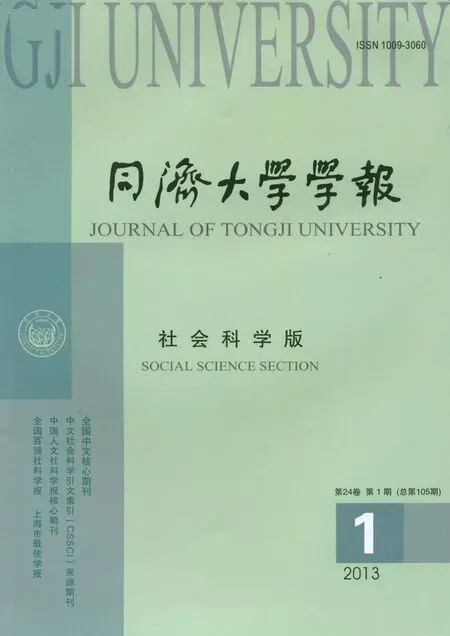意识形态的再发现
——论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
2013-02-14和磊
和 磊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250014)
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派别,它以对社会的激进批判为学术旨归,在世界范围的人文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媒介研究一直是该学派的兴趣中心之一。其实在伯明翰学派之前,媒介研究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了,尤其是在美国。但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在于它在对以前的媒介研究进行适时而恰当的批判中,借鉴运用了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hegemony,或译为“文化领导权”)理论,注重媒介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从而确立了它自己的媒介研究特色。
一、意识形态的再发现
早期的媒介研究主要兴起于美国,以经验主义研究为主,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注重媒介效果的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这种研究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忽视或回避了对社会的批判,把媒介仅仅看作是一种工具,而这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霍尔指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很早就对这种媒介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采用了一种意识形态框架的分析方法,即把媒介界定为一种主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被用来确定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以及在大众中传播和再生产(国家)意识形态的。为此,中心批判那种认为媒介文本是意义的“透明”承载者的观点,强调要对媒介文本进行语言的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分析,同时倡导积极的受众观念,强调受众在解码中的能动性。①CCCS,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1979,London:Hutchinson,1980,p.117.伯明翰学派的这一媒介研究思路在霍尔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标题中体现得非常清楚——《“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体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
在这篇文章中,霍尔首先延续了伯明翰学派对以前的媒介研究,尤其是对美国媒介研究的批判,明确指出讯息并不是对现实的纯客观的真实反映,而是被建构出来的。霍尔说:
“真实不再被看成只是一组给定事实的组成,它是特定方式建构现实的结果。媒体不只是再生产‘现实’,它定义了什么是‘现实’。藉着所有的语言实践,经由选择定义,再现‘真实’的作法,现实的定义就被保存与生产出来了。但是再现是一个非常不同于反映的概念。它意味着结构化与形塑,拣选与呈现的积极运用,不只是传送既存的意义,而且是使事物产生意义的积极劳动。它是意义的实践与生产——后来被定义为‘表意的实践’(signification practice)。媒体是表意的作用者。”①[美]迈克尔·古尔维其等:《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的观点》,唐维敏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84、90、97、92-93页。
借助结构主义,霍尔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结构主义告诉我们,意义不是给定的、先在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语言在这其中是意义生产的中介。推至媒介,媒介正是生产意义的机制,“媒体制度的特殊性就正在……社会实践被组织起来而产生象征产物的方式。建构这个(解释)而不是那个解释,必定需要某些手段的特定选择以及藉由意义生产的实践将它们接合一起。”②[美]迈克尔·古尔维其等:《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的观点》,唐维敏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84、90、97、92-93页。③ 即“话语”,台湾学者一般把“discourse”翻译成“论述”。也就是说,媒介运用各种手段,去建构它所需要的意义,并为此做出自己的解释,以使受众同意并接受这一意义。这其实正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问题的典型方式,也是霍尔所推崇的分析问题的方式之一。但霍尔又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分析问题的缺陷,即仅仅在静态的整体文化中分析意义的可生产性,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对于霍尔和伯明翰学派来说,需要用一种更为历史的概念取代这种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霍尔说:“意识形态的概念就要彻底地被历史化。一个陈述的‘深层结构’必须要被看成是长期且产生于历史之中的论述③,所形成的元素、前提与结论交织而成的网络,这些论述已经长年附着于社会形构沉淀下来的历史,而构成一个主题与前提的储存库。”④[美]迈克尔·古尔维其等:《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的观点》,唐维敏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84、90、97、92-93页。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一种历史化地分析问题的方式呢?这里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斗争的场域,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力量”。霍尔说:“在特定斗争的行径中,意识形态也变成了斗争的场域,变成了一个赌注。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不能被看成是因变数,仅是先前给定的现实在心灵的反映而已。它的结果也不是仅靠一些决定性逻辑的衍生就可以预测的。这些结果要看特殊历史时势之下各种势力的抗衡:也即是得看‘表意的政治学’。”⑤[美]迈克尔·古尔维其等:《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的观点》,唐维敏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84、90、97、92-93页。表意政治学正是霍尔和伯明翰学派媒介研究的核心。通过伏洛西洛夫(实际上就是巴赫金)的语言理论,霍尔进一步强调了巴赫金“语言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大命题,并以此批评了阿尔都塞太过片面的意识形态理论,即他只强调“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忽视了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这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二、文化霸权理论与编码/解码
1.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不再使用武力来强迫人民大众接受其统治,而是采取温和的文化策略,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葛兰西在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而一方要赢得另一方同意,并不是很容易的,其中就有着双方的谈判与斗争,有谈判也就有让步或折衷平衡的问题,正如葛兰西所说的:“毫无疑问,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文化霸权的前提,必须达成一定的折衷平衡”⑥[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也就是说当事双方都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葛兰西在谈到要成功组织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历史集团时说,这“就需要改变某些必须吸收的力量的政治方向。由于两种‘相近的’力量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或武力要么互相结成联盟,要么强行使一方服从另一方,方能接入新肌体,此处的问题是一方是否具有某种力量,使用这种力量是否‘富有成效’。如果两种力量的联合旨在击败第三方,诉诸于武力和胁迫(即使假定它们可行)不过是假设的手段;唯一具体的可能是妥协”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霍尔通过结合话语理论,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运用到了媒介研究上,强调媒介编码者与受众解码者之间的协商与谈判,而不是像早期媒介研究那样,认为编码后的意义会直接输入到解码者那里。这在霍尔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②Simon During(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3.中得到了最为清楚的体现。这篇文章被看作是伯明翰学派媒介理论的经典之作。
2.《编码,解码》
在《编码,解码》中,霍尔分析了三种解码立场,这就是主导—霸权立场、协调的立场和对抗的立场。在主导—霸权的立场中,传播是一种“完全明晰的传播”,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传播人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解码者并没有自己的主动性,只有接受。而在协调立场中,“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抽象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③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7、358页。在对抗立场中,“‘意义的政治策略’——话语的斗争——加入了进来”④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7、358页。。在这三种解码立场中,霍尔尤其关注协调立场,这其实也正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体现。但霍尔的这种“编码,解码”模式招致了许多批评,其中招致最多批评的是他对“优先意义”(preferred meanings)和“优先阅读”(preferred reading)的强调,原因就在于它们限制了受众的解读,限制了人的解码的能动性。⑤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2-173.
这样的批评也许并不为过,但霍尔有他自己的解释。在很久之后的一次访谈中,霍尔就《编码,解码》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也是在为自己辩护。霍尔指出,“优先意义”在编码一端,“优先解读”在解码一端,“我并不想要一种没有权力处于其中的循环模式”,“并不想要一种没有决定的模式”。⑥Stuart Hall,“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Jon Cruz and Justin Lewis(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1.霍尔在这里提出“权力”与“决定”问题,意在强调经过编码的信息是不可能被任意解读,或被解读为任何意义的,这也就是霍尔所说的:“我并不相信信息会拥有任何一种意义(has any one meaning)。因此我想在编码时刻获得一种权力与结构的观念。”⑦Jon Cruz and Justin Lewis(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3、p.262.这也就是霍尔强调优先意义和优先阅读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经过编码的文本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它总是会引导你按它的某种编码方式去解读,并由此“试图获得对受众的霸权”,这就是霸权的时刻,这也就是优先阅读的含义。但对霍尔来说,强调优先阅读并不是止于优先阅读,因为任何的优先阅读或优先意义并不能消除其他的可能的意义,正如霍尔所说的,编码对受众的霸权“从来就不是完全有效的,而通常是无效的。为什么?因为它们不能包含每一种对文本的可能的解读”⑧Jon Cruz and Justin Lewis(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3、p.262.。
在这里,霍尔一方面强调编码的优先意义,一方面强调解码的可能意义,似乎是矛盾的,但对霍尔来说,他实际上是试图在结构和能动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人一方面必然处在结构的限制之中(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观点),但另一方面则又必然以其自身的能动性进行着反霸权的活动,人实际上也就在这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中不断前行,忽视任何一方在霍尔看来都是片面的。“因此,一个优先解读从来就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它是一种权力的实施,试图去获得对受众解读的霸权。……我并不认为文本是无限开放的,没有任何因素在其中。”①Jon Cruz and Justin Lewis(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2、p.265.
也正由此,霍尔突出谈判式(即协调式)的解读方式:“谈判解读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运用的一种解读方式。只有在我们形成完美有机的、有着革命性的主体时,你才会获得一种完全的对抗式的解读。”②Jon Cruz and Justin Lewis(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2、p.265.这样,在限定与能动之间,人的主体性不断滑动,形成一种多主体的身份,进而形成对文本的多种解码方式。
三、批评实践:《监控危机》
《监控危机》是伯明翰学派的一部重要的媒介批判实践著作,它通过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具体分析了一件并不算太大的抢劫事件是如何引发了一场“道德恐慌”,这种道德恐慌又是如何最终被国家利用而成为其加强社会控制的借口,而这种控制又是如何通过赢得人民的同意而得以实施的。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1972年8月的一天,在伯明翰的一个黑人聚居区,一个领养老金的白人老人遭到了三名黑人青年的抢劫,并受了伤。但就是这一看似简单的犯罪案件,却在英国当时特定的形势下,变得不同寻常起来,引发了包括警察、法院、地方长官以及媒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大讨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这起犯罪案件中,警察、法院、地方长官及媒体形成了一个循环,一个不断强化犯罪与犯罪恐慌的循环。警察为了加大控制力度而夸大犯罪的数量,强调社会在不断出现“‘一波又一波’新的犯罪类型”,而犯罪数量上的增加使得加强控制犯罪变得顺理成章。③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38、p.52、p.73、p.221.报纸根据警察的陈述和卷宗记录加以编辑,宣传了犯罪扩大的“事实”,并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严厉审判;法官则又往往引用报纸所报道的人民的“心声”,说要严判;而警察反过来又根据法官的陈述要求新的权力以维持社会秩序。而所有的他们都在申明“‘道德恐慌’在发展”④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38、p.52、p.73、p.221.,一定要严惩处罪犯,否则会使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
其次,在这场道德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从新闻媒介对抢劫案件的报道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霍尔等人统计并分析了《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和《卫报》(Guardian)从1972年8月到1973年8月对抢劫事件的报道。根据他们的统计,这两家报纸总共有60篇关于抢劫的报道,其中就有38篇是关于暴力抢劫的报道,22篇是关于非暴力的报道,暴力与非暴力报道的比率近乎2∶1。就1972年和1973年的报道来看,1972年的暴力报道数是20篇,非暴力报道是15篇;1973年的暴力报道是18篇,非暴力报道是7篇。由此,1972与1973年暴力与非暴力的比率几乎从1∶1发展到了3∶1。而从1973年4月到8月比较来看,暴力(10篇)和非暴力的报道(2篇)的比率是5∶1。⑤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38、p.52、p.73、p.221.从这可以看出,宣传暴力倾向的抢劫案件的比率日益增多,而在这种报道中,一些并不是暴力的抢劫,如smuggle这类的“夺取”也往往被帖上了抢劫的标签,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犯罪的恐慌,也就是对道德危机的恐慌。
这样,通过警察、法院、地方长官及媒体的联合鼓动,社会持续地保持着一种“道德恐慌”,而“‘道德恐慌’显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的意识的形式,以此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被争取过来,去支持对国家日益增长的压制手段,并把其合法性让与给一个‘非同寻常的’(more than usual)的控制实施”⑥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38、p.52、p.73、p.221.。也就是说,道德恐慌使得大众主动地把自己交给了国家,同意了国家的控制,由此也就赋予了国家控制的合法性。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抢劫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符码,负载着国家控制的阴谋,正如霍尔他们所说的,抢劫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犯罪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破坏英国生活方式的社会现象,由此而来的种族、犯罪和青年人都“被压缩进了‘抢劫’的意象中”①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VII、p.323、p.321-322.,如吸毒、学生示威、嬉皮士,甚至女性运动等等,也都与抢劫这种行为联系起来,似乎他们也都在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都被经验为“对国家的威胁,社会生活本身的崩溃,骚乱的来临和无政府主义的开始”②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VII、p.323、p.321-32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大众需要政府,需要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大多数人的焦虑与对少数人控制的需要结合了起来。‘所有人’都发现,只有把他们的利益安置在那些领导人的保护之下后才会获得合适的保障。国家现在就可以公然地和合法地代表并保护少数人而展开反对极端行为的运动。”③Stuart Hall 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VII、p.323、p.321-322.这样,国家也就顺利地实现了自己加强对社会控制的意图。显然,这种意图是通过大众的同意而获得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渠道稀缺,大众传媒(以报纸为代表)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保持着对受众的强势地位,受众在其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也就很容易接受被编码的信息,这与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不同,④张冠文:《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表达与引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这也是造成大众的道德恐慌,进而接受国家控制的一个原因。
伯明翰学派批判了以前的媒介研究,把意识形态和霸权概念置于研究的核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媒介文本编码和解码的新视角,但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理论更多地着眼于编码与解码之间的斗争,对于编码的生产机制则很少涉及,也正因此而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比如英国莱切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两位学者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就批评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过分注重意识形态批判而忽视了媒介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比如,他们在《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就指出伯明翰学派媒介研究缺少对于相关文化工业运作方式的分析,“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说出这种工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其经济组织又是如何影响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它们也没有检视,人们的消费选择与他们在更宽泛的经济结构中的位置的结构性关系。考察这些原动力,正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⑤[英]彼得·戈尔丁、[英]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见[英]詹姆斯·库兰等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6、71-72页。接着,他们给出了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取向:一是关心文化产品的制造,特别是文化生产对文化消费有限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其次是检视文本的政治经济学,以阐明媒介产品中的再现与外在生产、消费的物质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三是评估文化消费的政治经济学,以说明物质和文化资源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⑥[英]彼得·戈尔丁、[英]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见[英]詹姆斯·库兰等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6、71-72页。从这一研究取向上,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媒介研究在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两种维度上的不同,而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后来媒介研究的一种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