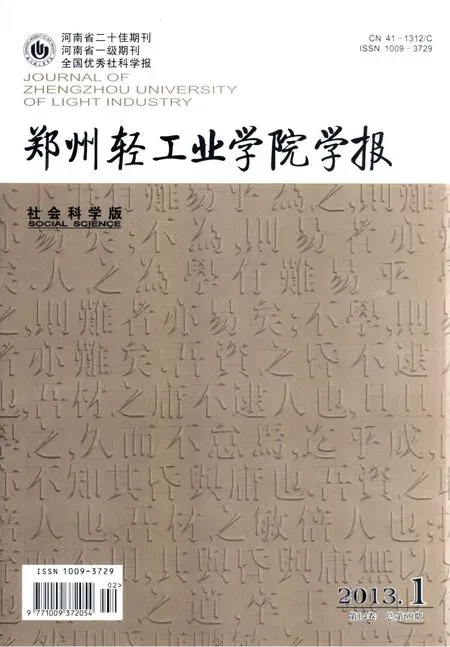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2013-02-01沈伟华
沈伟华
(南京林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苏 南京 210037)
古人注书,往往会借题发挥,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意见,王弼(226—249年)注《老子》是这样,郭象(约252—312年)注《庄子》亦然。王弼借助“得意忘言”的方法将《老子》之“无”发挥得淋漓尽致,进而开创了魏晋玄学。如果说他对《老子》某些观点的加工和改造与《老子》之原始意旨有出入,那也是王弼于那个时代解读《老子》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文本一经流传于世,便同时具有了原始意义和时代意义,然而后者并不脱离前者,且更能体现文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这正是文本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弼注《老子》而立“贵无”的本体论哲学,并试图借此调和名教与自然;而郭象则以其“寄言出意”的方法为指导,更为直接地对《庄子》中逍遥、自然等一系列关键性概念加以创造性解读,最终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独化理论,从而进一步调和了名教与自然,并将魏晋玄学推向历史发展的高峰。本文拟对郭象的这种努力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寄意《庄子》
自王弼“得意忘言”的方法论确立之后,玄学家们常以此来阐释自己的思想。郭象在注释《庄子》之《阳则》与《天道》两篇时说:“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得彼情,忘言遗书者也”。然而郭象在方法论上的使用并未止于此,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自觉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是他在方法论上区别于其他玄学家的独到之处。在郭象看来,《庄子》一书也正是以“寄言出意”的方法来表达庄子思想的,他在注释《庄子·山木》篇时说:“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郭象说庄子以“寄言出意”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实则是表明自己注《庄子》所采用的方法。在注《庄子·逍遥游》时,郭象就提示了他的这一基本思路:“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知耳。”郭象认为,在对《庄子》的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其根本意旨和精神所在并加以融会贯通,对于那些细枝末节或不能予以证实的地方,则可以在不妨碍把握其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存而不论。这样,郭象一开始就为他注解《庄子》留下了极大的自我发挥空间,而“寄言出意”方法的使用更使得郭象能够借力于《庄子》来展开其“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理论构造。这就从“我注六经”之郭象注《庄子》一变而成为“六经注我”之《庄子》注郭象,而这也正是后人诟病郭象“误读”《庄子》的原因所在。当《庄子·渔父》说渔父“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的时候,显然是其借渔父之口在对孔子及其所倡导的儒家思想进行批判,这是《庄子》之本意所在。但郭象注此章谓:“此篇言无江海而闲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岂直渔父而已哉!将周流六虚,旁通无外,蠕动之类,咸得尽其所怀,而穷理致命,故所以为至人之道也。”郭象这里强调,孔子不仅仅有游于外之境界,亦有游于内之情怀,这样一种游外以弘内的品行成就了孔子圣人、至人的人格。游外以弘内也是郭象融和自然与名教、融汇儒道的理想指向。由此可见,郭象的这种阐释,显然已离《庄子》本意甚远,而只是在阐发自己的理想。
二、逍遥之论
“得意忘言”与“寄言出意”在“出意”这一点上,其意义是很接近的,王弼以“得意忘言”之方法而出“贵无”之意,郭象借“寄言出意”之方法而出自由逍遥之意。但二者在对文本之外的自身思想的空间拓展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研究。如刘笑敢[1]将王弼注《老子》的方法定位为文义引申式诠释,认为此类作品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注者个人思想文化背景的干扰和渗透,不能完全摆脱注者个人的创造性发挥,但其基本思想是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与原文的基本思想大体上能够保持一致。而郭象注《庄子》,则是一种自我表现式诠释,刘先生认为此类作品虽然也会受到诠释对象之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的某些限制,但作品是以个人之精神和思想表达为主,因而会与原文本的精神方向有重要的或根本的不同。
对于《庄子》第一篇《逍遥游》,郭象题解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并注曰:
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安鸟之能下,桩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之有穷哉!所御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无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无所不能殊也。
这一段注解表达了郭象对《庄子》之自由思想的理解,同时也出现了“自然”、“性”等概念,是理解郭象思想之关键切入点。《庄子·逍遥游》中的自由思想,本意是从“有待”、“无待”的区分上立意,指出无所待的状态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逍遥,追求的是圣人、神人、至人的那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状态到了郭象那里却成了一种个体之自性的实现,于是才说“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无所不能殊也”。在郭象看来,个人只要能够把自身所秉承的自性充分发挥出来,就是达到了庄子所谓的逍遥。于是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曰:“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在庄子那里,自由的状态只有圣人、神人、至人能够达到,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无待”,不滞于任何条件,也就能够不为任何条件所限而达到“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的自由逍遥境界。但郭象认为,就世间万物而言,由于它们秉受自然之性而各有所分,也就皆受一定的限制;而在其性分之内,以其性分而行才能顺其所待,而顺其所待就是不滞于所待,也就是无所待,于是而得自由。在郭象看来,虽然不同事物实现其自性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仅就自适其性这一点来看,翱翔九万里的大鹏和徘徊在蓬蒿之间的小鸟并无分别,只要万物安于其各自所受的性分,即性命得安,其性自足,乃得逍遥;而事物如果不能够自得其性,在其性之外来追求逍遥,就会陷于一种“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的境地。显然,这是郭象自己对逍遥之义的理解,只是借助了注《庄子》这样一种形式。
三、性分思想
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立在其性分思想之上。在郭象看来,万事万物从自生到发展、到死亡,均有其内在根据。郭象注《庄子·大宗师》曰:“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郭象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称为“性”、“性分”、“自性”、“真性”等,如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曰“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跂尚之所及哉”,注《庄子·马蹄》曰“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注《庄子·养生主》曰“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注《庄子·齐物论》曰“性各有分,故知者受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注《庄子·外物》曰“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故圣人唯莫之制,则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等。
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是决定其之所以为此事物的根据,事物各不相同,正在于其性不同,而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对于秉承自性之外的空间,则不能勉强为之,此即所谓“性之所能,不得不为”、“性所不能,不得强为”。这正是郭象所认为的事物达至逍遥之境的状态。于是,本来只能圣人、神人、至人才能够做到的逍遥,到郭象这里乃成为凡人也同样可以达到的境界。郭象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他是否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崇高神圣的精神境界或者形上追求,而在于在为每一个个体树立了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自得之境,其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
在一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的层面上,郭象的“性分”与庄子的“自性”并无很大的不同,二者同指某一事物所固有的内在本质,是其本然如此的一种素质,《庄子·外物》篇也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然而依庄子之无待逍遥,其自性亦必然指向无人为修饰的天然本性;但在郭象这里,正同于其对自由逍遥之义的理解,当他说事物自适其性而得逍遥的时候,人为修饰亦可以包容进他所谓的自性之中。
庄子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来说明什么才是马的真性:“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而当伯乐说他善于治马,并对马烫毛削蹄,烙印戴笼,编进马厮,此时马已经被折腾死十之二三;更在马饿的时候不让吃,渴的时候不让饮,而让其按人的指挥而奔跑,前有马嚼之装饰,后有皮鞭之威吓,则马已经有一半要被整死。显然,庄子认为伯乐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马的真性。然而郭象对此注曰:“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或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以。”在郭象看来,马的本性显然不仅仅止于庄子所谓的“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而更在于它的奔走能力及供人骑乘的功能。善御者的所作所为,正是帮助马来实现它自身的能力而尽其本性。马之所以会死则只是因为“求其过能之用”,也即是上面所说的“性所不能”而强为之才导致的;如果能够任凭马来施展它的能力,“适迟疾之分”,则正可以全众马之性。按郭象的理解,世人以“放而不乘”来解释“任马之性”显然是错误地理会了庄子的意思,则“无为”自然也就不是什么都不做或者选择一种更轻松惬意的行为姿态了。
四、从自然到独化
郭象与庄子的不同,或者说是郭象对庄子思想的发挥,在郭象对庄子关乎“自然”的定义的理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庄子·秋水》篇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的时候,其本意当是对“以人灭天”这一状况的极力反对,认为牛马只有在其未被人类驯化的状态下才可以保持其本然天真的状态。对此,郭象注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到了郭象这里,牛和马被人类穿鼻落套变成了牛马之本性,是其本性规定了它们必然要接受这样一种被人类役使的命运,也只有如此才可以成全牛马之本性。人类驯服牛马这样一种在庄子处被加以驳斥的“人为”的行为,在郭象这里变成了顺应牛马之性的“自然”,而郭象的“人为”则显然就是上面反复提过的追求本性之外的行为,也就是让牛马超出它们的能力而超负荷工作了。
当人为被融摄进自然的立意之中,那么,把“有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在郭象这里自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思想进路。《庄子·应帝王》中有一则广为人知的寓言,表明了庄子对于“无为”的盛赞和推崇:“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显然,庄子认为“有为”会伤害事物的本性并进而导致其本性的丧失。而郭象对“无为”的理解与庄子可谓大异其趣。如郭象注《庄子·天道》曰:“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这里的“各任其事”、“自当其责”显然很容易包含进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有为”的意味,从而“无为”的意思也就变成了万物都应该各自去做它所应当做的事,而尽其所应当尽的责任,故而“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工人以斧刻木,主上以臣治事,这在郭象看来正是依其本性而行,故而可以称其“无为”。郭象在这里将工匠的“有为”一变而为“无为”,或者可以说,郭象的“无为”正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有为”。从而,郭象的所谓“无为之业”也就成了他在注《庄子·大宗师》篇时所说的“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郭象以“有为”释“无为”的做法实质就是在调和名教与自然。
当郭象将万物自适其性的发展解释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和行为,而最终达至自由逍遥之境的时候,万物自然也就指向了自生独化这样一种精神旨归。[2]在郭象那里,自由逍遥之境被称为“玄冥之境”。郭象注《庄子·大宗师》曰:“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可见,郭象并不简单地否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但也不认为这种联系和影响是事物之间的根本道理,在他看来,事物自身之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才是理之至极。
五、结语
郭象之理论起于对本体之无的驳斥,而终于对玄冥之境的追求。在提出“造物者无物”之后,郭象接着指出万物实际上是“自生”的。物各“自生”,则在万物之上也就不需要再另设一个造物主,“道”实际上成为空无的代名词。于是,万物乃可以各自安于其所处的地位而顺乎其自身的本性。事物立足于其自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独立自主地生生化化,此所谓“独化”。万物独化,并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根据,而只依托于其自性,事物自身即为根据,即“用外无体”。郭象由此证成了“体用一如”,从而在哲学思辨上将目标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
郭象的哲学思想进路几乎与王弼相反。王弼借助“得意忘言”的方法,由“以无为本”的命题开始,最终证成万物皆统一于本体之无,从而达成万物与宇宙的统一,圣人“与道同体”的境界乃是其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郭象则以“寄言出意”为方法,借注《庄子》破本体之无,重新诠释“自然”之义,追求的是最终达至“独化于玄冥之境”,从而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虽然他们各自的方法、进路及境界均不相同,但就其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现实目的来看,二者殊途同归。[3]
[1]刘笑敢.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及其外化——以王弼《老子注》及郭象《庄子注》为例[J].中国文史研究所集刊,2005(26):287.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95-96.
[3]徐小跃.禅与老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