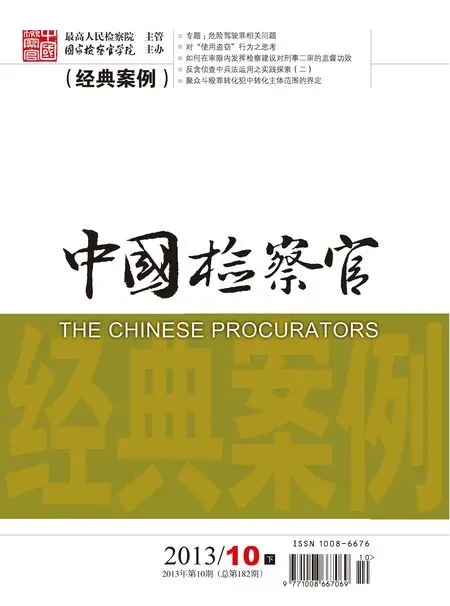同案定罪量刑差异化问题研究
2013-01-30曹建煜蔡兆卿梁国武
文◎曹建煜 蔡兆卿 梁国武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我们时常看到就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犯罪事实,不同侦查机关认定的罪名却大不相同,即使定罪相同,且其中的犯罪事实、情节、金额等相同或基本相同,但同罪不同刑也非常普遍。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对于定罪,我国虽已有相对完善的刑事立法,但因法律概念模糊及其司法解释不能穷尽一切犯罪事实等原因,常导致定罪产生争议。而对于量刑,因法律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空间非常大,再加上量刑方法存在不统一等因素,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出现的越多,普通百姓就越会对司法公平正义提出怀疑。
一、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表现及危害
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不但表现为相同犯罪事实的不同犯罪嫌疑人定罪不同与相同犯罪事实的不同犯罪嫌疑人量刑不同两种情况,有时,这种不统一更突出表现在案情类似,包括犯罪的情节、犯罪金额、犯罪手段等方面都相类似的情况下,定罪量刑却出现极大的差异。
(一)定罪方面
[案例一]胡某驾驶改装过的跑车以近10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杭州繁华街头与朋友飙车,将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谭某撞死(撞飞5米高30多米远),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胡某进行拘留。而同样是一种飙车行为,在四川成都的蒋某醉酒后驾驶一辆无牌照 “悍马”在成都二环路上高速行驶制造了一起连环撞车事故,造成一死五伤,但成都当地检察机关是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蒋某。两起飙车案在案情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定罪却完全不同。杭州飙车案中公安机关是以交通肇事罪对胡某立案侦查,但从案情来看,如果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似乎更为合理,因为闹市飙车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行为本身也对行人人身及财产安全、城市交通够成了极大的危险。胡某定交通肇事罪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蒋某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定罪不同会导致两人命运的完全不同。
(二)量刑方面
[案例二]陈大伟在醉酒的情况下窜至自家三楼租房户维吾尔族妇女XXX的房间,将其面纱撕开,上衣扣子扯掉,推倒在床上,强行对其进行搂抱、亲吻、抚摸。该案经过开庭审理,最后由镇平县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作出对陈大伟四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的判决。在定罪方面,这个案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陈大伟的行为确系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该案的焦点是在量刑方面,因为在此之前的李光要趁本村女青年李某某(聋哑人)一人在家之机,窜到李家,强行对该女进行搂抱、抚摸,由于该女极力反抗,后李光要逃离现场,与陈大伟命运不同,李光要最后以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这两个案件从案件性质、情节上看都差不多,也许涉嫌犯罪的细节有些差别,但在量刑上差别是不会太大的,而且陈大伟并没有法定的从重情节。为什么法律作出的判决会相差如此之大,从陈大伟案激发出来的民意看,大家矛头所指,并非是事实和证据,而是法律本身。这就是我们司法机关在量刑方面出现了不统一。
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重相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不得定罪处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则要求我们在适用刑法过程中,做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定罪量刑标准的不统一与上述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的司法理念是相违背的。准确的定罪量刑体现法律对某一犯罪行为的否定程度,能使罪犯真正感受到应得的惩罚,内心认服,自觉改造,而过轻或者过重的刑罚都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发挥不了法律震慑犯罪的作用。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常出现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我们的法律权威将受到挑战,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会降低,更谈不上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司法目标。
二、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原因
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定罪混乱、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不和谐的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立法上的因素,也有司法上的原因;既有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地域、体制与制度等客观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刑事立法的不完善对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产生了影响
刑事法律的不健全或滞后,使一些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在认定与否上产生了争议,比如新型贿赂形式中对收受干股的认定;刑法还出现定罪数额规定不统一、量刑档次交叉的现象,比如盗窃、抢劫罪立案数额的起点在沿海与西部地区就差别很大;另外是刑法总则与分则上的模糊用语很多,比如总则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悔罪表现、不会发生社会危险”的可以适用缓刑,这些设定的条件都不易操作,再加上我国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又非常大,这样就使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二)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尺度不统一导致定罪量刑出现差异
司法是否公正,对老百姓来讲,最直接、最感官的表现体现在打击犯罪尺度是否统一上。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不平等造成定罪的量刑不同在财产型犯罪中很普遍,如在贿赂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为了更好地查处犯罪而对主动交待犯罪事实的行贿人常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做减轻了案件查办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纵容行贿之嫌,而行贿又是产生贿赂犯罪的源头,且多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一律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处罚则不利于从根本上惩铲除腐败。杭州飙车案与成都飙车案等案件产生的定罪差异,广州许霆案和昆明何鹏案等案件出现的量刑标准不统一,只不过是我们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冰山一角,只是它们被媒体揭露出来了,我们才了解其中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问题,对于更多没被揭露出来的我们无从知晓。
(三)办案中的利益驱动及行政干涉司法导致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
有时,外在的因素也会对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地方的法院为实现创收而把缴纳罚金作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交换条件;犯罪嫌疑人如多缴纳罚金或非法所得就可以减轻、从轻或者免予处罚;检察机关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会出现追究一部分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另一部分与之有相同犯罪情节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往往产生了定罪与否及量刑失衡的争议。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司法机关在查办和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干涉。这种干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有的表现为官员个人干涉司法,而有的则表现为地方保护等“政府行为”的干涉,而后一种情况更为可怕。
(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同及量刑方法存在缺陷造成量刑的不统一
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审判主体因知识结构、对法律理解等不同常导致会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或同类犯罪因审级、适用的审判程序不同也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衡。我国法官目前量刑时一般采用综合估量式的量刑方法,具体是指法官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结合案件中的从重、从轻等情节,最后综合估量出应判处的刑罚,但因我国刑法对这些法定情节的限度没有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常会使量刑出现不统一。当然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代的不同造成时空上的差异及司法腐败也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原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准确定罪量刑的建议
综合对我国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表现、原因等的分析,笔者认为统一我国定罪量刑标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观念,树立尊重定罪、尊重量刑,重视定罪、重视量刑的基本理念
司法公正是定罪准确和量刑公正的统一体,定罪准确是司法公正的基础,量刑准确与公正是司法公正的目标,倚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可能导致司法的不公正。二是在司法过程中追求和践行真正意义上的刑法主观主义立场。刑法主观主义不仅仅重视刑罚个别化,重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同时也注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危险状态,因为这是判定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基础性的法律事实。在量刑过程中自然要考虑到被害人的反应、案件的社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这应作为个案酌定量刑的重要因素,由此而产生的刑罚个别化的量刑结果既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抚慰了社会情绪,量刑才能是公正的。
(二)完善刑事立法及其司法解释
当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定罪与量刑出现问题与刑事立法对这方面相关规定不细致、不到位有关。为此,我们刑事立法要尽快对法条中明显矛盾或不合理的条款进行清理与修正,对“两高”规定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修改;在立法时应尽量少用模糊用语,即使使用了模糊用语的地方,也要阐释具体、清楚,对分则中具体的量刑情节及量刑幅度要尽可能细化;对于自首、缓刑、从轻与从重等适用条件要明确限定;最高司法机关要对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界定,比如杭州飙车案中对飙车行为危险的界定。今年年初最高法、最高检颁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职务犯罪认定自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三)建立常见犯罪类型的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与非常见犯罪类型的判例指导制度
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办理的案件有70%左右都是日常常见犯罪类型,对此,最高法和最高检应进行调研,在刑法规定的定罪量刑幅度范围内作进一步细化,从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我国非判例法国家,之前的判例对法官裁判无约束力,但用判例来指导法官的裁判活动还是可行的。我们应借鉴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由最高法对生效判决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收集和公布,并推广实行,法官在对类似案件进行裁判时,要借鉴或参照判例来定罪量刑,避免和减少同类案件出现多种裁判结果。比如像许霆案这种新型的案例,最高法就应该将其作为非常见的指导案例进行推广。
(四)统一打击犯罪尺度,树立正确、统一的量刑观
打击犯罪不能出现多重标准,不能有“杀一儆百”的做法,不能等到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才开始严格司法,否则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平等。在司法实践中常有以此轻罪代替彼重罪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现象发生,如杭州飙车案中以交通肇事代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以嫖宿幼女罪代替强奸罪,这反映出侦查、公诉与审判部门对定罪量刑标准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案件在侦查终结、起诉、判决时出现定罪量刑的混乱。另外量刑思想在司法实践中轻刑化的趋势很明显,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适用缓刑的比率有上升苗头,如一些经济犯罪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缴纳非法所得、罚金就适用缓刑或不起诉。轻刑化并非都是错误的,但应建立在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否则会出现打击犯罪尺度不统一的现象。
(五)掌握科学的量刑方法
我国大多数法官还是采用综合估量式的经验型量刑法,也就是说法官在定罪后,在没有明确、稳定规则指导的情形下,凭其经验来决定其认为最适当的刑罚,这种凭经验量刑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对此,我们可以先将案件中从重和从轻情节予以排除,确立犯罪行为应受刑罚的一个量刑基点,量刑基准的确定以法定刑的中段或结合点为界。之后,再综合考虑各种从重、从轻等量刑要素,明确这些量刑情节的轻重幅度。比如从重情节与从轻情节同时出现,应分别计量后,根据案情冲减后最终量刑;数个从重情节同时出现,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应超出该法定刑上限;数个从轻情节同时出现,若其中无法定减轻情节,一般也不得减轻处罚。这样经过必要的调整,从而最后来决定宣告刑。
(六)量刑公正的程序性保障
为谋求量刑公正的程序性保障,目前有学者提出在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离,扩大被告人辩护的机会,提高被告人辩护的针对性,才能实现量刑公正。目前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立法、司法现状及司法适用传统和惯性,否定此观点并不等同于否定量刑程序的重要性,科学的诉讼程序设计和保障会提高定罪的质量、量刑的公正。结合我国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结合的诉讼程序特点,应倡导诉讼当事人和各方诉讼参与人要认真对待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拓展量刑阶段的辩护空间,同时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既作为一种权力也应作为一种法律监督的职责加以规定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