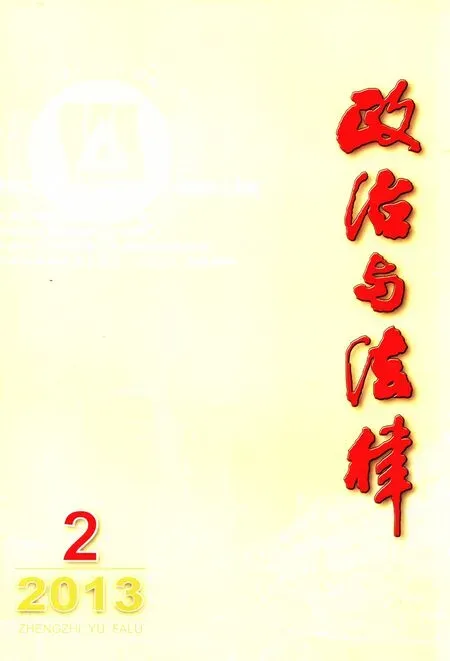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2013-01-30袁达松卢伊丽
袁达松 卢伊丽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袁达松 卢伊丽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类特殊的金融机构,其发生危机或无序倒闭将会对金融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破坏。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存在引发负外部性、溢出效应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对它的有效监管有赖于建立一套特殊的监管法律机制。从目前情况来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法律监管的重难点,体现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监管主体、监管规则以及监管合作上。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应根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结合本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推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制的构建。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律;法制构建
一、金融危机引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制反思
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的重创。与以往金融危机不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扮演了主角,是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制造者、传递者和受害者。1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浮出水面。
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成为与影子银行的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并列的国际金融治理最重要的三项议题之一。相比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更为棘手。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各国政府在危机前缺乏有效监管。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包括诸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于一般的金融机构,各国政府尚可从容应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有序清算;但对危机之中陷入困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各国政府无不应对乏策,最终只能诉诸政府救助。从美国到英国再到德国、法国乃至其它诸多西欧国家,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数额庞大的救助计划连续推出。
以作为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和重灾区的美国为例,2008年9月其放任雷曼兄弟破产,立即引发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为挽救颓势,不得不采取史无前例的救助计划,不遗余力地对其他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展开救助。2008年9月,美国财政部向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提供多达2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与9家主要银行(美国银行、美林公司、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道富银行和富国银行)签订协议,陆续注资1250亿美元;2009年1月,美国财政部再次向花旗集团注资2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联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宣布向美国银行注资200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为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超过4000亿美元的资产提供亏损担保。除此之外,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自2008年9月起先后三次对美国国际集团(AIG)施以援手,救助金额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23亿美元。2
与救助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的其它诸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大量的中小银行,并未获得政府的有力救助,最终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从2007年到2011年8月,美国共有402家银行倒闭。资料显示,本轮金融危机中倒闭的402家银行大多为资产规模10亿美元以下的中小银行,占倒闭银行总数的81.84,其中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80家,占倒闭总数的19.90;相反的资产规模大于1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仅为20家,占比4.98,且有11家受到政府救助。3
美国政府有选择性地救助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但同时放任其他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其原因在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监管法律所能处置的范围,它们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其无序破产将对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为此,各国政府不得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实施一系列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政府的及时介入,确实给了诸多大型金融机构以重获新生的机会,这也有利于尽快稳定金融市场,恢复金融体系秩序。但政府耗费纳税人巨额的资金去拯救那些冒险的金融机构,令本已沉重的财政支出预算负担进一步加重,更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乃至愤怒。
危机过后,国际社会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开始努力探索新的金融业监管与危机应对制度,意图在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带来的威胁的同时,减少或者避免政府救助。从此次金融危机吸取教训,构建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成为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法制变革的重要内容。
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法律界定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雷曼兄弟以及其他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随后各国政府在争议声中对陷入困境的其它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救助。在反思此次金融危机以及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国际社会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概念来称呼这些大型金融机构。
尽管人们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已有较多的研究与讨论,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并未形成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正式及统一的定义,事实上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本身的复杂性,也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义。
美国作为最早在国内立法中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与处置的国家,在其2010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中避免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直接作出定义,甚至都没有使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用语,而是笼统地将两类金融机构——合并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认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即FSOC认定的其重大财务困境或其性质、经营范围、规模、集中度、关联性或者业务活动的交叉性可能会给美国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质上归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适用特殊的监管和处置规则。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其发布的《处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措施》报告中,使用“由于规模、复杂度和系统关联性,其发生危机或无序倒闭将会对更广范围的金融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破坏的金融机构”来指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4目前,FSB的定义得到广泛使用。
从监管立法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类特殊的被监管对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可被界定为由相关监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标准而认定的特殊金融机构。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概念。
一方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本质上仍是金融机构。虽然被冠之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称谓,但其基本属性仍旧是金融机构,并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乃至影子银行等形式呈现。因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受到现有的相关金融监管法律的规管。根据其表现形式的不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受到不同类型的金融法律制度的规管:系统重要性银行,受到适用于银行的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系统重要性证券公司,则受到适用于证券公司的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则受到适用于保险公司的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当然,如果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影子银行的形式呈现,则可能游离于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之外,不受或只受到较少的监管。
另一方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别于一般的金融机构,是一类特殊的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性体现在,其身份必须经相关监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标准而予以认定:
首先,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系统重要性标准。理论上而言,任何金融机构都潜在地具备某种程度的系统重要性。5但是,只有当这种系统重要性达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标准之时,该金融机构才可能被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美国在《多德—弗兰克法》中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加以区分:对于银行控股公司,以规模大小为标准,判定合并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列出了包括杠杆程度、可替代性、性质、范围、规模、集中度、关联性以及业务活动的交叉性等在内的11项因素,作为评估系统重要性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09年10月共同发布的《金融机构、市场及工具的系统重要性评估指引:初步考虑》提出以规模(size)、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和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作为系统重要性的三个关键评估标准。6目前,规模、可替代性和关联性成为国际社会评估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最为通行的标准。
其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必须由相关监管部门予以特别认定。监管部门作出的认定,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一旦获得确认,被确认的金融机构将会受到特殊对待——适用特殊的监管法律制度。对于那些未被监管部门认定的金融机构,尽管其在事实上可能也具备系统重要性,但是其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而不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制框架范围内进行特殊管理。当然,监管部门的认定具有时效性,只在一定期限内有效。监管部门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名单,需要定期复审及更新,以反映金融机构发展的最新状况。此外,为规范和限制监管部门的裁量权,监管部门必须适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系统重要性评估标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认定。
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监管法制需求
作为一类特殊的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引发的巨大风险是一般性的金融监管法律所无法有效应对和处置的,因此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制应当有别于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制。
一方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存在负外部性(NegativeExternalities)。巴塞尔委员会(BCBS)认为,负外部性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本质特征,因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倒闭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给其他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不利影响。7不仅如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还会引发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或倒闭不仅会在金融系统内部产生动荡,其威力还会波及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冲击。这一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会“通过对其它商品和服务的供求的影响体现出来,且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逐渐体现的”8。
另一方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容易引发道德风险(MoralHazard)。基于其自身的特殊地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时,往往会获得政府救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政府的救助或对政府救助的预期,直接刺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引发其道德风险(即市场参与者因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而采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9),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甚至会因此出现逆向选择行为,即热衷于从事高风险的经营业务,成为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偏好者;另一方面,政府救助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其他利害关系方(例如债权人)形成激励,导致其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视为政府庇护下的“永不沉没的金融航母”,放松或忽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高风险行为的外部约束,从而市场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和自我纠正机制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言将在一定程度上失效,10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冒风险的冲动。从长远来看,伴随政府救助而来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冒风险活动的冲动及其外部约束的降低,客观上将导致其从事更多冒风险的活动,由此加剧了其自身的脆弱性,增加了其在面临危机之时倒闭的可能性。
伴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来的上述风险和问题,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之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对金融业监管的重点一直是微观审慎监管,即侧重于对单个机构风险的监管,努力防止和避免单家机构因为经营不慎、严重违规和过度承担风险而倒闭。微观审慎监管政策认为,如果单家金融机构实现了稳健经营,那么,作为所有金融机构集合的金融体系就同样应该是稳定的,而忽略了当所有金融机构同时从事诸如抛售问题资产、信用标准紧缩等行为时,一家机构的行为就可以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同时,微观审慎监管政策也没有意识到,一家金融机构会对其他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构成威胁。11因此,微观审慎监管,无法充分回应和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引发的宏观层面和意义上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在微观审慎监管之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一般金融机构受到几乎相同程度的监管,其因此而获得的“监管红利”使其经营更具风险性,增加了其遭遇危机或倒闭的可能;另一方面,面对陷入困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之下,政府相应的应对机制和管理工具的缺失使得其只能在承受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的巨大冲击和承受政府救助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两者均将使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纳入宏观审慎监管范畴,构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别监管法律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四、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制的重难点问题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监管,是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后才逐渐为国际社会所重视。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了诸多探索和尝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方面,包括我国在内,国际社会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重难点问题。
首先,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审慎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的基础。早在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即提出,评估单家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应同时考虑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与规模、可替代性有关,间接影响取决于关联性。11在此基础之上,相关国际组织根据不同类型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出了不同的认定标准。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规模、关联性和可替代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增加全球(跨境)活动和复杂性这两项标准,作为认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标准。12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则在规模、关联性、可替代性和全球(跨境)活动的基础之上,根据保险行业的特点,加入“非传统与非保险活动”(Non-traditionaland non-insuranceactivities)这一标准,作为认定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人的标准。13不过,在具体监管立法以及实践中,还必须进一步将这些概念性标准,分解成易于判断和识别的定量性标准,使得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客观而公正,不枉不纵。
其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主体的确定问题。确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主体,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首要环节,也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律应解决的重要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其有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措施建议的报告中,首先就要求设立监管机构,并且有足够的专家资源、权力和独立性,以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其依法行使监管职责的行为应获得法律的豁免保护,相应的权力和合作机制应当明晰或者有领导机构予以协调。14就此,从目前国际社会的立法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设置专门部门的方式,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例如,美国在《多德—弗兰克法》中规定,除了合并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外,其他非银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都由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负责认定,同时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获得授权,协调和监督其他监管机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下专门设有一个特别监管部门,来监管瑞银集团(UBS)和瑞士信贷集团(CreditSuisse)这两大巨头。15总之,集中监管资源和监管力量以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再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相关监管法律规则。基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的特点,要有效控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有赖于创新监管方法,构建一系列特别的监管法律规则。为此,国际社会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第一,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损失吸收能力,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抵御危机的能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必须执行更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和具备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中,就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需要满足附加资本要求。第二,改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损失分担机制,减少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的诱因。基于对获得政府救助的预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良好的诱因去从事高风险活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将过度承担风险所获得的收益私有化,而将其所造成的损失社会化,在经济繁荣时期,大肆承担风险所获得的收入由其自己享有,而在濒临倒闭或倒闭时,却需要花费纳税人的钱财救助,这一机制招致广泛的批评。16为此,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建议,监管体系的改革在降低由纳税人承担损失风险的同时,也必须探讨使股东、无担保和未保险债权人按照优先次序吸收损失的途径,以减少由纳税人承担风险的情况,同时迫使债权人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进行监督,从而强化市场纪律。17第三,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危机处置机制。考虑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无序倒闭的重大负面影响,构建特殊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危机处置机制,可以在其陷入困境时能够得以恢复或者有序地退出市场而不至于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目前,国际社会对于这种特殊的危机处置机制的探索,主要体现在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向监管机构提交恢复和处置计划(recoveryandresolutionplans,RRPs)。恢复计划旨在通过业务剥离、出售资产、筹集新资本、改善治理结构等方式恢复其资本、流动性和经营状况,以阻止破产的风险;处置计划则是为了建立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减轻纳税人的负担。18
最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问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涉及金融体系跨境、跨业的多种机构、产品、市场和基础设施的监管,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仅仅依靠单一行业或单一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所获取的信息和实施的监管行为,远不能满足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需求,需要国内和国际监管机构密切合作。19从监管合作角度而言,应当通过相关的立法,给予相关的监管机构明确的授权,以有效地展开国内监管合作以及国际监管合作。
五、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制的构建
虽然本轮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相对较小,但金融危机凸显出来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漏洞,同样值得我国重视。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法律尚未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作出充分回应,20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引发的种种风险在现有的监管法律体系之下难免得不到有效处置。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在2012年11月2日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2年第三季度)》中,在做出下一步货币政策部署时,明确提出要“研究提出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政策措施”。21
我国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在借鉴国际社会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以及金融业内的不同部门的各自特点,制定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就此,一方面,我国应当吸收国际社会的研究成果,将规模、可替代性和关联性三个方面的内容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之中,因为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核心特征,同样适用于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另一方面,鉴于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尚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技术和手段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业务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监管部门受到较大的限制和制约,因此应考虑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这一现实情况,将复杂性这一要素纳入认定标准之中,以实现对这类金融机构的专门、有效的监管;此外,根据具体行业的不同,还应考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进行一定的调整,例如,对于保险行业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考虑将“非传统与非保险活动”这一因素纳入,因为这一因素最可能引发保险机构的风险。根据媒体报道,银监会就此已经采取了一定的行动:银监会于2011年年末向商业银行下发了关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划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拟通过“规模、关联度、不可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复杂性”四个指标衡量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每个指标占据25的权重。22下一步,我国应进一步推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标准出台的进程。
其次,立法授予相关部门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权利。在我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是宏观金融风险的监管和调控者。此外,2008年7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83号)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其中包括“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负责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鉴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主要引发的也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风险,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之下,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去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相比之下,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主要着眼于微观监管,如由其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先天性的权力和资源的欠缺),因此,可以考虑立法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直接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内设机构的分工,金融稳定局的职责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任务密切相关,23因此具体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的金融稳定局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再次,由相关监管部门逐步起草和完善相应的监管法规,从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损失吸收能力、改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损失分担机制以及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危机处置机制这三个角度入手,构筑严密的金融监管网,以实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的有序处置。具体而言,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授权,制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如上基本内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此基础之上,包括证监会、银监会以及保监会在内的微观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各自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规则,进一步落实上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内容。
最后,在监管合作方面,应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国内以及国际监管合作。就国内监管合作而言,在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之下,为实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的有效监管,在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层面的统筹监管的同时,还必须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权的行使提供协助,包括对各自领域的金融机构实施微观审慎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从国际监管合作来看,可考虑立法授权前述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的金融稳定局统一负责相关的国际监管合作,包括由其负责参与有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传递相关数据和信息以及协调国内监管法律使之与国际标准和规则保持一致。
注:
1郑联盛:《大而不倒、系统重要性与金融宏观审慎管理》(2011年10月25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info/content.asp?infoId=5366。
2SeeFinancialCrisisInquiryCommission,GovernmentalRescueof“Too-Big-To-Fail”Financial Institutions,PreliminaryStaffReport,August31,2010,availableathttp://fcic-static.law. stanford.edu/cdn_media/fcic-reports/2010-0831-Governmental-Rescues.pdf.
3王去非、应千凡、焦琦斌、易振华:《美国中小银行“倒闭潮”的回顾与启示》,《银行家》2012年第1期。
4SeeFSB,PolicyMeasurestoAddress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November4, 2011),availableat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11104bb.pdf.
5、6、11SeeIMF,BISandFSB,GuidancetoAssesstheSystemicImportanceofFinancialInstitutions, MarketsandInstruments:InitialConsiderations,October28,2009,availableat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091107c.pdf.
7李文泓,吴祖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目标和政策框架》,《中国金融》2011年第3期。
8陈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的构建》,《西部金融》2012年第1期。
9道德风险是对一种由保险而产生的动机的描述,即保险引导了那些受保人去承担比他们没有受保时更大的风险,因为这种风险的负面结果是由保险人来承担。See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ReformingFederalDepositInsurance,September1990,p.163.
10张显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含义及其风险防范》,《金融时报》2011年1月31日第011版。
11SeeLuisI.JácomeandErlendW.Nier,Macro-prudentialPolicy:ProtectingtheWhole,availableat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basics/macropru.htm.
12SeeBCBS,GlobalSystemicallyImportantBanks:AssessmentMethodologyandtheAdditionalLoss AbsorbencyRequirement,November2011,availableatwww.bis.org/publ/bcbs207.htm.
13SeeIAIS,GlobalSystematicallyImportantInsurers:ProposedAssessmentMethodology(Public ConsultationDocument),May31,2012,availableathttp://www.iaisweb.org/view/element_href. cfm?src=1/15384.pdf.
14SeeFSB,ReducingtheMoralHazardPosedby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 October20,2010,availableat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01111a.pdf.
15孙芙蓉:《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访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首席执行长帕特里克·拉夫劳伯》,载《中国金融》2011年第8期。
16、19刘福毅、邓大海:《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趋势浅析》,《金融发展研究》2012年第3期。
17SeeFSB,EffectiveResolutionof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RecommendationsandTimelines(ConsultativeDocument),July19,2011,availableat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10719.pdf.
18管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武汉金融》2012年第6期。
20虽然银监会陆续发布过相关文件(例如《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1]44号)、《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以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予以规定,但是这些规定相对粗疏,所适用的范围也非常有限。我国尚未出台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系统性的法律制度设计。
21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2年第三季度)》(2012年11月2日),载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2/20121102180612519935265/20121102180612519935265_.html。
22由曦:《银监会拟框定四大指标筛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载一财网(第一财经日报):http://www.yicai.com/news/2012/01/1323009.html。
23根据2008年7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83号),金融稳定局的职责为:综合分析和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评估重大金融并购活动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承担会同有关方面研究拟订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的工作;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承办涉及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的金融企业重组方案的论证和审查工作;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或金融重组有关的资产;承担对因化解金融风险而使中央银行资金机构的行为的检查监督工作,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或机构重组等工作。
(责任编辑:)
A
1005-9512(2013)02-
袁达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卢伊丽,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