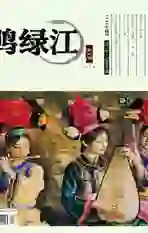孝心不能等待(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之九)
2012-12-31何庆良
鸭绿江 2012年9期
2007.6.6 周三 重庆
妈妈与厨房
“民以食为天”,可见一日三餐对人是多么重要。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可见操持一家人的生计是多么不容易。
妈妈的一生差不多都在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养家糊口用尽了她毕生的精力。厨房是妈妈为这个家贡献最多的地方。
作为家庭主妇,任何一个有家的女人都会与之打交道,都听过锅碗瓢盆的交响曲。
厨房,是妈妈50多年来天天工作的地方,是她为一家老小最操心的地方。经历过困难生活年代的妈妈,为了一家人能吃饱吃好,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妈妈是全家人中吃剩饭剩菜最多的人。
她曾经说过,六二年困难时期,她就发过誓,将来有饭吃的时候,绝不浪费一颗粮食。过怕了苦日子的妈妈到了丰衣足食的晚年,依然保持着节俭的本色。我们经常为她吃剩饭的事和她理论。老太太倔强得很,任凭儿女们说破了天,依然我行我素。节俭是她人生的写照。
在妈妈的大半生中,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几乎都是细水长流,很少让她不用算计着过日子。
从打记事起,妈妈系着围裙,烧火做饭的形象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那是农村的大锅灶。灶堂前,火堂里柴草冒出的青烟和锅里冒出的饭菜香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农家一日三餐特有的乡土味道。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做饭就象给民工做大灶一样,全然没有烹调技术可言。那年月能保证全家人都按时吃上饭,就是妈妈一个人的本事了。
后来,我们一家人进了城市。先是借住别人的一间半房,一间是住房,半间是厨房。对面的邻居也是一样的面积,只是他们条件更差些。全家八口人,大约只有一间十二平方米左右屋子。
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能居住的容积率,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屋檐下,竟然居住了十四口人。两家的厨房紧挨着,主妇做饭时都要互相让着,否则就要发生肢体冲撞。
记忆中,这是全家人生活中最艰难的日子。六十年代因难时期,狭小的厨房,上顿不接下顿的主副食供应。妈妈都是每天掐着指头过日子。
地上长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想方设法地吃。
还记得,那是最困难的六二年,为了接济口粮的不足,邻居孙大伯给了妈妈一张酿造厂的酒糟票。这张票可以购买的是高梁酿酒后留下的糟糠。这根本不是能吃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可以救命的口粮。
按照厂里门卫的规定,一张票只能放行一口袋。孙伯伯出个主意说,一张票限量一袋,但袋子大小没人计较,可以把两条麻袋拼接在一起。
于是,妈妈和爸爸动手剪开一条麻袋的一端,与另一条麻袋缝在一起,制作了一条迄今为止都忘不了特大号麻袋。在娃娃的眼里,那条麻袋就像巨人一样。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妈妈推着车子进门时,门口太窄,麻袋是在门外卸下来的。
妈妈把麻袋里的高粮糠一盆盆地掏出来,晾晒在塑料布上。连续几天,妈妈在太阳下守着这堆摊开的高粮糠,就像守望着一个希望般的喜悦。
一大堆高粮糠最终变成了盘中餐,而那条作出了贡献的巨大麻袋再也没有派上用场。
后来,几经搬家迁居,居住的条件越来越好。厨房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旧式的风箱改为蜂窝煤,再由煤气罐改为天然气,甚至也用上电烤箱、电磁炉、微波炉、抽油烟机、电冰箱、饮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