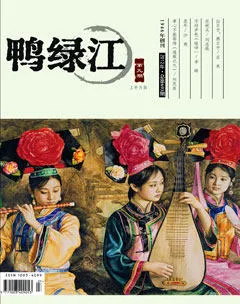是年
2012-12-31沙爽
鸭绿江 2012年9期
沙爽,女,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品见诸《诗刊》《散文》《钟山》《天涯》《山花》等,文章多次被转载及收入多种年度选本。出版有散文集《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光》。其中,散文集《手语》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签约作家。曾获辽宁文学奖青年作家奖、辽宁文学奖散文奖等。
是年春
这个春天突然到来的时候,我像一个厄运缠身的人,一时间难以相信这自天而降的好运。但是街两旁的柳树真的长出了叶子,并且打定主意一直绿下去,这让我慢慢放下了心。这天傍晚我下楼吃饭,猛一抬眼,正望见不远处的半空里盛开着的一团淡粉色烟霞。这一树迟开的杏花一时间让我感动万分。没错,就在那儿,就在那半空里,在不久以前的同一个时辰,我以为我看见了一个人或者一整个人世最黯淡的命运。
那时节是三月小阳春,但是真冷,因为雪断断续续地下着。我站在书房的窗前往外看,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怪异的雪,它下得又寂静又绵密,使大地与楼群之间呈现出微小的倾斜。我回到电脑前,看到三十里外的芷正在QQ上说:“这雪下得怪怪的。”我说:“是呀。”我想我们两个人不像在对话,更像是自言自语。后来雪停了,天空依然阴沉。晚间6时15分左右,我下楼,看见西边的天空出现一抹诡异的玫瑰红。我以为是错觉;但前方的两幢居民楼高处的窗子又分明被染成了淡红色,而与此对应的,是更多的窗玻璃反射着的青灰色天空……距离我几米远,一根晾衣绳打斜刺里伸出来,把我的视野陡然切割成上下两半。那是一根铁制的晾衣绳,一小坨冰溜子正从上面瑟瑟缩缩地披垂下来。——直到今天,我仍无法描绘出我内心的惊惧和震动,连同那一连串噼里啪啦滚过心头的小闪电。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末日将临的悲凉预感。——这或许近乎荒诞可笑的心灵体验,但是它确切无疑地降落在我身上了。我疑心是因为这段时间里我看了太多关于末日和灾难的电影,但是我没有办法抵御它们,一如我没有办法阻止毫无来由的洪水在我的梦境里一再呼啸和蔓延。听了我的叙述,芷说:“不会是海啸吧?——如果真有那一天,你提前来我这里。”我不由得失笑起来:“要真是海啸的话,你那里也一样危险呀。”
又一天晚上,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不大不小的雨,芷匆匆忙忙地通知我:今晚可能发生地震,不知是真是假,小心为上。我问:消息哪来的?芷说,是她婆婆的一个朋友,女儿住在黄家峪。傍晚五点多钟,村里的大喇叭连续喊了两遍,让大家注意防震。女儿赶紧打电话告诉住在县城里的母亲,于是母亲通知了几个老友。芷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的时候,她六岁的儿子正在身边,一听说要地震,小家伙登时眼泪汪汪。虽然出生以来从未亲历过地震场面,但两年来席卷整个地球的地震恐慌,让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孩子熟谙此中的惨痛和危险。芷一面安抚敏感的儿子,一面给地震局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朋友说:“没听说呀!”想了想又说,“还是小心点儿好。”芷理解朋友的苦衷,她转而叮嘱我:“今晚睡觉别脱衣服了吧。”下线之前,她祈祷似的说了一句:“但愿到了明天,我们还能像今晚这样聊天。”正是这句话利刃一样劈中了我的心。我谨慎地通知了几家亲友,把现金、存折、银行卡和保存有作品的U盘装进背包,又在背包里放进两瓶矿泉水、三只苹果、两包饼干、一支手电筒和一把折叠伞。我试了试背包的重量,把它放在床头伸手就能抓到的地方。然后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把笔记本装回电脑包,靠在结实的写字台旁边。把平底鞋端端正正地摆在门前,以保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套到脚上。然后我下楼给儿子送豆浆,仔细观察了一番家里的三只狗狗,尤其认真地看了看它们的眼睛。狗狗们从不说谎,它们的眼神明亮天真,快乐地向我摆摆尾巴,露出狗类真诚的愉快笑脸。其中的两只狗狗照旧要用湿漉漉的鼻子亲亲我的小腿。我说:“好啦,好啦。”它们便跑回各自的窝,准备安寝。
我回到楼上,给芷发短信,告诉她我家的狗狗们安静正常,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让她别太担心。芷没有回复,估计已关机入睡。我换了睡衣,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自然醒。
然后小城终于等来了南风。南风它也许不知道,纷纷攘攘的人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把呢大衣收进柜子里,穿着一件紫风衣走来走去。我在单位门前遇见了几棵榆树,这才想起几年来它们一直站在这里。每年春天,它们都把圆滚滚的小榆钱藏在心形的叶子下面,看起来充实而富裕。我踮起脚,犹犹豫豫地摘了两枚榆钱放到嘴里。我犹豫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太多成年人自我否定的苦恼经验——那些早年被我列为美味的东西,比如槐花啦,羊奶子菜啦,事实证明我的大脑储存了有关它们的错误信息。但是这一次,我吃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些榆钱还像三十年前一样清香甘美。也许这甘美与这个迟来的春天大有干系,与我在这个春天的梦境也有干系,或者干脆是许许多多的事情纠缠在了一起,让我分不清传说和真实。又或者,以上这些猜测都是错的——从古至今,榆钱一直保持着它原来的滋味。
这个春天雨水丰沛。在细雨刷新过的大街上,我被街对面一棵高高的大杨树迷得迈不开双腿。它可真美。在雨中,这些新生的叶子的颜色多么让人惊羡,让人从沉重的胸腔里面扑闪出一颗爱慕的心。现在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它苍黑的枝干,它柔软湿亮的无数枚叶片。它让人哽咽,像一个人面对疾掠而去的无数个春天。
会走动的树
搬迁工作进行得很快。从冬末到春初,只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一千六百户人家已经迁走了大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试探着去找婆婆商量。
我婆婆住的是一楼,窗子底下开辟了一个小花坛,种了些细花碎草,还有些黄瓜芸豆之类的蔬菜。应该说,我的生来就是城里人的婆婆并没有多少种菜经验,有一年她种的玉米连一只成型的棒子也未能吐出来。她当然见识过我母亲家院子里那棵李子树,但她并不像我这样了解它的诸般好处。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好处仔细描述给她听。我不需要动用夸张拟人之类的修辞手段,因为这世上有些事物当真天生完美,人类能在转述中努力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就已经足够。有一瞬间,我婆婆显然有些心动;但是她马上想到了一个实际问题,语气便坚决起来。我婆婆忧虑的是:这院子里有许多淘气的小孩,等不到李子成熟,就会被他们祸害个一干二净。我说,瞧您说的,哪能呢。我的语调软塌塌的,一听就知道泄了底气。我并不了解那些被我婆婆指为淘气包的小孩子,但是我了解这棵李子树。它哪里懂得韬光养晦的人世哲学,哪里知道提前暴露的美貌更易于招致灾祸。这些将熟未熟的李子早早地出落成红粉佳人,那种华贵而闪亮的绛红色,温润地裹住它们饱满欲滴的身子,只在背面的浅沟处透露一抹青涩的翠绿。当这抹翠绿悄悄地转化为金黄,果肉的甜香气味便开始四下里漫溢。但只有真正品尝过这果子的人,才明白它骄傲的外表下面有一颗谦逊的心——它的果肉如此丰美,果核却小巧得惊人。别说那些热爱猎奇的孩子了,就是喜欢假装矜持的大人们,也禁不住在它面前猛咽口水。我用什么才能挡住那些向它伸过来的未知的手呢——再说那样似乎也有违它的本意。
这棵慷慨的李子树,我不得不放弃了试图挽留它的小小努力。过了没多久,我母亲代它找到了合适的新主人。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我只看到一小块微凹的空旷。它像一个离家远嫁的女儿,离开时并没有带走多少嫁妆。我忽然疑心它提前预知了这场大迁移的命运,因而早早地陷进了悲伤——早在去年夏天,它对开花结果这件事的热情远远逊于往年。对此我母亲的解释是:所有的果树都有大小年之分,如果有两三年结果过丰,那么必将在其后的一二年里产量锐减。虽然自小在乡村长大,这样的常识性课程仍让我觉得新鲜。这棵让人没法不心疼的李子树,它被人带走之前已经在我家的院子里开过了花,我不知道这一年它的枝叶间躲藏了多少枚小小的青果,这许多只青青的瞳孔,惊惧地目睹了铁器上闪着寒光的疼。
据说西方有一套植物学理论,说的是移植树木最适宜在冬天进行。在树们睡着了的时候,人为地更改它的住处不会引起太多的慌乱。等它在春天睁开眼睛,呀,世界有些变化,不过这也正常嘛。变的是别人而非它自己,于是它便安安稳稳地一路活下去。
但是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更像一则童话。成人世界的植树节固定在公历四月,北方的土壤从冰冻中苏醒,有利于人间进行的表演和挖掘。
那个带走了我的李子树的人,有一个我全然陌生的姓名。这个面目不清的人,带它到达一个我丧失了想象力的院子。这整个悬疑片一样的事件让我忧心:这棵一直娇惯着自己的李子树,它到底有没有充足的力量,来面对与它旁边那棵枣树相似的命运?
与李子树不同,那棵枣树是外来户口。三年前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家里搬迁,这棵树干有碗口粗细的大枣树便移栽进我家的院子里。彼时也是春天,它带来了它刚长到指甲盖大的叶子们。看得出它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撑住了那些叶子上的绿。从春到秋,它努力地让这些绿大了一圈又深了一点,就再也没有力量做其他事情了。它甚至忘记了还有开花这回事儿。我们全家站在屋檐下担忧地望着它,有几次,我听见我母亲自言自语:“这树活了吗?是不是根留得太少了?”
这棵伤了筋动了骨的枣树,经过一个冬天的喘息,在第二年神奇地开出了花,然后把这些花的一部分变成了果子。这棵贪心的树呀,它忘了它的身体有多差,它还想一口气喂大这么多孩子。有一些果子长到一半大,开始纷纷地坠到了地下;另一些坚持着挂在枝头,但是再也没有长大。这棵伤心的枣树,到第三年咬紧牙关,把一半的孩子坚持培养到成年。我摘了两枚枣子放到嘴里,嗯,味道可真不坏。我拍拍它的枝干,它的叶子对我好一阵儿细语喧哗。就在这第四年的春上,它去了另一个地方。
我不知在一棵树的血管里,究竟隐藏着多少面对九死一生的勇气。我不知道树们会不会像人一样,拿自己与命运或者人类赌气。这棵挨过了一场浩劫的枣树,它会不会以永不认输的坚忍,继续挨过第二场甚至第三场拼杀?
在城市里,做一棵树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你不是一棵有身份的公家的树,你可能需要学会到处流浪,学会四海为家。
晚蚕
在梦中写一篇题为《晚蚕》的文章,洋洋洒洒,下笔万言,甚至写到某会议前夕,有人来找我拉选票。醒来后想想,不禁哑然失笑。
拉选票的人其实和蚕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同样是吐丝,但他们更像蜘蛛,张开一面巨大的网,是整个世界皆为我所用的意思。而蚕退守一隅,惯于作茧自缚。
如果必须选择做一只完全变态型昆虫,我更希望自己是蝴蝶。它没有负担,也多数不为他人利用。我有个近乎恶毒的猜想:实质上,多数人并不真正向往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这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梦境,它仿佛来自时光的一小段投影——有几年“十一”长假,我和好友阿芷在大山里度过。那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这个叫“枣木沟”的小小山村,除了家家房前屋后的枣树和漫山遍野的酸枣林,还有美味的榛子和娇艳的山里红,大山深处还隐藏着一片片比酸枣树更蔚为壮观的栎树林。在我的家乡,波罗栎那清香而肥厚的大叶子最多也只能用来代替屉布,蒸蒸馒头和花卷;而在物产丰饶的枣木沟,波罗栎被承包给各户村民,用于养柞蚕。
九月末到十月初,正逢收茧时节。在吐丝之前,每一只蚕都会给自己挑选一只平展的叶片,蚕丝的粘度会使这枚叶片微微卷起来。看上去,宽大的波罗叶就像一只手掌,握住掌心里千丝万缕的秘密。阿芷的父母把这些叶子摘回家,我和阿芷就负责把茧子从叶片里剥出来。
有一年我来得更早一些。时间大约是在初夏,正赶上孵蚁蚕。我和阿芷居住的里间,脚前脚后,都是铺满了蚕纸的匾。本来以为会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场面,但刚出世的蚕宝宝们非常娴静,虽然外形既黑且小像极了蚂蚁,却并不像蚂蚁家族那样集体患有操劳型多动症。我站在那儿看着它们,心里奇怪地溢出温暖。
由茧和蚁蚕,我看见的是一个物种生命里程中的两个端点,却一直无缘得识它精力旺盛的青壮年时代。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阿芷的母亲特意带回了一些还没有来得及结茧的蚕。它们身宽体胖,肤色鲜艳,以草绿色居多,夹杂有鹅黄、纯白、墨绿与微褐,构成世界地图一样的复杂图案。阿芷捉起一条蚕放在我的手背上,最初几秒钟的心理不适过去后,我惊讶地感受到来自一只虫子的信赖和温柔。它薄皮革般的微凉皮肤,依稀渗出丝绸般轻盈的暖意。它懒洋洋地在我的手背上走了几步,并未发觉它的口器下方正铺开一片美味丰沃的蛋白质,丰富的营养含量远远超过它单调的日常食谱。作为贯彻始终的素食者,蚕的口器保持着缄默者强韧的排他性。
当晚,阿芷的母亲为我做了一道当地独有的时令菜:蚕肉炒青椒。在一阵吱啦作响的扑鼻异香里,阿芷说起村子里的一个人,极爱吃这道菜,却偏生对丝胶过敏。每次吃完,必浑身起红疹,呼吸困难,只得送医院急救。但是到了翌年,他还是忍不住要吃,即使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其人其事在整个乡间传为美谈。
在阿芷一家人的殷切注视下,我夹了一筷子这道让人视死如归的美味,只觉得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直到第二年,我才终于适应了这道菜。和许多东西一样,我们必须把它视为生存所需的蛋白质来源,才能克服掉渎神者的心理障碍。蚕体内的丝液遇热后凝结成细小的颗粒,口感柔韧,像某些难以咀嚼和消化的——情感或想念。
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解释:“早蚕”是指春蚕,所以秋蚕亦即“晚蚕”。我猜测,是羞涩的梦境,委婉地吐露了我的焦虑:作为一只晚熟的蚕,它怀抱着有一颗孩童的心脏,却偏偏长了一张和别人一样老成的脸。错过了转瞬即逝的吐丝结茧的最佳节气,它是不是,只能带着被突兀的寒冷凝结住的柔软丝绸,那无限绵长却永远来不及倾吐的梦想和思念……消失于从天而降的第一场霜寒?
责任编辑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