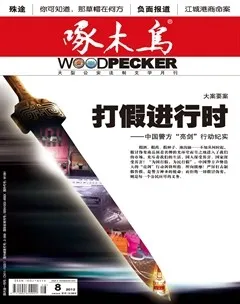遗案处理的几种方式
2012-12-31孙方友
啄木鸟 2012年8期
从颍河镇往北走五里路,有个村落叫王双楼。村西头有个叫王囤的人,两个儿子在外打工挣了钱,要盖一栋小楼,在扒老屋挖地基时,挖出了一罐儿银元。因为是包工队揽的活计,见的人就多。人多嘴杂,消息就传得快,不一会儿,全村人都知晓了。
村东的袁留香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怔了许久,然后才很长地“啊”了一声,像拾起了一个梦幻,对孙子王大全说:“王囤挖出的现大洋可不是无主货,那可是咱家的财宝!”
王大全笑道:“奶奶,你怕不是在做梦吧!”
袁老太太虽然年近九旬,但眼不花耳不聋,除去腰有点儿弯,脑子还好使。她对孙子说:“全儿呀,你不知,那现洋是当年你太爷爷让我亲手埋在家里的,不止这一罐儿,一共埋了三罐儿。闹土改那年,咱家被划为地主,贫农团天天逼我交出浮财,我都撑过去了。你太爷爷被打折了腿,第二年就离开了人世。那时候,王囤他爹王老根是民兵队长,打人特狠,奶奶我胸前这块花疤,就是他王老根用火香烧的!”
王大全此时算听明白了,问袁留香说:“奶奶,你还能记住三个罐儿里共有多少银元吗?”
袁老太太问道:“你先说说王囤挖出的这罐儿有多少块?”
王大全说:“听人说,是三百三十三块!”
袁老太太想了想说:“这就对了,还有一大罐儿和一小罐儿他没挖出!”
王大全此时已经显得很激动,双目熠熠闪光,急急地问:“那两罐儿里有多少你还记得吗?”
袁老太太说:“我是用命换来的,咋能忘了!大罐儿里是四百块,另有三块银元宝——是四十八两的大宝!小罐儿里共三百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
王大全经常去城里打工,知道眼下银元的价格已升到近二百元一块,并且有不少稀有银币颇具收藏价值,价格已不可估。三罐子银元加起来一千多块,那就是二十多万人民币,别说盖三层小楼,盖五层也够用。他高兴得一蹦老高,对奶奶说:“奶奶,真没想到老太爷还给我留下这份财产!”说完就要去村西头王囤家讨宝,可还没走出大门,又犯了愁。心想平白无故去要宝,那王囤会给吗?便问奶奶说:“如果人家不承认是咱家的咋办?”
袁留香说:“土改以前,那是咱们家的老宅。咱村为啥叫王双楼,就是以前咱家老辈子留下的两座土楼命的名,这十里八村的人哪个不晓得?王囤家分的只是咱们马房!”
王大全说:“是咱家的老宅不假,可人家完全可以说老宅是你们的没错,可谁能证明这银元也是你们家的!说不准还是王囤他爹王老根埋的呢!”
袁老太太听了这话,怔了一下,许久没说话。急得王大全直走柳,说:“奶奶,如果咱没证据,不但是猫咬尿泡瞎喜欢一场,怕是还会给村人留下笑柄!”
直到这时候,袁留香才像是从梦中醒来,望了望孙子说:“这个你甭怕!他王囤只挖出了一个,还有另两个,只有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埋着。”
王大全一听这话,转愁为喜,高兴地说:“这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嘛!你若不说出,我咋会知道!我看这事儿你老必得亲自出马,让众人看看,咱可不是无故讨宝!”王大全说完,就搀着奶奶直去了王囤家。
那时候,王囤家还有不少人在瞧稀奇。皆夸王囤有福气,盖楼挖出了地财。还有人说:“再找找,再找找,说不定不止这一罐儿哩!”
恰巧这时,王大全搀着奶奶袁留香赶到,当着众人宣布道:“当然不止这一罐儿!我奶奶说一共三罐儿,是当年我太爷爷王耀先让我奶奶埋的!”
众人一听话音,知道来者不善,大有半路夺宝之意,反应不一。刚才有点儿嫉妒王囤发外财的人现在开始幸灾乐祸。当然,更多的人以为王大全是见财起心,想分宝哩。更惊讶的是王囤,三百块大洋扒出的那会儿,他简直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冷静下来,就产生了可能是老地主家当年偷偷埋下的猜测。因为他爹王老根活着时常给他讲当年闹土改的事,说地主老财们如何狡猾,把浮财藏起来,怎么拷打都不愿交出,所以当年分房时,自己才执意要这片地主家的马房,说不准哪一天真能挖出他们的浮财呢!现在土改已过去近六十年,当年地主家的浮财果真就出土了!他望着长满绿毛的银元,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见了意外财宝,担心的是老地主家的人会不会来凑热闹——正担心着,王大全和袁留香就来了。也说不清为什么,王囤一见王大全和他奶奶袁留香来了,心里就有点儿虚。尤其是听到王大全宣称还有两罐儿未挖出,便知道这麻烦事儿真的来了。但既然事已至此,自己并不见得理短,总不能将到手的宝物拱手让人,说白了,就是要争一争。想到此,王囤便鼓了鼓勇气对王大全说:“大全侄子,你说什么?这罐儿银元是你们家的?”
王大全说:“没错!我奶奶说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时,我太爷爷让她埋下的!”
王囤此时心中稳定了不少,扫了众人一眼,见众人的目光很复杂,便猜出这人群中有得意者有妒嫉者也有看笑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突然得了一笔外财,有点儿眼红。现在讨钱的来了,他们在心中也很明白这银元十有八九是王大全家的,但也不太甘心让老地主家的后代如此轻易地发这笔横财。他们的心情肯定是两家都得不到为好。两家都得不到的后果要么交国家,要么大伙儿分,但决不能让一个人独吞!王囤越想越觉得应该争一争,就是自己争不到,也要为大伙儿争一争,只有这样,才能顺大伙儿之心,让他们倾向自己。王囤的心一顺,就觉得理直气壮,先“咳”了一声,然后抬高了嗓门儿说道:“大全侄子,你这不是空口说空话吗?银元是在我家宅基地上挖出来的,凭什么说是你太爷爷让你奶奶埋的?若这么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可是更有理由说这是我爹活着时让我娘埋下的!”
王大全一听王囤果然狡辩,笑道:“王囤大叔,没来时我就猜中你有这一招儿,所以我就连老奶奶一起搬来了!”说着,急忙搀过袁留香,“奶奶,你看王囤叔果真不认账,怎么办?你给他说个明白,也趁机让大伙儿听听,咱可不是平白无故来讨宝!”
袁留香拄着拐棍朝前晃了晃,先看了看众乡邻,又看了看王囤,没牙的嘴动了几动,才心平气和地说:“王囤大侄子,如果光凭一句空话,别说你不信,连大伙儿也不会相信!不过话说回来,我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婆婆,是决不会无缘无故来跟你装赖要银元的!要说起这几罐儿现大洋,话就扯远了!土改那阵儿,你爹王老根是民兵队长,为挖浮财,将我公爹的一条腿都打断了,但他到底没说出这笔财!我家是土财主,地不少,粮食也有得吃,就是钱不是太多!实言讲,攒下这几罐儿现大洋是我公爹干半辈子的积蓄,所以他才认死也不愿说出来!你刚才说是我家的有什么记号,我也记不清了。但有一条我记得清,那就是当年我一共埋三罐儿,你挖出的这个罐儿里是三百三十三块,还有一大一小两罐儿没挖出。那大罐儿里是四百块,除此之外,还有三块四十八两重的大元宝!另一罐里是三百块整,一块不多,一块不少。如果我指出地点挖得出来就证明我老婆子没说谎!如果挖出来与我说出的数目不符,那就算我老婆子丢人现眼了!”袁老太太说完,对王大全说,“孙子,找家什,照我指的地方挖!”
王大全闻声精神陡增,顺手操起施工队的铁镐和铁锹,问奶奶说:“奶奶,你说在什么地方吧!”
袁老太太朝四周左左右右地望了望,又闭目回忆了一阵儿,这才从王囤挖出第一个陶罐儿的地方朝前走了几步,然后颤巍巍地朝东迈了两步,说:“这地方儿当年有一棵拴马的老槐树,你朝下挖一挖,挖片儿大一点儿,找找看!六十年了,一场梦似的!”
王大全开始挖,有几个男的急于揭开谜底,也上前帮忙,不一会儿就挖了一个方坑。挖到大约三尺深的时候,果然挖出了一个陶罐儿,打开一看,内里果真有四百块银元和三块四十八两重的大银锭。再细看,罐儿底上还写有毛笔字。墨迹虽有些模糊,但还能看得清,上写“王老耀记”。而王老耀,正是王大全的太爷爷袁留香的老公爹王耀先的雅号。这一下,众人都惊奇得哑了,望望王囤又望了望袁留香,不知如何是好了。袁留香见罐上有字,而且是她公爹的亲笔,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心想老公爹办事真是心细有远见,这一下可算是胜券在握了。为乘胜追击,她又找出另一小罐儿的位置,几个年轻人不一会儿就将那个小陶罐儿也挖了出来。打开一看,不多不少正是三百块大洋;又看了看罐儿底,写的也有字,但写的却不是“王老耀”三个字,而是“民国叁拾捌年春月贰拾伍日置,扣人王中立,叁佰”。
怎么又冒出了一个王中立?
王中立是谁?
众人皆不知,便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袁老太太。袁老太太并不见慌,她先扫了众人一眼,方说道:“当年公爹兄弟三人,早已分家,公爹是老大。老二早年因吸鸦片败了家产无后。这王中立是老三,也就是我的三叔。三叔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王大香,远嫁新疆,至今下落不明。小女儿叫王小香,嫁到咱们的邻村梁营,有一子,叫梁照清。当年公爹老弟兄三人虽然分家,但相互间还常借用东西。我刚才想起来了,上面书有‘王中立’字样的这只陶罐儿,八成是我公爹准备借给三叔的!”
就是说,这三罐儿银元全是她家的。
有凭有据,不但众人没的说,连当事人王囤也找不出想分一杯羹的理由了!王大全此时极其兴奋,先对着众人拱手,然后就要集银元于一堆准备运宝回家。不想这时候,有好事者已从邻村喊来了梁照清。
梁照清已年过花甲,虽然已现老态,但耳目仍清晰。他来到王囤家,一看地上的几罐儿银元,惊得嘴巴张了几张才合拢。他走过去捧起那个小罐,让人念了上面的字,很长地“噢”了一声之后,接着就拾起了脑际间久贮的一片记忆,他说这三百块银元是大外公王耀先借亲外公王中立的。土改前一年,大外公家要买胶轮马车,给亲外公借下了这三百大洋。不想车还没买,土改运动来了。因为两家都是地主,都没了自由,大外公怕此时将钱还给弟弟不合时宜,会给弟弟和自己带来灾祸,所以才将三百银元埋入地下,并写上因由,好让后人偿还。
袁留香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白了梁照清一眼,嘴巴动了好几动斥问道:“你当时才两岁不到,怎么知道这么清?”
梁照清说:“大妗子,这都是我娘活着时告诉我的!”
袁留香说:“要说起这档子事儿,我想起来了,只是和你说的恰恰相反!那年可不是我家要买大车,是你亲外公要买,向我家借钱。只是钱备好了土改也来了,我公爹心想这运动过一阵子就平活了,等平活了再给你亲外公送去,但又怕贫农团搜走了,所以才埋在地下的。”
梁照清说:“大妗子,你这么说就与我娘说的不对口了!俺娘说外公临死时还跟她说过这件事儿,说你大伯借的三百大洋刚刚送去,工作队就进了村,真不知他放起来没有!”
袁留香说:“大外甥,你这话咋说哩?我家又不缺钱,就是买马车也用不着给你外公借呀!大伙儿都看着哩,这明摆着的又是现洋又是大元宝,评评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照清呀,这三罐儿大洋明明都是在我家老宅上挖出来的,你来插这一杆子干个啥?若不是我还活着,怕是这两罐儿大洋难见天日!大全,咱的东西咱拿走,挖了王囤叔家的地咱包赔他十块大洋,王囤你说中不中?”
王囤刚才正无计可施,现在见冒出来个梁照清将清水又搅浑了,又来了精神,他笑了笑对袁留香说:“大婶子,你说你有理,可我咋听着照清表哥说的也有理!再说,你那两罐儿上面都有字为证,我挖出的这一罐儿可没什么记号,凭什么说也是你家的!这事儿若私了,干脆咱们三家一家一罐儿,你要你那个最大的,照清表哥拿走写有他外公名字的那一罐儿,我挖出的那一罐儿归我!你若不同意,那就公了,咱们叫村长过来评评这个理,看村长咋说!”
王大全一听让村长评理,坚决反对,因为村长是王囤的侄子,肯定不会向着他们。
于是他悄悄走近梁照清,小声说:“表叔,你傻呀!这银元不论是你家的我家的,都是咱家的!你如此一整,不是让外人占了便宜!快改口说这三罐儿全是我家的,先把东西弄回去咱再作商量!”
梁照清一听王大全说这话,幡然醒悟,急忙改口道:“大妗子,不论是大外公借我外公的,还是我外公借大外公的,反正都是咱们的,干脆把银元弄回去再说!”
王囤一听两家联合了,很着急,望望这个望望那个,急中生智,面部也严肃起来,放高了声音说:“你们想得轻巧,别忘了,你们可都是地主!这是土改成果,银元是你们的浮财,当初贫农团没挖出来,现在挖出了,权力仍然归农会!大伙儿说对不对?”
众人一听这话,正中下怀,都齐声应和。
有人说差点儿把这茬儿给忘了,在前些年,这可算是反攻倒算哩!有人说,阶级一取消,连地主都想翻天哩!还有人说,当年挖出浮财归贫农团处理,现在还应该交给贫农团!
一说到贫农团,有人就说村里还有三个老贫农团员健在。支书的老爷爷还是当年贫农团团长哩,请他们出来看如何处理不就是了!
这时候,恰巧有人喊来了村长。村长叫王丰收,是王囤大哥的儿子。王囤是老小,所以就守了老宅。王丰收到了现场,先挨个儿看了看三罐儿长着绿毛的银元和银元宝,惊叹一番,又略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才对袁留香和梁照清说:“银元是在这儿挖出的,具体数目大伙儿都知道,为了保护现场,所以要先放在我叔家,少一块由他包赔!因为情况特殊又复杂,村委会要专门为此召开一次会议,等研究好处理方案再作决定!都散了吧!”
众人都散了。
因为是村长说话,袁留香和梁照清也没的说,只是王大全有点儿不放心,一步几回头地望着那三罐儿银元,最后还有点儿不相信地看了村长王丰收一眼。
事实上,王大全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当天夜里,几个老贫农团员集中在王囤家,将一千多块银元作为土改成果全分了。而且还是按当时的政策分的:赤贫五块,雇农四块,贫农三块,下中农一块。贫农团员各加一块,贫农团长加五块。这一下,全村的贫农、下中农都惊喜万分,没想到土改运动过去了六十年,还能享受土改果实!真是让人做梦都不敢想呀!
袁留香听到此消息,一下气病了。
王大全见奶奶病倒,银元被分,也没了主意,便急忙唤回在外打工的哥哥王大中。王大中上过高中,当年差几分没考上大学,后来就去了佛山,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积攒了一些钱财,在家中还盖了小楼。世界经济出现问题之后,他从广东回到了省城,听到消息,急急赶回。他毕竟见过世面,一张诉状将王囤他们告上了法庭。
法庭接到诉状,派一名叫常江的法官前去调查。常法官先到了王大全家,问明了基本情况,又去梁照清家调查了一番,最后才到王囤家,取出三个空陶罐儿,见到一大一小那两只陶罐儿上写的字,知道袁老太所言均为事实,而且有证有据。接着,他又问王囤一一核实了银元数目,发现无差错后,才找到村长王丰收,让他协助办案,负责召集分到银元的人家到村委会开会。人到齐后,王丰收代表村委会讲了几句官话,然后推出常法官。常法官也是按部就班地先说了此行的目的和调查的结果,然后就搬出法律条文,他说针对王双楼出土银元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
常法官开头说的一大溜法律条文名称村人听不大懂,但对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都听得明白。一听说老地主家的财宝还受法律保护,不但王囤想不通,那些刚分到银元的人家也想不通。尤其是活着的几个老贫农团团员,不但不答应退钱,还大喊这个常法官把屁股坐歪了!当初共产党能得江山坐天下,全靠的是穷人。共产党就是俺穷人的党,不信读读党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当年闹土改,我们的老村长被反共暗杀团刀卸八块,全家六口人被残杀四口!再说了,我们斗地主容易吗?当年为挖这王老耀家的浮财,我们每天都陪他们熬夜,下雨下雪还照样跟踪盯梢儿贴墙根儿偷听他们的私房话,但这狡猾的家伙到底没交代!还有那个袁留香,包庇公爹,让她游街示众鞭打棍敲吊梁头,可她仍然顽固不化,还说我们违反了政策!怎么样,现在浮财挖出来了,当年斗她亏不亏?这一千多块大洋不说,谁知他们放的还有什么宝物,说不定还有金砖金条没挖出哩!再说,谁知他们放的有没有变天账!当年的地契什么的始终也没找到,是不是找到地契了你们法院还准备把俺们分的土地还给他们?嗯?
常江见犯了众怒,急忙解释说:“乡亲们,建国初期,咱们国家的法制还不太健全,当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由政策调整,这种政策也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制定的,所以,当时把王老耀家的土地、房产分给村里的贫农、下中农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但别忘了,这涉及到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和政策并不矛盾,它们都是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起着维护国家秩序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有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根据一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政策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较大,其相对稳定性较小。而法律需要的是一定时期的稳定性。说明白一些,就是政策不能替代法律,法律对政策起着制约作用,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大家都知道,如今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各种社会关系均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宪法》及一九八六年颁布的《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公民个人依法享有财产所有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本案的事实有明确的解释,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一通有关法律的解释,庄户人听得似懂非懂,但听到最后还是明白了,就是转了一个大圈,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银元还是应该归袁留香他们所有。几个老贫农团员觉得这事儿让他们想不通,说常法官若是按你所言,如果要是挖出地契来,你们保护谁?
常法官说:“老爷爷,这不矛盾,刚才我说过土地和房屋分给你们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
一个老贫农团员摇了摇头说:“那我再问你,如果这批浮财当时被挖了出来,应该归谁?”
常法官说:“如果当时被挖出来,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归农会,属土改成果。”
那老汉又问:“我再问你,当时王老耀和袁留香私藏财宝对不对?”
常法官想了想说:“按当时的情况,他们是不对的!”
那个老贫农团员一听这话,笑道:“这不就是了!当年他们是错的,现在他们错藏的浮财被我们挖了出来,就还应该算土改成果,俺们按当时的成分和人口将其分了,有什么不对呢?”
常法官无奈,又将刚才的那套言论叙说一遍,众人仍是不理解,最后说,反正钱已分了,法不治众,你们看着办吧!
常江回到法院,向院长汇报了情况,院长觉得此案具有典型意义,既然调解不成,只好在人民法院民事庭开庭审理,原告袁留香、被告王囤和几个老贫农团员全部出庭。经过一番争论,法院判决如下:被告王囤现居住宅院土改前系原告袁留香家所有,后挖出的银元系根据原告指认的地方挖出,其中一罐儿银元明确书写有原告王老耀的名字,该罐儿银元、银元宝应视为当时原告家的财产,应归还原告所有。被告王囤挖出的一罐儿银元,也因该宅院系原告家祖上所有,可排除他人埋藏的可能,罐儿内所藏三百三十三块银元确定归原告所有。另书有“王中立”名字的一罐儿银元,此罐儿银元的产权可能涉及他人财产利益,该部分事实不清,本院将另外审理。
王囤和几个老贫农团员一听法院坐歪了屁股,审来审去没了他们一点点儿,顿时哗然,法庭上一片乱哄哄,法官连连击槌也没挡住,最后只好宣布休庭。
法院通过合议,决定强制执行,一定要将分过的银元收上来归还原告。
可是,村里分得银元的人没一个上缴的。
村人集体抗法,法院执行人员也犯了难。因为摊到每户的银元数目太少,总不能因几块银元就动法,没办法,他们只好向院长汇报。院长也觉得棘手,最后便给颍河乡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央求乡党委协助一下,也可借机给村民们讲讲法律。乡书记姓胡,是与院长同时从县委大院里走出来的干部,很熟。一听是这事儿,也犯了难,问法院院长说:“是不是你的法治不灵了,想利用我搞一回人治?”
院长笑道:“这也是无奈之举呀!”
胡书记说:“那好吧,我可以帮你摆平这档子事,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院长问:“什么条件?”
胡书记说:“就是你欠了我一个人情,有机会再让你偿还!”
院长一听是空头支票待填写,笑道:“老伙计了,这话说得有点儿外气!”
胡书记放下电话,就给王双楼的支书、村长打手机,要他们配合法院执行判决,尽快将分下去的银元收回来,三天以后交到乡政府,再听候处理!
因为是乡书记下的命令,分量就不一样,王丰收和支书一商量,便开始在大喇叭里通知让得到银元的人家限期交货,而且是支书带头做爷爷的工作,第一个先交出了所得的十块银元,接着是村长王丰收的家人也交出了分得的六块。由于是村干部的家属带头,就再没人抗议,三天不到分下去的一千多块银元全部收齐,当天就送到了乡政府。胡书记很高兴,立刻给法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更高兴,说既然收齐了,就将待审的三百块留下,剩下的让原告打个收条领回去就行了。
王大全接到村里的通知,急忙用三轮摩托带着老奶奶去了乡政府。颍河乡乡政府的府址是过去大地主崔二老家的宅院,三进深,内里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生人进去如进迷宫。镇上人都称其为“老院”。崔二老的小儿子叫崔洪波,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县参议员,土改时被枪决。袁留香的母亲是崔洪波的大姐,因其下世早,袁留香几乎是在外公家长大。只是自从土改过后,她已近六十年未来过这里了。过去的“老院”现在虽然面目全非,但袁留香一进大门立刻就走进了自己的记忆里,泪水止不住就流了出来。
胡书记对他们很客气,让人取出他们应得的那一大包银元对袁留香说:“老人家,这是你们家的七百三十三块银元,你点点吧,看对不对?”
袁留香感激地说:“不点不点,俺相信政府,感谢政府对我们的保护!”
胡书记一听这话有点儿别扭,忙解释说:“应该说这是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袁留香连连称是,为拿出行动感谢书记,亲手从包里捧出一捧银元,对胡书记说:“书记呀,这捧袁大头,给你留着玩儿,毕竟是老辈子的东西,也是我老婆婆的一点儿心意不是?”
胡书记忙拦住,说:“老人家,这银元我可不能要!我不能执法犯法呀!心意我领了,谢谢您!”
袁留香见书记是实意,便不再让,只是一个劲儿地道谢,最后竟要让王大全给书记磕头,引来一片笑声。
交接完毕,王大全带奶奶急忙回了家。他们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数银元。袁留香对自己六十年前的所藏之物重见天日,感慨万千,她拿起一块,用没牙的嘴先吹了一下,然后急速地举到耳旁听银声。这是过去人们试银元真假的一种方法。当她连试几块之后,面色陡变,惊叫道:“全儿,大洋假了!”
王大全一听,大吃一惊,忙学着奶奶的样子试听,试了几块只有一块有银声,惊呼道:“奶奶,有真有假,咋办?”袁留香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全试一遍!”说完,祖孙二人开始挨个儿试听。试听了两个时辰,七百三十三块中只有一百八十块是真的,剩下的全是假货。望着那堆假银元,王大全简直傻了,愤怒地说:“肯定是有人调了包,走,咱们找书记去!”
袁留香面色凝重,抬头望了孙子一眼,说:“是哪个调的包你知道吗?”
王大全一下听怔了,想想也是,银元是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又经支书、村长送到政府,然后又由乡书记亲自交到他们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说不清!怕是连公安局都难查出哩!他望着那堆假货,颓丧地出了一口气,问奶奶说:“奶奶,咋办?总不能吃个哑巴亏呀!”
袁留香也一直盯着那堆假银元,许久才说:“既是吃了哑巴亏,就别再声张!”
王大全说:“我咽不下这口气!”说完就要给哥哥打电话,被袁留香拦住了,说:“咽不下去也要咽!这是无头案,你告哪个去?别费那心思了,认了吧!银元虽假了,但咱总算争了一口气,赢了官司!这口气憋了我六十年了,这回总算出来了!”
没办法,王大全也只好认了。
可是,袁留香虽然宽慰孙子,但自己却最终没咽下那口气,不久就病了。毕竟是熟透的瓜了,病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袁留香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理,平常颇有人缘,再加上她属村里为数不多的长寿老人之一,众人都送了纸钱,葬礼办得很隆重。
只是王囤没去,因为他恨袁老太太死得不是时候,若早死几天,自己到手的那一罐儿银元怎么会花落旁家!
他非但没参加袁老太太的葬礼,而且还很气愤地找出那三个盛银元的罐子,恨恨地摔了个粉碎……
只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所摔碎的三个罐子中,有一个是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价值不菲,能顶三罐儿银元总价值的两三倍!
两个月后,他得知了真情,又悔又心痛,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责任编辑/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