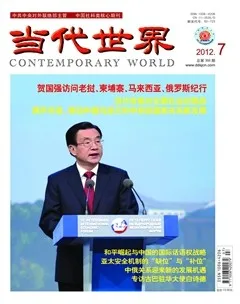希腊:欧债危机中绕不过去的坎儿
2012-12-29陈新
当代世界 2012年7期
2012年6月17日,希腊举行第二次议会选举。此轮选举将决定希腊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因此牵动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神经。最终,支持欧元区援助计划和承诺将继续奉行紧缩政策的中间右翼新民主党在大选中以2.4%的微弱优势胜出,并与大选中位居第三的泛希社运和其他民主左翼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6月20日,希腊宣布组阁成功,因希腊大选带来的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悬疑终于有了结果,但希腊的债务问题前景仍没有答案。
欧盟对希腊的二次
救助计划降低希腊债务门槛
欧债危机始于希腊。进入2012年后,欧洲已经经历了希腊带来的三道坎儿。
在2010年5月匆忙推出1100亿救助希腊计划之后,欧盟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的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希腊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尤其是自实行救助之后,希腊的债务水平不但不降,反而受到利息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上升。希腊经济中更多的问题被暴露出来。希腊是否会破产、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2011年7月21日,欧元区首脑会议出台了一项新的决定,即对希腊提供二次救助,救助金额计划为1300亿欧元。
针对希腊的二次救助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实施,涉及私人部门参与的程度。在做出二次救助决定时,第一轮救助希腊资金才使用过半。对于希腊的二次救助计划出台如此之早,除了媒体报道的希腊财政不可持续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常人不太关注但却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法律因素。
希腊现有的债券基本上是按照希腊法律发行的。按照希腊法律规定,如果希腊破产,希腊政府可以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因此,3000多亿政府债券中,绝大部分可以在希腊宣布退出欧元区时不了了之。随着希腊违约的可能性加大,希腊宣布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也在增大。作为希腊债券的持有大户,德法对此坐立不安。为了保证投资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欧元区的稳定,防止希腊采取玉石俱焚的做法做出极端决定,需要对现有的希腊债券进行置换,改成按照非希腊法律发行的债券。为此,德国和法国做出妥协,以私人部门自愿参与减记的方式,换来希腊政府债券的置换。希腊政府也心知肚明,不愿意把这层窗纸捅破。由此,债券发行和持有双方在第二次救助希腊计划的名义下进行了持久而又艰难的谈判,从2011年7月到2012年2月,期间的博弈过程跌宕起伏,险情不断,最终于2月21日达成第二轮救助希腊协议。
第二轮救助希腊协议的关键部分是希腊债券交换协议。根据该协议规定,希腊政府债券的私人部门持有人被要求用其目前所持债券交换根据英国法律而发行的希腊新债券,以及由欧洲救助基金发行的证券。这些债权人必须将其所持希腊债券的名义价值减记53.5%;在计入未来的利息付款之后,其实际损失将会达到投资价值的74%左右。该协议将把希腊债务削减1000亿欧元(约合1320亿美元)。
希腊政府2012年3月9日宣布,私人部门参与债务置换计划的比例达85.8%,高于设定标准。这意味着希腊的债务置换计划“过关”,希腊将可以甩掉至少1000亿欧元债务包袱。随之而来的是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方案细节陆续敲定。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于3月12日召开会议,批准发放355亿欧元的援助款,避免了希腊因3月20日大量债务到期而无法偿还所引起的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月15日同意参与第二轮救助希腊计划,提供28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新注入的资金约180亿欧元。希腊局势暂时得到控制,希腊债务危机的核心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希腊退出欧元区风险伴随
5月选举后的组阁失败而加大
希腊2012年5月的选举使希腊状况急转直下,希腊再次成为危机的焦点。
5月6日希腊大选结果揭晓后,在希腊总统的斡旋下,希腊进行了三次组阁努力,但均告失败,希腊不得不宣布在6月17日举行第二次大选。三次组阁均未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方对是否要继续执行欧盟和IMF主导的紧缩计划的态度不一。希腊的选举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希腊选民复杂和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继续留在欧元区,而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继续紧缩,但又不愿意承认“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现实。希腊大选给市场发出了非常负面的信号,关于希腊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的疑虑瞬时增大,3月份希腊债务重组以来形成的市场趋于平静的局面几乎被毁。
在希腊是否退出问题上,跟2011年10月份相比,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目前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时欧盟极力挽留希腊留在欧元区,并且明确表示希腊退出欧元区不是一个选项。主流观点也认为,希腊的退出将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危及欧元的存亡及欧洲一体化出现重大挫折,因此希腊不能退出。时隔6个月,欧盟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仍表态继续挽留希腊留在欧元区,但另一方面,鉴于希腊是民主国家,欧盟也必须尊重希腊人民的选择。为了防止希腊二次选举出现欧洲人最不想看到的结局,因此,各方也正在制定“B计划”。
欧盟及主要成员国对希腊退出问题的态度转变,可以有以下几点解读: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希腊选民施加压力。市场很敏感,认为希腊退出欧元的机率在加大,因此,资本加速从希腊外逃,希腊老百姓也开始到银行提现,发生挤兑。欧盟通过这一方式试图向希腊百姓发出明确信号,即如果希腊退出,百姓遭受的损失将更大,并借此提醒百姓在6月17日的第二次选举时投好自己的选票。
第二,通过提前释放希腊可能退出这一信号,来缓冲市场的反应。这样,即使希腊6月的二次大选果真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那时,市场的紧张情绪因大部分已经得到释放,对欧元区的冲击将会相对弱一些,进而达到欧洲人所说的“有序”退出的目的。
第三,通过一次救助和二次救助谈判,欧洲人对希腊的真实状况有了更细致和更清醒的认识,由于希腊的竞争力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加上有可能出现的第三次救助,因此,希腊将有可能成为欧洲人挥之不去的痛,并有可能成为欧洲的“无底洞”。在这种状况下,希腊的退出对欧元区可能是种解脱。而希腊只占到欧元区经济的2%,如果是有序退出,对欧元及欧洲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基于上述分析,在欧盟和希腊之间的博弈中欧盟已经变得日益现实和实际,一方面继续表示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另一方面则向希腊民众发出明确的信号,说明希腊退出欧元区对希腊自身来说代价是如何巨大,敦促希腊民众在第二次大选中不是靠情绪而是用理智来投票,进而影响希腊选举的结果。此外,欧盟也在制订应急计划,应对最坏的结果。
对于希腊来说,在欧元区的去留问题上有以下几个选项:
一是,希腊人主动说退出欧元区。按照欧盟现有条约,欧盟无法将某个成员国开除出去。因此,除非希腊人自己主动退出,否则希腊退出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希腊央行发布的报告,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希腊人均收入将下降55%,新币将贬值至少65%,失业将从目前的22%增加到34%,通货膨胀将达30%。市场估计希腊退出欧元区对希腊的冲击还要大。希腊民调的结果显示,70—80%的民众愿意继续留在欧元区,这也说明了希腊人主动退出欧元区的这一可能性不是很大。
二是,希腊人愿意留在欧元区,但拒绝执行紧缩计划。目前,欧盟及德国等一些成员国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希腊拒绝执行紧缩计划,那么向希腊提供的救助将立刻停止。而对于缺乏资金的希腊来说,停止救助资金的发放无疑是被掐断了口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希腊开始自己发行货币,那就意味着自动退出欧元区,这与希腊当前的民调结果是不符的。
三是,希腊人愿意留在欧元区,但希望就紧缩计划进行谈判。德国的态度是紧缩计划没得可谈。欧盟委员会的态度是,在遵守基本承诺的基础上,在具体操作和执行方面可以对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行商谈和修改。鉴于有舆论指责目前的希腊救助方案是外界施加给希腊的,希腊对该方案没有归属感,因此,欧委会也希望,如果希腊新政府能够提出商谈和修改方案,那通过新一轮商谈和修改谅解备忘录可以进一步促使希腊政府把救助方案看做是自己的方案,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方案,这样为今后的实施奠定基础。
希腊第二次大选成功
组阁并未终结债务危机
自1974年希腊推翻军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制以来,希腊的政治命运就一直为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所左右,两党轮流执政,一直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不容否认的是,正是两党为了迎合选民不惜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资金,最终落得国家债务累累,这也是民主的悲哀。激进左翼联盟在本次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希腊人民换一种方式生活,以期结束两党轮流执政30多年的状况,但该党过激的“国家重建计划”引起欧盟对希腊执行救助计划的担忧,以及市场对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的疑虑。激进左翼联盟在6月17日的选举中位居第二,至少也反映出了希腊民众的心态。如今,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这两党在激进左翼联盟的强大挑战下,握手言和,准备联合执掌希腊今后几年的命运,这可能也是当初帕潘德里欧没有料到的结果。同样,帕潘德里欧当初爆料前政府做假账,可能也没有料到会给希腊和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制造如此大的漩涡。
希腊新政府能够组阁成功,主要是基于两大党同意留在欧元区并愿意继续执行救助计划,但同时两党也都希望就救助计划的实施条件重新进行谈判。联合执政可以避免两党相互指责,但是否能够做到同舟共济,还得拭目以待。
对于希腊新政府,以及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这两大党来说,目前首当其冲的任务并不是就救助计划的实施条件进行谈判,而是需要对自己进行深刻反思并确定在危机中的定位。两党应该有勇气面对这一事实,即两党彼此给希腊留下了巨大的债务黑洞。民主应该有道德底线,民主也应该有良知,靠蛊惑民心来向救助方施压,将无助于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只有希腊两大党联合执政的政府从危机中凤凰涅槃,把救助计划看做是弥补自己过去10多年的过失的机遇,而不是看做是外界强加给希腊的紧箍咒,希腊债务危机的逻辑关系才能理顺。新政府给希腊债务危机的前景带来了新希望,但希望是否会变为现实,还需要新政府认清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古代希腊有几件事情闻名于世,一是古希腊哲学,二是民主的发源地,三是希腊悲剧。我们相信凭借当代希腊人的智慧,拯救希腊和希腊人民将不再是幻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经济室主任,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