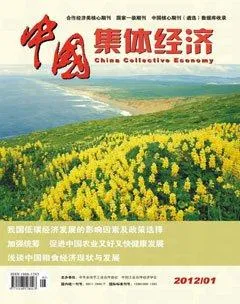浅谈农村土地资产化的收益分配机制
2012-12-29薛红霞
中国集体经济 2012年1期
摘要:农村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行政权力侵蚀财产权利,集体所有权利未得到足够体现;未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农民个体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主体、农村土地收益分配的具体形式,理清各主体间的关系,构建收益分配总体框架。
关键词: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
一、引言
土地资产化,是指把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作为资产来经营,发挥其资产化效益,从而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过程。农村土地资产化主要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等进行市场化配置,使权利主体获得经济报酬和收益,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高效利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和“理性行为”假设,各产权主体以谋求最大收益为目标,土地开发、经营和管理等经济活动最终都要体现在土地资产收益的分配上,产权关系实质上是土地产权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构建农村土地资产收益分配的机制、保障农村土地各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减少各权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促进土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土地资产化保值目标的关键。
二、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现状
在物权法语境中,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自物权与私权,包括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等权能,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或处分其财产,并享有其收益。而国家依靠其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获得土地上的收益称为税,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固定税额和固定税率)而不体现任何对等的交换关系。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权力的控制,并不具备自主性、完整性与自治性,在收益分配上未能体现所有权利益,而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收益的获取已远远超出了税收的范畴。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特点是集体内的农民“共有私用”,在这种所有制下,集体的任何个人首先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这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中所有者的二重性。由于二重性矛盾的存在,任何个人都是所有者又不是所有者,因此,任何个人都不能单独行使所有权职能,人们必须通过某种集体行动来行使和实现公有权。然而,通过集体行动是极不经济的。
三、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机制构建
(一)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主体
1.各级政府。马克思在谈到国家权力时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利: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国家关于土地资产权益的实现主要是依靠这两种权利。在我国,马克思所指的“所有者的权力”则是指城镇国有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而对农村土地而言,主要是指农民集体而不包括国家。在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中,国家只能依靠其第二种权利即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来获得土地收益,这种收益即称为税。
2.农村土地所有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其实质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取的土地收益,是土地产权人凭借土地权利分享的一份生产成果。地价则是地租的资本化,指农村土地所有者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将一定年限使用权一次性的出让给土地使用方所获得的收益,也指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按照某种约定出让所应得的收益。农村土地资产化中农村土地所有者得到地价,应该是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最高最佳使用的土地价值,包括土地转换用途产生的增值收益;这个地价必须是公平市场条件下达成的市场价值,未受行政权力侵蚀的地价。
3.农村土地承包者。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农民个人拥有全部集体财产的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种与农民集体成员身份不可分离的权利。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具有物权的性质,具有排他性且具有长期稳定性。因此,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中,农村土地承包者理应获得土地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垄断地租的一部分。
4.农村土地经营者。农村土地经营者是农村土地的最终使用者,通过资金、劳动、技术等各种要素投入来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加土地收益,也就是马克思地租理论所论述的级差地租Ⅱ,对于这部分资产化收益应该根据要素投入“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分配。
5.其他利益主体。在农村土地收益分配中,除了政府以及以上三个直接利益主体外,还有一些间接利益主体,主要包括基层农村经济组织及农村土地资产化中介组织等。随着农村土地资产化的推进,它们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分享土地资产化收益。
(二)农村土地收益分配的具体形式
1.地租。地租,即指农村集体所有者或承包者通过合同、合约,将一定期限内的土地承包权出租给其他使用者,所收取的费用。
2.地价。地价在我国一般是指土地所有权不变时出让若干年期的土地使用权所应支付的代价。因此,土地价格的内涵实际上包含土地资源价格和土地固定资产价格,前者是以“虚幻的价格”形式出现的“真正的地租”——地价;后者是土地资产的折旧和投资利息。土地价格为二者之和的资本化。
3.分红。分红,亦称利润分享,即分配红利的简称。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中,分红是对农民将土地产权参与股份合作的投资回报,这种形式可以使农民获得长久的、有保障的收益,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是一种很好的分配形式。
4.利润。利润的形式有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和税后利润等。实现利润是销售收入减去各项费用支出的余款;上缴利润是按规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而税后利润是实现利润按国家规定上缴一定比例后留归的部分等。
5.土地管理费。土地管理费,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者在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中所获得的部分收益。根据我国《物权法》及《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农村土地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在土地资产化过程中,它们代表农民个体参与土地产权市场交易谈判,使土地资产化收益得以实现,是农村土地资产化中重要的环节。
6.土地税收。税收主要包括契税与土地增值税,前者是针对土地流转与征收一定数额的税,后者是按土地价格增加值征税。对土地资产化收益进行征税既体现了政府的政治权力及在土地资产化中投入的管理因素,也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因社会发展所增加的土地价格还诸于社会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收入、保持社会公平发展的作用。
(三)农村土地收益分配总体框架
经过对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的主体及具体形式分析之后,可以对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形成一个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这一分配框架表明在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中,土地的所有者、承包者和使用者是直接的受益主体,国家政府机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及中介服务机构是间接的受益主体。并且在具体的利益分配(税率、管理费的确定)方面,要着眼于切实保护各土地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各权利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体现,而不应该是满足于“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更不能随意使用行政权力侵害土地产权主体的财产权利,过多地占有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框架中参与土地资产化的相关主体具体分配比例,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量标准,因为,资产化的形式多样、各地所处区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分配的具体标准应根据所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按照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来确定。
四、促进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的措施
农村土地资产化过程中,土地通过市场进行流转,并通过市场功能对土地收益实现了初次分配。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二重性矛盾的存在,因此,任何农民个人都不能单独行使所有权职能,必须通过法定的常设机构来代表农民行使所有权,参与土地资产化市场初次分配,再由所有权行使机构向农民集体中所有成员进行再次分配,具体如图2所示。
笔者认为完善的委托代理机制,保障农民个体权利关键问题在于完善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治,加强对代理方的制约与监督,增加委托方的话语权。
第一,建立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并赋予其决策权和监督权。《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调整以及土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等,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但未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笔者认为集体所有土地毕竟是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必须代表农民集体的意愿和利益。建议通过明确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为农村土地资产化收益分配的权力决策机构,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执行机构,分配方案及土地权利流转方案均需经过村民大会表决方可生效。赋予村民会议对其他集体组织就一般事项做出的决定享有监督权,为集体成员提供一种更有效可行的救济途径。集体成员对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管理人员做出的决定认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请求村民会议审查,做出维持或撤销的决定,对村民会议的决定不服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消;或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撤消。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启动村民会议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显然要比启动诉讼程序容易得多。在通过村民会议仍得不到救济,或村民会议直接做出的决议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时,诉讼程序充当保证村民权益的最后屏障。
第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农民维权团体。学者于建嵘经过调查发现,目前全国农村的许多地区存在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组织,但由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没有具体化,政府有关部门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对农民维权组织进行必要的核准登记。由于得不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它们大都还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的“非正式”组织。于建嵘认为如果只是一味对此类组织进行打压而不是有效引导,很可能会使农民组织发展为秘密社团,从“以法抗争”转向“非法抗争”的方向,进而发展成为反体制的力量。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一步明确公民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及其行使的条件与程序,允许并规范农民维权团体的建立,增加对弱势农民群体的救济渠道。
第三,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加强对农民的组织和教育。我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足,据调查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7年。而农民参与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村民自治,行使其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都需要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民合作组织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的最有效、最方便的载体。只有农民组织才能产生对村干部所实施的政策、决定的影响力,才能构成一个阶层的力量,而力量的大小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的组织程度。
参考文献:
1.罗士喜.基于土地资产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构建研究[J].郑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