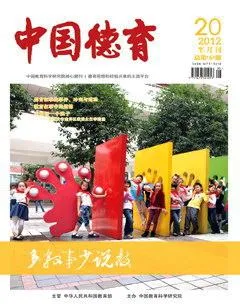三十年一路走来
2012-12-29麦志强
中国德育 2012年20期
三十年,我一路走来,有幸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完成了从一个中学班主任到一个德育理论工作者的转型发展,也见证了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和德育改革实践的发展过程。而今,在我眼里,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中小学的德育改革实践,从事理论研究与从事一线工作的德育工作者们,已经呈现出一幅“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象!
一
记得那是1983—1984学年,我接到了学校通知,让我以初中实验班班主任的身份,参加一个全国重点课题——研制中学德育大纲的实验研究工作。接到这项任务,我激动了很长时间。
自从1973年春走上讲坛,至今已有将近四十个年头了!曾经,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见证了“文革”对学校造成的颠覆性破坏。1977年冬,我国重新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时的中国,就像《春天的故事》里所唱的:“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希望和朝气的春潮涌动中,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教师,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青春活力与时代豪情相互激荡,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声中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就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和青春情怀中,我接到了参加全国重点课题研究的任务,能不激动吗?我欣喜能在这个小小的教学班里,参与一个全国性大课题的研究,我愿意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为一个年轻的班主任,我仅仅是凭着自己的朴素热情和年龄优势,在和学生打成一片中形成了一些班集体建设的感性认识,对于什么是德育,什么是班集体的形成规律,怎样在知、情、意、行诸方面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等等,只有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是,我始终在探求着,作为一个班主任,我在带班的这三年之中,应该给学生施以怎样的教育和引导?其中,有没有一个类似学科教学那样的知识结构?有没有类似教学目标那样的目标序列?有没有类似教科书那样的内容体系?如果有,班主任的教育工作,就可以摆脱那种“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主观随意状态了。
在参加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一批名家大师的悉心教诲和指点。北京的张志义老师、胡筠若老师、齐炘老师,上海的胡守棻老师、古人伏老师、梅仲荪老师,南京的班华老师,东北的王逢贤老师,等等,正是在这些高人的指点下,我在按照课题组的设计完成了相应的实验研究任务之外,也与其他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们共同完成了我一直在探索的“班课系列”设计——每个学期均围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学习指导”“心理素质指导”等五个专题进行班课教育,每个专题则根据每个年级每个学期的不同特点,各设计一个课题内容。循此,便构成了一个覆盖3个年级6个学期共5个专题30个课题,结构上具有横向系统性和纵向层次性的班课内容序列。
这就是我在参与课题研究中走进教育科研正规队列的一段宝贵经历。在“教官”们的悉心教诲下,我懂得了,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必须从那种朴素的热情中超越出来,自觉提升理论素养,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在一线工作的班主任来说,形成一种“在日常工作中开展研究,以研究引领日常工作”的自觉性,是自我提升的最有效方式。
二
1986年9月,我从华南师大附中调到了华南师大教科所德育研究室,开始了从实际工作者向理论工作者的转型发展。
到了德育研究室之后,我才全面了解到,原先我在中学时所参加的“六五”课题名为“我国学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是教育部“六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共同承担,并分别在各地的学校开展实验研究,分别向国家教委提交各自的大纲版本。
1986年10月,国家教委原中学司和中央教科所在江苏扬州联合召开“《中学德育大纲》研讨会”,总结了“六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各地研究中学德育大纲和实验工作的初步成果,会议达成了研制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的共识。
1987年8月,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将以研制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为主要任务的“中学德育整体改革研究”列为“七五”国家级重点课题。1988年3月,课题组提交了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版本,在同年6月举行的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上征求意见后,于1988年8月由国家教委颁布在全国试行。
作为这两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参与者,我觉得有些研究过程中的细节是值得提示人们关注的。“六五”期间三个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在研究过程中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把原来的课题名称——“我国学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中“政治思想道德”的排列顺序进行了调整,在各自的大纲版本中均表述为“中(小)学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大纲”。大家认为,通过调整“思想”与“政治”的排列顺序,显示出我们告别了“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突出了“解放思想”这一时代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五”期间华南师范大学提交的大纲版本中,其德育目标结构与其他两个单位有所不同——在共同的“思想”“政治”“道德”序列之外,增加了一个“个性心理品质”序列,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过程之中。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计,是因为在学校的实验研究中,在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我们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人的心理素质提出的新要求。1981年底,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竖起了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这句口号连同“深圳速度”,对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种全新的时效观念面前,人们需要有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去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不确定性。
1988年3月,一批德育专家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起草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我以课题组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这次活动。我记得,在讨论到德育目标的内容结构时,专家们不得不直面由广东版本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心理学放入德育的范畴合适吗?把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变成了德育要求,那德育不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吗?讨论的结果是,课题组于1988年6月提交给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的征求意见稿中,建立起“思想、政治、道德、个性心理品质和能力”的德育目标结构。时至今日,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一项必要内容。实际上,在国外,人们早就运用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研究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规律及教育要求。而在广东提交自己的德育大纲版本时,我国学者也已经出版了《德育心理学概论》等著作。
现在,再讨论把个性心理品质教育归纳到中小学德育范畴是否合理的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当年围绕中小学德育中的个性心理品质教育问题引发的争论,却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认识。
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不同视阈与要求,可能导致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除却边缘学科,各个独立学科之间必须有严格的学科界限,有独特的研究范畴,德育学就是德育学,心理学就是心理学,不容混淆,但从中小学的德育实践来看,各种教育内容和要求往往综合统一在一个活动过程之中,由一个综合性的教育主体(诸如班主任)对学生施加综合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小学的教师队伍结构中,原来就没有从事心理教育的专业教师和专业科组,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德育范畴,让班主任及其学校德育工作队伍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则具有一种历史的合理性。
这就是我对当年那些争论的理解。
三
从1983年参加“六五”规划课题研究到现在,已有30个年头了,我见证着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和德育改革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
“六五”“七五”期间,从事德育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来自于教育哲学、教育原理的学科范畴。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等六所院校教育系在1986年联合编写出版的《德育学》,则标志着德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支以德育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研究队伍逐渐形成。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我国的德育理论建设主要以引入、评价国外德育理论为主,先有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前苏联德育理论的重新引入和评介,后有20世纪90年代对欧美、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的德育流派与学校德育的引入和评介。经过了近20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已经开始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进入新世纪后,更有一批德育理论工作者自觉进入中小学德育实践领域,以各自的理论假设,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型,与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共同构建异彩纷呈的德育模式。
他们当中,有的把德育学与美学融会贯通,把德育与审美教育、德育过程与审美过程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充满艺术魅力的德育理念——如果可以把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处理成一幅美丽的画、一曲动听的歌(即实现德育过程的审美化),那么与这幅画、这首歌相遇的人就会在“欣赏”中自由地接纳这幅画、这首歌的内涵和价值,那么,道德教育的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这两个方面就可以在“欣赏”过程中得以统一,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欣赏型德育模式。有的让德育学与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相互结合,针对有些区域自然和社会和谐度不足的客观现象,希望通过营造体验场、创设开放式对话、进行反思性表达与提升等手段,设计并创造出相对和谐的微观生态环境,使学校德育的微观生态环境与大自然、大社会的生态环境之间保持适度的开放性和一定的张力,启发、引导受教育者自觉养成关心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建构起自己的生态体验德育模式。
许许多多的德育学界同仁,以自己的劳作与睿智,创造出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喜人景象。如果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相比较,我国中小学的德育模式研究已经从“回顾性研究”发展为“验证性研究”,从先实践后总结的“归纳方式”转变为根据一定的理论模型设计相应操作模式的“演绎方式”,从“一校实验”变为“多校共同实验”甚至是“跨地区协同实验”。这些,都标志着我国中小学德育实践研究进入了一个理论与实践更紧密结合、更具理论自觉性的发展阶段。
三十年,我一路走来,有幸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完成了从一个中学班主任到一个德育理论工作者的转型发展,也见证了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和德育改革实践的发展过程。而今,在我眼里,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中小学的德育改革实践,从事理论研究与从事一线工作的德育工作者们,已经呈现出一幅“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象!
责任编辑/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