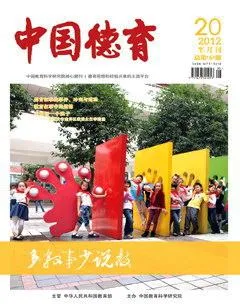德育叙事的事件、冲突与道理
2012-12-29刘良华
中国德育 2012年20期
一个德育叙事是否可观、可读,关键是这个叙事本身是否有某种事件。只有情节构不成有价值的叙事,真正能够引起人共鸣的叙事总得有令人牵肠挂肚的冲突,以及,隐含在事件冲突之中的令人共鸣或扼腕的道理。
一、德育叙事的事件及其冲突
当我们认为故事有情节时,也就是说讲故事是有“事”的,讲故事总得讲述某个事件。任何故事,总意味着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生了某个突发性事件,这个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偶然的变化,一个不确定的波折。它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起伏,一个跌宕。正因为它是日常生活的波折、起伏、跌宕,它才显得曲折、委婉而动听、可读。这就使故事具有了动听性和可读性。
故事的情节说白了,是由一个或几个冲突构成的,而且多半是人性内在的冲突或内在的欲望。它让那些隐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力量悄悄显露出来。如果某个叙事作品的制作是成功的,这个叙事作品必显露出人的本真状态。有时为了叙事的需要,作者常用的技巧是:寻找几个不同性格、不同追求、不同信仰的人,用这几个人来分别代表人性中的内在冲突。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冲突?这些冲突不过是一种表象,真实的内涵是人的多种需求和欲望。
故事的情节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自从来到人间,就已经生于天地之间,而天地之间原本就充满了冲突。人被抛掷到天地之间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就构成了人的生活情节,也构成了教师的教学生活的情节。教育中的事件、教育中的现象、教师中的故事,是教育理想与教育传统的冲突,或许,这种冲突源于天空与大地的冲突?
德育叙事是对某种冲突的记录和回忆。没有这种冲突,就无所谓教育事件,也无所谓案例、事例、故事或现象学描述。德育叙事作为一种制作、一种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品,它不仅忠实地描写教育理想与教育传统的冲突,而且可以想象这种冲突,除此以外还可以隐喻这种冲突。艺术品既把“别的东西”敞亮,也把“别的东西”隐藏,至少不过度地、喋喋不休地把“别的东西”公布出来。好的案例“但开风气不为师”。“指导教育实践不一定都需要采取教育学这种理论形式,教育随笔、教育小说或许是更适合传播教育思想的形式,卢梭、裴斯泰洛齐的先例,足资说明这个问题。”[1]
好的案例是敞亮地叙说事件,但它又隐含地表达“别的东西”,它把“别的东西”隐喻出来。这“别的东西”习惯于“道隐无名”,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多受后人指责。其实,韩愈所关注的主题原本就在“道”不在“文”上。如果说“文以载道”对“文”尚有所损害的话,那么,“文以载道”对“道”而言却值得推广。孔子也讲,如果只讲内容而不重视文采,则显得粗俗野蛮;如果只讲文采而不重内容,则显得浮华虚夸。只有既讲实质内容,又讲文采,这才是君子所为。
传统哲学以及教育学研究使用的方式是论证(逻辑论证),叙事研究开发出来的道路是描述(解释性描述)。
论证与描写的区别,其实也就是狄尔泰提出的说明(explain)与理解(understanding)的区别。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者可以说明,但后者必须理解。
为何论证、说明的方式只能用来研究自然而不适合思考人的问题?因为某人如何,不在于他有什么普遍的本质,而在于他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在于他的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事件。用说明的方式追问人的本质就像用剥洋葱的方式寻找洋葱的本质,这种追问和剥离总是离开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隐藏在人的生活事件中。德育研究者如果将某人的生活事件及其德育冲突描述出来,这个研究者就已经领悟此人的气质,读者或者听者也就可以经由对这个人的生活事件及其德育冲突的描述领悟此人的气质。既然描述已经能够让研究者以及读者、听者获得某种领悟,自然科学研究意义上的说明、论证则已经成为多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荷兰心理学家拜登狄克注意到,“比起社会心理科学书籍和杂志中那些典型学究式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些伟大的小说家那里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见解。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把普通的人类经验变换(小说化、诗化、再塑造)得林林总总。”[2]
二、德育叙事的道理
德育叙事虽只是对某个德育事例的描述,它却具有普遍的象征、比喻的意义。每个德育叙事总是像某种“别的东西”。事例之所以能够道出事情的真相,与“像”的本原意义相关。“像”的本原意义是什么?是道或道理。当老子说,“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时,也大致可以说“大音稀声,大道无形”,相当于老子所谓“道隐无名”。既然“大象无形”“道隐无名”“道可道非常道”,人又如何能够知“道”呢?老子本“道法自然”的思路,建议人们以自然中的事例来理解这种隐藏无名之道,老子在《道德经》中大量地描述自然(包括社会)中的事例来道破天机,比如为了澄清万物生于“有生于无”的道理,老子描述了车毂、容器、房子等自然事例:“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当老子说有了车的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时,当老子说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时,当老子说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时,老子所描述的这些事例皆有助于人们对于“无形”、“无名”之道的领会。无形之“象”(或“道”)无法直接道说,“象”与“道”就有通过“某事某物像什么”(事例)的方式来获得显现。虽“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却可以经由事例领悟“道”之在。
成功的描述是对某人的生活体验的阐述,它引起同样具有生活体验的读者产生共鸣。这有点类似现象学描述所可能引起的“现象学点头效应”(phenomenological nod),它让读者频频点头,因为成功的现象学描述总会让读者发现,现象学描述的生活体验读者也曾经拥有或可能拥有。[3]“现象学的目的是将生活经验的实质以文本的形式表述出来。通过这种转变,文本的效果立刻成为有意义事物的重新体验和反思性拥有:通过文本,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就会被激活,产生与文本的对话。”[4]
成功的描述总是内在地具有某种“邀请性”。凉水邀请我们去喝,海岸邀请孩子去玩,一把舒适的椅子邀请我们疲惫的躯体陷入其中,德育叙事文本邀请我们与之对话。[5]这种描述使作者,也使读者或听者获得对自己生活体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将帮助人恢复人(包括作者、读者或听者)与世界的联系。
成功的事例是一件艺术品。讲述某个动听的德育叙事,就是制作某件与德育相关的艺术品。
艺术品、故事总是有所意图,或者说,讲故事总是有目的的,任何人讲故事总得有个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的目的。能够称得上德育叙事的描述总得有个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意图,或者称之为意象。这个目的、意图、意象与这个故事的主题相关,而且,这个目的、意图、意象和主题就是这个故事所要暗示的某个或几个道理。它暗示的道理可能是小道理,也可能是大道理。目的、意图、意象、主题、道理是故事的灵魂,是故事的最基本的结构。
道理往往隐身在现象背后,这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道理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或“情结”。就此而言,叙事研究的方法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那里已经被提出来。而且,叙事研究在其发展的道路中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
从这个视角看,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是理解德育叙事方式的前提。或者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分析方法在社会学中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德育叙事的描写方式就会提供多大的成就。德育叙事的描写似乎在叙说人的有意识的生活事件,但德育叙事的真正魅力却在揭示人的日常生活事件背后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结构,包括“集体无意识”。这种“潜意识”往往处于受压抑状态,它成为人的心中的一个结。如何解开这个结,就成了德育叙事的任务。为了解开人的某种情结,可以借助于梦的分析,由梦的事件揭示它的象征意义;也可以借助于某些生活事件的描写和叙述,并由描写、叙述而获得顿悟,这有些类似心理学研究中的“格式塔”方法。
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意义。要求一个德育叙事有道理实质是要求这个德育叙事有意义。
什么是有意义呢?要求一个故事有意义,也就是让听者听了德育叙事之后,明白了某种道理。有意义的叙事总是以藏而不露的方式表达了某种关于教育的或人生的道理。
什么是有道理的叙事?它表明一个叙事能够让听者听故事之后被感动。一个德育叙事是否隐含了某种道理,看这个叙事是否能够让听者感动。
听者为谁感动?感动什么?听者表面上是为情节感动,实际上能够感动人的只是道理。于是,一个德育叙事是否有分量,就看这个德育叙事是否有教育道理、教育理论。但德育叙事不能直接地讲道理或理论。真正的道理是不能直接讲的,它必须隐藏在故事背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形”。
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论文或实证研究报告不是有教育道理、教育理论吗?教育论文不是没有教育道理,而是可能道理太多、太直白、太泛滥。懂得讲道理的人从来不讲道理,他只讲事,让理在事中,一起构成事理。教育的道理常常隐藏在教育事件和教育故事中。道理有两个特性,第一,道理本身就是隐匿的,“道隐无形”,它是一团漆黑。能够讲出来的道理依然是道理,但不见得具有可读性和可听性,“道可道,非常道”。第二,道理不能直接传授。道理是否能够让人接受,需要人亲自去领悟。人可以讲授道理,但讲授的方式只能“知其白,守其黑”。讲授者须让道理隐藏为“黑”,它是一团漆黑,但又或隐或现,就像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几颗光亮微弱的星星。
有了事件,又在事件的冲突之中隐含了道理,德育叙事便具有了潜在的可读性和可听性。它将使人们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它将创造性地损坏习以为常、或已成为标准的东西,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前景展现出来。这有些像诗人的工作,诗人意在瓦解常备的反应,创造一种升华了的意识,重新构造我们对现实的普通感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世界而不是糊里糊涂承认它;或者至少我们最终设计出新的现实以代替我们已经继承的而且习惯了的现实。[6]
有了情节,又有了结构,便具有了解释的空间。好的叙事有足够的解释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桂生.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近代教育学史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4.
[2][3][4][5][加]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