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读:寻访藏书楼
2012-12-29
中国收藏 2012年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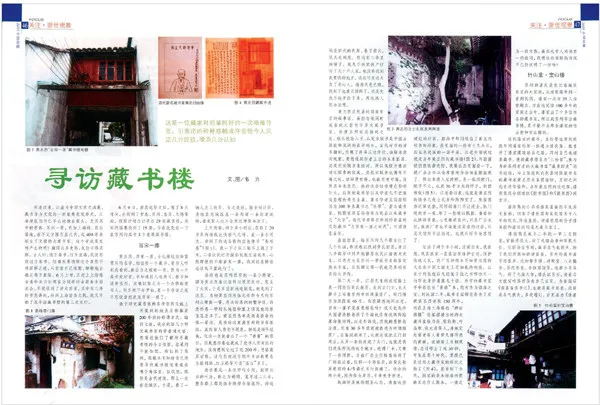

编者按: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藏书楼?几千座,其中有一定影响的就达1000座。而从明末到清代中期的著名私家藏书,几乎没有超出苏州府方圆一百里的范围。诸如明末虞山毛(晋)氏汲古阁、钱(谦益)氏绛云楼、清初钱(尊王)氏述古堂、昆山徐(乾学)氏传是楼、清中元和黄(丕烈)氏百宋一廛等等,都没有出此范围,此地藏书之盛由此可窥。
本文作者韦力,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已逾百架,四部齐备,唐、五代、宋、辽、金之亦有可称道者,明版已逾800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有数架,亦可谓贫儿乍富”,可谓当今藏书家中佼佼者。2001年,韦力在江浙一带开始寻访藏书楼之旅,并将其所见所闻写成《寻访藏书楼》一文,由本刊发表。在此,本刊节选部分,以飨读者。可以说,这是一位藏家对前辈同好的一次艰难寻觅,引发出的种种感触或许会给今人沉淀几分经验,增添几分认知。
明清以来,江南为中国文化之渊源,藏书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江南地区仍当仁不让地独占鳌头,尤其其中的常熟、苏州一带,再加上湖州、昆山等地,在不足方圆百里之内,近400年来诞生了无数的大藏书家。这个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翻阅众多史料,我仍不得其解。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没有读过万卷书,但看来要破解这个百思不得其解之谜,只有靠自己腿勤、脚勤地去凑足那万里路。6月上旬,正赶上上海博古斋和朵云轩两家分别举行古籍善本拍卖会,早就收到了拍卖图录,其中有几件好书想得到,趁到上海拍卖之机,就又开始了我寻访藏书楼的第二次出行。
6月9日,拍卖完毕之后,用了8天时间,分别到了常熟、苏州、南京、无锡等地,按照计划总计寻访29座藏书楼,实际的结果找到了19座,今在此先谈一下在苏州的其中3个重要藏书楼(编者注:过云楼为其中一个,在此不赘述)。
百宋一廛
黄丕烈、百宋一廛、士礼居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相信每一个藏书、爱书人听到或看到,都会为之眼睛一亮。作为一个藏书爱好者,不知道别人还尚可,若不知道黄丕烈,则难以称之为一个合格的爱书人。到苏州下车伊始,第一个寻访之处不用说自然就是百宋一廛了。
黄丕烈是乾嘉时期最有名的藏书家,虽然与他同时或在此之前有很多大藏书家,但黄丕烈有其独到之处。他从校勘入手,认定宋版书是中国古籍能够见到的最早刻本,后代对书的诸多翻刻,出现了许多以讹传讹、曲解本意的现象,要想还其作者主旨的本来面目,必须用宋版书来校对。所以他极力推崇对宋版书的收藏,虽然宋版书也偶有不确之处,但即使有错,也能有迹可循,还原其本来意思。他的这套校书理论影响巨大,后世的藏书家以及学者无不把他这套理论奉为圭臬。近代学者陈登原称乾嘉时代的藏书“为百宋一廛之时代”,可谓推崇备至。
在旅馆里,给苏州的几个朋友打了几个电话,都说难以找到黄氏旧居,并且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推荐我找江澄波老先生。江老先生是苏州一带最有名的鉴定版本专家,从他祖父那一代就是苏州有名的大书商。
第二天一早,江老先生到旅馆接上我一同前往黄氏故居。走到正门口,见大牌子上写着苏州市丝绸服装厂,而门牌号为葭巷46号。我很疑惑地问江老,百宋一廛不是在悬桥巷吗?我又把我昨天围着悬桥巷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的结果向他询问,江老告诉我,您找的悬桥巷没错,但在30多年前就被改造成丝绸服装厂,后面封起来了,也就是说把正门封死后,从另一条街改建了大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找的这个地方。进得厂来,又费了一番周折,才由厂办主任陪着转到了厂的最后面,仅剩一小角旧居,而黄氏故居原有的4/5都已另行拆建了。仅余的两小处,因为作仓库用,才幸免于拆迁。
我满怀虔诚的朝圣心态,看着这些破烂的旧居,脑海中却闪现出了黄丕烈校书的形象。最里面的一排有十几米长,四五米进深的一溜平房,江老介绍说这就是当年黄丕烈的藏书楼。外面窗棂仍然保存完好,我要求进里面看一下,被厂办主任以仓库重地为由直接拒绝了。转过来进入左跨院,是一弧形院门,院子不大。也就30平方米的样子,但很雅致。江老告诉我这就是黄丕烈的读书之处礼士居和陶陶室了。房屋保存还算完整,同样锁着门不让进去,扒门缝向里一看,堆了一些破旧机器。看着如此惨破景象,心里难说高兴,问及厂办主任,他说厂里也不清楚这是谁的旧居,只是文馆所不让拆迁,也就只好作仓库用了。
忙活了两个多小时,道谢出来,我在想,现在国家一直在宣传保护古迹,保护传统文化,而厂里却根本不知道黄丕烈大名在中国文献史上是如此的响亮,以至于到他逝后凡经他手批之书哪怕只有一行字也身价暴涨几十倍。所有的藏书家手中若能有“黄跋”本,均可作为镇库之宝。到民国二年,藏书名家缪荃孙为了庆祝黄丕烈诞辰150周年,还在上海三马路的“醉沤酒楼”设宴招请当时的大藏书家徐乃昌、张钧衡、叶昌炽、张元济等人,并规定赴宴者每人要带几部得意的黄跋,在酒席上互相观摩,总计带去了近30种。可见在那个时代,黄跋已是这些大藏书家的珍玩之物了。甚至到了今天,国家的善本标准将黄跋无论什么版本,一律定为一级文物,虽然还有人对他有一些微词,我想这些实际的情况不已经说明了一切吗?
竹山堂·宝山楼
苏州的潘氏是在江南地区有名的大家族,从清乾隆年间一直到民国,潘家一共有35人金榜题名,而在这延续100多年的家族史当中,潘家出了十多位有名的藏书家,所以到苏州寻访藏书楼,是不能不去拜会潘家的竹山堂和宝山楼的。
谈到潘家的藏书,自然要追溯到乾隆年间潘家的第一位进士潘奕隽,他首开了潘家谋取功名之路,同时自己也极喜藏书。他的藏书楼名为“三松堂”,他与当时苏州有名的大藏书家均有过往,与黄丕烈关系也很密切,互相之间均有诗作唱和。
潘奕隽的小弟弟潘奕基虽然不比其兄显赫,但其子潘世恩却是乾隆五十八年的状元,仕途显赫。而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和潘祖同均是大藏书家了。
潘祖荫是咸丰二年的一甲三名探花,官做得很大,到了礼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祖荫仕运亨通,藏书名气也很大,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滂喜斋,另外的藏书斋号还很多,比如攀古楼、功顺堂、八求精舍、芬陀利室、小脉望馆等,也都小有名气。到了光绪九年,潘氏回苏后,请著名文献家叶昌炽住在自己家里,为他编写《滂喜斋读书记》,也就是藏书目录。此目录名气很大,多次增订,后更名为《滂喜斋藏书记》,从目录上看藏书水平很高,宋元本就有58部之多,而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宋本《金石录》十卷。
有些藏书论述中均谈到潘承厚、潘承弼兄弟是潘祖荫的后人,其实是错误的,而是潘祖同之后。潘祖同是潘祖荫的表兄,他是咸丰六年的进士。潘祖同亦是藏书名家,我到苏州所要寻找的藏书楼就是潘祖同的竹山堂以及在竹山堂的基础上由其两名孙子潘承厚和潘承弼所建的宝山楼。
一位热心的老太太领我们进入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街巷内,又向前走了约20米,这条小巷是带有屋顶的,走在里面黑黢黢的感觉,20余米过后豁然开朗,里面是二进大院。老太太指着说,喏,这就是你们找的地方。我道过谢,静下心来细细看着这偌大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杂居着十多户居民,院落显得破旧杂乱。从院落的规模和雕梁画栋所透出的气势,仍然透着昔日的富贵和大气。同院中的居民聊天,得知原来的规模要比这大得多,从南石子街到进深20多米其实原来都是院内的建筑,而现在都已拆改过了,现剩最里面的这二进院子,才是当时仅存的一小点儿旧居。在第一进院子门楼上砖雕刻着“媚玉辉珠”,是嘉庆年间的题款。尤其能透出大家之气的是第二进楼上的雕花饰板,整个是用楠木所雕,一反江南的细巧而显得粗犷有力,也带出了官家的霸气。楼上的其中一家住户,人很不错,知道我们要拍照,赶忙将楼上他家的几扇窗子都关上,并且还要下楼把晾在院子里的衣服都收起来。我赶忙告诉他不用动,我们要拍的不只是藏书楼,而同时拍摄这些文化遗址今天的现况。
潘祖恩当年在此建竹山堂,在咸丰和光绪年间就已有名气,《吴县志》记载,“(竹山堂)蓄书至四万余卷,皆手自钩校,分部而处”。他所藏4万卷藏书都归其后人潘承厚和潘承弼兄弟,而兄弟两人又将竹山堂更名为宝山楼,更名的原因也有一段书林小掌故。
民国十八年秋,苏州书市上出现了一部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由于此书纸色较差,所以市场上都认为这是明代的翻刻本染纸充宋,而无人购买。兄弟两人经仔细研究认定这是宋版无疑,花了200元以明版书的价格买了下来。后经许多藏书家鉴定都认为是宋版无疑,为此兄弟两人也惊喜不已,特为此将祖父的竹山堂改为宝山楼。这部书在民国年间被大藏书家傅增湘在潘宅见到,也认定是惊世秘籍。
竹山堂原藏书4万余件,经过兄弟两人的努力,在鼎盛时期宝山楼的藏书达到了30余万卷,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藏书楼了。可惜好景不长,正当兄弟两人努力收书之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宝山楼遭到了炮火的袭击,部分藏书被炸毁了,兄弟两人避难到了上海,家中书又遭到了盗窃。正在这困难之时,潘承厚又在上海病逝了,年仅40岁。连遭打击,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潘承弼陆续将余书出手,其中大部分归了合众图书馆,而此馆在解放后又由张元济等人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其余宋元部分在解放后由潘承弼捐给了北京图书馆。这基本上就是宝山楼的结局,也是中国大多数藏书楼的结局。
现在有许多人讴歌这种藏书楼的结局,认为这是“化私为公”,我不这么看。民间藏书楼的继承正说明了人民对文化的崇拜,在这里古籍不只是可读的一部书,而是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崇拜。现在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崇拜,不也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
抗日结束后,潘承弼先生经其姐夫顾延龙先生介绍,到合众图书馆工作,后一直在上图工作,在晚年仍写许多研究古籍的题记和书跋。这是我所拜访过的30多座藏书楼中惟一一个还健在的楼主了。
编者手记:
中华大地曾有过数以千计的藏书楼,但随着岁月变迁,现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大都岌岌可危。近年来,也不少听闻一些藏书楼将要修复或复建的消息。不管怎样,至今幸存下来的藏书楼及其珍贵藏书,应该得到政府的重视与保护,保护是为了展示中华文化的遗迹,再现藏书文化的历史。读书、藏书的活动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更多的人参与才是根本。
链接
浙江宁波天一阁
明代著名藏书家范钦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共藏7万卷明刻本。是当今全中国收藏地方志最多、最完整的地方。其收藏的370种明代科举录,占全国总产量的80%。
浙江湖州宋楼
晚清末期湖州人陆心源所建,藏书总数约有十五万卷。陆心源后来将湖州月河街老宅一分为二,其一取名“宋楼”,专藏宋代、元代的旧版书;其二取名“十万卷楼”,专藏明代以后的秘刻及精抄本、精刻本。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因经商失败,在1907年将其家中最精华的大部分藏书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
建于清乾隆年间。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
山东聊城海源阁
清道光二十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
浙江杭州八千卷楼
丁国典所建,因慕其远祖、宋代丁藏书八千卷,而名其藏书楼为“八千卷楼”。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毁于兵燹。丁国典之孙丁丙沿用楼名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千卷楼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 、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入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