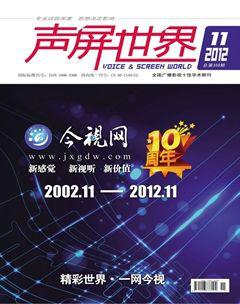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古装片电影意识形态的“表达”
2012-12-28谭征
谭征
意识形态是一整套的政治话语观念体系,统治阶级要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而电影正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法国学者阿尔都塞1970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强调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文化和传播媒介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功能是向个体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接受现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在生产关系体系内“自愿”接受社会角色,以非武力或非强迫的方式迫使个体服从现存社会关系。①电影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无论就电影的生产机制、表现内容和形式以及电影的基本装置而言,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电影既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也生产这种意识形态。
然而,新世纪以来,备受国内电影市场青睐的古装片似乎越来越多地展现大众文化的流行、消费主义的盛行趋势,让电影中意识形态的呈现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
新世纪古装片中意识形态的“缺失”
古装片是国产电影的一个重要样式。所谓古装片,是指其叙事时间和背景是古代的,但不同于历史片那种基本上按照史籍记载的线索,遵循“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叙事原则,而往往在人物和事件上进行大胆虚构,充满着一种传奇色彩。②
陈凯歌的《赵氏孤儿》中对程婴、屠岸贾等进行了颠覆传统的塑造,程婴是一个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的有着几分无奈的小人物,毫无以往的疾恶如仇和大义凛然。他是简单的,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只是想好好地活着,把赵氏孤儿带到仇人面前,然后让赵孤一剑砍了屠岸贾。影片似乎整体上是在讲述程婴如何十多年来“卧薪尝胆”,实现个人的复仇计划。另外,二元对立的叙事表现也被打破了,作为坏人的屠岸贾也被重新塑造成了一个散发着人性色彩的人物。他痛恨赵家却不愿伤害庄姬,面对身份已被自己怀疑的“义子”的求救,他铤而走险出手相助。影片摒弃了宣扬正义与民族大义的复仇意识,注重个人的情感宣泄。
一些追求暴利美学的影片注重发掘动作和场面的形式感,却忽视或弱化了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③《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可以看作是通过暴力消解意识形态的代表。影片中对暴力的展示几乎完全脱离了道德制约和价值内涵,变成对于暴力的坚定信仰和狂热崇拜。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皇帝用皮带活活将小儿子打死,就叙事方式而言,影片都采用了“模糊立场”的方法。我们很难做出具有倾向性的道德判断,究竟哪一方才真正代表正义,哪一方明确象征着正义和良知。暴力场面除了用特技吸引我们的眼球之外,没有给人们以基本的道德遵循和价值标准。
恶搞片明显的娱乐倾向,让意识形态的内涵更是容易被忽略、削弱、分离甚至走向对立。影片《越光宝盒》移用了一些电影叙事片段,充满了对近几年公共事件、传统文化的调侃、消解甚至反讽其原有的意义。例如,影片中捕快们在竹林中追逐山贼“清一色”时,山寨了奥运会上李宁的点火仪式,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重大事件拿来戏仿,消解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火仪式的神圣性;片中有一段曹操吩咐手下人给赵龙奶粉时说道:“给他三打奶粉,你知道是哪种牌子吧。”对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进行了隐喻式地调侃,和网络一样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表达。此外,对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古代名人,也进行了恶搞,使其身上承载的气节、精神荡然无存,如刘备训斥关羽“又在看黄书”等等,武将的英勇完全被恶搞进了“色情”的元素。
可以说,一些影片抓住了观众对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疏离,在影片中不再明确地表达强烈的阶级性诉求,而是表现出经济社会语境中的商业实用主义,以及在文化语境中的消费主义。
新世纪古装片意识形态的“在场”
古装片虽然是最能避开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类影片,其影视文本中虽然出现了淡化、对立甚至反意识形态的表达,但并不是完全对“意识形态”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一些古装片仍然试图通过真实表现或者以现代观念改编的方法,对观众进行某种意识形态的“询唤”。它们没有采取极端的方式,而是将其中的政治意图含蓄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尽量避免国家权力对意识形态建构的直接干预,但意识形态的“去宏大化”在根本上也只是一种方法,其最终还是为有效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所用,毕竟作为电影就无法避开意识形态的问题。电影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因此,一方面这种设置不但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同时,从观众深层心理来说,也符合大众文化的基本诉求。“英雄”的最终被追认,符合观众对于英雄的潜在期望,也能在更大程度上真正产生电影所具有的抚慰功能与“世俗神话”功能。
《英雄》华丽的画面造成了叙事的弱化,人们难以把握其故事主题,但最后的谈话还是表现出了契合“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影片使用的“天下”这一词语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天下”使得处心积虑的刺客放弃刺杀秦王变得有理。虽然这一转变在叙事上给人感觉铺垫不够,逻辑不强,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归于对中华民族“定于一”的传统价值进行传播和推广。
《孔子》的口碑不尽如人意,抛开其票房收入和观众反应平平不谈,可以看到影片没有自始至终贯彻一种主题,导演和编剧通过历史人物的重新把握,采用了英雄叙事和理念叙事,以展现一种符合现代社会语境的意识形态。
首先,影片彰显了一种“国家主义”情怀。影片主要讲了孔子的几个故事:从“孔子仕鲁”“周游列国”到“孔子归鲁”等。在影片的上半部分,给孔子设置了一个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的环境,将孔子塑造成一个事业、思想和生命都与自己的国家——鲁国的内政外交和与统治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孔子成了救百姓于水火,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另外,影片中孔子成为“国家主义”政治实践的激进政治家。在“孔子仕鲁”片段中,围绕一个对内强化中央集权、对外抵御强齐的国家主义路线斗争的故事,大量使用了“善恶二元对立式”的剧作强化“国家主义”的寓意。其次,影片的下半部分中,孔子的主角地位弱化了,但通过讲述其学生的一些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传统道德价值观。例如,颜回为挽救书简牺牲,表现出了尊师重道的观念;子路为保护卫国幼主而遇害,体现的是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冉有率兵打仗挽回鲁国败局,弘扬了一种爱国主义情怀。影片通过孔子学生的种种举动,体现出孔子的精神理念,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期望。
《画皮》属于一部虚构类型的古装片,它借用了聊斋故事的外壳,但是在古代背景下讲述了现代家庭婚恋问题、多角恋问题,其中所潜藏的现代婚姻家庭的伤痕,却不言而喻。然而,虽然影片反映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家庭婚姻危机有契合,但是结局还是给观众画了个理想主义的“团圆结局”:小唯虽积极攻占爱情,但是最后只能在绝望中长啸,一切都是那么真挚与痛楚。影片要给观众一个符合传统婚恋观和社会道德的交待,于是影片最后下了一个结论:所有人必须符合体制,符合各自的身份,符合道德规范。影片符合中国人鉴赏心理习惯,为第三者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完成了影片的走向“人间正道”的“说教”意义。
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变换
新世纪以来,随着消费主义、全球化等思想观念盛行,具有古代故事背景的古装片也不再和以前传统的古装片一样,类型和题材单一,通过直奔主题的叙事方式,表达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重塑型古装片、虚构型古装片,抑或恶搞型古装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有了新的表达方式:要么继承传统古装片的叙事特点,鲜明弘扬伦理道德、家国情怀的主流意识形态;要么通过改编我们所熟知的故事,融入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淡化“宏大叙事”,发掘“微观”的情感;要么采用一种复调式叙事策略,对故事内容进行多重编码,影片既承担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又通过个人化叙事杂糅了个体生命价值观。另外,那些走纯娱乐路线的恶搞古装电影,它们完全消解、颠覆了对“意义”“价值观”的倡导,一味想将人们“娱乐至死”。
然而新世纪以来,无论古装片在内容题材、类型、叙事策略上有多少变化,对意识形态的表现有何种不同,但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品,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表达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先并且主要是利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虽然在终极意义上讲,它只是淡化的、隐蔽的,甚至是象征的。④影片中出现的“国家主义”、“天下”意识,自然是直接对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诠释;而其中出现的个体价值理念,虽然看起来消解、淡化了宏大的、崇高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实则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理念。另外,恶搞古装片虽是最不承担意义的作品,但仔细想来,它们却是通过“搞怪”“调侃”甚至反讽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缓解激烈竞争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并通过与观众站在“统一战线”上给他们一个宣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的“出口”,在欢声笑语中麻痹人们的意识,放松其对社会的警惕性。古装片在合法化、世俗化的框架之内,完成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化。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
① ④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700页,第702页。
② 范志忠:《全球语境古装片的类型化困境与突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1)。
③陈 颖:《论暴力电影中意识形态的缺失》,《淮海文汇》,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