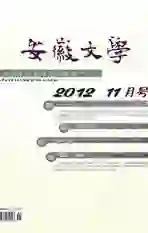固镇
2012-12-18金萍
安徽文学 2012年11期
固镇是一个地名,是淮北大平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坐落在京沪铁道线上,南临南北方气温湿度分水岭淮河岸边的重镇蚌埠;北接兵家必争之地陇海线上的枢纽之城徐州。两座城池似乎都与战争有关:徐州是解放战争中有名的淮海战役中心,至今还建有雄伟的淮海战役纪念馆供人瞻仰;蚌埠更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渡江战役的前线指挥所所在地,又称总前委。至今还有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旧址——孙家圩子纪念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了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脚踏徐州大地,心头感慨万千!那遍地金黄色的银杏叶让我惊叹不已!从徐州坐火车返回的时候,途中路过一个小站:固镇!当火车一节节倒着回行时,我看着车窗外满眼的寂寥仓皇,心里想:还有这样一个寂寥的地方?
做梦也想不到,就在那个苍黄的秋天,我揣着一颗仓皇的心,调到京沪线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来了!
有人说,人生就是不断的迁徙。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次迁徙组合而完成的。说得轻巧,殊不知每一次迁徙都凝结了当事人辛酸的泪水和锥心的疼痛,那些疼痛的伤疤该需要多少岁月才能抚平愈合?
1985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涡河岸边的一所农村中学里,从来没有过的热闹!那正是我们要搬家走人了。
调到哪儿去了?有人高声问。
到固镇去了!
固镇在哪里啊?
不知道。没听说。
远得很啊!肯定是鳖不下蛋的地方!
从听到这句话开始,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一直到搬家的卡车开出校园,我终究没敢睁开眼睛。
是啊,固镇在哪里?就是火车上看到的那一片寂寥苍凉吗?
车子上坐着我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还有我工作多年积攒的家产:一张为了迁徙搬家新买的铁床,一窝开春新养的仔鸡,一捆去年深秋薅下来的棉柴,还有两只瞪大了眼睛望天的小乌龟。
车绕荆涂二山跨涡淮二河,没多久,就快到固镇地界了,这一片片垄垄相连的土地,都属于皖北地带,连地名都带有皖北风情。你听听:苏集、何集、陈集、鲍集、火庙瓦坦集。皖北的地名大多都是这样,不是什么集,就是什么庙,或者什么圩子、什么湖、什么寨、什么铺子、什么庄子、什么台子等等。
固镇是个典型的皖北小县城。说它小,是因为全县人口只有五六十万,县城也就几万人,土地总面积只有1450平方公里。城不大,水却多。自北向南有属于崇潼河水系的沱河、浍河、泻河、北淝河,还有新开挖的人工河怀洪新河。南端的北淝河属于淮河水系。境内水源丰富、水质好、储量大。城边的浍河逶逶迤迤地贯穿全境。
来到固镇之后我才知道,这里的地名和其他皖北各县有很大区别。我前面说的那些皖北地名特色,在这里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这里的村子有叫“钓鱼台”的,刚听说时,我一下想到中南海的一个地方,禁不住心生敬意,怀疑此台与彼台有没有什么联系,说出来后被人笑为脑子进水。县城南去不远,有个乡叫“磨盘张”,这个名字有点像外文的排序,姓在后,名在前。这在北方农村并不多见。但在固镇的方言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后置句式,比如:吃过了吗你?烧开了吗水?至于为什么叫“磨盘张”?是此村盛产“磨盘”,还是主要加工面粉?我没有更多调研,不敢妄加论断。公平乡、清凉乡、仲兴乡、王庄刘集曹老集、宋店壕城新马桥,前三个乡名含义清新大气,代表了当地农民的内心向往;中间的三个是皖北多用的模式,只不过曹老集是有些名头的,不可小觑,传说中三国时期,曹操曾在此屯兵、屯粮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一代枭雄随烟云而去,留下一个古老的集镇在淮北大地上续写遗篇。后三个乡名两个极点,小如“宋店”,是否就是宋氏家族的店,或者以此乡宋姓人为主?以前都是如此:一个村子诞生了,大户人家的姓即为村名,或者有钱人家的姓为村名,这和江南大不一样!江南以功名为重,如状元、探花、举人等等。江南多祠堂,功成名就之人,有了钱财大多归乡建祠堂立牌坊,把远亲近邻能上得了名录的全都一网打尽,列在祠堂里,述说先祖荣光,供后人学习和景仰。在皖北这种现象不多见,祠堂也极少。这或许就是南北两地的文化差异吧!但皖北多庙堂,解放前的时候,几乎村村有庙,大庙小庙土地庙,烧香上供敬神灵。庙里香火旺盛,村民求神不停。每年还有人山人海的庙会,到后来,那些庙会就成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场所。皖北地区地属淮河流域,大多是低洼地,多湖河塘沟、多沼泽。就固镇这个县来说,从汉初起,先后设置县、郡、州等十余处,至唐咸亨三年废尽。自金承安四年(1199)起,黄河屡次决口南下夺淮,导致水旱灾害频繁而严重。解放以前,这里曾经是土匪盗贼兴风作浪的地方。各地土匪拉夫抓丁、催款逼税、抢劫民财、奸盗邪淫、滥杀无辜。我刚来就听到一个笑话,说的是杨庙乡解放后选村长,选来选去找不到人,问其原因竟然是:这个村,没有谁没当过土匪。水患无穷,土匪横行,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文化传承呢?因此,多庙堂是留求神的,没祠堂就没有最简单的传承!比如农家的孩子,大多不知道爷爷的名字和辈分。上了三代,就等于在家族里消失了。这是很可悲的,一代人就顾一代人的嘴;一代人的温饱不能顾及,哪里还能顾上前几代魂的归宿呢?无数的先辈们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在后辈们的手里弄丢了。丢掉了先人,丢掉了我们的前世过往,也丢掉了我们微小生命出发的地方!写到这里,木然间陡生罪恶之感,连我也是不知道我上三代名字的,甚至连我的祖父都叫不清楚。是贫穷造就了皖北的风土人情,是水患造就了皖北人的粗砺困窘。
后几个乡除宋店、新马桥是皖北多见地名外,就剩下大名鼎鼎的壕城乡了!
说壕城你可能不知道,但要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说刘邦、项羽,你肯定是如雷贯耳。壕城其实不是城,就是一个乡村集镇,是壕城乡的乡政府所在地。这里有闻名中外的垓下遗址。垓下俗称霸王城,为楚汉垓下决战时项羽大本营和汉代洨国、县治所故地。垓下遗址北临沱河(古称潇水),遗址有四面坍塌的城墙,现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说这个遗址有多重要,一时半时纠缠不清,但是要说垓下大战的重要性,那可是读书人心里都明白的。先不说它是东方的滑铁卢之战,是一个朝代灭亡和一个朝代开启的交界线;单就说它与我们汉民族的关系就够惊人的了!若不是这场大战刘邦胜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那就没有我们汉民、汉族、汉字、汉文化;若是项羽胜了,我们就是楚民、楚族、楚字、楚文化了!楚汉之争千年过往,只留下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汉墓堆子,以供后人不间断的开发研究。年年岁岁风雨里,大楚儿男魂歌哭。垓下故地这几年愈发名声大震了,不仅仅是因为刘邦和项羽,也不仅仅是因为名扬中外的垓下之战,垓下之战同去年新发掘的中国最早的城址相比,在历史的遗迹中只能是小小的逗号了。去年这里发现了史前的古城遗址。全国哗然,当年就被评为国家级考古九大新发现。到此为止,没有谁再讥笑壕城没有城了。壕城不仅是个城,而且是个史前城,把中国的城市记载一下推前几千年!地上地下的遗存都在说明,固镇这个地方到底有多老逼!全国有吗?全世界有吗?没有!壕城牛、垓下牛,因此也就有了今日固镇县的牛!
壕城垓下的汉砖曾经名噪一时。那时,很多的达官贵人、行业名流,都想方设法讨要一块汉砖。有的说,可以作为文物在家摆着,提升家庭品位;有的说,这汉砖是制作汉砚的绝好材料。在垓下的出土文物中,珍品众多,如鎏金龟、弩机、契刀、蚁鼻钱、秦剑青铜矛等等,有的如弩机,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被省市博物馆收藏;县城文物所里也是馆藏满满。因为太多,文物的行列里从来就没把汉砖列上。那时的壕城,到处可见秦砖汉瓦,犁地耕田,遍野尽是铜矛箭镞。庄稼长在汉墓上,豆花开在铁釜里。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并不知道身边的汉砖是好东西。猪圈里,牛槽上,粪堆边,厕所上,到处都是。有绳纹的,也有带文字的!忽然有一天,无数的外地人马浩浩荡荡地开拔来了,这些外来的家伙油头粉面、长“枪”短“炮”,在壕城的大街小巷背朝天、眼瞅地,歪着头到处寻找汉砖。老百姓醒悟了,再也不像原来那样,随手把家院旁的汉砖无代价的送人。后来是要钱,并且愈来愈贵了!为了给朋友找汉砖,我曾经数次深入壕城腹地,夜探百姓之家,也曾经小有收获。但更多的时候是无功而返,遇上朋友不理解,而就此绝了交情的也大有人在。最后一次到壕城小住,是为了写固镇地方民间传说。那次我和县文化馆的老孙同行,白天忙了一天,夜晚住宿在供销社的招待所,填写登记表的时候,招待所服务人员问我们出差事由,老孙说,找故事!那人眼睁得就像铃铛似地说,俺这里没故事啊!你跑错地方啦!老孙说,没错,就是这地方!那人疑惑地看着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老孙见那人文质彬彬,就问他可知道“许慎”,那人说:干什么的?老孙说,曾在这里当过潇长!(固镇在夏商时期为淮夷之地,自汉起先后设置谷阳县、潇国、潇县,壕城就是当时的潇城,也有说是潇国的,许慎当年在此做潇长。)那人揉了半天脑门子才说,打从建县,我就在这里干!没听说过有个姓许的乡长!老孙说,写书的,写了一本《说文解字》。那人立刻说,这就更不对了,这里的乡长念书的都不多,更不要说写书了,我说,老孙,你别给人家出难题了,我对那人解释道:壕城历史上叫潇城、许慎曾当过潇长,就是那个写《说文解字》的许慎,那人听了我的话,仍旧嘟囔不已地说,我怎么就没听说呢?
那晚住在壕城,算是领略了古城的动静:风雨大作,夜黑如磐。8HbJ/SEn6PvyoujFmrXXnA==招待所的窗子破烂不堪,随着狂风无情地击打着枯旧的木边窗棂。乡村的夜声奇险怪异,是城里人无法想象的。风声尖脆刺耳,一会像疯女人长嘶,一会儿如狼狗狂吠,一会儿高亢亮响,一会儿粗沉低吟,一会儿像口哨,一会儿似军号,一会儿如千军万马,一会儿又如咽如泣。千百种怪声使我联想起那场惨绝人寰的厮杀,一个朝代的寿终正寝,无数儿男的冤魂归阴。是否正是这些沉寂了几千年的青壮年兵丁无家可归、飘流零落的魂灵,闹得我一夜未眠,第二天眼睛红肿了起来。我问老孙夜里睡得可好?老孙说,一梦到天亮。我说夜里可听到动静?老孙说,除了被自己的打呼声惊醒一次,别的啥也不知道。我说了自己的不眠之夜。老孙说,你是被刘邦、项羽的垓下大战迷住魂魄了!可听到兵士的哭声了?听到了!可梦见刀光剑影呢?没有,没睡着,哪有梦呢?
壕城的小豆饼子很好吃。多少年以后,还常常想起那油而不腻,脆而不粘的爽口感觉。只是那次的夜宿记忆使得我以后的日子里,轻易再也不敢夜宿乡间了。
壕城人叫吃不说“吃”,叫“赤”,讲喝酒喝一杯,不讲喝,叫“贺”,有时把喝一杯,也说成“斗”一杯。话一出口,就现爽劲,挺热乎的。
壕城城牛,可以算做中国现有城市的祖爷爷的N次方;壕城人也够牛,有一次,我带北京来的摄制组去拍淮海战役镜头,到了接近壕城的地盘时,有个赶牛车的挡了路。那时乡村大道不宽,连三米三也达不到。摄制组的大车小车还有转播车,轰轰隆隆一大串,赶牛车的老爷子在前面仰卧在架子车上,尽管后面的无数车辆喇叭声声,就是不让路。不让也就算了,还拿一条白毛巾蒙上眼睛,优哉游哉地哼着小曲儿,得得戛戛地扬起鞭子赶着前面那头老牛,那头牛甩着尾巴,就像在自己家院子里散步似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串铃铛,走一下就会叮当作响。摄制组的人没有办法,只得尾随而行。俗话说,没有文化,啥都不怕。可是,那天我分明看见躺在牛车上的老爷子上衣口袋上插着一支黑颜色的钢笔,要知道,当时插钢笔的已经很少了。一支笔足以说明老爷子是识文断字的。我们就这样尾随了一个多小时,急不得、骂不得!比农村吹喇叭迎娶新媳妇的婚礼车还慢。那一次的乡路之行,我是彻底感受到壕城的牛人之牛了!
在原来的老地图上,壕城一度隶属宿州的灵璧县管辖,到了1965年,为了改变以往黄河决口南下夺淮,导致淮流倒灌浍河,水患灾害频繁的现象,国务院于1964年10月31日决定,在宿县、灵璧县、五河县、怀远县的边缘交界部分设置固镇县。1965年7月1日,固镇县正式成立。由此可知,这个县城的许多乡镇,都是来自宿县、怀远、五河、灵璧。县城本来是没有的,是重新组合,因此我说它也是个迁徙而来的城,是个组合之城。它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完整的文化积淀,需要更多的包容整合和建立,需要在整合建立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自我。
前面我已经说了,固镇水资源丰富。辩证地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可变成水利,也可翻脸变为水患。固镇尝尽了水的甜头,也吃尽了水的苦头。
说固镇水多,并非空穴来风,还是要从地名谈起。固镇原名叫“固镇桥”(架在浍河上的大石桥)。传说是鲁班建造,张果老曾从桥上过。不管是真是假还是传说,固镇桥曾经一度是固镇的代称。
在固镇,称桥的地名还有很多,固镇桥、许桥、新马桥、一碑三孔桥、任桥……有桥的地方必定有水,没水哪里需要桥呢?
固镇不光桥多,还有许多地名足以见证固镇当年是水之乡。比如:石湖、陈渡、九湾、湖沟、稿沟、陈海子、单海子,还有大名鼎鼎的汾红江,你看,江河湖海沟都有了!特别是那条眼下一滴水也看不见的汾红江,来头可大了!
我到固镇的时候,曾经采访过县里的一个叫做“汾红江”的林场。这个场就因坐落在古汾红江古道上而得名。汾红江发源于今河南开封东的上集贤村,向东流入浍河,沿江串联着十八个湖泊,又称一溜十八湖。白驹过隙,沧海桑田,汾红江枯竭,众湖泊夷为平地。十八湖早已演变为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因此也就有了固镇境内的刘湖魏湖赵湖王湖田湖任湖路湖叶湖苏湖等等以湖命名的村庄。
汾红江的名字来头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当年刘邦、项羽大战时,刘邦带的家眷早晨在洗脸时,脸上的胭脂把水都染成了粉红色,因此就有了“汾红江”的说法。另一说是,江的上游直通隋炀帝后宫,是众多嫔妃和宫女的脂粉水染成了粉红色。其实,隋都不在开封,而在西安。也许这就是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王骄奢淫逸的罪恶罢了。
如此之多的河湖江沟海给这个皖北之地的小县城带来了灌溉通航之便利,但也常常患水灾。仅我在固镇那几年,就不断的抗洪救灾跑乡下。哪一年若是没洪灾,那必定是旱灾或者风灾虫灾了!1991年淮河发大水,固镇县连连告急,就是因为要在境内的周集乡炸坝行洪,省市领导、舟桥部队、抢险民工、预备役、悉数到位,箭在弦上。可是,村里的老百姓还没有全部撤出。省市县的各级工作人员一次次、一趟趟地进村劝解说服,终于把村民们从家里劝了出来。炸坝行洪是舍小家保大家之举,村民们是理解的,他们虽然哭哭啼啼,但还是拖儿带女走出了家门。他们亲眼看见了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辛辛苦苦垒起的家园是怎样在刹那间白浪滔滔,一片树叶都不见的。若不是亲历,我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份不舍。那次炸坝行洪,我亲眼看到了《常郢人的眼泪》,看到了武警部队浪里穿行的《生命之舟》,看到了曹老集高老家被水淹没的土地上《蛇鼠同栖坟顶树》的凄惨场景;难忘大水中撑船的艄公《周老大》;难忘打赤脚在水里指挥多日的妇女主任和县长书记,还有水利系统的工程师、技术员、工程队;更难忘那里的享受水利和遭遇洪灾的老百姓!那一年的抗洪文字记述,在我的写作经历中,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是因为发表,主要是经历。一个亲历行洪炸坝、亲耳听到洪水吼叫、和灾区共度难关的记忆对一个文字记述者是至关重要的。
不光是洪水来临,水患无情。就是平时的年份,涝灾也是频频光临。春季连阴雨、夏季连阴雨、秋季连阴雨,暴雨、雷暴雨、冰雹,多如牛毛。有一年雷暴雨,刘庄的村民在未装门窗的毛坯房里休息,一个笆斗大的火球突然滚进屋内爆炸,当场击死一人,另两个休克的也只救活一个。暴风雨和冰雹袭击的灾害常常困扰着这个县的干群,其实何止是水患,这里的干旱、蝗灾、虫灾、风灾也是极多的。自然条件的恶劣,资源的匮乏,就决定了固镇总是要花费比别的县更多的精力和心血,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收获或许比别人更微小的成绩。在固镇的民间语言里,就有关于县级领导的许多版本:据说建县初期,全县只有一部吉普车。除非重要会议,重大事件,谁也不敢轻易动用。书记下乡照样骑自行车。想那时,书记县长骑着自行车下乡检查工作,一溜儿车铃叮当一串儿笑声飞扬,不用警车开道,不必随员陪同,不用专人讲解,不必结伙儿迎送。书记认得路,县长认得工程;书记了解庄稼,县长知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行情!那时的书记还会修车,骑行半道,链子掉了,书记跳下车,歪着头倒腾来倒腾去,沾了两手油泥,抓了一把道边的细土,使劲的在手掌中搓搓,然后抹了一把汗湿的额头,正想骑车赶路,却见到对面的薅草农妇叽叽嘎嘎的笑,原来书记被自行车油污的黑手如此一抹,已成大花脸了!民间语言的版本还有更加离奇的,现代人听来可能都觉得是天书!
说的是建县以来其中的一位县委书记。他不光是骑自行车下乡布置工作,检查三夏和三秋,他还有俩宝贝:粪箕子、粪铲子。那是一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怎样才能广积粮呢?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就是这个县委书记,每天早晨起了个大早,背起粪箕子,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拣拾人畜遗留的粪便。估计那时的对话应该是:书记早!你早!拾粪哪?是啊!很多的记述无法依靠想象,因为真实的存在可能更有合理性,我无法依照今人的感觉去完成过往的遗存;我也无法依照今人的价值观去判定书记的工作细节,但凭我朴素的猜想,当其时,书记这样做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很正常坦然的。他认为那样做是工作需要,群众也没觉得他是做秀,是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诞生出“做秀”和“形象工程”这个词。
那时的固镇县城很小,主街道就是一条。有人形象地说,东头喊话,西头就听见了。县委大院也不大,像过去的老式兵营。四方四正,中规中矩,路东路西,对称排列。院里遍植苍松翠柏,花草树木。房子都是老式大屋,就像我们小时候看惯了的公社大礼堂。不管地点大小,房屋样式新旧,但里面的一任任领导,一届届主持,就是在这里打理着全县的治县大业,带领着全县的老百姓与贫穷落后与自然灾害,做持久不息的斗争。自然灾害危及群众,也打造了干部。为完成闸坝桥涵工程,一批批、一届届的人物在老百姓的传说中留下永久的记忆。固镇县的土地大多属于砂礓黑土,分布在三河两岸和平坡洼地,建县前水利工程少,涝灾多损失大,人穷地漏。县领导和水利部门走访群众听取民声,做出了如此的规定:即在湖洼地万亩左右开挖一条大沟;千亩左右开挖一条中沟;百亩左右开挖一条小沟。并将大中小沟相连,构成了完整的排水网,定名为“三沟一网化”水利工程。大挖沟渠、除涝防旱;加厚土层、改良土壤;建闸蓄水、发展灌溉。连年的兴修水利,基本达到了“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要求,粮食生产有了保障。那时开挖的三八河、珍珠沟、沱浍新河、九九河等十七条骨干大沟在皖北是大有名气的!三八河以女青年为主开挖,培养了一批著名的铁姑娘,这批女青年成了固镇县多年来用之不尽的女干部源泉,县乡级不说了,正处级许多,省部级也大有人在。这些女干部大多都是工作狂,我亲历的就有几位。那时还不讲究衣着打扮,她们大多就像渡江侦察记里的女连长,短发短衫、一身短打。上工地、下农田、扛挑走跑全都不在话下,特别是午收三夏,机关里的干部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女干部的厉害就显现出来了:她们弯下腰来就不见站立,呼啦呼啦地朝前直窜。一天下来,原来白白的面孔全都成了猪肝色。所以后来机关里的男人们就说,再美也禁不住一天晒,不信就试试。也才有了:脸白是抹的,发黑是染的,双眼皮是拉的,丰乳是垫的,细皮薄肉是圈的,小鸟依人是做给外人看的。女干部也不让人,说机关男人攒私房钱“几毛几块兜里攒,办公桌里有机关。哪天小偷红了眼,一夜成为穷光蛋!”你还别说,这话真应验了。有一次,组织部办公室夜里上了小偷,接连撬了几个科室的门。损失惨重,却又有口难说。攒私房钱是机关男人的共性,不攒的少。其实这种积累也算不上恶习,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少生气。女同志若是想得开,应支持男人的这种积蓄方式。
过去常讲男人是山,女人是水。但在固镇,给人的印象总觉得女人是山,好像是女人当家做主的机会总是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人当家还真当得不错!那时有一个女行长,说话风风火火,干事雷厉风行。别说去开她后门了,从前门进来都怕挨熊,公事私事都是铁着面孔,人称铁娘子。还有一个女县长,每次她开会,各单位的领导参加时都很紧张。那时开会松懈惯了,总是八点开会九点到,十点不耽误听报告!但是轮到她可不行,谁晚了,就得在门口站着。所以有好多次,某单位参会者一看表,过了进场时间,立刻就不敢再去了,惟恐挨熊!她要是熊起人来,那真是一点面子也不讲啊!大老爷子们,大小戴着顶乌纱帽,平时都是长着一张熊人的嘴,这时众目睽睽被人熊、况且还是一个个子不大的小女人,你想,谁能受得了啊?说不清是从哪一届就开始配备了女县长,名气大多还不错,是否与固镇这个地方水特别丰盛有关呢?不敢断定,这话有些离题了,就此打住。
固镇的官员还是男的多,中国到底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小小的固镇焉能例外?到此为止,就没有过一个正职的女县委书记,都是配角的多。男性官员也不错,男的有男性的优势。传说中有个副县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下乡吃喝都到农家院。所谓的吃喝,就是咸辣椒就窝窝头。县长同志检查下乡,到了大中午,看到一建筑工地上,几个农民兄弟正在房壳廊子里喝着一元钱一斤的老白干,就走过去一起捏着花生米、大辣椒干了起来。那时,农民见县长很容易,一块吃大馍喝凉水很正常。农民兄弟拿县长当正常人,吃喝拉撒都是一样的,县长要是喝多了,就让他在房壳廊子里头枕苫房的木耙睡下。什么话都可说,什么意见都敢提。吃过后县长说要丢下几个钱。农民就说,曳个熊吧!你和俺一起吃,就是看得起俺们大家了,俺们面子就比脸盆还大了,回家吹牛都有话了,还要个熊的钱吗?更有个初小毕业生,当时任小队会计,算得上是村子里的文化人,他的解释更叫人啼笑皆非。他说:语录说,什么叫干群关系,干群关系就是鱼水关系;什么叫鱼水关系,说白了,就是鱼和水的关系;老百姓就是水,干部就是鱼,干群鱼水情,鱼喝水是正常的,鱼不喝水喝熊吗?不喝水才是不正常的!这么一想,就能理解干部吃群众了。小队会计说完了,觉得说得很有学问,正想讨个表扬,不料被县长一巴掌拍在屁股上,“熊孩子,一嘴胡吊扯!要是文化大革命,就凭这几句话,你就管进去喝稀饭了。”这都是过去的老段子了,现在可就远远不行了。现在还有谁敢这样和县长对话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那时经常下乡,和许多大队干部混得较熟。记得有一次采访大河大队的书记,人称大河老母。讲起他的名字,知道的不多,但说起老母,方圆几十里,妇孺皆知。挨过穷受过伤、抬担架送军粮、互助组高级社,老母是大河村第一任村长。先领一个村子干,后领几个村子奔。大河村紧临浍河,两千多亩土地有一千多是河湾地,每逢阴雨连绵,河水猛涨,颗粒无收是家常便饭。老百姓说,浍河湾啊浍河湾,十年就有九年淹。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那些年,老母经常跑到外淹内涝的河坡地上发呆,听着群众的顺口溜:大河村大河村,一年到头累断筋。屋里没有隔夜粮,口袋难翻三五分。解放的锣鼓敲了多少年,老百姓的日子改变了多少?老母常常自责,自己这个支书咋当的啊?老母开始寻找致富路了,村里办起了铁木业社、垒起了小鸡炕房、河坡地盘起了小窑厂、建工队、铺路队、运输队、面粉厂,为村里拉电修涵闸、建学校、修公路、建旱涝保收的电灌站,大河的穷帽子终于甩掉了。老母数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有一次,省市记者拿着介绍信到城北区塘南乡采访他,问到“何金昌在哪儿?”几乎所有人都犯愣:何金昌是谁呀?
好多年过去了,常常回忆起在大河村头听老母大叔讲村子远景规划时神采飞扬的样子;也常常念起浍河湾里那次老白干大战:那是一次男人的对决,为了一个项目,老母大叔一气干了一斤老白干。扔了瓶子、抹干嘴巴,仰天长啸,“我们要二次翻身!”
老母是个农民,是个地地道道没有文化的农民。今天,像这样立志于农村彻底改变翻身的地道农民还有多少呢?以前的老母有一群青年粉丝,只要是他一声吆喝,就会有无数响应!那些年轻人要跟他奔富路走,有青年就有力量,就有希望;若是今天,老母还有那么多的追随者吗?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前些日子下乡听到的段子,说的是市领导带人来乡间考察,当然肯定不是大河村。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稀稀拉拉的老弱病残们。领导来了,当然要找几个人来座谈一下,了解当下农村情况。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走了,村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只好动员老年人出来应酬着。老村长、老书记,再加上一个老妇女主任。气喘吁吁地到村头把领导迎接到村办公室坐定。领导问,我们主要想了解一下你们村子GDP(鸡的屁)情况。三位村干部听了以后莫名其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领导说,没关系,直话直说吧。三个人还是东瞅瞅西瞅瞅。互相看几眼之后,老村长挺起胸膛,颇有些大义凛然地站了起来,愤愤地看了其他两人一眼,咳了一声,清清嗓门道: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们村鸡的屁情况是这样,年轻人都走了,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干得慢,进度不行。但我们村牛的屁统计了,猪的屁也统计了,就是鸡的屁还没弄好。为啥呢?小鸡这几天正好出窝,全村有多少只鸡都还搞不清楚呢。这事也怪我人老脚慢造成的。但我敢保证,等你们下次来,全村剩余人挨个摊派任务,哪怕把小鸡宰了,也要把鸡的屁统计好,给我们市争光,汇报完毕。
真是难为了这个老村长!像这样老村长遇到了新问题的例子,在当下农村还真不少。天高皇帝远,神经末梢谁来管?
事过境迁,现在的村长也拿工资了。还有不少村长已经开起了轿车,跟县局没啥大区别了。更有靠近市、县城边的村干部,因丰富的土地资源也出现了几百万的巨贪。像老母那样累死累活拼命干事的村官到底还能有多少?不得而知了。
一个地方因有水而灵动。固镇,河、湖、沟、渠贯穿全县,因水而丰富,因水而丰收。这才有了固镇的人才辈出;但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因水而多灾多难,因水而年年抗洪,因水而留下的遗憾也不少。成也水,败也水,成成败败或许就是一代代的生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