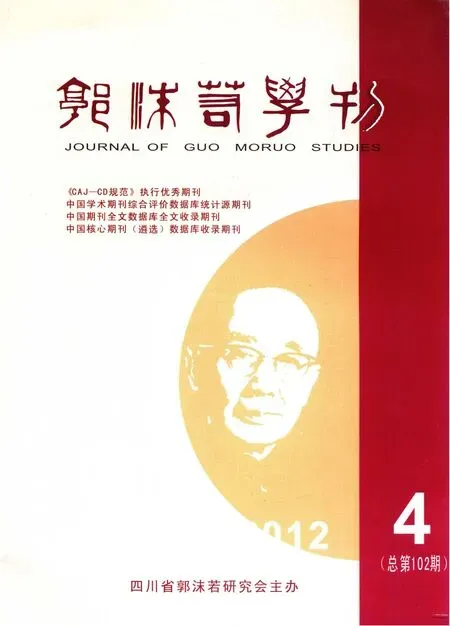略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崇高美
2012-12-18朱立元王文英
朱立元王文英
(1.复旦大学 中文系 200433;2.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 200020)
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六大历史剧的社会学价值已经举世公认,这些历史剧的艺术成就和特色也得到了较细致的剖析。本文将着重从总体上探讨它们最重要的审美特质,即崇高的悲剧美。
首先必须指出,郭沫若这六部历史剧全部采用了悲剧样式。除《屈原》外,它们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所以,可以把它们称为历史悲剧。但是这些作品并不给人以悲惨凄凉的感受,恰恰相反,它们在人们的心头激荡起一股悲壮激烈的情怀。
中外悲剧史上大体有两种不同质调的悲剧:一种以悲为主,着重写人物的凄苦命运。通过无辜的主人公被黑暗势力迫害、吞噬的悲惨事件来激发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谴责旧的伦理道德,抨击社会的冷酷和不平。如我国的元杂剧《窦娥冤》《汉宫秋》,现代悲剧《雷雨》《日出》,歌剧《白毛女》等;西方近、现代悲剧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奥尼尔的《毛猿》、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在悲剧美的质调上大致可归入这一类。
另一种以壮为主,着重写人物对命运、对权贵、对不合理社会的抗争,虽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主人公最终仍摆脱不了悲剧下场,但回荡于剧中的却是昂扬壮烈的斗争精神,它们不仅博得人们的同情,更加激发人们的斗志,它们给人的不是凄惨哀伤——而是感情的震撼与高扬,表现出一种悲壮崇高的质调。如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歌德的《浮士德》;我国的古典悲剧《赵氏孤儿》《清忠谱》《桃花扇》等,大致可归入这一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第二类悲剧,才是典型的悲剧。因为典型的悲剧,必须与审美上的崇高相通。悲剧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悲,痛苦的命运、残酷的结局,甚至尸横遍地,并不必然是悲剧的特征。悲剧必须让它的人物,以积极的迎战姿态,去经受严重的考验,战胜痛苦,并使人物在经历严重斗争的冲突中,焕发出崇高的精神,从而使观众在感受中,把痛感转化成快感,即悲剧的崇高感。因此悲剧的本质在于:必须创造崇高。
席勒在美学史上是较早自觉地把悲剧与崇高范畴联系起来的美学家,他从心理学角度指出:构成崇高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一个生动的痛苦表象,以便引起适当强度的同情的情感激动;第二,反抗痛苦的表象,以便在意识中唤起内在的精神自由。只有通过前者,对象才成为激情的,只有通过后者,激情的对象才同时成为崇高的。”席勒的意思是,崇高的前提是对痛苦事物的同情,但只停留在同情上并不能形成崇高,只有人的内在道德意志对痛苦表象进行反抗,并压倒痛苦,体现出人的道德自由和精神胜利,同情感才会升华为崇高感。席勒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悲剧艺术,他认为:从这条原理中产生出悲剧艺术的两条基本法则:“第一,表现受苦的自然;第二,表现在痛苦时的道德的主动性。”[1](P194-195)他肯定悲剧是崇高的艺术,并指出悲剧的崇高美来自于表现痛苦的对象、以及主体的道德意志对痛苦的超越和克服的过程。可见,崇高感的质调是由痛感向快感转化,是正义感压倒痛感后升起的一种自豪和喜悦;这就从审美心理角度说明了悲剧何以悲而不伤、痛而不哀,反而给人以自豪的快感与壮烈的美感。应该看到,席勒对于悲剧本质的阐述,还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展开的。恩格斯则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加强和发展了悲剧本质的意义,他指出,悲剧应当表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2](P560)。恩格斯的这一科学阐述,深刻地揭示悲剧性冲突的社会历史内涵,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悲剧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
在我国现代话剧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很自觉地追求悲剧的崇高美的剧作家。他认为:“悲剧在文学的作品上是有最高级的价值的”[3](P318-319),“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4](P165)。郭沫若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和他卓越的艺术才能的结合,就产生出了他的悲剧的崇高、悲壮、雄浑的审美特质。
占据郭沫若抗战悲剧舞台中心的,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如那撼天地、惊鬼神的民族灵魂屈原,那舍生取义、抗斗暴秦的英雄聂政、高渐离,那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还有那些为真理、为正义而殉身的女豪杰聂嫈、如姬、阿盖妃及酒家女等形象。这些人物都有优美的人性,高尚的情操,而且在风云突变的历史转折关头,都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倾向,因此他们的斗争动人心魄,他们那为真理而舍生忘死的英雄举动壮怀激烈,感人肺腑。这使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表现出英雄悲剧的鲜明特色。
郭沫若按照悲剧崇高的审美需要,从两个方面构筑了表现他的英雄们的伟大痛苦和崇高精神的悲剧舞台。他从广阔的历史背景着眼,努力开掘悲剧冲突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质的方面揭示出悲剧的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另外,他又在量的方面加深加重了人物所面临的斗争的困难,让他的人物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以便他的英雄们有用武之地。
郭沫若曾经批评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他说:“剧情系由误解而成为悲剧,悲剧既无必然性,因而也缺乏历史的时代意义。”从这句话中很可以把握到郭沫若注重社会历史本质揭示的悲剧观。他认为:“革命时期是容易产生悲剧的时候,被压迫阶级与压迫者反抗,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一切的反抗是容易归于失败的。阶级的反抗无论由个人所代表,或者是由团体爆发,这种个人的失败史,或者团体的失败史,表观为文章,便是一篇悲剧。”[3]
可以看出,郭沫若主张悲剧必须表现重大的历史冲突,必须反映出那代表历史进步的新生力量产生和壮大的“历史要求”和“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必然性。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它的深刻性。郭沫若强调屈原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还是楚国的悲剧,甚至还是中国的悲剧。
他就是在这样一片时代悲剧的基调上展开他的历史悲剧的画幅的。
郭沫若有四部悲剧是写战国时代秦灭六国之争的,当时,要求统一是大势所趋,但是由谁来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则关系到整个民族历史的发展。在郭沫若看来,秦虽然统一了六国,但它并不代表历史的新生力量,秦始皇残暴地屠杀各国人民,因此他只是用一种新的枷锁去代替了旧的枷锁,最终是违历史意愿的,秦二世而亡绝不是偶然。但是,屈原则与此相反,他以诗人赤诚般心怀,关心人民的疾苦,又以政治家的胆识,识破张仪的阴谋,从某种意义上看,屈原是为了阻止历史车轮的逆转而竭尽全力。屈原是一个自觉地意识到历史责任的,“以天地之心为心”的民族灵魂。他的主张把人真正当作人的思想代表着战国时代的进步思想。因此,如果以屈原的思想统一中国,那么中国就会走上一条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的历史道路。然而,由于楚国君臣奸佞的阻挠,酿成了一个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从这样的历史高度上,透视出屈原斗争的伟大意义。与屈原在同一条战线为民族前途而战的,在郭沫若的笔下还有聂政、信陵君等。郭沫若竭力突出这些人物斗争的正义性,让人物处在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焦点上,也就从质方面,规定了这些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所进行斗争的严正性,而奠定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崇高的审美基调,表现出了他的悲剧的历史深度。
如果说从质的方面揭示悲剧本质可以表现其深度的话,那么从量的方面,加大悲剧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则可以加强悲剧的力度。在这点上,郭沫若是充分自觉的。几乎在每个悲剧中,他都在悲剧人物的对面,树立起形形色色的、有权有势的反面角色。这些反面人物为了维护他们暂时的私利,拼命地维护腐朽的制度,破坏和抵制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措施,他们和立足于民族前途的志土仁人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利害冲突,双方的矛盾呈现为复杂的胶着状态。这就展示出悲剧人物面临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等和秦使张仪,内外勾结,愚弄利用昏君楚怀王,在屈原的周围交织成一张巨大的诬陷网,用卑劣的手段,破坏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把屈原一步步地逼到真狂的边缘还欲置之死地。魏王和韩相侠累,甘愿称臣于秦,他千方百计地打击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信陵公子、严仲子、聂政等。如果说,屈原、信陵君、聂政还有某些斗争主动权的话,那么高渐离则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上。当时秦已灭六国,始皇帝权天下,在这种情况下,高渐离等的反秦义举,真是步履维艰,一步步陷入始皇势力的陷阱。高渐离含垢忍辱,被刺瞎了双眼,被上了腐刑;怀贞夫人被逼毁容。他们经受着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巨大苦难。郭沫若有意识地把人物推入艰危苦难的漩涡中,以形成一个足以展现人物深重痛苦,并从这痛苦中升华出崇高精神的悲剧大舞台,在塑造崇高的悲剧形象同时还创造了崇高悲剧的形式容纳了如此巨量的忧愤和苦难的悲剧舞台上,郭沫若着力塑造以积极的姿态去战胜、超越苦难的悲剧英雄形象。一般地说,苦难并不能自行产生崇高,崇高只有在各种严重的斗争中才得以展现。黑格尔指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5](P222)在弱小的正义面对着疯狂肆虐的邪恶迫害的情势下,作者让这些人物历尽考验,焕发起昂扬的精神,保持住性格的伟大和刚强。屈原虽然受到诬陷,被罢官驱逐而终致身陷囹圄、手足被铐,但是他一心系念楚国,系念楚国百姓,使他在精神上超脱了个人的痛苦,他的人格在个人痛苦的超脱中张扬升华起来。他面对着黑暗的世界,以荡涤天下一切污浊的气魄,喷出暴风骤雨一般的正义的愤怒,他那炽热伟大的情感,虽被不断地打击.仍然是不可阻挡地奔涌出来,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他那磊落伟大的人格,喷发出崇高的光芒,同时也照尽了张仪、南后等人物的卑劣和渺小。被刺瞎了双眼和受了腐刑的高渐离,在秦始皇看来,无异于一只被捕在手、可以随意玩弄的小雀。然而在郭沫若的笔下,高渐离的人格显现了无比的伟大和坚强,他虽然受尽凌辱和痛苦,但是他以自己的痛苦而感受到天下人的痛苦,因而他终于以一片无限的仁爱胸怀,把个人的小我化入了永恒的大宇宙之中。他从永恒的大宇宙中汲取到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因此,在外在世界上看,他是一个只能引起怜悯的阶下囚;但在内面世界上看,他的精神力量比暴虐的始皇、卑鄙的夏无且等伟大得无可比拟。他以自己的生命化作了永久的宇宙光明,而追求长生不死的秦始皇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度浮起的沫而已。夏完淳因叛徒出卖,束手就擒。他是明知大明气数已尽,但不甘心当亡国奴,也不愿意颓废沉沦。因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要“挺立两间扶正气,长垂万古作完人”。他胸中有股维系我民族命脉的正气,所以他在精神上远远压倒了那贪生怕死的民族叛逆洪承畴,虽然在法庭上,洪承畴坐在审判宫的位置上,可以主宰夏完淳的生死,但是在民族正气的法庭上,夏完淳视洪承畴猪狗不如,虽生犹死。夏完淳虽然被害,但他作为民族精神的化身而永生于世。他以17岁的横溢的诗才和绚烂的生命光辉,完成了他作为顶天立地的“完人”的崇高人格理想。
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志士仁人往往免不了流血牺牲的结局。对于这种牺牲,郭沫若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在夏衍处理秋瑾被捕问题上说过:“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正的‘鉴湖女侠’。”[6](P13)因此,他写婵娟、聂政姐弟、如姬、高渐离、阿盖公主、夏完淳……都为他们所追求的真理而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显现了英雄本色,同时也预示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前景,从而使全剧高扬出乐观主义的音调。当代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曾指出那种认为“悲剧必然和悲观主义相联系”的论调的错误,指出“悲剧作家在悲剧中蕴藏着比喜剧更丰富的乐观主义,而悲剧的最后效果应该就是加强观众对于人类的最光明美好的信念”。[7](P170)郭沫若写悲剧促人猛醒与感奋,鞭策和鼓舞人们为正义事业而奋斗,乃是具备最严格意义上的崇高品格的悲剧。
崇高的悲剧必须借助于完满的完善的悲剧形式。郭沫若不仅能够塑造崇高的悲剧形象,而且同时创造了崇高悲剧的形式。他说:“除人物的典型创造;心理描写的深化之外,‘情节曲折’而近情近理,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悲剧的要素呢?”[8](P176)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郭沫若把悲剧人物放在曲折跌宕、大起大落的情节中去表现,这就为加深加重悲剧人物的苦难,造成一个有力的悲剧环境,以便使人物在经受最严峻的考验、进行最严重的斗争过程中,发挥出他们生命力的夺目光彩。正如朱光潜指出的:“悲剧给人以充分发挥生命力的余地,而在平庸敷衍的现实世界里,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9](P91)与此同时,悲剧的感染力,使观众在心理上经历了一场由压抑到昂扬的情感过程。当悲剧人物在经受种种苦难时,观众的情绪上自然地产生一个被阻遏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随着情节的跌宕起落而加强、而迭进,当悲剧人物在精神上超越、战胜了对方时,观众被阻遏的情绪感受也得到一种解脱、一种升华,那种潜在的要求积极向上的生命力感,那种要求伸张正义、驱除邪恶的伦理道德感,都得到了某种满足。当屈原、高渐离、夏完淳、如姬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悲剧形象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时候,他们那伴随着某种痛感的情绪,就转入了属于崇高的情感境界。因此,郭沫若适当地加剧冲突、推进情节,加强情绪的刺激,是完全符合表现悲剧力度和气势的艺术需要的,这些艺术手段能有力增强剧作的悲剧色彩和浓度,能恰到好处地调节和引导观众的情绪感受。这样,郭沫若创造了一种很典型的表现崇高的悲剧形式。
郭沫若的历史剧,揭示出悲剧内在的深刻本质和崇高的美学精神,展现出悲剧形象的绚烂的人格光芒,它以雄浑、豪迈的“阳刚之美”卓然独立于我国现代话剧之林,具有无可争辩的开创性的审美价值。
[1]席勒.论崇高[A].席勒全集第20卷(第1册)魏玛1962年德文版.第194-1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郭沫若.革命与文学[A].沫若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郭沫若.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A].沫若文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夏衍.秋瑾不死[A].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7]悲剧与普通人[A].考瑞根编.悲剧[M].1981年英文版.
[8]郭沫若.《孔雀胆》的润色[A].孔雀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9]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