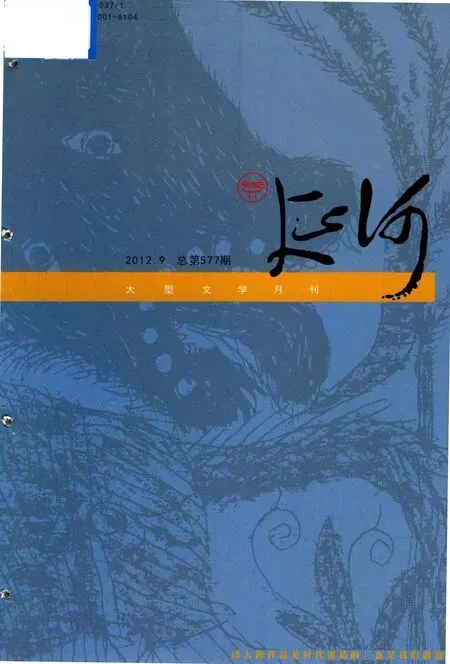柿子,柿子
2012-12-18冯积岐
冯积岐
站在窑洞前,姚世华向下俯瞰,满山坡的柿子红了,柿叶落了,赤裸裸的火晶柿子如同正月十五晚上坟地里点着的一盏一盏红灯笼,闪烁不定,鬼鬼祟祟。挂在枝头的柿子连成了一片,把山坡染红了,山地是红的,石头是红的,柴草是红的,树木是红的,天空是红的。姚世华看见,自己吸进去的空气是红的,吐出来的气息也是红的。坡地里仿佛一团一团的血在流淌在涌动,多看几眼就眩晕,恶心。一嘟噜一嘟噜的柿子把树枝压弯了,柿树承受不住重压似的,喘息着。
这半山腰里,只有姚世华一家人。清早起来,没有人和他说话,他站在院畔,注视着他并不想多看一会儿的柿子,在地上唾了一口,叹息了几声:柿子,柿子,柿子,柿子,狗日的柿子,你把我害苦了。
几年前,政府号召广栽柿树的时候,他就犹豫过,他知道,柿子这东西贱,和人一样是贱皮,不值钱。人老几辈子住在山里,他还没有听说过,谁家靠柿子卖钱发了家。十五六岁的时候,他也曾经去县城里卖过柿子,挑上一担柿子,从东街转到西街,从南街转到北街,转上一整天,一担柿子才卖二块多钱。西安来的女知青,蹲在笼子跟前,吃了十几个柿子,不给一分钱,两只手再抓两把,钻进女厕所去了,他有什么办法?每年摘柿子的时候,他就用棍子打用脚踩,故意把柿子弄烂,他恨柿子,又不得不采摘它。柿树栽进坡地里,他没有管,这些柿树竟然成活了,竟然挂果了。这果树,有一把土就生长。几年了,柿子每年卖不了几个钱。
姚世华抬眼看时,只见一个人正在朝坡上面爬来,来人腰弯下去,屁股撅起来,看不清面目,秃了的顶在残秋的阳光下仿佛脏衣服上的一只别致的纽扣。来人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好象捅了一刀子的一头肥猪被搁在案子上抽搐。来人走进了柿子林,即刻被那血红色淹没了,当他从柿树之间闪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象一盆猪血上面中蹲着的一只苍蝇。来人从那柿子树之间里钻出来了,尽管,火红的柿子按在身上的血色还没有褪尽,可是,满脸的络腮胡子和黝黑的脸把他脸上的颜色和神情固定住了。来人站在了姚世华跟前,他从短胡子里掏出来嘴:
老哥,雇人不雇人?
啥工价?
一天八十元。
讹人呀,得是?
我在县城里的工地上干小工,一天八十,还管两顿饭,不信?你去问。
听你说,你比当皇帝还受活,跑到山里干啥来了?
上当了,进了山才知道上当了。人都说,山里人老实、憨厚,昨日个在后山给人砍了一天玉米杆才挣了八十块。
说实话,到底多少钱?
七十块。
另说。
六十块。
那你就要我八十?连你也不老实,哪搭有老实人?老实人都在坟地里埋着哩。你走人,快走。我不跟你磨牙了。
我走了,你叫满树的柿子烂在树上呀?
烂了就烂了,关你球事。
你说给多钱?
摘一天柿子,三十五个元,带管饭。
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五十个元,咋个向?
四十。
四十五。
四十一。
四十二。
姚世华眼皮一翻,瞅了来人一眼,想了想,说:四十二就四十二,我还没问你姓啥?
姓胡,叫我胡三。古月胡,排行老三。
两个人刚敲定工价,女人从窑里出来了。女人叫姚世华吃早饭。
胡三说,给你家女儿说,给我把饭做上。
姚世华说,谁是女儿?会说话不?那是我婆娘。
胡三笑了:老兄艳福不浅!婆娘年轻得跟豆芽菜一样。
姚世华说,年轻年老就那么回球事。一样着哩。
胡三再看女人时,女人已向窑里走去了,她的背身小巧玲珑,头发挽了个鬃,垂在脑后。吃饭时,胡三偷看了女人几眼,这女人大概有三十五六岁,脸庞白净,只是眼脸下有几颗显眼的痣。她的眉眼偷偷地转动着,当胡三目光里的那一缕光直射过去的时候,女人正好张开了眼,她象双手接住一棵落地的柿子似的接住了胡三的目光——在这山里,她一年里很少见到陌生人的,尤其是胡三这样的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的精、气、神仿佛柿子一样垂挂在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上,虽然秃顶了,可是,十足的雄性如同火红的柿子一样不可掩饰。这女人十五岁就从秦岭腹地来到凤山县的北山里给姚世华当了婆娘。如今一儿一女都大了,都在城里打工,长年四季不回家。只有女人和姚世华守着三只窑几面坡。在冬天漫漫的长夜和春天里慵懒的黎明,当女人把一只小巧的手伸向姚世华两腿之间的时候,年过六十的姚世华用一长串扯不断的咳嗽回答了女人枝叶茂盛的欲望。女人狠狠地骂了一句:狗,一只老狗。连老狗都不如。女人背转身去,把自己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身体里——还不到四十岁的女人,尤其是身体健壮的山里的女人,一旦失去男人的安抚就烦躁不安。过几天,女人就到山下面的镇子上去一趟,回来之后,她牵着两只羊出了坡,羊在坡地里吃草,她坐在坡地里,静静地看着远处的山头,看着几朵浮云在山腰间缠绕,看着山头把浮云赶走了,云朵又把山头咬住了。她掐了一枝草,放在嘴里,咬一节,吐出去,又咬一节,又吐出去。等手里的草枝儿咬完了,她趴在山坡上,身体在坡地上蹭,蹭,蹭,这还不够,她又朝坡地里抵,抵了再抵。等女人翻过身,面对头顶的蓝天时,泪流满面了。
胡三在坡地里的柿树上摘柿子,女人用笼子将摘下来的柿子朝家里担。姚世华坐在窑门前在一块磨刀石上磨砍刀。哧啦——哧啦——哧啦——姚世华磨砍刀的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他的一只手抓住刀把,一只手的三根手指头按在刀背上,仿佛一个老中医按住了人的脉博在诊脉。刀和磨刀石相触而发出的声音很沉、很重、很利、很粗。当他举起砍刀用大拇指试当锋的当口,砍刀飞上去的寒光一闪,被女人挑回来的堆在窑门前的柿子染成了血红色,院子上空,仿佛开出了一道血口子。这把砍刀跟随姚世华几十年了,他上山砍树砍柴用的这把砍刀,跟集上县时腰里别着这把砍刀,睡觉时,枕头底下压着这把砍刀。他第一次把女人(十五岁的女孩子)领回来,第一次趴上她的身体的时候,他受活得不知道该咋办,他从枕头下面抽出来砍刀要砍自己的手,女人吓得叫了声,他放下砍刀,粗野地笑了:你这么碎个女娃子,比刀子还厉害?我受不了了。女人说,难受吗?姚世华说,把我没好死,狗才难受哩。女人一听,哧地笑了。姚世华把砍刀磨快,他准备在胡三摘毕柿子之后把柿树的枝桠砍去一半。这样,冬天里有了柴禾烧,来年也能少结些柿子——柿子是贱皮,不值钱。他早就认定是这样。
蹲在树杈上的胡三只顾摘柿子,没防顾,一颗杮子掉下来,不偏不倚打在了女人的头上了——女人正在树下向竹笼子里装柿子。女人抬眼一看,拾了一颗软柿子,站起来了。她将那颗软柿子朝胡三抛上去了,那颗软柿子不偏不倚正好粘在了胡三的秃顶上,他那比较平坦的肉色的脑门上仿佛涂上了一滩血,血是刚刚凝固住的血块,那血块像梅花似的在怒放,怒放,怒放,怒放。女人看着胡三,笑了,笑得弯下了腰。女人在大笑中又仰视了胡三的头颅一眼,她的联想惹得她笑的更粗野——四周是毛发,接下来是肉色,再接下来是一团血红,再接下来的中间是一个开口——血红色的开口——这和女人分娩时的下身没有两样——人就是从那个血红色的口子降生到人世上的——它看起来既好笑又动人。女人自己把自己惹笑了。她正无所顾忌地大笑不止,胡三从树上跳下来了。他抱住了女人,准备把她放倒在柿树下。他的一只手搭在女人的腰里,另一只手顺着女人的裤腰伸下去了。他伸到了女人的那个地方。女人并没有恼怒,只是,她的笑改变了——不再张口大笑,而是吃吃地笑,把玩笑转化为痛快的笑。女人笑了几声挡回去了胡三的手。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一句话没说。女人挑着笼子走了。胡三重新上了树。
第三天的晌午,姚世华给女人说,他要到镇上去看牙,他说,他大概上火了,牙疼得不行。女人说,你去,你去,回来的时候给咱买几斤醋,刚好没醋吃了。姚世华说,姓胡的干的是天天工,一天要几十块钱工钱,你把他看紧点,叫他老老实实地干活儿。女人说,我能叫他白挣咱的钱吗?你走吧。姚世华腰里别着砍刀,手里提着一只盛醋的空塑料桶下了山。走几步,吸溜几声,似乎牙很疼。也许,这样长长地呼吸,牙疼就能减轻几分。
女人也在吸溜。女人抬眼一看树上的胡三,一看胡三的秃顶就吸溜,牙疼似的吸溜。胡三的秃顶像火晶柿子一样发亮。假如把他的秃顶搂在怀里,那块肉疙瘩一定会使她浑身发痒的。女人正在树下给笼子里装柿子。她忍不住笑出了声。她不由得仰起了头。胡三假装掉下来似的从柿树上跳下来了,他将女人扑倒在满地的柿子上了。胡三紧紧地搂住女人,两个人在柿子上打滚,坡地里被压烂的柿子象血一样满地流,他们仿佛在血水中挣扎,那血水在两个人的身体周围涌动着,涌动着,涌动着,柿树林里象燃烧的一团火,柿子压裂的声音烈焰一般,啪啪作响,火光熊熊。女人将沾满了柿子浆的双手腾出来,抱住了胡三的秃顶,她用手在他的肉色的秃顶上抚摸,拍打,血色的柿子浆将胡三的秃顶染红了,他的脑袋如五月的石榴花一样。胡三的双臂撑在柿子上,柿子浆从手指缝里挤出来,指缝里好象向外冒血。他的动作幅度很大,频率很高。女人大呼小叫,柿子林里象红色的波浪翻滚。
事毕。两个人长长地躺在柿子堆里。女人呢喃着:你真好。我好长时间没这么好过了。
胡三说,你说的是实话?
女人说,谁还哄你?
胡三说,我要叫你天天好。
女人说,我是姚世华的女人。
胡三说,你就是这柿树,长在谁家地里就是谁的。
女人说,是呀,我长在姓姚的地里。
胡三说,我要叫这块地姓胡。
女人说,你咋弄呀?
胡三说,好弄,好弄。等收完柿子,我把姓姚的做销了,带上你远走高飞。
女人一听,猛地坐起来了。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厉害。
胡三说,咋了?你不舍得?
女人假装用手揉眼睛,她将柿子浆给自己抹了一脸,脸上仿佛向下流着血水。女人说,你说咋弄就咋弄。
胡三说,再过两天,我向姓姚的要工钱,钱要到手,先给你买一身好衣服。
女人说,你比他好。
女人又扑向了胡三。
站在院畔的姚世华看见,坡下面的土路上停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上走下来了两个年轻人。姚世华下了坡一问,这两个年轻人是进山来收柿子的。
多少钱一斤?
二毛五。
胡说哩吧?去年都四毛钱,咋那么便宜?
四毛?我们卖给人家,才四毛钱。二毛五,也不想进山来收这破玩意儿。跑上一天,赚不了几个钱。
二毛五不卖。
不卖算了。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农民,农民的东西不值钱,一斤小麦才卖多钱?说到底,还是农民不值钱,你去城里问问,农民的女娃做小姐,一晚上才赚几个钱?你老汉钻在山里,啥事都不知道,这是商品时代,一份钱一份货。城市里的一把土都比农民地里的土贵上几千倍哩。不卖算了,我们还不想收哩。
年轻人一只手去拉拖拉机的门,准备上车。姚世华拽住了年轻人的衣角说,小老弟,能不能多少添一点?
年轻人的手松开了,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你诚心要卖,二毛七,一分也不再多了。
姚世华咬了咬牙说,卖,我卖。
柿子是胡三和女人一担一担的担在拖拉机跟前的。总共卖了一千斤柿子。姚世华得到了二百七十元。
姚世华一算帐,把自己吓了一跳:胡三给他干了七天,工价要二百九十四元,柿子全部卖掉(除过烂了的几百斤),才卖了二百七十元。他把这二百七十元给胡三开了工钱,还欠二十四元。即使柿子烂在树上,他也不摘了。他要打发胡三走人。胡三刚上了树,姚世华就从树上把胡三喊下来了。胡三说,叫我走人,好说,把工钱给我。姚世华从身上掏出来一百七十元给胡三,他说,我只卖了二百七十元,先给你这些。剩下的一百二十四块钱先欠下。胡三说,不行,一分也不能少。姚世华说,我一分也再没有了。胡三说,你不给,我就住在你家不走。姚世华说,你不走?一天扣你三十元伙食费,住够四天一百二十块钱就没有了。胡三说,你少我一分,我就把你做销了。姚世华说,我不是吓大的,走着瞧。两个男人,一个瞪了一个几眼,他们并没有动手,各自蹲到一边去了。
当天,胡三没有出工。他看见,女人牵着两只羊到后坡去了,就撵着女人到了后坡。他把姚世华给的一百七十元拿出来,抽了一张一百的,给女人塞进了衣服口袋,他说,这是给你买衣服的钱。女人将钱掏出来,举起来,在太阳底下看了看,重新装好了。胡三把女人扳倒在草坡里。胡三说,姚世华不给我工钱,我就天天守着你,叫你受活。女人说,怕没有那么好的事。胡三说,等我做销了他,好事就来了。女人吭吭吭地笑了。
胡三在姚世华家里吃住了四天。姚世华叫胡三走人,胡三说,你不给工钱,我就不走。姚世华说,你不走,我有办法叫你走的。胡三说,你有球办法。胡三冷笑一声,向姚世华跟前逼了两步,姚世华后退了两步。胡三又是一声冷笑。他拧过身去后坡找女人了。胡三以为姚世华是山里人,以为山里人好收拾——象捏软柿子一样那么容易。
姚世华蹲在院畔,看着坡地里的柿树上还没有摘的柿子不时地朝地上跌落,火红的柿子象滴血似的,象下雨似的,天地间全是红的。滴在地上的柿子碎了,象人的一滴血种在了黄土地里,连坡地也红了一坨一坨。姚世华看了一会儿,进了窑门,他拿出来砍刀,又在磨刀石上磨起来了。
女人是凌晨两点左右被姚世华叫起来的。女人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她一看,姚世华站在炕跟前,手中提着一把砍刀,蜡黄的电灯光下,砍刀上的血渍一点儿也不鲜亮,连砍刀本身也变成了一把搁置了好多年好多年的古董似的。女人说,啥事吗?我还没有睡醒呢。姚世华说,你穿上衣服,跟我到隔壁窑里去看。女人已经嗅到了砍刀上的血腥味。她颤颤抖抖穿上衣服,跟姚世华来到了隔壁窑里。女人一进窑,首先看见的是胡三的秃顶,那秃顶不再秃,被姚世华砍了两刀的秃顶象开旺的花儿,血水依旧向出噗儿噗儿的冒,好象花瓣一张一闭地诉说什么。胡三的嘴唇并没有抿紧,似乎缺氧的冠心病人在吃力地呼吸着,他的眼睛没有合上,似乎是迟纯地、麻木地看着窑顶,仿佛担心垂掉的烟灰掉下来弄脏了他的脸面。他的脸面象磨刀石一样冷峻,唯独两腮象捏了两把的软柿子,陷进去了。胡三的两只手臂搁置在身体两边,舒舒坦坦的样子,左手张开,右手半握着,手心里似乎含着女人的奶头,没有血色的手指头一副贪恋的,抓取的什么东西的姿势。女人看了几眼,十分恶心,用手捂住了嘴,生怕自己呕吐。姚世华说,狗日的,再也不会要工钱了,再也不会赖在家里不走了。
女人说,是你干的?
姚世华说,还用问吗?
女人说,咋弄呀?
姚世华说,埋了。
黎明前,两个人把胡三埋在柿树林的一棵柿树下了。
从那天起,姚世华挥动砍刀开始砍柿树。砍倒的柿树连同枝桠一同堆在埋胡三的地方。十多天后,坡地里的柿树被姚世华砍得一棵也不剩了。胡三的身上堆了一座柿树山。
许多年以后,在堆柿树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怪树。这棵怪树象中草药冬虫夏草一样,冬天是动物——一只虫子;到了夏天,变成了植物——一棵树。晚上,它是一个活物,一个人,根扎在土地里的人;白天,就成了一棵树——红躯杆,红叶子,不结果,风一吹,象人说话似的,在呓语。可是,谁也听不懂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