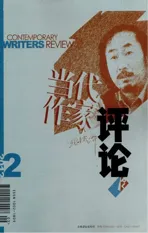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隐现
2012-12-18孙洁
孙 洁
北平/北京和老舍创作的血肉关联已不必再证。暂不论老舍写的那些北京城的三教九流、男女老少、风物流转、市井沧桑,他一生写作的成败也往往与能否终于“求救于北平/北京”①老舍:“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语出《我怎样写〈离婚〉》,《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相关联。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北京以“符号”、“人物”或“文化”的方式在老舍新中国时期创作中出场的情形,探讨“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隐现,厘清老舍第三次在文学上“回归”北京的始末因由。
一
老舍一生的文学创作经历过三次回归北京,②说明:为了行文方便,除了注引,本文一律把“北平”和“北京”统称为“北京”。分别是一九三三年写《离婚》,一九四二年动笔写《四世同堂》和一九五六年写《茶馆》。
返归北京,是因为离开在先,每一次离开,都是因为要写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每一次回归,都是因为一写指向政治的作品,老舍就找不到自己了——作家本人更多地表述为“生活”。
和几乎所有小说家一样,老舍的创作生涯也是从写故乡背景和少年经历开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③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从《老张的哲学》到《二马》,旅居英国期间写的三部小说都是写北京人的日常起居和心理状态的,唯一的不同是第三部《二马》,故事展开的背景改为了伦敦,老舍把老马和小马两个北京人抛掷在伦敦人的白眼和偏见之中,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企图从中完成中英两国国民性比较的伟大事业。④老舍:“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语出《我怎样写〈二马〉》,《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但是,老舍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从背景到人物完全地离开了北京,写的是南洋小朋友的生活和梦境,老舍说,到新加坡之前,他在写一个爱情小说《大概如此》,但是,“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⑤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显示了对政治的关切,从此老舍不再是那个用写作填补寂寞的老舍,这也为他归国后写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大明湖》和《猫城记》埋下了伏笔。《小坡的生日》、《大明湖》、《猫城记》这三部长篇都有很强的政治隐喻或政治指向,并且都不是以北京为背景的,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小说中有北京人的形象。①目前唯一有关《大明湖》的介绍文字就是老舍的《我怎样写〈大明湖〉》了,但是从这篇文章介绍的故事梗概看不出《大明湖》的人物设计里有确切的北京人的形象,而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济南。而从《我怎样写〈离婚〉》所表白的“求救于北平”,也猜想出《大明湖》没有写有关北平的人和事。关于《大明湖》和《猫城记》因“故意的禁止幽默”导致的作品枯燥无趣——其实就是失去了作者本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述特长,老舍调侃道,可以让人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只猫”。②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我认为这两部作品和此前的《小坡的生日》因为,北京和北京人的不在场导致的作品本身的空洞也可以如是理解。因此,随后《离婚》的“求救于北平”不仅仅是一次写作策略的变化,还应理解为老舍终身的写作密钥。
从《离婚》开始,老舍一直走在“求救于北平”的轨道上,这造就了老舍创作的无可替代、时不再来的高峰,直到抗战爆发。
抗战伊始老舍的亢奋是和文学史的亢奋完全同步的。大致上,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大众文艺作品,并且努力地探讨怎样写大众文艺的技巧和方法,这四年几乎颠覆了老舍前十年写作的全部努力,也包括“求救于北平”的自省。也是在这四年内,新文学从五四发源汇成的壮丽河流几乎被阻断,一时间,除了大众文艺不可替代的当家花旦的地位,由报告文学取代了五四的小说传统,由街头剧取代了五四的话剧传统,由朗诵诗取代了五四的新诗传统,而此前已蔚为大观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只在“孤岛”残存了些许余绪。现在回过头去再检视抗战前四年的文学史,说满目荒凉有点过了,但属于文学本身的起色却也未见端倪。一九○二年,梁启超曾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开启了五四新文学的道统的一面。这个侧面在“启蒙派”、“救亡派”、“自由派”各有胜擅的二三十年代没有更多的腾挪空间,但到了全民御敌的抗战年代却大放异彩、独步文学领地了。
从文学史综合分析,发生于一九四一年的“中心源泉”问题的大讨论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之所以一九四○年代的文学史又能显露出承继五四文学传统的侧面,和这次讨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老舍的第二次文学回归即发生于这个时间点。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老舍在《抗战文艺》发表长文《三年写作自述》,反思此前三年因为抗战宣传放弃自我的经历,“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的抬轿的吗?绝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还知道暂缓淘气,何况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孩子呢”!③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6卷,第6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这一席话明确表示了老舍企图再次“求救于北平”的努力,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和调整,老舍在一九四二年动笔写全北京背景、全北京人出场的超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后,他又写了重庆背景、反映一个北京家庭离合悲欢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此后便是老舍充满“狂喜”的新中国时期了。建国之初,老舍创作了立意非常接近的《方珍珠》和《龙须沟》,但《龙须沟》之后老舍再次离开了北京题材。一九六六年一月,老舍在回答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自称这是因为他对新北京不熟悉,写不好,“我很想来写新北京的人民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生活不是那样子的丰富了。因为,像刚才我们说的,它现在是新起来的一班人了,这种生活,我了解得不够全面。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发展,特别是跟青年人能够多接近,比如到工厂去长期地住下来”。①老舍:《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老舍全集》第15卷,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对比文学史,我觉得真实原因老舍没有说出来,也不可能说出来。其实不是老舍不熟悉北京了,而是老舍不熟悉新的文学规范和文学要求了。在“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之下,在“三红一创”类型的小说走红的大背景下,老舍努力地追赶新时代,回应新要求,他写《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志愿军,写《青年突击队》歌颂建筑工人,写《春华秋实》配合三反五反,写《西望长安》揭露军内巨骗,却一次次无功而返。终于,在百花年代,他第三次求救于北京,开始写作《茶馆》。
《茶馆》得到隆重的礼遇是新时期老舍已经沉潭十多年后的事情了,虽然在发表之初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学褒奖,但是,第一,它受到了当时北京人艺空前的重视;第二,它唤醒了老舍的写作自信,特别是关于北京这个老舍的写作之根和制胜法宝。从此,老舍对北京题材便不离不弃,直到《正红旗下》被迫中止。
综上,本文谈到的老舍的“北京”界定为“求救于北平”意义上的北京,它是老舍创作折返的一大表征。求救于北京,每每标识着老舍创作生命又一活跃期的到来。
二
紧扣本文论题,我们重点来看发生于老舍新中国时期的第三次回归北京。
当“北京”体现于老舍的文学创作中的时候,它呈现出三种形态:以符号样式存在的北京、以人物形式存在的北京、以文化形态存在的北京,为论述方便,本文分别简称为符号的北京、人物的北京、文化的北京。
第一,符号的北京。
作为符号,就是“北京”和“上海”、“天津”、“杭州”……和新中国时期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只是一个为了发生各种政治事件而存在的符号,它是没有个性可言的,仅仅是一个地点。作为符号的北京是老舍新中国时期的作品中出现最为频繁的那个“北京”,它是散文《我热爱新北京》里的那个“清洁、明亮、美丽”的新北京,是《龙须沟》第二幕之后的那个“干干净净大翻身”的龙须沟,是《红大院》里那个充满了政治口号和乌托邦幻想的四合院,也是老舍最后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的“粮食多,猪肥壮,经济、科学、文教、卫生,齐兴旺”的新农村……总之,它毫无疑问是北京,但随时可以替换为新中国的任何其他城市。在这一类作品中,北京只是一个空洞的地名,几乎没有血肉。一九五五年,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谈到,束缚作家创作的“理论刀子”之一,便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技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①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302-30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这其实是新中国时期困扰了很多作家的一大难题,也是众多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且以写某些地域为擅长的作家的最大障碍,诸多作家在同一时段的失语或滑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二,人物的北京。
如果说作为符号在老舍作品中出现的北京是抽象的北京、政治意义的北京;作为人物在老舍作品中出现的北京则是具象的北京,作为背景在老舍作品中出现的北京更是文化意义的北京。后两者都是在老舍领悟到抽象的北京(符号的北京)使得他的作品大大地缺少了生活的实感之后憬然折返的结果。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城”的展现首先是靠“人”的描绘来实现的。符号的北京之所以不能准确地展现北京风土本身,首先是因为“人”的缺席。这里的缺席,不是说作品里没有人物,而是指没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物。
类似的问题,老舍在抗战时期第二次“求救于北平”的时候已经碰到过,如前述。正是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决计折返的时候,老舍从人物入手开始第二次的“求救于北平”。这个人物便是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一九四二年七月)的章仲箫。和此前的多部抗战话剧不同,《谁先到了重庆》把地点放在了北平的皇城根。由于这一设置,读者非常欣喜地从这一剧作中找回了在老舍创作中睽违已久的北平底层民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处世、性格特征、生活环境。一切都是曾经在老舍山东时期的创作中早已熟识了的,而其中最为鲜活的章仲箫的形象更是直接从大杂院群落中信手拈出的普通一员。惟其是信手拈出的,这个人物身上方才令人信服地具有北平市民根性中难以祛除的善良、狡诈、愚昧和怯懦,这是老舍揣摩透了的一种人物类型,故而不须斟酌,不须拔高,也不须丑化。正是章仲箫这个“小人物”使得《谁先到了重庆》这个在情节上过于刻意的话剧显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老舍也从这次重新写北平获得的乐趣和成功之中渐渐向那个“生活的北平”回归,终至写出整个故事完全浸泡在北平血液里的《四世同堂》。
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创作的“章仲箫”出现在《茶馆》(一九五七年七月)之中,不是一个章仲箫,而是一群,这些人各有貌的北京人仿佛是从天而降,这应是由于此前老舍的北京情结被压抑得太久、太深而导致的,也与《茶馆》之前的《西望长安》的人物造型过于脸谱化密切相关。《茶馆》之后,老舍的话剧《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神拳》全部都是以北京人作基本人物的,直到《正红旗下》残篇,那已经是一个无一角色不是北京土著的作品,也是一个空气中无处不氤氲着北京气息的作品。
第三,文化的北京。
相对于作为人物的北京,作为背景的北京要更丰满。作为人物的北京在作品中呈现,可以只呈现一个人物,比如章仲箫,但是作为背景的北京,是说这个被取景的北京应当有最丰富意义的民俗内涵,这从意义上保证了那个老舍像故旧一样熟悉的文化的北京昔日重来。因此,如前述老舍从《茶馆》开始的第三次在创作上回归北京,虽然从《茶馆》到《正红旗下》,除了民间题材和儿童题材的少量作品,主要的作品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也都有北京人作为主要人物,但是严格地说,以“文化的北京”为背景的只有《茶馆》和《正红旗下》残篇两部。
换句话说,同样是回归北京,当落实在不同层面上的时候,这个“北京”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人物的回归固然是回归北京的重要表征,但泛泛的人物回归,呈现的“北京”可能仍是“符号的北京”;而只有当人物的回归和背景的回归合一了,这个“北京”才是老舍一九三○年代第一次“求救于北平”之后回归的那个文化的北京,人情世故、鸡零狗碎的北京,气象万千、仪态万方的北京。
新中国时期文化的北京在老舍作品中呈示,在《茶馆》和《正红旗下》这两个作品中完全态地实现,亦即达成了“人物的北京”和“文化的北京”的同时实现,这分别对应了老舍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的最后两次向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
总结一下,符号的北京是出现在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每个时段的;但是人物的北京却从《方珍珠》和《龙须沟》异曲同工的后半段被政治口号湮没后,只有在老舍一九五六年第三次文学回归后才重又出现;以文化背景样态呈现的北京更只在《茶馆》和《正红旗下》残篇两部作品里才得以被有力地展现。由是我们能更深切地体会“北京之子”老舍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困境。
三
老舍的悲剧有很多方面,在个人身份归属这方面,体现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民族身份被迫隐匿和一九四九年之后面对文化的北京被驱逐的无可奈何。这在老舍分别于一九五四年参加“戏改”讨论、一九五六年投入“百花年代”并写作《茶馆》,以及一九六二年回应“广州会议”、写作《正红旗下》并半途而废的过程可以约略见出。二十世纪几乎是一个作家自身的文化定位永远不可能安然稳妥地安置的世纪,但于中我们大概也能看出《茶馆》和《正红旗下》残篇的珍贵。
“我热爱新北京”,这几乎是老舍新中国时期所有著作的共同主题。一九五四年,老舍说:“自从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五年来北京起了很大的变化。它已不是我幼年间所看到的北京,也不是前十年的北京;甚至于今天的北京已不是昨天的北京!”①老舍:《北京》,《老舍全集》第14卷,第5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在这里,我们发现,老舍之所以在新中国时期留下那么多远离“文化的北京”的作品,不仅仅因为老舍本人受到政治任务的包围和挤压,他需要全身心地为人民写作,也是因为“文化的北京”在变成“新中国的首都”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变化。
在一九六六年一月答NHK记者的谈话中老舍说:“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②老舍:《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老舍全集》第15卷,第2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杨东平在《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中更精确地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北京概括为“气象非凡的全能型城市”。总之这个新的北京已经因为重新成为首都,最大限度地祛除了作为“北京”自身的“市井气”,增添了大量作为“首都”必备的功能,它变得面面俱到了。因此,杨东平在论著中一再提醒我们,要“区分作为首都的‘中央’和作为地方的‘北京’”。③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10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这大致能解释,为什么写北京的老舍在异国或他乡二十多年长途漂泊之后重又回到故乡北京后,反而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呈现出远离“文化的北京”的形态。
除了上文分析的完全回归到“文化的北京”的《茶馆》和《正红旗下》残篇,老舍新中国时期其他写北京的作品主要都是围绕北京的“首都新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龙须沟》、《女店员》、《红大院》这三个话剧,它们反映的北京新貌各有特点,主题分别指向旧城改造、妇女就业和大跃进。我们从这些话剧中看到的是鲜明的政治主题,但属于北京的独特的地理的、民俗的、习惯的、语言的特征已大大地被消解,归根结底,正是“首都”的政治主题消解了“北京”的文化特质。
老舍一生写文化的没落和无可追挽,一九三○年代第一次回归北京之后直到抗战爆发是一个高峰,《断魂枪》题记借用的西方墓志铭①《断魂枪》选用约翰·盖伊的墓志铭作题记:“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见〔美〕D.J.恩莱特《人的末日》,第125页,华进、石香、钟鸣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和结尾“不传”的回声成为一组醒目的记号,提醒我们老舍曾经带着如此半是滑稽半是悲凉的眼光看“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的事实。一九四○年代写《四世同堂》(第二次回归北京)是第二个高峰,《四世同堂》几乎啰嗦地、不厌其烦地写北京的四时节令,每个季节乃至每个节气的风物流转,老舍想用他的笔留住什么?他是怕北京的文化(生活方式)②老舍:“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做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含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大地龙蛇·序》(1941),《老舍全集》第9卷,第3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被日本人夺走。一九四九年归国后,老舍正是在文化的中心、自己的故乡北京目睹了文化的渐次凋零和彻底没落,终至被“大革命”,一九五○年代老舍在创作上的第三次回归北京虽然为文学史带来了《茶馆》和《正红旗下》残篇这样的杰作,却无法阻止新文学本身的式微和中华文化渐渐走到被“大革命”的境地。值得深思的是,作为北京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老舍本人写作的滑坡也正是北京文化没落的一个部分,一九六六年八月发生的老舍之死作为一个事件更是为一个时间段里北京文化被政治驱逐的残酷事实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一九八○年代,“文化的北京”在寻根文学中再次呈现出亮色,这大致可以认为是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文学”的第四次回归北京,但老舍本人已经溘然长逝,文化的北京其实亦未能真正振兴。因文化是一种只能守护,不能轻易改变,更不能随意破坏的东西,它由漫长的历史层层积淀而成,一旦被毁坏,便是不可逆转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诗人穆旦写下长诗《隐现》,询问救主之隐现、真理之隐现,姑且抄几行穆旦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束,也来追问一下老舍的文化北京的隐现,是否也如穆旦所言——
等我们哭泣时已经没有眼泪
等我们欢笑时已经没有声音
等我们热爱时已经一无所有
一切已经晚了然而还没有太晚,当我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③穆旦:《隐现》,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244页,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