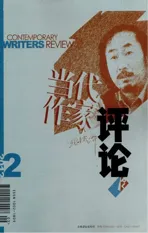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论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
2012-12-18杨小滨
杨小滨 著 愚 人 译
小说写作……使我有可能重获无法表达的现实经验和记忆。
——格非
格非是他那一代中国先锋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与绝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不同,他的职业是在学院教授文学。也许是由于学术生涯的缘故,格非的小说在处理历史和个人经验方面似乎专注于叙事技巧或形式上的可能性。格非通过揭示集体与个人记忆在不可调和的叙事碎片中的缺陷,来挑战主流话语赖以构成的宏大历史总体性。在格非的叙事中,主体的声音颇为清晰;但是,它并不是用另外一种绝对的声音取代宏大历史话语,而是展示了其自身游离分散的表述。格非小说中“无法表达的”经验与内存表现为不可知的、无法消解和遗忘的叙事碎片。
重新认识或重新呈现过去的陷阱
《陷阱》是格非的早期短篇小说之一,格非的叙事者甚至在小说真正开始之前就承认了他的叙事局限。更加离奇的是,故事是“从她的自叙开始的”,①格非:《迷舟》,第1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她是一个名叫牌的女孩,那是离家出走的“我”偷听来的。偷听本身出于与故事毫不相关的一个偶然意外,它不仅成为“我”即将深陷其中的现实,而且也是叙事者现在讲述故事的原因。换句话说,主要叙述完全来自一个不带任何决定性的历史历程的偶然事件。叙事者不再对叙述的真相承担责任;确切地说,一种叙述可能始于另一种叙述,或者可以不加组合地任意切换成另一种叙述。在某种程度上,牌的叙述是不连贯的:她一会儿声称她离家出走是因为害怕,继而又说她不得不离家出走。谭运长在他讨论这个短篇小说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他却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牌的叙述本身是不可信的,那么她的所有陈述都是不真实的。②谭运长:《形上学游戏:评格非的小说〈陷阱〉》,《广东文学》1987年第12期,第40页。当牌后来再次讲述她的过去,声称应该对她离家出走负责的父母(根据她先前的陈述)早已死去的时候,这样的疑虑更是有增无减。
前后矛盾的陈述瓦解了叙事的总体性和绝对性。如果我们将这个片段与五四时期妇女离家出走的同类主题故事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格非的叙事并没有为女主人公的离家出走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年轻女性子君或者冯沅君书信体短篇小说《隔绝》中的“我”是离开(或者决定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去追求“自由恋爱”。鲁迅与冯沅君的小说至少部分地顺应了从父权压制到自我解放的历史理性秩序的解放话语。在鲁迅的小说中,这样的历史后来当然变成了毫无结果的哀叹。格非通过脱离解放话语来击破这样的历史:牌离家出走的理由令人困惑,这就打乱了整个宏大历史的逻辑。
格非也探讨了真实与幻觉、可以预期与不可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另一个关于导致她离家出走的故事中,牌说她看见一个老人用一些细长的树枝在河边搭桥。她试图说服老人这样的桥是没有用的:
你的桥不牢。我说
它是给鸽子走的
鸽子能飞过河去 不用桥鸽子也能飞过去
它是给没有翅膀的鸽子走的
所有的鸽子都有翅膀
没有翅膀的鸽子没有翅膀①格非:《迷舟》,第20-21、20、2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对话一直在继续,直到她回家并发现一些不相识的老人占据了她的家。她无法进入她自己的家,因为老人们认为她进入屋子是非法的。在格非的许多故事中,非现实压倒了现实。在很多情况下,现实似乎只能服从于那些导致不幸的美好或者戏剧性的幻觉。
这些梦境般的幻觉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还可能是喜剧性的或者荒诞的。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都寓言性地直指现代中国无法实现的文化想象。牌向她从前的男朋友黑桃讲述她离家出走的这后一个版本的故事,当牌和“我”一起去拜访黑桃时,黑桃竟然没有认出她来。黑桃可以被寓言性地诠释为曾经为“寻根”文学所钟爱,现在被喜剧性地戏剧化的一个怀旧形象。甚至在他回想起牌的时候,他的旧情复燃也只不过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接着他又恢复了他“木然而立”②格非:《迷舟》,第20-21、20、2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的姿态。重温旧梦的初衷根本没有希望。作为一个流浪者,牌“一直朝北走”去“寻找救星”③格非:《迷舟》,第20-21、20、2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的努力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历史救星应该是远见卓识的社会解放者或者怀旧的精神赎救者,这样的角色不再具备把整个叙事引向一个完美的结局的超强功能。因此,牌对黑桃的拜访就是对回到原初的戏仿性探索,因为黑桃自己就是“遗忘心理学家”,象征着逃离原初。
黑桃以各种方式毁灭了牌的幻觉,所有这一切都与审美想象或创造的危险有关。他暗示那是为鸽子搭桥的老人设下的陷阱。这个老人必须被看成艺术或者幻象的象征,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幻象(“没有翅膀的鸽子”),完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正如黑桃认为的那样,他的不切实际和审美的活动仅仅是具有特殊实际指向的一种伪装,那就是把牌从家里引出来,好让老人占据她的屋子。这是审美的危险陷阱,这样的伪装给现实带来了灾难。占据了牌的屋子的那些人好像在演戏:美/幻与恶/真在他们的表演中融会一体。然而,陷阱不仅存在于牌关于她自己的故事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她的故事叙述之中,由此可见,她的叙述作为艺术(人为捏造)就像老人的桥一样不稳定,或者就像伪装成占领她屋子的那些人。换句话说,对陷阱的表现本身就是一个陷阱:自反的形式暴露了再现性叙述的自我解构倾向。
黑桃说服牌把遗忘和回避的艺术当作重新找回或构想过去的天籁福音来接受。原初恰恰可以被寓言性地理解为对再度体验的拒斥。究竟什么是真实也受到了质疑。他警告“我”,牌已经“成了你众多记忆混合物的复制品。这都是你过于沉湎冥想记忆泛滥所致”。①格非:《迷舟》,第24、24、24、30-31、33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正如黑桃暗示的那样,牌现在只不过是叙事者精神形象的“复制品”,我们不仅会怀疑牌的陈述,而且还会怀疑她是否存在。然而,根据黑桃的暗示,牌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牌也否认黑桃的存在。叙事者后来确实收到过牌的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黑桃在他们进城拜访他之前就已经死了。叙事者可以“推测我们深夜拜访黑桃可能是一次幻觉”。②格非:《迷舟》,第24、24、24、30-31、33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叙事中的这种自我否定破坏了表现过程的连贯性。因此,陷阱(尤其是表现陷阱)不仅是其他人安排的,而且还可能是那个人自己的设计。叙事者声称(同时又是自我反驳),“实际上”③格非:《迷舟》,第24、24、24、30-31、33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这样的“实际”总是可疑的),当天夜晚,他们没有找到黑桃,却参加了一个葬仪。在这个似是而非的葬仪上,人们穿着溜冰鞋滑翔而过,计算机操纵着灵车,立体音箱里播放着事先录制的哀号。最滑稽可笑的是,“我”最终发现死者原来是一头猪。表现的“事实”或者“表现性”就这样被理性叙事的迷惑错置,这正是横贯整个短篇小说的最大陷阱。
《陷阱》的叙事是幻觉、幻想、伪装、欺诈、游戏和闹剧的杂烩,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对表现与现实的谎言的彻底揭露。最为显见的是,故事的发展逆转了各种宏大叙事对真实的见解,这样的见解正是中国现代叙事的核心。所有的表现继而被揭示为误现,所有的现实则被揭示为非现实。任意和冒险的叙事逻辑破坏了宏大叙事的总体性。
格非通过不断地否认先前的陈述或与先前的陈述自相矛盾来引起我们对叙事自足性危机的关注,表面上整合的叙事变得断断续续和前后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非戏仿的不是某种特殊的叙事种类或者类型,而是所有在整体上一致或者稳妥的叙事,尤其是严格同质的宏大叙事。如果说历史的基础是记忆和叙事,那么格非复原的就是记忆与叙事中的那些不确定因素。在他的《褐色鸟群》里,叙事者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没有日历和时钟,他根据迁徙的褐色候鸟估算季节的变换。一个名叫棋的女孩走过来,向叙事者展示她的画夹,叙事者感觉到“我的记忆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但并未就此而唤醒往事”,他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粘接起来”。④格非:《迷舟》,第24、24、24、30-31、33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夜晚,叙事者对她讲起自己的故事,“尽量用一种平淡而真实的语调叙述”。⑤格非:《迷舟》,第24、24、24、30-31、33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然而,他的关于他遇见另一个女人的叙述却并不“平淡而真实”,他在他所谓的结尾处停住了。只是在棋这个故事讲述的倾听者不可思议地接着讲完了他的故事之后,叙事者自己才继续他的叙述:他徒劳地跟踪一个女人来到郊区,以及他在女人消失后遭遇的神秘事件。棋再次为他讲述了故事的结尾,叙事者后来也确认了这一点。叙事者与叙事对象的角色互换破坏了表现的稳定性,打乱了话语的制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叙事者在小睡之后被迫讲述了很多年后发生的事情:“我”在另一个城市遇到了那个女人,但是她否认她在十岁以后去过他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城市。然而,她记忆中的某些部分与叙事者的叙述交迭在一起。⑥在此之前,叙事者诉说他跟着一个女人来到一座木桥,他看见女人穿过木桥,但是她的靴印在河边消失了。他遇到了两个人:半路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迎面而来,跟他擦袖而过;另一个是手提马灯的花白胡须老人,老人告诉他没人能穿过这座木桥,因为木桥早在二十年前就被洪水冲毁了。正当“我”准备赶回去的时候,他发现了沟渠边的自行车以及先前跟他擦身而过的那个人已经僵硬的尸体。这个女人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她丈夫提着一盏马灯来到那座木桥(据她说,毁坏木桥的是偷窃木材的小偷而不是洪水),她看见了一些鞋印和自行车的胎辙;第二天,人们在河里找到了一具尸体和一辆自行车。接着,他与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终于结婚,而她却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死去。当棋知道故事已经真正结束的时候,她离开了。几年后,叙事者看见棋穿着同样的外套,挟着同样的档夹走来,然而她一点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她否认她就是棋,然后消失在远方,就像不知疲倦的褐色鸟群。
《褐色鸟群》在叙述中套叙述,由无数古怪事件组成的多层叙述构成。叙述“框架”包括棋的来访以及叙事者讲述他的神秘爱情故事。尽管叙事者的记忆经常被棋的陈述所悸动,他仍有记忆困难,因为他的“意念深处一定存在着某种障碍”或者“压抑”。①格非:《迷舟》,第 33、33、42、43、29、6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可以假设,心理障碍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他的爱情和婚姻结局悲惨。那就是为什么他意识到他对棋的叙述就像一个病人在对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倾诉。②格非:《迷舟》,第 33、33、42、43、29、6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叙事者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中间他停顿过几次。在第一个停顿中,他像是在否定他的痛苦记忆,声称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棋还在贸贸然继续向他讲述这个故事,依据是(正如叙事者假定的那样)她对叙事常规的敏感。在这里,叙事者将叙事常规解释为叙事的心理学基础,而棋则在其中扮演了不断进行盘问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角色。
第二个停顿发生在棋所谓的“非常庸俗的结尾”③格非:《迷舟》,第 33、33、42、43、29、6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之后,棋再次讲述了他在沟渠里发现尸体的故事。至此,叙事者的“大脑像是一个空空落落的器皿,里面塞满了稻草和刨灰”,④格非:《迷舟》,第 33、33、42、43、29、6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他回想起棋先前提到过的一些人。叙事者似乎只有通过部分释放压抑才能重新获得他失去的记忆,他只有通过唤醒他对愉悦的记忆才能避免或者至少延迟痛苦不堪的记忆。很显然,叙事者与中国现代文学范式中自信的叙事主体不同,他被围困在强制的表述与压抑的表述之间。更有甚者,他作为叙事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一名女性听者讲述故事——的身份是可以替代的:他中断的叙事必须由她来补充。他的完整叙事依赖于这样一位替代他、从他异化而来的叙事者。因此,叙事主体的力量不再是绝对的,而且变得无能为力和自我瓦解。
遭到瓦解的恰恰就是无法提供一幅没有瑕疵的过去图景的连续独白。甚至相互补充的叙事对话(叙事者与棋之间的对话或者“我”与那个女人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使整个故事变得统一完整,而是揭开了交流中无法弥合的差异。棋对叙事者的叙述的补充中也存在着误会、省略和疏漏。这个女人对过去的记叙与叙事者的记叙互相重叠却又相互矛盾。叙事者与棋,叙事者与女孩的相遇包含了遗忘或者误会。
故事的结局显示了叙事者的困惑:棋来了——也许她不是棋,也许她就是棋,只是她已经不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正如开头的叙事者那样,或许她只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个场面与开头那个部分一模一样;然而,那不仅仅是重复,而且是带有反讽意味的重复,或者失败的映射,映照出映射的无能为力。在小说的开头,叙事者看见棋的时候,她身穿“橙红(棕红)”的衣服,“怀里抱着一个大夹子,很像是一个画夹或者镜子之类的东西”裹在“草绿的帆布”⑤格非:《迷舟》,第 33、33、42、43、29、6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里。大夹子确实是画夹,因为棋向他展示了绘画。在小说的结尾,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开头:“她依旧穿着橙红色(或者棕红色)的罩衫。她怀里抱着那方裹着帆布的画夹,而远远地看起来,那更像一面镜子”。⑥格非:《迷舟》,第 33、33、42、43、29、6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然而,叙事者的假设错了。那个女孩不是棋,那个看上去像是棋曾经怀抱过的夹子其实只是一面镜子。
这里出现的问题,比如真实与镜像,就是所有叙事表现中固有的问题。显而易见,叙事表现的基础就是对真实的假设。毫无疑问,再现的符号是要读作符合“本真的”对象。然而,在格非的叙事中,这个貌似透明的再现符号具有反讽意味地产生了模仿本真却又无法还原其实质的镜像。所以,落空的不仅是叙事者对棋的期望,而且还是读者对叙事中表现本真的期望。格非通过质疑叙事再现的本真性,戏仿了在目的论式的团圆中达到高潮的时间概念。就这样,叙事者再次被留在了一个无限的空白之中,一个缺乏时间逻辑的空白,为此叙事者一开始就担心“这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一同带走”。①格非:《迷舟》,第29、10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时间本身向非同一性或者异质性开放,而不是封闭在同质的结尾之中。
叙事框架中对真实性的疑惑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在叙事者对他的爱情故事的记叙里。“我”相信他先前遇到而后来再次邂逅的那个女人就如同棋的“镜像”,她否定了他们曾经相遇的可能性,尽管再现的符号,比如她的栗树色靴子,可能确证了叙事者的陈述。除了女人的否认之外,叙事者的记述并没有遭到彻底的驳斥。总而言之,女人承认坍塌的桥的存在(尽管她对桥之所以坍塌的解释与叙事者的解释不相符合),她甚至回想起她丈夫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看见的事情,她的记叙与叙事者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模棱两可:像这样包含了相互争讼的种种次要叙事的叙事既不是绝对确定的,也不是绝对否定的。再现叙事遭到了彻底的戏仿(而不是被完全舍弃):格非的小说通过揭除再现性“现实主义”的面具,突出了解构的潜力,即坚持在质疑的过程中而不给出任何确定答案。
宏大历史的岔道歧路
在格非的小说中,解构的力量只有在与个人经历和民族、地域或者家庭、历史相关联时才会产生作用。格非的小说绝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对表现以往历史的原型或模型的再书写甚至戏仿。原型或模型的关键因素得到了保留,但却无助于它们通常假定会产生的意义。例如,在《迷舟》和《大年》里,“北伐军”和“新四军”的正统历史形象遭到个人欲望或者日常事件的污染。这些名词所标志(或者虚构)的统一历史“本质”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打着历史叙事幌子(通过简短的开场白介绍的历史背景)的《迷舟》并没有导致历史事实的客观化,而是导致了主体表现的脱漏。这段开场白用确切的日期、地点、部队番号、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以及新闻报道风格的叙事表现了历史真实,最后才提到故事的主角,孙传芳部守军三十二旅萧旅长的失踪。然而,小说中站在北伐军(历史进步势力)对立面的主人公萧不像是一个“反面人物”。他身陷风流韵事、违反军纪、家庭变故这样的麻烦之中,等等,所有这一切打乱了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注定应该扮演的角色。萧的下落不明不仅给“雨季开始的战役”,而且还给应该把反面人物明确地放在确定的敌对位置的历史叙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②格非:《迷舟》,第29、10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他的失踪在编好程序的历史地图上留下了一个空白。
故事从媒婆马三大婶带来萧的父亲意外死亡的消息开始。萧回到他的故乡小河村是为了他父亲的葬仪和侦察任务。他很快与刚刚在小河村跟三顺结婚的杏暗中私通,他仍然在记忆中保留着对自己在榆关的青春回忆,然而榆关现在已经被他哥哥率领的北伐军部队占领。他们的私情暴露之后,作为惩罚,三顺阉割了杏,杏被人送回了榆关娘家。落到三顺手中又被莫名其妙放掉的萧决定去榆关再次看望杏,他回来后被他的警卫员杀死,因为后者接到了命令:如果萧前往他哥哥占领的榆关就杀死他。
格非这篇小说的故事逻辑并没有像他的其他许多叙事那样离经叛道。然而,这样的逻辑放在宏大历史逻辑的背景中就变成了藐视现成秩序的一种戏仿。萧不时地置身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没有行使他被赋予的历史功能。小说一开始,他身负历史任务回归小河村,他的使命的纯洁性却由于他父亲滑稽地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死在水缸里意外死亡而遭到玷污。再者,他此行的侦察任务无非就是参加祭奠仪式。有意思的是,萧的父亲会摆弄洋枪,是为数不多的小刀会头领之一。小刀会(十九世纪中期盛行一时的地下反叛会社)的失败是因为仅仅想依靠小刀(一种传统的中国武器)改变历史,萧的父亲能够熟练使用洋枪这个事实就是杂交的独特历史现象。有一天,萧询问父亲为什么投身于一支失败的队伍,父亲的回答是必须用狼和猎人取代失败或者胜利的概念。当时,年轻的萧提出的问题已经表现出他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传统定义的困惑,萧的父亲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更加暧昧的隐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历史似乎被等同于不可靠的自然世界。事实上,萧的父亲扮演了一个重要但失败的历史角色,他死得毫无意义。像这样充满喜剧色彩的死亡,带来死讯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村里的媒婆,一个传播丑闻的类型化人物,她的话语微不足道。
事实上,萧“曾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他不知急于回家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对母亲的思念,或者是对记载着他童年的村子的凭吊的渴望”。①格非:《迷舟》,第108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从表面上看,萧受到了许多冲动的驱使,然而,其中没有一种冲动与宏大历史的中心主题有关。确切地说,根据接下来的叙述,驱使他的是“更深远而浩瀚的力量”,是深埋在他的记忆中对一个姑娘朦胧暧昧的个人欲望。萧的侦察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因为他从他不得不参与的历史戏剧中抽身而退。罗纳德·詹森(Ronald Janssen)将之理解为“中心化权力的意象在故事中被萧在关键时刻所经历的命运线索所驱使”。②Ronald Janssen,“Chinese Voices:A Review”,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8(1994),p.197.他的命运既不像宏大历史要求的那样意味深长,也不像道家告诫的那样可以预测。当历史戏剧转向个人欲望的舞台的时候,萧的命运和格非叙事的命运都变得离奇古怪和不能确定。
最戏剧性和荒谬的情节发生在结尾。杀死萧的既不是他军事上的敌人,也不是他的情敌,而是他自己的警卫员,后者没有意识到萧是去榆关探望杏。小说中的历史逻辑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位或者改变方向。首先,萧的家庭意外取代了他的军事行动。参加父亲的葬礼被他与杏的约会所取代。过去的延续似乎取代了现在。当我们即将透过个人传奇目睹错位的历史戏剧全景的时候,历史力量并没有忘记其责任及其始终蕴藏的潜在活跃性和致命性。萧的警卫员杀死他是假定萧会背叛他的历史角色。这样的处决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尽管他没有叛变和投降敌人,他却歪曲了自己的历史作用。然后,小说的结尾再次让纯属个人悲剧的虚构故事与笼罩个人命运的历史幽灵的冲动之间产生错位,尽管是以一种似是而非和不合理的方式。
然而,错位不仅是一个内文的现象,而且也以互文的方式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迷舟》是对规范的中国现代叙事的戏仿,后者中的历史责任与风流韵事往往协调一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互利互惠。③哈琴在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书中对戏仿作出了(重新)定义,戏仿就是“具有批判间距的重复,在相似性的中央允许对差异的反讽显示”(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New York:Routledge,1988,p.26)。在中国先锋派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戏仿与原型保持的“批判间距”并不是对一维空间的颠覆,而是一种在内在化和神话化的话语中挣扎的文化反省行为,因为parody(戏仿)一词中的希腊语前缀 para同时含有counter(反面)或 against(反对),和 near(邻近)或 beside(旁边)的意思(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New York:Routledge,1988,p.26)。例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的叙事模式。林道静生活中的男性形象卢嘉川、江华和余永泽分别起到了不同的历史作用,而林道静必须在实现她对历史主体的追求的同时实现她对爱情的追求,反之亦然。林道静追求的主体性很难用自足来评价,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样的主体性仍然处于一种依附状态,依赖于男性历史话语的塑造和操纵。这样的结构原型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年晚期:丁玲的《韦护》、洪灵菲的《流放》、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等等。在这些作品当中,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牵强附会,以致两者之间只有冲突才具有潜在的永恒性。(比如,只要想一想《韦护》中的文丽嘉的意识形态转变有多么不自然。)
如今,在格非的《迷舟》里,这样的冲突被推到了前台。恋爱情事不能被纳入宏大历史的图景,反而变成触发历史的非理性力量的致命或凶险要素。杏与“性”同音,这个字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浪漫情调变得庸俗,而且还彻底阻断了对历史远景的展望。然而,杏转移了萧对他的历史责任的关注,虽然她不是直接导致萧的悲剧的祸水红颜,但她却是萧不由自主地违犯禁忌的诱因。总而言之,杏不再充当协调历史与浪漫的中介,她最终导致了萧的历史角色与浪漫角色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历史反讽就这样从历史剧男女主人公的“角色误扮”中诞生。
缠绕不休的历史叙事
在格非看来,非理性挫败了理性的历史,原因不仅在于盲目的欲望(比如萧对杏的欲望),而且还在于想必是理性的假设(比如警卫员的假设)。这样的历史多重决定论正是格非叙事的根本动力。格非小说中的反讽始终就蕴含在自我困惑的叙事当中。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青黄》就是“追踪‘不在’”①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第108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的故事,一个没有目标的调查最终产生了《青黄》一词各种各样、甚至不可思议的结论。那是关于大约四十年前一支叫做“九姓渔户”的当地妓女船队。根据一位教授的理论,《青黄》是一部失传的妓女生活编年史,而不是民间盛传的一位漂亮少妇的名字。然而《麦村地方志》对妓女船队被禁后的情况语焉不详。格非从一开始就展示了指向蕴涵在官方或者知识权威炮制的历史中的含混暧昧、充满裂隙和自相矛盾的叙事。
小说的主要章节描述了叙事者对麦村不同的人的采访,他们对过去的个人回忆构成了当地历史的复杂图景。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老人,他特别提到那个姓张的男子和他女儿的到来。然而,他没有详细述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只是大概描述了那天的气候以及他们身后熊熊燃烧的船只。他在记叙中承认他的不知情并且提出了疑问:“他也许担心村里的人不肯收留他们而放火烧掉了那条船”;“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女儿好像叫小青”;“以后的事我也不怎样清楚”;“中年人……也许是对村子里的水土不太习惯”;“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父亲”。②格非:《迷舟》,第176-177、176、17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重点为我所加)老人的陈述本身就是对范式化的历史叙事的戏仿,它昭示了表现的不确定性。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看,对叙事者来说,老人的叙事之所以难以捉摸的原因也是不可确定的。显而易见,老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吃力”,③格非:《迷舟》,第176-177、176、17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重点为我所加)然而,他的模样却“造成的一个奇怪的印象”,“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④格非:《迷舟》,第176-177、176、17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重点为我所加)也许只是因为“他说话时齿音很重,喉音混浊不清,这使我在记录时遇到了一些麻烦”。①格非:《迷舟》,第176、183、189、19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因此,由于各种各样有意或者不可避免的原因,历史充满了脱漏或者困惑。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九年前在家里接待过叙事者的外科郎中。他在采访中声称,他还记得那个姓张的男子的葬仪,然而当话题转向他自己遇到那个姓张的男子的时候,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说,他“从来没有和那个外乡人说过一句话,他的心思……也许……他的女儿……”,②格非:《迷舟》,第176、183、189、19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他甚至没有把话说完。“九姓渔户”的历史再次变得若即若离和令人生疑:这样的历史仅仅存在于没完没了的引述或者无法复原的省略之中,而真实的事件却被不断推迟。至于“青黄”这个词,外科郎中认为它指年轻妓女(青)和年老妓女(黄)的划分。
然后,一个名叫康康的年轻人讲述了大水是怎样冲毁了姓张的男子的坟墓的,漂浮的棺材里空无一物。人们甚至怀疑姓张的男子是否真的死了,尤其因为外科郎中在棺盖钉死之前没能看见死者的尸体(根据先前的采访)。老年小青关于她儿子的死的故事更是加深了这样的怀疑。小青告诉采访者(即叙事者),她的儿子在淹死之前声称自己看见过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在各方面酷似死去很久的姓张男子。然而,小青儿子看见的那个老人是否就是姓张的男子也同样难以确定,也许那只是另一个跟他长相酷似的人,也许那只是幻觉。更有甚者,小青还无动于衷地声称,她的父亲“也可能不是亲生的”,③格非:《迷舟》,第176、183、189、19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这更是增加了那个姓张的男子令人迷惑的神秘感。不同的叙事声音之间的关联和冲突再次制造了叙事的不连贯和绝对历史的紊乱,这样的历史被瓦解成为不可能统一的神秘碎片。
小青在提到“九姓渔户”的时候声称,她没把卖淫的职业像村民看得那么严重。她对继母为了保护她不受性侵犯而招致杀身之祸感到歉疚,而她自己对强暴已经习以为常。虽然如此,她在说明船队形成的历史背景时对传说的解释是,“直到后来”④格非:《迷舟》,第176、183、189、19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发生了严重饥荒,船上的女人才逐渐变成了妓女。她为这段历史所作的辩解,其中的讯息显然可以被读作她对卖淫无动于衷的一种开脱。小青对卖淫的态度模棱两可。我们看到,不仅村民们(对他们来说,船队和船民是不光彩的)与小青(声称对卖淫无动于衷)的叙事声音互相冲突,甚至连同一个采访对象的叙事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小青,她至少是不知不觉地希望澄清自己声名狼藉的家族史的起源。
格非的叙事通过唤起空缺,即总体性话语压制下的时间成为一种“多元声音”,其中的每一个叙事声音都与潜藏的对手发生外在的或内在的冲突。
历史的霸权与总体声音的瓦解同时也呈现在一个意义与表现难解难分的世界里。叙事者“我”在对《青黄》一词或者“九姓渔户”的调查没有结果之后,拜访了九年前曾经在外科郎中家里过夜的卖麦芽糖老人李贵。那天夜晚,当外科郎中离家外出急诊时,被雷雨惊醒的“我”发现李贵在失踪了几个小时后又浑身泥泞地出现在门口,脚趾头还在向外渗着血。李贵是另一个反复无常或者自我否定的叙事者,他现在否认他曾经在那天夜晚离开过他的屋子,但是他又承认他经常梦游。“我”惊讶地发现,李贵的狗名叫“青黄”是因为皮毛的颜色。然而,在整个故事结束之际,“我”又在一本明代《词综》里偶然看到了“青黄”这个词条,青黄是一种草本植物。
至此,对“青黄”一词原意的探索终于有了结果。然而,这样的结果却衍生出偏离了既定意义的各种不可确定的结果:《青黄》唯一能够肯定的意义与历史预设没有任何关联。把握历史真实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从中产生的一切成为某种偶然多样和前后矛盾的东西。对过去历史的不同叙事也偏离了原初,无法在想象中拼凑出一部完整的编年史。然而,没有任何叙事能够避免主观介入:任何叙事者,包括作为作者的叙事者,似乎都加入了从自身的位置出发重新构建过去的行列。
我们可以从吴洪森为格非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迷舟》所作的序中读到与这个故事的来源有关的一则有趣的轶事:
记得一九八六年夏,我俩(吴洪森与格非)去千岛湖(名为考察的)旅游……县文化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当地风土人情,其中关于九姓渔户的故事使我们极好奇,特地到该渔户的所在地去了一趟,结果空无所获。那儿的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是陈友谅的部下,可这所谓的“知道”是因为县志上这么写的。他们矢口否认该船队的妇女史上有卖淫的传说,他们关于祖先所记得的是帮助太平天国打过胜仗,可县志上并无记载。两年后格非把这次经历写成了《青黄》……①格非:《迷舟》,第3、17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这段文字至少为我们指明了格非这篇小说的由来。这个段落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真正的过去或者被信赖权威历史的人们合法化,或者被希望增强历史的地方色彩的人们神话化。格非显然深入阅读了这些历史读物。《青黄》中每个叙事的片面性同样来自对道德禁忌的内在诱惑和抵御。在某些情况下,道德禁忌对真实经验进行了审查过滤。例如,第一个老人“与村里的许多人一样,对于那件‘不光彩的事’不愿重新提起”。②格非:《迷舟》,第3、17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那就是“我”觉得他的叙事中既有所揭露又有所隐瞒的原因。外科郎中对张姓男子之死的好奇,看林人(另一个采访对象)对后者张姓男子性生活的好奇分别使他们看不见整体。通过不同的声音拼凑出来的残破画面无法产生完整和绝对的过去的记载。
张旭东在他对格非的研究中敏锐地观察到《青黄》(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格非小说)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沉思的和自我凝神的叙事主体。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像这样一个由不同声音编制的网络所构成的现代主体实际上打破了叙事者声音的一统天下。因此,“自我形象的建构”③Xudong Zhang,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7、p.197、p.198.必须得到解构,不是透过叙事者的自我瓦解倾向,而是透过他的无法将他对过去事件的反思理性化。叙事主体的“遭遇想象性解放的自我意识”④Xudong Zhang,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7、p.197、p.198.以及“恢复过去的冲动”只能面对经久的意义传播,无法企及可能确立他历史身份的绝对自足的认识。张旭东认为,“人的开端”作为比“人的终结”⑤Xudong Zhang,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7、p.197、p.198.更为恰切的阐释仍然被悬置在对构形的欲望与毁形的现实之间。格非展现了叙述历史真相的困难,他奇迹般地创造了现代认知主体,虽然如此,这个主体的探索历程却经常遭到打断和回避。
似曾相见和迷乱的主体历史
叙事的异质模式在格非的《湮灭》(一九九三)中再度出现,多元声音在对那个名叫金子的女人的描述中相互冲突。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锦瑟》(一九九三)是在无穷无尽的叙事中套叙事,形成了一种自我吞噬的回旋叙事。小说的标题沿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著名诗篇《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格非小说中的主人公冯子存多次提到这首诗的第三行,他在整个转世来生中沉迷于庄子的“梦蝶”。①庄子的这段原文如下:“庄周昔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有知周也,俄而觉,则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为周,周与蝴蝶必有分矣,此谓物化。”(60)。庄子的寓言质疑现实的真实性,李商隐的诗关注记忆的朦胧,而格非的叙事则是一个对记忆与历史迷惑不解的自我吞噬的迷宫。李商隐的诗注定了格非叙事的抒情格调,冯子存就像李商隐那样迷失在他记忆或追忆的遐想之中。遐想的主体就像庄子那样变成了不稳定和自我质问的主体。
在安葬美少妇的那个夜晚(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就有一种神秘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冯子存听见有人在河对岸呼唤他的名字,他昏昏沉沉地穿过一片竹林走向墓地。村民捕获了他并且将他处死。从此之后,故事的叙事结构开始逆向展开。在冯子存死去的前一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京城求取功名,冯子存讲述了他是怎样去省城赴考,写不出以《锦瑟》为指定标题的文章的故事。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的姐姐向他讲述了她从茶商那里听来的故事。冯子存趁着她沉睡之际在一棵树下悬吊而死。在茶商的故事中,身患重病的冯子存接到皇帝召见的邀请。他在病榻上翻来覆去地阅读《锦瑟》这首诗以期感悟其中的深刻含义。他向妻子讲述了他刚才做的梦,但是直到他死也没有讲完。根据冯子存的记述,他在梦里变成了沧海国的国王,亲自出征讨伐西楚国。西楚国包围了他的王国,冯子存带领他的百姓离开沧海去蓝田牧羊采玉。②沧海和蓝田暗示了李商隐的诗(见李商隐《锦瑟》第5和第6行)。一天,在王子前来刺杀他之前,他正在向园丁讲述他前一天夜晚做的梦。他讲述的梦境又回到了整个故事(叙事框架)的开头,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在安葬美少妇的那个夜晚,冯子存听到她在窗外呼唤他的名字,他不知不觉地穿过麦地朝墓地走去……这个最后的梦也可以被读作他转世轮回的先兆,因为叙事的时空是自我吞噬的。
这个无穷套结构与庄子的寓言相应: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反过来蝴蝶又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如果说庄子的梦境就是蝴蝶的现实,那么他的现实必然就是蝴蝶的梦境。现实与梦境在叙事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传统的中国神秘主义的一部分,格非以此抗衡线性的宏大叙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格非的《锦瑟》也驳斥了被现代理性化了的庄子寓言,比如在王蒙的短篇小说《蝴蝶》中,历史辩证法对混乱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样引用了庄子寓言的这篇王蒙小说展示出目的论的时间性,在这样的时间性中,个人历史只是国族历史的一个提喻(synecdoche)。叙事的基本线索围绕着主角张思远,他回想起他过去从党委书记(政治动乱之前)到老张头(他流放山村时期),再到副部长(他平反之后)的(政治)“生命”的“转世”。这里的“转世”显然包含着辩证历史的本质:张思远(或者中国)只有通过在政治动乱中洗涤灵魂才能净化他的精神并且最终进入一个灿烂光明的新时期。尽管王蒙叙事运用了意识流技巧,故事的线性发展是显见的。
比照之下,《锦瑟》中用来揭示转世来生的叙事是倒退发展而不是向前发展,甚至是杂乱的。宏大历史不再占据主导优势;更加确切地说,故事中晦暗不明的事件萦绕着不可追忆性。格非的故事戏仿了用居高临下的主体讲述模式强化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理性。在格非的《锦瑟》中,依然还在的叙事主体陷入了个人追踪的无尽的自我吞噬之中。再者,叙事的抒情性带回了古代哲人和诗人旨在挑战现代主体绝对理性的自我魅惑之声。叙事框架由环环相套和层出不穷的叙事组成,直到最后的叙事回到原来的叙事框架。一个叙事主体被另一个应该是从属的叙事主体所替代,直到最微不足道的从属叙事主体取代了最主要的叙事主体。因此,这里没有任何自足的叙事主体,如果每个叙事主体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元叙事主体的话,那么就根本没有元叙事主体,没有任何绝对和超越的主体能够操纵这个陷入既连续又回旋的叙事沙漏之中的整个叙事。抒情的声音再也无法展望目的论的时间性或者将解放的理性历史绝对化。更加确切地说,接连不断的回想促使叙事朝着不可追忆逆向发展。
冯子存这种追忆前世般的叙事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精神轮回,无法最终展现完整的主体形象。记忆的困难与似曾相识的经验交替出现。对冯子存来说,“那些琐碎的在事仿佛突然藏到了时间的背后,他对过去时光的追索常常一无所获”。①格非:《雨季的感觉》,第 178、182、182、190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94。与此同时,冯子存在一开始第一次见到这位美貌少妇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②格非:《雨季的感觉》,第 178、182、182、190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94。这个让他遭遇不幸的女人的视觉形象让冯子存陷入了模糊记忆的陷阱之中。在上述片段中,冯子存第一眼看到这个女人“浮糜而俗艳的笑容”③格非:《雨季的感觉》,第 178、182、182、190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94。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的死“昏昏沉沉”走向墓地的时候被捕的(没有任何理由)。这样一个形象在冯子存讲述的关于他在乡试考场上失利的故事中再次出现:在考场上,面对指定的试题《锦瑟》,冯子存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妓女搔首弄姿的笑脸”,④格非:《雨季的感觉》,第 178、182、182、190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94。这让他无法静下心来写文章。至于使冯子存从一种人生转向另一种人生的,是否就是他的追忆无法确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使一种叙事转向另一种叙事的正是追忆。追忆这个词在李商隐的诗中被用来追踪仅仅是“惘然”的“当时”,这也是冯子存的体验的隐秘动力。小说人物冯子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陆续改变自己变迁(转世来生)的叙事功能,行使不同的功能,却再也没有找到他原来的家。叙事中呈现的怪诞和叙事自身的怪诞(Unheimlichkeit,即“无家可归”,正如海德格尔所提示的)表明了处于流放状态的小说人物和叙事主体。从叙事的层面上来看,叙事的声音相互交迭。从情节的层面上来看亦是如此,初次来到村庄的冯子存与率领民众逃难的冯子存都体现了无家可归的人类,无论他是一个独善其身的文人还是最高权贵。
格非叙事的无穷套结构起源于西方文学和艺术,比如埃舍尔(M.C.Escher)的石板画和木刻画,其中的拓扑游戏达到了自我迷乱的巅峰。在格非的作品中,冯子存不能从统一整体上把握的复杂个人经历偏离了线性的历史观念。叙事主体无法维持它的全知全能并且经常暴露出这种叙事主体自身的缺陷与不稳定身份,以此质疑作者主体性的绝对理念。